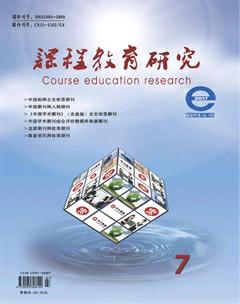“缺席”的背后
耿直
【摘要】本文將老舍小說《微神》與《灰姑娘》和同時期其他愛情題材的文學作品進行比較,從兩個角度歸納出其故事情節的悲劇根源,即作者本人的生活經歷和20世紀20—30年代的社會思想狀況導致的作家自我意識的缺失。
【關鍵詞】老舍 微神 悲劇
【中圖分類號】I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7)07-0082-02
《微神》是老舍唯一一篇愛情小說,收錄于1934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趕集》。小說通過夢境引出回憶:文中的兩位主人公幼年相識,但迫于封建制度的壓力,二人無法向彼此表露心意,只得將愛深埋心底。后來男主人公下了南洋,回國后卻得知女主人公已做了暗娼,男主人公希望能接濟女主人公,但得到的只是幾聲狂笑,當男主人公最終下定決心要娶女主人公時,女主人公卻因打胎而死。在夢境中男主人公再度遇見了女主人公,這次二人終于能正大光明的相擁在一起,女主人公向男主人公敘述了當年的經歷:由于家道中落,母親早逝,在男主人公離開后,她先是接受了一個青年的愛,后來又將自己賣給了一個富家公子,但因為對男主人公始終難以忘懷,這兩段戀情都沒有好結局,她的父親又染上了大煙,被掃地出門的女主人公只得靠出賣肉體繼續維生。在男主人公回國后女主人公自覺失去了精神寄托,同時為了保持女主人公在男主人公心中少年時的美好印象,便選擇了放棄自己的生命。
老舍先生的發小羅常培在《我與老舍》一文中回憶道:“我還可以告訴你,他后來所寫的《微神》,就是他自己初戀的影兒。文中說的老舍先生的初戀對象應是“宗月大師”劉壽綿的女兒,她大老舍一天,與老舍同為師范學校的畢業生,然而當時二人也只有像小說中一樣的朦朧情愫。后來,劉壽綿因經營不善家道敗落,出家為僧并攜妻女帶發修行,老舍則遠赴英國,這段感情也畫上了句號。雖不知劉小姐的結局究竟如何,但可想見的是,當時的“佛門圣地”并非清凈之所,劉小姐的結局也絕不是平安順遂地終其一生。將這段經歷與《微神》進行對比,我們可以發現許多共同點:二人青梅竹馬,兩情相悅,卻礙于傳統無法坦誠相對;她家遭遇不幸而落敗,他遠走異國他鄉卻想念著她,及至重逢,已是物是人非。由此,我們可大膽推斷,《微神》中愛情故事的原型,就來源于老舍先生的真實的初戀經歷,或者說小說的悲劇,就脫胎于現實的悲劇。
盡管有了現實的原型,我們還是可以看出《微神》具有“灰姑娘”式愛情故事的鮮明特征。這些故事在人物設定上有著共同的特點:男女主角身份地位懸殊,女性善良美好,男性忠貞深情。而故事的結局則有著鮮明的文體特征和時代特征。例如,在童話故事中,灰姑娘和王子有大團圓的結局,而在寫實性的文學作品中,二人則很難“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一系列作品,又有一種相似的結局:女子殉情或死于非命,男子悔恨追憶或是以受害者的身份憤懣控訴封建禮教。周作人的散文《初戀》中,“我”對楊家三姑娘有著朦朧的好感,結果她在“我”離開時死于霍亂;巴金的小說《家》中,少爺覺慧愛上丫頭鳴鳳,鳴鳳即將被送給一個高齡的老爺做妾,覺慧毫不知情,鳴鳳絕望之下投湖而死;而在《微神》中,“她”也是在“我”出國期間流落風塵,而“我”對此毫不知情。不論是虛構的小說還是脫胎于真實經歷的散文,這些故事中的男性總是恰巧在愛人落難之時缺席,這種缺席不可謂不詭異。
僅從《微神》來說,“五四運動還沒降生呢,男女的交際還不是普通的事。”“提婚是不能想的事。許多許多無意識而有力量的阻礙,象個專以力氣自雄的猛虎,站在我們中間。”這樣的句子在接近的段落中出現,似乎是為“我”的不作為找到了充分有力的理由。而在二人同時任職于平民學校期間,她用“女子的尊嚴與神秘”躲避著“我”,“我”仍舊無法做出行動。如果說之前的這些缺席還是合理的,是刻意的,甚至是具有影影綽綽的“距離美”的,那么之后的幾次不得見,對于悲劇的釀成則有著無法開脫的責任。“我”上南洋前找她辭行,她恰巧“沒在家”;“我”在南洋期間由于無法直接通信又不好意思直接探問,也沒有一點她的消息;回國后“我”得知她的下落去找她,她搬了家;友人代“我”提婚失敗后,“我”鼓足勇氣,志在必得地親自去求婚,去了三次她都“沒在家”,第四次她終于在家了,卻是裝在棺材里。可以說是她的“不在家”使“我”在她要淪為暗娼時毫不知情地去了南洋,也是她的“不在家”使她錯過了我的誠心求婚,打胎而死。愛情的悲劇幾乎全都源于她的“不在家”,“我”則因為不在場而沒有一點責任。也許老舍先生也覺得這樣的巧合有些牽強,所以在夢境的世界里,“我”做出了承擔責任的假設,而得到的結論竟然是:“假使我那時候回來,以我的經濟能力說;能供給得起她的父親嗎?我還不是大睜白眼地看著她賣身?”也就是說,“我”和她都供養不起她抽大煙的父親,所以不管怎樣她都得去賣身,而若是“我”不在還則罷了,她還可以揣著一個愿望勉強活著,“我”一回來,她就得去死了,即使“我”不計前嫌愿意與她結婚她也無福消受。在這一段感情里,“我”根本就沒有選擇或者說是爭取的權利,因為當“我”意識到要爭取時,陰差陽錯間一切都已塵埃落定了。既然“我”是不知情的,那么“我”便是無辜的了,她更是受害者,那么這一切悲劇一定歸咎于社會制度了。與此相似,《初戀》中的楊家姑娘沒有等到我“救她出來”的諾言兌現就死了,《家》中覺慧也由于不知情而沒有進行曾許諾的抗爭導致了鳴鳳的死去。這些男性無一例外地以“不在場”、“不知情”的方式,看似被動,實則主動地放棄了為愛情抗爭的權利,卻不必為悲劇負責。
在這些文章里,我們好像反復看到一個被預設好的、強大的來自于社會的阻力,它似乎是扼殺愛情的元兇,可我們總看不到愛情中的自由選擇和個體特點。即使是在完全同樣的社會背景下,各自愛情也不應有完全相同的面貌,可是在這些故事里,主角的個性化抗爭被無限的弱化和忽視,時代特征和社會制度成為了左右愛情的“上帝之手”。那么究竟是為什么,使本該做出選擇的人物缺失了選擇的意識呢?我想,這與作家在創作時精神狀態密切相關。上世紀20~30年代,“五四”思想星火燎原,在文學界掀起巨浪,啟蒙思想引導著人們,尤其是敏感的作家們去發現自己,去重視個體的價值和幸福,人們在這種前所未有的思潮沖擊下,迅速打破了封建禮教的桎梏,看似獲得了極大的思想解放。可是,“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的狀況使得人們好像對自由有一絲茫然,尤其是當人們發現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自己要為自己的一切行為負責時,他們反而有了惶恐。簡單地說,如果社會制度本身極度不合理,那么個體的不幸幾乎是注定的,這可以完全歸咎于外因,而如果不合理的制度被打破,那么每個人有了更多爭取幸福的自主權,權利意味著責任,也就是說不幸福的個體就不再有任何開脫的借口。啟蒙為人們解開了枷鎖,也除去了庇護,此時,群體的自我意識已開始覺醒,個體的自我意識還不足以強大到承擔個體命運,社會制度只得在替罪羊的崗位上多值一班。控訴社會制度可以讓弱小而不幸的個體得到極大的心靈慰藉,也就是說《微神》等“灰姑娘”模式的故事就像在告訴一個愛情不幸的人:“社會黑暗,不怪你。”在寫作者本身無法確定個體的抗爭是否真的能起到作用的情況下,他們甚至設置了這種男主角缺席的理想化情境,這樣個體就能徹底地又合理地逃避了選擇和抗爭的重負。不得不說,魯迅在這一問題上表現的更為果決,在他的《傷逝》中,涓生與子君雖然突破封建束縛走到了一起,但生活壓力所帶來的精神差異的突出導致兩人的家庭最終破裂。魯迅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這個世界的,所以他借《傷逝》明確表達了自己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即使人打破了封建制度的束縛,人自身的缺陷依然會導致悲劇的發生,自我意識在當時遠遠不足以使人為自我的選擇負責。
在《微神》的故事里,男性是無辜的,所以“我”可以一直扮演癡情的追憶者,也可以懷著失去愛人的悲痛對社會制度進行討伐。近代文學中的“我”們沒有為自己的幸福負責任的機會,是否也能折射出一代知識分子沒有能力為個體幸福負責的精神狀態?
她在夢中對“我”說:“懼怕使你失去一切”我想,這一句斷語對于我這淺層次的探討很是合適,不管是從老舍先生的親身經歷來看,還是從同時期同題材故事的時代特征來看,正是對于承擔個體命運的懼怕,導致了《微神》中悲劇的發生。
參考文獻:
[1]陳引馳.文人畫像:名人筆下的名人[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