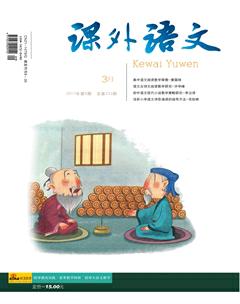論“博弈論與翻譯”的實質
2017-05-10 01:48:08鄧麗蓉
課外語文·下
2017年3期
【摘要】隨著博弈論研究的發展,博弈論也逐漸被應用于翻譯理論研究方面。已有很多文章運用博弈論對翻譯策略中的“歸化”與“異化”進行了分析,而鮮少有文章直接指出博弈論與翻譯的實質問題。因此本文將博弈論與翻譯活動進行了比較分析,從而指出了博弈論與翻譯問題的實質。分析結果表明博弈論在翻譯活動中的應用,其實質就是對翻譯策略的選擇問題。通過此分析,希望人們可以對博弈論在翻譯過程中應用的實質有一個直接簡明的認識。
【關鍵詞】翻譯活動;博弈論;實質;翻譯策略
【中圖分類號】G634 【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一)博弈論
博弈論又被稱為對策論(Game Theory),它是現代數學的一個新分支,也是運籌學的一個重要組成內容。博弈論就是研究互動決策的理論,所謂互動決策,即各行動方(即玩家player)的決策是相互影響的,每個人在決策的時候必須將他人的決策納入自己的決策考慮之中,當然也需要把別人對于自己的考慮納入考慮之中……像這樣重疊考慮情形進行決策,選擇最有利于自己的策略(strategy)。
(二)博弈論的研究現狀
博弈論思想古已有之,在我國,博弈論可以追溯至春秋時的《孫子兵法》,它不僅是一部軍事著作,而且算是最早的一部博弈論專著。博弈論最初主要研究象棋、橋牌、賭博中的勝負問題,人們對博弈局勢的把握只停留在經驗上,沒有向理論化發展,正式發展成一門學科則是在20世紀初。1928年馮·諾依曼證明了博弈論的基本原理,從而宣告了博弈論的正式誕生。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