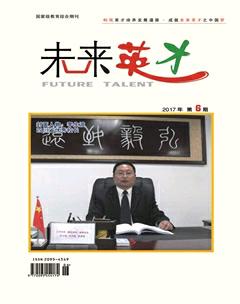勸誡是一種心靈的創(chuàng)造
徐春娃
作為一名小學(xué)教師,尤其是班主任,每天面對(duì)孩子數(shù)不勝數(shù)的“爭(zhēng)斗”,還要應(yīng)對(duì)學(xué)校繁瑣而又必須的校規(guī)校紀(jì)檢查,勸誡便顯得司空見(jiàn)慣。而很多時(shí)候,教師在忙于工作的同時(shí),便忽視了勸誡的藝術(shù),要么簡(jiǎn)單過(guò)問(wèn)一下,“嗯、哼”了事;要么拉過(guò)來(lái)不問(wèn)青紅皂白便斥責(zé)一通;再嚴(yán)重的讓學(xué)生直接通知家長(zhǎng),把責(zé)任推給家長(zhǎng)一了百了。學(xué)生在經(jīng)歷了一次兩次這樣的無(wú)趣后,便從內(nèi)心開(kāi)始疏遠(yuǎn)、抵觸并且嘗試反抗教師的簡(jiǎn)單粗暴,結(jié)果,該有的“爭(zhēng)斗”仍然繼續(xù),該有的違規(guī)仍然層出不窮,讓老師愈發(fā)惱火的同時(shí),本該和諧的師生關(guān)系也愈走愈僵。
至今仍讓我記憶猶新的是陶行知先生的“分糖”藝術(shù)。有一天,陶行知校長(zhǎng)在校園里看到一個(gè)男生用磚砸另一男生,當(dāng)即制止了他,并要他放學(xué)到校長(zhǎng)室去。當(dāng)陶行知走到辦公室時(shí),該生已早早來(lái)到校長(zhǎng)室低頭挨訓(xùn)。陶行知走來(lái),一面先給他一塊糖,一面說(shuō):“這塊糖是獎(jiǎng)給你的,因你按時(shí)到,我卻遲到了。”該生驚疑地接過(guò)糖。接著,陶行知又掏出一塊糖放到他手里,說(shuō):“這第二塊糖也是獎(jiǎng)你的,因我不讓你再打人時(shí),你立刻住手了,這說(shuō)明你尊重我,應(yīng)該獎(jiǎng)你。”學(xué)生更驚疑了,睜大眼睛看著校長(zhǎng)。陶行知又掏出第三塊糖,說(shuō):“我調(diào)查過(guò)了,你砸他是因?yàn)樗圬?fù)小同學(xué)。這說(shuō)明你正直、善良,敢跟壞人作斗爭(zhēng),應(yīng)該獎(jiǎng)勵(lì)你啊!”這名男生聽(tīng)到這里感動(dòng)極了,流著淚說(shuō):“校長(zhǎng),你打我兩下吧,我錯(cuò)了,我砸的不是壞人,是我的同學(xué)啊。”陶行知滿意地笑了。他隨即掏出第四塊糖,遞過(guò)去,說(shuō):“為你的正確認(rèn)識(shí)錯(cuò)誤,我再獎(jiǎng)你一塊糖。我的糖獎(jiǎng)完了,我看我們的談話也該結(jié)束了。”在處理學(xué)生的磚砸人事件時(shí),陶行知沒(méi)有火冒三丈,沒(méi)有厲聲呵斥,有的只是循循善誘。在引導(dǎo)學(xué)生主動(dòng)認(rèn)識(shí)錯(cuò)誤的同時(shí),還教會(huì)了學(xué)生守時(shí)、尊重人、勇于認(rèn)錯(cuò)是美德。相信如此輕描淡寫(xiě)、潤(rùn)物無(wú)聲的勸誡一定會(huì)令孩子終生難忘并受益。
如果我們每一位教師都能像陶行知這樣處處考慮學(xué)生的感受,理解和尊重每一位學(xué)生,那我們和學(xué)生的矛盾怎會(huì)愈演愈烈?學(xué)生對(duì)于我們的良苦用心又怎會(huì)置若罔聞?
冰心先生曾說(shuō)過(guò):“有了愛(ài)就有了一切。”適時(shí)的寬容就是一種愛(ài),它會(huì)使學(xué)生心存感激,從而迸發(fā)前進(jìn)的動(dòng)力。
記得一年級(jí)剛開(kāi)學(xué)不久,我班的一個(gè)“調(diào)皮鬼”就做了一件讓我惱火的事——他把花壇里還未盛開(kāi)的月季花給摘了下來(lái)。乍聽(tīng)到這件事,我的火氣“騰”地一聲直沖頭頂,都三令五申多少遍了,他還敢摘花,這不擺明了讓我難堪嗎?不行,絕不能輕饒了他,否則,其他同學(xué)豈不是也會(huì)“照葫蘆畫(huà)瓢”!想到這兒,我便大踏步走進(jìn)教室。
“銘銘,上來(lái)!”如此高分貝的叫聲,自然吸引了全班同學(xué)的視線,當(dāng)然也包括他。可能已有同學(xué)向他告知了此事,他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來(lái)到我面前。我剛要發(fā)火,忽而一個(gè)小案例清晰地浮現(xiàn)在我腦海中,和我眼前的場(chǎng)景是那樣的相似:校園的一角,紫薇花開(kāi),美不勝收。一位校長(zhǎng)走進(jìn)教室,發(fā)現(xiàn)學(xué)生的課桌上插了兩三枝紫薇花。校長(zhǎng)皺了皺眉頭,并未說(shuō)什么。當(dāng)放學(xué)鈴響過(guò),這位校長(zhǎng)便笑瞇瞇地走進(jìn),問(wèn)同學(xué)們:“放學(xué)后,你們要去哪里呀?”學(xué)生們異口同聲的回答:“回家。”校長(zhǎng)接著問(wèn):“你們都回家了,它怎么辦?”校長(zhǎng)伸手指向了瓶中的紫薇花。孩子們頓時(shí)不知該如何回答。校長(zhǎng)神色嚴(yán)肅地說(shuō):“它們也有自己的家,就是那棵紫薇樹(shù),可是,他們?cè)僖膊荒芑厝チ恕K鼈兛蓱z不可憐?”孩子們大聲說(shuō)可憐,而摘花的孩子則羞愧的低下了頭。從此,這個(gè)班再也沒(méi)有人偷摘學(xué)校里的紫薇花。
一瞬間,我的心平靜下來(lái)。我示意銘銘回到座位上。我也若無(wú)其事地離開(kāi)了教室。快放學(xué)了,我瞄著已經(jīng)明顯坐不住歸心似箭的一班同學(xué),開(kāi)始了案例中的對(duì)話。結(jié)果,銘銘后悔地痛哭出聲,好多同學(xué)都跟著流淚了——為月季花再也回不了家而難過(guò)。大家紛紛表示:再也不隨便破壞花草樹(shù)木了。
看著那一張張生動(dòng)的小臉和純真的眼神,我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好險(xiǎn)哪,差一點(diǎn),就差一點(diǎn)點(diǎn),我?guī)Ыo孩子們的就是無(wú)盡地傷害呀!勸誡,真的也可以悅耳動(dòng)聽(tīng)而自然有力。
從此,我明了:勸誡,不僅僅是一種口頭的勸說(shuō),更是一種心靈的創(chuàng)造。聰明的人,懂得擷取最美麗的詞句,引領(lǐng)那些一時(shí)迷失方向的心靈走向回歸。
蘇霍姆林斯基說(shuō):“教育其實(shí)很簡(jiǎn)單,一腔真愛(ài),一份寬容,如此而已。”讓我們都能以關(guān)注、寬容乃至欣賞的目光去善待學(xué)生,給勸誡穿上美麗的外衣吧,也許在我們不經(jīng)意間就能成就一個(gè)未來(lái)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