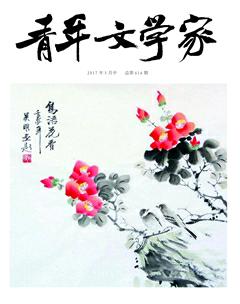始于故事,止于生活
摘 要:《江邊記》是張稼文先生的一本半自傳體性質的成長小說。借用江邊“男孩”第三人稱這一故事主角,它采用一種更加平實樸素的敘事筆調及一種客觀冷靜的立場,以作者自己青春期在滇西瀾滄江峽谷邊的成長經歷為藍本,用文學的手法書寫的作者由少年至青年的成長蛻變。
關鍵詞:故事;生活;非虛構
作者簡介:范明娟(1979-),女,漢族,河南南陽人,云南民族大學碩士,廣東技術師范學院天河學院任教,主要研究方向: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14-0-02
《江邊記》是張稼文先生于2013年付梓問世的又一部小說類文學作品。它采用一種非虛構的紀實手法書寫而成,通過作品中一篇篇親切平常如鄰里家常般的故事,作者也完成了對世事、人生、社會和時代的初步認識,由一個懵懂的江邊少年跨進人生青年的門檻。小說中的故事或溫情,或冷靜,或讓人略略沉重,但在作者清新的筆觸下,讓人最終不禁莞爾。若將作品的悲劇色彩比作一種大紅大綠的配色,則《江邊記》不啻為一種淡雅耐品的小素描。言簡意深,真實可感又趣味無窮。
一、故事中記憶的復活
《江邊記》是由一篇篇獨立成篇的小故事組成。從人生的中年回望,以年少生活記憶為主線,作者將自己真實的人生經歷變為書寫藍本,江邊“少年”的視角便是小說化的作者自己,作品里出現的如“婦人”“鄉村教師”“阿華”“周國有”“阿璞”等等人物也多是少年時期作者身邊的親人或熟悉的鄉鄰朋友。
雖然沒有用第一人稱的表達,但置身小說之外,文字中,我們更多看到的是一種鄉村生活溫暖的親情,一種瑣碎但平實親切的日常俗事,一種和諧而自然的成長體驗。
以回憶為主線,作者把我們帶到了一個鮮活生動的滇西生活場景里。與多數人對鄉村生活單調乏味落后艱苦的定義不同,透過《背娃娃》、《看山》、《紅雞蛋》、《回鄉知青》、《秘信》、《餅干》、《火把花》、《薅甘蔗》等等一篇篇與植物、動物、節令、物候,生活習俗密切相關的滇西鄉村生活記憶,我們回到了尋常的自然與熟悉的年少生活記憶里,故事充滿人間煙火味,往事生動如在眼前,鄉鄰親人如在身邊,樸素的鄉村在這種對記憶的書寫中被賦予了更多的靈氣,鄉村的春夏秋冬,生活的喜怒哀樂都因此鮮活。可以說,《江邊記》為我們保存了一份來自鄉村生活的最美圖景,是一份詩意流淌而又彌足珍貴的私人記憶。 與記憶相關的整冊文字自始至終散發出一種更接地氣的親切可感。文字傳達給讀者的在場感和溫度始終存在。
二、高于生活的文學表達
《江邊記》寫的是張稼文的滇西瀾滄江邊家鄉的故事。與眾多厚重蒼涼的史冊類的文字表達不同,張稼文在作品中同樣重視語言的生動與準確,但這種語言的功力,拋卻了現代人慣用的機智與裝飾,老實的文字風格中,他為我們呈現的則是銘心刻骨的細節,入木三分而又醇味綿長,純熟而干凈。我們感受到的是一種文字至簡與色彩至簡的意境與不凡功力。
恰如詩人于堅所講:“他講故事很平常,不是故事本身而是如何講這些故事才是他的文章的魅力所在,如何樸素低調地講出生活世界被遮蔽著的語言之美才是他的魅力所在。”
讓我們在作品中感受一下這種文字的魅力:
“鄉村教師笑了笑,然后,瓷杯兒遞近自己嘴邊,略略揚脖,咕嘟一聲。那樣子,很得意,很舒坦。”
“院壩里多了一些成天嗡嗡叫的東西。它們跳著八字舞,白天出去采蜜,傍晚歸巢。”
“這世間的事情哪個說得清楚?反正,轉眼間,阿允成了一個可憐的怪物。”
“峽谷二月天,瓦藍瓦藍。一團糯米面一樣的白去在慢悠悠地飄著,變幻著,像閑牛懶馬,也像一塊大手帕,輕輕翻卷,滾動——仿佛有隱形的巨人,拿著它們在擦洗天空。”
……
可以說,“他是一位優秀的漢語工匠,很久不見這種老實而空靈的語言了。”身處喧囂的當下,當每個人都在感嘆著真實與本色的缺失,沈從文或汪曾祺式的清新作品離我們越來越遙遠時,我們卻在張稼文的文字里重新讀出了一種從平凡的生活中提煉出的盎然生機,這種審美趣味詩意、閑散、平和,有種久違的自然與親切。不偽裝,不刻意,不虛偽,敘述家常自然,細節完勝人心。
同時,將自傳與小說融合,通過“男孩”這個替代的角色,張稼文將自己的個性和成長體驗都滲透在了文中生動而并不裝飾的生活細節里。故事一篇篇累積,“男孩”也逐漸成長。通篇文字的簡約干凈貼切,主題的干凈清澈,達到了一種直逼本質的效果。
因了文字表達的魅力,樸素的鄉村更像世外桃源,遠去的生活定格在書里,成了可收藏的藝術品,一個人在偏僻山村豐富的生活記憶有一種鄉村生活檔案般的史料價值。作品主題:“或許,生活不容易,或許,要活下去也不難。”也在這種如溪水般獨特清新的文學表達得到了提煉和升華。
三、非虛構書寫的文學意義
所謂非虛構文學,就是對文學真實的追求。真實性從來不是恒量一篇文學作品優劣的唯一標準,任何一種文學作品都屬于作者的“創作”,絕對真實的文學作品首先就很難存在。任何一種非虛構的作品,都首先是基于對事實背后的思想和感悟以及人性的流露,從而予人以生存的尊嚴,喚醒人心底的溫情。憑著對生活的深刻認知以及對記憶的大量復原,張稼文在《江邊記》里,盡最大可能地呈現事件的真實和原生態的人物,同時照顧著讀者的審美需求與文學的想象空間。
《江邊記》是作者半自傳體性質的小說,其書寫的故事內容全都基于作者在滇西江邊的成長經歷。作者的寫作初衷,或者只是“自己在跟自己的記憶玩”。書的首頁,作者寫著“給鄧歌兒”,想把這本書寫給自己最親愛的孩子及無所不能容的時間。故事里的所涉及的人事,皆有生活中的原型。各種自然風俗節慶習慣,也多為作者親歷。文字和故事起源于生活,卻遠比生活更典型,更概括,更本質。即使這種還原后的真實因為記憶的距離打了一點點的折扣,我們也能在這種非虛構寫作中捕捉到作者在書寫時對生活真實本身的尊重與努力。歷史所關心的那些政治人物與風云變幻,在這里被替換成一種鄉村少年內心特有的云淡風輕,在對成人世界的審視過程中,客觀冷靜,隨心而行,成長也因了這份真實變得單純而從容。這種非虛構的紀實寫作在呈現生活真相的背后,也表達出一種溫情的力量及深入人心的人文情懷,其真實感與現場感是所有虛構或喧囂而夸大其詞的想象作品所不能比擬的。
四、結語
成人眼中的生活是往往是平淡而乏味的,多數日常的鄉村更有一種與“桃花源”無關的粗糙貧困,但生活的內涵卻因為每個人不同的內心體驗而有巨大的差別。通覽全書,《江邊記》尊重現實,還原生活。盡量避免所謂“生動”的書寫,盡量以本分和原生態的態度,立足于眼前和現實的生活,記錄每一個可感可知的生活此刻,讓生活的沉重變得輕盈,在文字呈現中賦予其生命本身的豐富性與廣闊內涵,這一切遠離了想象,也并不僅僅是故事,這種用“在場”替代“虛構”的寫作卻深刻闡釋出文學的意義與生活的真諦。
生活的美也恰恰就蘊含在這種平淡和真實里!
參考文獻:
[1]張稼文:《江邊記》,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
[2]于堅:《讀〈江邊記〉》,張稼文《江邊記》,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頁.
[3]錢映紫:《平凡鄉村的隱秘神跡》,張稼文《江邊記》,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頁.
[4]張學昕 梁海.時間之上:“非虛構”的歷史與人生 南方文壇 2013.2第24~29頁.
[5]張檸 許珊珊.當代“非虛構”敘事作品的文學意義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叢刊 2011.2第106~114頁.
[6]劉璐陽.重述生命中最隱秘的心事.牡丹江大學學報,2014年第2期,第55~57頁.
[7]黃慧.非虛構基本問題研究.文學研究,2015年第9期,第86~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