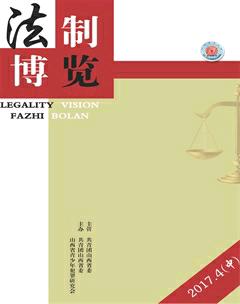從知假買假行為看新《消法》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完善
摘要:本文先介紹了知假買假行為的含義以及知假買假行為引起的爭論,在厘清含義以及相關的爭論觀點后,筆者認為,知假買假行為應受《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保護并給出了相應的理由。然后,透過知假買假現象,捕捉新《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懲罰性賠償制度的不足,并相應地提出一些彌補這些不足的建議。
關鍵詞:知假買假;懲罰性賠償;消費者;欺詐;賠償標準
中圖分類號:D923.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4379-(2017)11-0169-02
作者簡介:徐道波(1967-),男,漢族,江蘇云臺山律師事務所,主任,從事律師工作。
知假買假行為,其反映出來的一系列問題以及引起的一系列爭論早已不是什么新的話題。眾所周知,我國于2014年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法》)做了修改,固然,新《消法》存在很多進步之處,但是,面對知假買假行為反應出的諸如“消費者”定義模糊,賠償標準不足以及缺乏層次性等一系列問題,新《消法》并沒有給予根本性地解決。知假買假行為究竟該不該受《消法》的保護,知假買假行為反映出新《消法》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問題有哪些,這些問題對完善新《消法》中的懲罰性賠償制度有什么啟示,都將是本文研究的對象。
一、知假買假的含義
1995年山東無業青年王某,無意中得知當時的《消法》第49條的雙倍賠償,認為有利可圖,四處買假,并根據當時的《消法》第49條向商家索賠,曾經因此獲得8000元的賠償,一時間“王某知假買假現象”引起了社會各界熱議,全國各地的“王某們”爭相知假買假,人們和學界把王某這樣的買假行為稱為知假買假行為。
二、對知假買假行為《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應予保護
關于知假買假行為,理論界和實務界均存在不同看法,沒有形成統一的觀點。筆者認為,對知假買假行為,《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應予保護,主要理由有以下兩點:
(一)打假并不只是政府的責任
公力執法與私力執法各有其專有領域,但他們之間的界線并非絕對、恒定,政府的能力大小、政府的公益性程度、政府的執法效率、私力執法的成本與收益等因素決定了這條界線的偏離方向及程度。①如果政府的執法能力低、執法效率不高、公益性程度低,而若私力執法的成本相對較低,則其并非不能予以考慮。因此,有必要考慮將公力執法和私力執法的優勢組合起來以產生最高的效率。
(二)指導案例的肯定
在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案例23號,孫某訴南京某超市有限公司江寧店買賣合同糾紛一案中,孫某于2012年以其在南京某超市購買的15包,價值近600元的香腸中,有14包已過期為由,將南京某超市訴至法院,要求被告人支付過期香腸的十倍賠償金,共計5586元。法院的判決最終支持了原告的訴訟請求。本案的裁判理由中明確指出:法律并未對消費者的主觀購物動機作出限制性規定,故對被告的主張不予支持。可見,假設超市證明了或者孫某自認其主觀上明知食品過期仍然購買,孫某仍然有權要求十倍的懲罰性賠償因為法律并未對消費者的主觀動機作出限制性規定。從孫某案可以看出,雖然法院是根據《食品安全法》作出本案的判決,但是食品購買者也是消費者,且新消法中同樣沒有對消費者的主觀動機作出限制,即知假買假者仍然有權要求懲罰性賠償,應當受到《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保護。
三、知假買假現象反應出的新《消法》懲罰性賠償制度的不足
我們知道,新《消法》關于懲罰性賠償的規定主要體現在第55條,相對于舊《消法》,該條有許多進步之處,但第55條仍然存在很多不足,尤其是面對生活中屢見不鮮的知假買假現象以及這一現象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時,這種不足更是明顯。
(一)消費者定義模糊
對消費者的認定問題,長期以來一直都是學界爭論的焦點,主要是圍繞知假買假者是不是消費者的問題展開討論。對于這個問題學界兩位知名的學者分別有不同的看法,王利明教授認為:在市場中,消費者往往是與生產者以及經營者相對的,三者之間往往是非此即彼的關系。商人購買商品和接受服務往往是為了將商品或者服務再次轉手或者專門從事商品交易活動,如果他或者她購買商品和接受服務不是為了以上目的,往往其便是消費者。即使是明知商品有一定的瑕疵而購買的人,只要其購買商品不是為了銷售,不是為了再次將其投入市場交易,我們就認為其為消費者”。②而梁慧星教授認為:知假買假者不是消費者,不受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保護。③而新《消法》并沒有關于何為消費者的清晰表述。很多人認為,《消法》第2條對何為消費者作出了規定,即消費者是指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人。然而,第2條不是在界定消費者內涵,而是在界定該法的適用范圍,以致長期陷入“知假買假者是否屬于消費者”的邏輯怪圈。④新《消法》更沒有對知假買假者是否是消費者的相關規定,而知假買假者是否是消費者關系到知假買假者能否依據《消法》要求懲罰性賠償或者主張其他權益。
(二)“欺詐”認定障礙
我國《消法》規定中并沒有關于何為欺詐行為的概念。關于欺詐行為,有的學者認為,應當依據民法關于欺詐的一般認識來理解《消法》第四十九條,主觀故意為欺詐行為的構成要件。⑤有的學者則認為,《消法》具有特別法的性質,被控售假者的主觀狀態是無需考慮的。⑥在一些案件的審判中,因為法官對“欺詐”含義有不同的理解導致不同判罰的現象并不少見,試舉兩個案例:
“趙某訴上海某生活購物有限公司蕭山分公司買賣合同糾紛”一案中,杭州市蕭山區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被告作為經營者對商品標志的使用有效期間已過的事實事先并不知情,無論從經營者的主管角度還是客觀角度,都無法判定經營者存在欺詐行為,故判決駁回原告請求,并沒有適用懲罰性賠償的規定。
與此不同,在上述提及的孫某訴南京某超市有限公司江寧店買賣合同糾紛一案中,判決結果指明:某超市作為食品銷售者,未按照保障食品安全的要求儲存食品、未按要求及時檢查待售食品,清理不符合要求的食品,或者即使某超市履行了上述義務,但是其履行為瑕疵履行,即其并沒有按照相關要求清理過期商品,導致其仍然擺放并銷售超過保質期的某品牌香腸,可以認定為銷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⑦趙某案中法官認定被告并不存在主觀的欺詐故意,而孫某案中,法官卻推定被告存在主觀上的故意,兩個案例中,面對同樣的情況,法官對于被告主觀是否存在欺詐的故意卻有不同的看法,導致兩種不同的價值取向和審判結果,這一切都要“歸功”于我國《消法》并沒有對“欺詐”作出明確的定義。
四、知假買假現象對完善新《消法》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啟示
(一)明確懲罰性賠償制度的適用主體
知假買假者究竟是不是消費者?知假買假者究竟受不受消法保護?適不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這一系列點問題都亟待解決,而最好的解決方式并不是通過經驗原則去判斷,因為經驗本身就具有主觀性,并沒有一個明確的客觀標準,依據經驗原則容易造成司法的不穩定。筆者認為,應當在《消法》中單獨加入一個條款或者出臺相關的司法解釋明確消費者的定義,以用來解決知假買假者是不是消費者,適不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等問題。
(二)明確欺詐行為的含義
新《消法》中無論是因為違約損害中還是在侵權損害中,經營者主觀上是否具有欺詐的故意均是是否適用懲罰性賠償的判斷標準。因此《消法》領域中如何定義“欺詐”成為是否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的關鍵。基于此,欺詐行為的具體含義和判斷欺詐行為的方法都應當在《消法》中有所體現,為懲罰性賠償的適用提供準確的法律依據,以便理論界以及實務界更好地適用懲罰性賠償的規定。
首先,可以把欺詐定義為:經營者未謀取不法利益,故意告知消費者不真實信息、隱瞞真實信息,且上述行為的程度足以導致具有一般注意的一般消費者作出錯誤的意思表示。
其次,關于如何判斷欺詐行為,筆者認為,經營者的主觀認知和客觀行為都應被顧及,即主客觀兩方面都應有相應的規定。主觀認知方面,應將經營者故意、重大過失、一般過失都劃入欺詐的主觀標準范圍,應適用過錯推定責任,不能適用無過錯責任,即不能完全不考慮經營者的主觀因素;客觀行為方面是指經營者是否以隱瞞缺陷的方法提供了不符合客觀標準的物品或服務。
[注釋]
①應飛虎.知假買假行為適用懲罰性賠償的思考——基于法經濟學和法社會學的視角[J].中國法學,2004(6):118.
②王利明.消費者的概念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調整范圍[J].政治與法律,2002(2).
③藍壽榮,周艷芳.論消費者傾斜性保護的邏輯[J].南昌大學學報(人文與社會科學版),2015,6,46(3):104.
④稅兵.懲罰性賠償第規范構造——以最高人民法院第23號指導性案例為中心[J].法學,2015(4):101-102.
⑤梁慧星.<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的理解與適用[N].人民法院報,2001-3-29.
⑥王衛國.中國消費者保護法上欺詐行為與懲罰性賠償[J].法學,1998(3).
⑦指導案例23號:孫銀山訴南京歐尚超市有限公司江寧店買賣合同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1.
[參考文獻]
[1]應飛虎.知假買假行為適用懲罰性賠償的思考——基于法經濟學和法社會學的視角[J].中國法學,2004(6).
[2]王利明.消費者的概念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調整范圍[J].政治與法律,2002(2).
[3]稅兵.懲罰性賠償第規范構造——以最高人民法院第23號指導性案例為中心[J].法學,2015(4).
[4]梁慧星.<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的理解與適用[N].人民法院報,2001(3).
[5]王衛國.中國消費者保護法上欺詐行為與懲罰性賠償[J].法學,19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