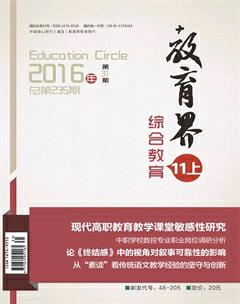紀錄片的鏡語風格與特色
李珣+魯莉卓
【摘 要】紀錄片作為影視類型片中一個重要的片種,其最大魅力可能就在于所展示內容的本色自然。為達到本色自然的藝術效果,紀錄片鏡語的三個組成部分畫面語言、文學語言、音樂音響語言均體現出了和其他類型的影視片截然不同的風格與特色。
【關鍵詞】紀錄片 鏡語 畫面語言 文學語言 音樂音響語言
紀錄片是以客觀紀實的手法,對歷史和現實生活進行真實、客觀地再現,并給人以一定審美享受的影視作品。正如中國電視紀錄片批評家任遠先生所說:“紀錄片是現代社會人們借以闡明抉擇、解釋歷史和溝通彼此的強有力的手段。它集‘說服、告知、娛悅于一身,使我們的屏幕閃耀著‘文化使者的靈光。”[1]作為影視類型片中的一個重要的片種,紀錄片的最大魅力可能就在于所展示內容的本色自然。圍繞著本色自然,紀錄片鏡語的三個組成部分畫面語言、文學語言、音樂音響語言均體現出了和其他類型的影視片截然不同的風格與特色。
一、畫面語言:大量長鏡頭的合理使用
紀錄片畫面語言最大的亮點,莫過于對長鏡頭的大量、合理的使用。長鏡頭就是在一個統一的時空內不間斷地展現兩個以上的動作或一個完整事件的鏡頭。換言之,其就是指攝像機與攝影機從開機到關機不間斷地連續一次拍攝的視頻片段。過程的持續性,時間的連續性,空間的整體性,只有長鏡頭能夠完成。長鏡頭是紀實風格最重要的表現手段之一。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長鏡頭幾乎成了紀錄片的代名詞,因此,長鏡頭運用的好壞,是決定紀錄片畫面語言成功與否的關鍵。
作為中國紀錄片史上的里程碑,《望長城》里就有一段長達五分鐘的長鏡頭段落,描述焦建成找到牧羊人談論民歌,邀請牧羊人唱一段,牧羊人開始不愿意唱,后來在焦建成堅持下,牧羊人高聲唱出富于地方特色的民歌。這一長鏡頭將事件發生的地點、人物、牧羊人情感的變化都一一展現出來。從牧羊人不愿意演唱,感到為難的面部表情到自然地進入演唱狀態,攝像機不斷變換著機位和角度,但是鏡頭始終未斷,完整地保留了事件進程,使人感到真實可信。此外,片中無論是對包爾呼一家探親的跟蹤拍攝,還是表現發掘長城磚,抑或是對新疆庫車漢代烽燧的尋覓,都幾乎讓你看到了整個事件的全過程。尤其是王相榮母親對攝制組依依惜別的情景,讓你切實地體會到了大西北人,像黃土地一樣質樸的情感。
在優秀紀錄片《最后的山神》《龍脊》中,長鏡頭的使用都有著精彩的表現。如《最后的山神》中“孟金福等人制作樺皮船”的段落;《龍脊》中“爺爺進考場”的段落,攝像機就好比觀眾的眼睛,在事件發生的現場觀察、感受所發生的一切,使觀眾體會到一種強烈的現場感和參與感,這也許正是紀錄片吸引人的地方之一。當然,長鏡頭的使用必須“量體裁衣”,倘若只是為紀實而濫用長鏡頭堆砌素材,紀錄片的藝術價值就會蕩然無存,更不用說達到紀錄的真實感了。
二、文學語言:引導觀眾,補充畫面
紀錄片中,解說詞是文學語言的核心和主干。由于紀錄片以真實作為生命,所以紀錄片的畫面時空被嚴格限定在現在進行時,對過去時和將來時卻鞭長莫及。此外,對于人物復雜的內心世界、事物發展的規律等抽象、無形的因素,畫面就更加無所適從了。所以在紀錄片中解說詞承擔著畫面局限所不能完成的職責。
紀錄片中,解說詞的作用主要是引導觀眾、補充、升華和銜接畫面。解說詞是以畫面為基礎,為畫面服務的,不會取代畫面語言和被采訪者,代替觀眾去審視和思考。因而,解說詞一般不能太滿,只在畫面轉場和必要的地方做畫龍點睛的說明。此外,由于紀錄片本色自然的風格,所以其解說詞既淺顯易懂,又朗朗上口;既精練深刻,又充滿感情。
紀錄片《最后的山神》中有這樣一句解說詞:“在老一輩人眼里,山林是有魂靈的;而在年輕人眼里,山林不過是山林。”短短的一句話,將兩代人在思想觀念等各方面的差異說得通脫透徹,這句近乎白描的語言不是評論,而是陳述語氣,巧妙地把創作者的主觀情感融入平靜客觀的陳述中。
紀錄片《藏北人家》結束時的畫面是:晨光中的草原,萬物生機勃勃,遠山,逆光中的草原,措達微笑著走出帳篷去草原牧羊。與之相對應的解說詞是:“新的一天開始了。這一天同過去的每一天都一樣。對措達·羅追來說,昨天的太陽,今天的太陽,明天的太陽都一模一樣,牧人的生活,就像他們手中的紡錘一樣,往復循環,循環往復,永遠是那樣和諧,那樣寧靜,那樣淡遠和安寧。”這段解說詞揭示了全片主旨,表達了創作者的淡淡羨慕,超越了畫面內容本身,是全片內容的概括和深化。
紀錄片《沙與海》中有打酸棗一段,畫面長達5分鐘,解說詞卻僅有100多字,它這樣寫道:“離劉澤遠家門不遠的地方長著幾棵沙棗樹,是種植的還是自生的,誰也搞不清楚,也從來沒有人為它澆水,然而這幾棵樹每年都開花結果。”這平淡、簡練的解說,引發了觀眾無限的聯想,想到劉澤遠一家也像沙棗樹一樣,克服生存環境的艱難而生活著,并且“開花結果”。
三、音響語言:展開了真實的生活氛圍
音響語言也稱為同期聲(包括現場采訪),是指用電子采錄設備在記錄視頻信號的同時,記錄與視頻信號保持同步的真實的現場聲音。同期聲包括畫面上出現的和未出現的人物語言、動作聲響、環境音響。紀錄片中營造紀實風格,一靠長鏡頭,二就是靠同期聲。
同期聲能夠增強現場的真實感,把觀眾帶入現場音響所營造的環境和氛圍中去,達到對真實世界的完整復原。同期聲還具有強大的敘事和傳遞信息的能力,拓展對事物表現的縱深度。同期聲還可以增強紀錄片的參與性和可看性,使片子不再是單方面的解說詞的播讀。當出現人物同期聲采訪的時候,通常情況下會要求被采訪者出鏡,因為這種聲畫同步的形式可以增加影片的真實感和現場感,也可以豐富敘事的方式,增加傳播中的信息含量。美國的一位心理學家對人們進行交談時信息傳遞的情況進行了研究,最后得出這樣的結論:“人們在交談時,傳遞某項信息的總效率=言詞7%+聲音38%+面部表情55%。”就聲音而言,它還有音色、音高、力度等聲音的表情特征,這些特征也可以從某個角度反映出人物的性格特征或者人物在特定狀態中的心境,伴隨同期聲出現的人物形象都能傳遞出更多的信息。在紀錄片《沙與海》中,記者與納鞋的女子關于戀愛、婚姻談話的同期聲與該女子的動作細節密切結合,非常生動地展示了人物心理活動。除此之外,持續的同期聲、現場聲還能在很大程度上彌補鏡頭轉換給影片帶來的斷裂感和生硬感。
四、音樂語言:烘托畫面,深化主題
紀錄片中的音樂,一般是后期根據片子的需要配上去的。紀錄片在恰到好處之時,用音樂來烘托畫面,深化主題;音樂語言運用得好,不僅能增加紀錄片的色彩,而且還具有獨立的表現力。紀錄片《最后的山神》片中的主題音樂,作曲家采用了單主題音樂貫穿式。樂曲帶有遠古的氣息,像古老山林的悠韻古調,和片子的畫面基調相得益彰。
紀錄片中的音樂應該少而精,因為音樂帶有強烈的主觀性,而紀錄片追求的是客觀的真實。只有在畫面語言、文學語言、音響語言都無法表達感情廣度和深度的時候,音樂才會有用武之地。音樂可以是語意的延伸,人物感情的深化,也可以是抵達觀眾心里的橋梁。
五、結束語
紀錄片將畫面語言、文學語言、音樂音響語言完美結合,相互補充,去再現人物或事件的原貌,挖掘人物或事件的主題思想,從而成就了紀錄片獨有的風格與特色。
【參考文獻】
[1]任遠.電視紀錄片新論[M].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
[2]林旭東.影視紀錄片創作[M].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2.
[3]高廷智.電視聲音構成[M].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4]倪祥保;邵雯艷.紀錄片專題片概論[M].蘇州大學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