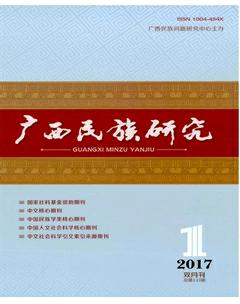再論族格
【摘 要】通過分析民族自決權、少數民族文化權利保障存在的問題,認為,現有法律體系對民族權益的保障存在結構性的障礙。通過引入公法人制度,賦予民族公法人地位,是解決該問題的關鍵。在此過程中,國家及其法律確認了民族有其族格。
【關鍵詞】民族;民族自決權;少數民族文化權利;公法人;族格
【作 者】朱俊,重慶大學法學院教師,法學博士。重慶,400045
【中圖分類號】C955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4 - 454X(2017)01 - 0012 - 010
一、引言
當代社會正處于一個價值多元的時代,強調不同文化及其價值對整個人類社會的獨特意義。這不僅是客觀現實,也是多元文化主義的理論主張。多元文化主義興起于20世紀60年代的西方世界,是一個諸多學科都普遍接受的社會思潮。從人口角度講,多種群文化團體構成了現實世界;從意識形態角度講,宗教寬容與相互尊重普遍存在,文化在各文化群體內部有序傳承;從政策角度講,政府出臺旨在減少歧視的全方位政策,并確保資源的公平使用。簡言之,多元文化主義主張現實世界的文化多樣性,并在理論上強調文化的平等和多元。[1 ]在此背景下,我們發現,少數民族①的文化正遭受現代化的侵蝕,亟需賦權以保護。
事實上,民族學界的馬俊毅、席隆乾在《論“族格”——試探民族平等與民族自治、民族自決的哲學基礎》一文中,從政治哲學角度論證了族格的存在,從而為法律賦予少數民族集體性權利奠定了理論基礎。他們認為,“族格”是“自然賦予的,即天賦的每個民族無論大小強弱都具有平等的權利和尊嚴”。其中,人格是“族格”的哲學基礎,少數民族完整“人格”的實現需要“族格”的保障。既然人格是天賦的,那么族格也必然是自然賦予的。因而族格就其內容而言,是“民族政治權利的平等和文化上的多元”。[2 ]拙文《也論族格——從“天賦人權”展開》也從政治哲學角度論證族格的正當性。民族是人的社會性及其文化性的自然載體,從天賦人權之權利根源于人這一立場出發,民族也當從人的社會性出發享有其集體性的權利,在民族集體性權利得以證成之時,民族族格就已經蘊含其中;從民族歷史來看,是民族建國,即先有民族后有國家,民族在簽訂建國契約時就已經預設了族格的存在;民族自決權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本身也預設了族格的存在。因此,理論與實踐均已表明,民族確有其族格。[3 ]
然而,即便我們在政治哲學上證成了民族族格的存在,也僅僅只是觀念上的,并不意味著它在制度上的存在。作為一個法學術語的“族格”,它必須在法學理論上被證成。必須肯定,現有民族權益保障面臨著結構性的障礙,無論是民族自決權還是民族文化權利保障,都需要進一步確認民族作為一個集體,有其法律人格。并且,作為擁有法律人格的民族,就是公法制度上的公法人;作為公法人的民族必須接受公法人理論的改造,一方面有其集體性的權利,另一方面又必須有所克制。
二、民族權益保障的結構性障礙
現代法律體系對民族權益的保障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民族自決權,二是少數民族文化權利。但是,就當前民族權益保障的現實來看,一是民族分裂主義活動猖獗,二是少數民族文化正面臨著消亡的危險,這意味著現代法律體系對民族權益的保障在某種程度上是失敗的。實踐的失敗有其理論上的原因,當前民族理論的研究也正著眼于對該原因的探究。
(一)民族自決權及其限度
所謂民族自決權,就是“每個民族獨立處理自己事務、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4 ]351,不僅涉及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事務的自治權,還涉及政治上的自決權。有關民族自決權的正當性論證,主要有文化解釋和民主解釋兩種模式。[5 ]159
文化解釋主要以費希特為代表。他認為,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獨特性是一個民族的獨特性所在,是民族享有自決權的基礎。共同的歷史命運使一個群體形成了“民族”。但他忽略自然因素的重要性,只強調歷史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對于日耳曼種族在被征服國家與當地居民混血的情況,人們也同樣不必重視;因為勝利者、統治者也好,由混血形成的新民族的締造者也好,都不外是日耳曼人。除此之外,在國外同高盧人、坎塔布里人等等發生的混血,與在國內同斯拉夫人發生的混血相同,而且范圍并不更小。”[6 ]56-57并且,是共同的歷史經歷、生活習慣締造了民族特征。法國的民族特征就是有教養、有愛心、好父親或好主人或好仆人,等等,[7 ]52-53這與其他民族都不同。
民主解釋以馬志尼、列寧等人為代表。他們在論述民族自決權時,實際上并未區分“民族”“人民”“國家”等概念,這些概念是交替混用的。“17世紀后,西方用‘民族(nation)指稱主權國家的人民,而不問其種族和語言是否一致。實際上它是對一國之民的統稱。”“從法國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歐洲大陸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們也常使用‘民族這一概念來指享有主權的民族國家。”[4 ]5馬志尼認為,民族自決是通過本國人民而非貴族、外國勢力來實現意大利的國家統一、獨立與民主。[8 ]列寧認為,當今帝國主義大國壓迫其他民族是一個普遍現象,因此,反對帝國主義就意味著需要同這種民族沙文主義進行斗爭,這應該成為社會民主黨民族綱領中基本的、主要的、決定性的觀點。[9 ]82
在上述論述中,我們發現,民族自決權與自由權利、人民主權、民族主義聯系在一起;同時,自決權的主體既有民族,又有人民,是反對民族壓迫的權利。這里有兩點值得關注:一是有關主體問題,二是權利的產生及其行使問題。
關于主體問題,有論者指出,民族自決權的主體是“國族”而非“民族”。首先,民族自決權伴隨近代民族國家的建立而產生,要求一定疆域內的各族群統一和團結,呼吁國族意識和愛國精神,以形成一國一族的政治國家。無論是費希特還是馬志尼、列寧都是如此。其次,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只有通過國家才能定義,是民族這一概念滿足了現代國家內部的集體身份認同問題。最后,從歷史來看,民族自決權與人民主權不僅密切相關,而且有其一致性。歐洲現代民族國家是建立在將人民這一抽象概念賦予民族這一公民團體之上的,人民與民族、公民與民族身份重疊而且一致。[8 ]但是,有學者分析聯合國工作語言后指出,聯合國翻譯人員并未去深究“民族”與“人民”的不同,時常將二者混同。[10 ]關于權利的行使問題,有學者分析,民族自決權可分為對內自決權和對外自決權,后殖民時代的主權國家內的各民族只是擁有對內自決權,而且由政治自決權轉向了經濟自決權。[11 ]有學者通過分析國際條約后認為,民族自決權的行使不能破壞既存國家的政治統一和領土完整,而且主要適用于聯合國托管下的非自治領土、處于殖民統治或異族壓迫下的民族;對于是否允許既存國家內的民族獨立,各國意見嚴重分歧。[12 ]有學者從法理上指出,被壓迫民族通過武裝斗爭方式行使自決權;后殖民時代的人民通過公民投票行使自決權。對殖民地人民的武裝行使自決權,理論與實踐都沒有太大分歧;但對公民投票這一方式,理論與實踐都有不同見解。從理論上看,公民投票受到了主權原則的限制,應當是全國人民投票而非某個試圖獨立的民族投票;從實踐上看,公民投票的效力主要取決于國際政治中的力量對比,究竟有幾個大國予以承認。在蘇聯解體時的國家獨立潮中,公民投票并非是決定國家獨立,而是確認國家獨立,這是政變而非公民投票的結果。[10 ]
就此而論,民族自決權存在理論與實踐的困境,權利主體的不確定性帶來了民族分裂的可能,權利行使上的政治性帶來了民族分裂的機會主義。從字面上講,民族自決至上論認為,每一個“民族”都應當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這是民族分裂主義分子最直接的主張。[8 ]而實踐上的困難,很顯然并沒有完全的通過權利主體為“國族”、權利內容在后殖民時代轉向對內的經濟自決權而得以解決。民族自決權理論解決民族分裂主義存在結構性的困難:首先,它未能明確權利主體問題,人民與民族畢竟不同。實踐上既有單一民族國家建立,又有多民族國家建立。如果說民族自決權由“國族”行使,那它與人民主權又有何區別?其次,民族自決權即便是只有民族享有,那究竟是只有被壓迫民族才享有,還是所有民族都享有?這是民族自決權在發生學上必須回答的問題。但事實上,該問題在理論之間、理論與實踐之間還存在諸多分歧。復次,民族自決權的行使,所有理論都承認有限制,那就是主權原則,但主權原則與民族自決權的相互關系怎樣,理論上卻并不是很清晰。最后,民族自決權在理論、實踐上都預設了民族是一個客觀存在,但并沒有將之明確化,因而有以上的結構性障礙出現。
(二)少數民族文化權利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根基所在,但在現代化趨勢下,不少少數民族文化都面臨著生存危機。現代化描述的是一個更為復雜的過程,即一種具有特定社會形式的復雜產物,它并不局限于社會現實的一個方面,而是包括社會生活的一切基本領域。[13 ]26,28對少數民族文化而言,現代化不只是機遇,更是挑戰——它不得不面對現代化所帶來的文化城市化、國家化、工業化、商業化(傳媒化、網絡化)、博物館化、全球化(西方化)的問題。①
少數民族文化受到了城市化的影響。首先,城市化改變了少數民族族裔長期形成的生活方式,使傳統文化的傳承環境受到了根本性的影響。其次,城市化使得人口流動頻率加快,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承秩序被阻斷。復次,城市化對少數民族內部凝聚力產生了消極的影響,使少數民族文化的載體逐漸脆弱。最后,少數民族文化傳承機制受到城市化影響,少數民族文化傳承人越來越匱乏。[14 ]而在國家文化面前,少數民族文化面臨著主流群體文化的沖擊。與此同時,全球化、國家權力、少數民族文化三者正以國家權力為核心進行著博弈,[15 ]即現代民族國家面臨的全球化對國家文化的普世性挑戰,更使得少數民族文化面臨普世性挑戰。在工業化方面,少數民族的手工業在價格上無法同工業化大生產相抗衡,如曾廣泛存在于各地的扎染、蠟染等紡織品以及繡花鞋等,現如今僅成為各地旅游市場的紀念品,無論是規模還是數量都已急劇萎縮。[16 ]商業化也正對少數民族文化產生影響。以甲居藏寨為例,旅游與藏族的神圣民族性呈現出雙向、雙因的互動:一方面,在商業開發過程中,藏族文化開始去神秘化,這導致藏族同胞的內部認同削弱;另一方面,旅游產業選擇性地加強了異質感,強化了藏族與游客之間的身份差異,又使得當地藏族同胞的外部認同呈現增強趨勢。[17 ]但從其他民族地區的文化旅游開發看,過度的包裝、任意的曲解、商業的炒作層出不窮,這是對少數民族文化的毀滅性傷害。[18 ]同時,旅游開發還有可能僅使開發公司受益,少數民族并未從中獲得多少收益。[19 ]少數民族文化的創意產品開發也存在類似問題。
此外,大眾傳播對少數民族文化的表達也有局限性:第一,它以自身的理解重構少數民族文化,使觀眾對該文化不可能有一個真實的了解。第二,少數民族文化的價值、情感在傳播過程中,受到來自不同價值標準的觀眾的不同理解和評價。第三,傳媒化改變著少數民族文化主體的感知和權益。因為它使得該文化脫離了生存和發展的環境,接受著新價值體系的評判,導致該民族文化及其主體無所適從。第四,作為商業化特殊過程的傳媒化往往會歪曲或奇觀化少數民族文化,導致該主體的抗辯甚至是抗爭。[20 ]
然而,少數民族文化的最大危機卻應當是博物館化。雖然有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制度(這一制度實質上也是少數民族文化技藝的博物館化形式)出現,但少數民族文化仍然面臨著年輕人不愿意學的尷尬局面,且在苦苦尋找著合適的傳承人。
這表明,現有的法律體系無法幫助少數民族及其文化應對現代化危機。因為從根本上講,現代法律體系并沒有將權利建立在文化保護的基礎上,它考慮的更多的是個體的權益保障,而非群體的權益保障。用加拿大學者金里卡的話來講,這是自由主義法律體系的邏輯結果,權利在建立之初預設的就是原子化的公民,沒有文化的因素,因而它只是保障個體而非群體。[21 ]134-158即便有多個國際條約確認民族的文化權利,但在國家法律體系當中,它仍然是不成體系的。[22 ]
總之,無論是民族自決權還是少數民族文化權利,在保護民族集體權益保障方面都存在著某種法律上的困難,它亟需解決。
三、作為公法人的民族
從以上分析看,現有法律體系強調從個體角度保障少數民族文化權益,存在結構性的困難。就結構性困難本身而言,它意味著這種法律體系在設計之初就出現了問題,即少數民文化權益保障不應當從個體出發,而應當從群體出發。民族是一個以文化為單位的客觀實在。從法理上講,將民族作為一個群體,即視為法律上的特殊組織——法人,然后設計其文化權益保障的法律制度,并不存在理論上的困難。
(一)公法人理論
將團體視為法律上的主體,萌芽于羅馬法,帝國后期的羅馬法已經開始承認某些特殊團體在法律上享有獨立的人格。[23 ]82通過人格這一法律概念,羅馬法賦予特定團體以法律主體資格。而人格是羅馬法上的重要法律概念,只有羅馬的自由市民才享有完整人格,奴隸沒有人格,婦女的人格也是有缺陷的。正是人格這個概念,羅馬法實現了人與人格的分離。換言之,法律意義上的人并不一定就是生物意義上的人。法律上的人是法律技術運用的產物,其與主體是否有生命現象并無必然聯系,因而賦予無生命的團體以法律人格便有了可能。[24 ]而根據羅馬法,“為了形成一個真正的團體,即具有法律人格的團體,必然有數個(至少為三人)為同一合法目標而聯合并意圖建立單一主體的人”[25 ]52。日耳曼法觀念認為,團體是人的自然聯合,有共同力量,應當區別于個人,二者在權利上不完全相同。[26 ]50中世紀教會革命后,教會社團法得到了較快發展,并認為可以通過人的主觀擬制賦予團體以法律上的權能,“任何具有必要機構和目的的人的集團——例如,一所救濟院、一所醫院、一個學生組織或者一個主教管區乃至整個教會——都構成一個社團……依照教會法,社團的財產是其成員的共同財產,如果沒有其他方法償還債務,便可以向它的成員征稅。”[27 ]264
正是在教會法、羅馬法的基礎上,法人概念在中世紀的英國正式出現,一方面繼承了羅馬法有關法人特許的理念,另一方面又繼承了教會法創設法人團體的理念。但法人作為一個明確的法律術語,首次出現于1798年德國法學家胡果的《實定法哲學之自然法》一書。而1896年頒布的《德國民法典》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了系統而完整的法人制度。此后,基于法人制度在社會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各國均在其法律中予以規定。其核心理念在于:一是一個組織或實體只要得到國王、政府、議會的許可或法律的承認,就是一個法人;二是該組織或實體作為一個法人,在法律上已經同其成員或任何第三人區別開來,因為它有了獨立人格;三是它可以以自己的名義擁有法律利益、實施法律行為、進行訴訟等自我保護活動。①
在法人制度中,人格是核心的技術工具,一方面只是法律對團體的確認,并不改變團體的性質;[28 ]另一方面,賦予法人人格是為了保護自然人的團體人格利益,從根本上講,就是為了保護自然人。[29 ]② 但是,正是人格制度將團體與個人區別開來,在權利賦予、義務承擔和責任承擔方面,法人可以不同于個人。德國法學家梅迪庫斯認為,民法上的法人的這種獨立性表現為四個方面:一是不存在與成員相關的解散事由,二是成員可以更換,三是決議適用多數票決制度,四是有專門機關負責對外。[30 ]818
隨著社會發展,法人制度開始從私法領域進入公法領域,出現了公法人制度。通俗來講,公法人就是按照公法而設立的法人。它與私法人的區別是它是行政組織,與行政機關的區別是它是獨立的權利義務主體。[31 ]從理論上講,公法人的出現與兩個概念聯系在一起,即人格和自治。簡言之,公法賦予某個自治團體以人格,它就是公法人。因此,是自治的概念導致公法引入法人制度。
法學上的自治有其嚴格定義。Paul Laband和Heinrich Rosin提出的團體自治論解釋了它的法律內涵。Laband認為,自治是一個介于國家、個人之間的公法主體,為國家用來履行國家任務服務。Rosin以該理論為基礎,體系化了自治概念,并將之區分為法律意義和政治意義兩種:自治的法律意義的定義是,上級統治團體承認下級團體具有行政管理的法人人格,并稱這個下級團體為自治團體;而以參與為特征的古典意義上的自治行政,則歸屬于政治意義上的自治概念。[32 ]從治理手段層面看,分權與自治相伴,自治是行政分權意義上的,公法人制度就是法律意義上的自治的制度表現。根據自治目標的不同,德國法上的自治團體有兩種類型:一是地方自治團體,諸如鄉、鎮等;二是功能自治團體,即負有特殊功能并用以履行特定任務的自治團體,諸如大學、社會保險機構等。而側重于分權理論的法國法上的公法人也有兩種類型,分別是地方分權意義上的公法人和專門公務分權意義上的公法人。[33 ]
在現代行政組織體系中,公法人制度的出現是希望通過法人的身份獨立與行為自主以實現行政的自治與效率。因此,自治與效率是公法人的核心功能。所謂公法人的自治功能,就是公法人制度滿足公共行政承擔者對自治的需要。根據自治與分權理論的看法,公法人是一種國家治理的組織手段,是介于國家和個人之間的行政組織,因而它必須具有獨立于國家的行政能力,這就是自治。自治保障了公法人享有獨立的財產和人事任免權,有獨立預算等權利能力,并以自己的名義從事相關事務,進而實現其存在的特殊目的。所謂效率功能,就是公法人制度的出現是為了更好地滿足社會公眾對政府更優質且高效的“公共物品”供給的需要,這是國家之所以讓公法人組織自治的原因所在。從資源優化配置的角度講,國家將其部分權利分配給公法人,不僅是為了實現分權的目的,還在于更好地滿足社會公眾對公共物品的需求。[31 ]目前,德國的公法人制度較為完善,設計出了三類公法人:1.公法社團,這是基于公法而設立的公法人,由社員組成并實行自治,在國家法律的監督下以公權力的行使來執行國家任務。更具體講,公法社團包括了以下五種類型:一是地域性公法社團,是以某一地區的居民為成員的公法社團,主要是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如聯邦、州、鄉、鎮等;二是屬物性公法社團,是人民基于對某種不動產或產業的所有權或經營權而形成的公法社團,如工業總會、水利協會等;三是屬人性(或者身份性)公法社團,是成員基于特定身份或職業組成的公法社團,諸如工商業協會、高等學校學生會等;四是聯合性公法社團,是由公法人作為成員所組成的公法社團,諸如由各州律師協會組成的聯邦律師總會等;五是非典型公法社團,例如德國公立大學既是公法社團又是國家設施等。2.是具有權利能力的公營造物,是由一定設施和行政工作人員組成的以適用關系的形式為人民提供特定服務的公法人,諸如鐵路、銀行和圖書館等。需要說明的是,德國法上為特定公共目的而設立的公營造物或基于法律的規定或基于行政主體行為而設立,雖然都是公法組織,但不一定都具有權利能力,其內設機構以及與營造物主體之間的關系需要根據公法來判斷。3.公法財團,是國家或者其他公法社團為了實現公共目的而捐助財產并根據公法設立的沒有成員的組織體,諸如普魯士文物基金會等。①
因此,公法人是國家為了滿足公眾特定公共物品需求而根據公法設立的特殊團體,它享有獨立的法律人格,并具有權利能力,能夠作為獨立主體以個人或國家為被告提起訴訟。[34 ]作為權利主體,公法人的法律特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公法人的設立須有法律依據;二是享有固定的任務、執掌、管轄和權限;三是必須受到母體機關的監督;四是作為行政組織在作出行政決定時必須遵循行政程序法——行政相對人可據此提出行政救濟。在德國,公法人還享有憲法所規定的基本權利。[35 ]即便公法人享有憲法上的基本權利,其權利能力也是受限制的。根據代理權限制說,公法人依法確定的目的范圍,是它的代理權的界限。而對于它超出目的范圍的行為,可以根據無權代理的規則來處理,這有利于保護第三人利益,保護交易安全,促進交易發生。盡管如此,公法人卻通常不具有破產能力,因為如果要破產清算,它管理社會的目的就無法實現。當然,某些特殊的公法人,諸如律師協會等還是具有破產能力的。[36 ]總之,公法人制度的出現,滿足了社會公眾的特定公共需求,既實現了公民自治,又滿足了時代的效率要求。
(二)作為公法人的民族及其族格
耶林說:“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創造者。”[37 ]公法人就是國家為了滿足公眾對自治、效率的需要和某種特定公共物品需要而創制的法律制度。質言之,只要能夠實現這個目的,國家都可以通過公法賦予某個團體以公法人資格,即法律人格,進而使之享有公法人的特定權利義務。事實上,民族既有自治的需要,又有效率的需要,這正是它目前所面臨的結構性障礙所要解決的問題。
1. 民族符合設立公法人的目的
民族需要自治。雖然從本質上來講,這是“一種缺乏嚴格定義域的民族政治設想,限制我們只能從民族政治人格平等的角度來解釋它和理解它;如果把民族自治與自我為政、自我統治等主張聯系起來,由于在自治的目標、外延和操作工具上人們各有各的看法,因而難以成為當代多民族國家處理民族政治問題的可行方案”;即便將民族自治理解為“自主管理本民族內部事務”等,仍然只是一個可以多方證偽且無法實踐的假命題。[38 ]但是,我們仍然認為民族有其自治的必要。
首先,多民族國家是由多個民族共同構成的。從歷史來講,也確實是在各民族同意建國的基礎上組建了政治國家。即便我們認為社會契約并不是一個真正的建國文件,而只是一個思想實驗,但仍然不能否認各民族同意建國這個事實。因此,是民族將本民族關于國家管理的權力移交給了國家,這些權力只是民族不適宜享有且為了獲得更大范圍的權益而移交的,這意味著民族手中還保留著某些與其密不可分的權力。即便民族將全部權力都移交給了國家,但現代國家畢竟不是“利維坦”,它仍然需要對民族這個集體予以保障。在此意義上,民族有其自治的可能。
其次,雖然民族自治在理論上被確證為一個不嚴格的命題,但在實踐中,各國仍然通過各自的政治制度安排使之融入國家政治當中,有公民化方式、社團化方式、政黨化方式、議會化方式、一體化方式、多元文主義方式、土著人保留地方式、民族地方自治方式等。[38 ]這些制度安排并非是嚴格意義上的自治,但都考慮到了民族的特殊性。換言之,國家在政治活動過程中必須考慮到民族的特殊性。因此,民族自治有其可能性。
最后,民族自治作為一個理念可以是一個民族的自治,但這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從實踐來看,民族必然是有其地域的分布,進而其自治是依附于地方而實現的。①質言之,民族自治是民族地方的自治,根據民族分布的情況而建立,并非整體民族自治或單一民族自治。在這樣的自治結構中,它保障了少數民族在地方民族事務管理上的主導權,但并非排斥其他民族公民參與地方政治生活的權利。民族自治地方事務有兩類:一是單純的地區性事務,所有本地區的公民均有權參與并決定;一是內涵了民族事務的地區性事務,其他民族的公民有參與權,而該民族公民有決定權。
此外,從民族自決權的角度看,民族之所以有此權利,根源仍然在于其民族地方的自治,只是這種自治提升到了建國的高度。民族自決權的賦權,是給予那些被殖民的民族的,賦予他們自由選擇國家的權利,這與人民主權聯系在一起,而人民主權的核心在人民的自我統治的實現,即自治。②簡言之,民族自決權就是民族自治在建國層面的表現,屬于國際法層面的事務;在國家建立之后,民族自決權隱退,民族的地方性自治凸顯出來,這是國家法層面的事情。因此,民族有其自治的需要,部分源于民族特殊性,部分源于民族所在地方的自治。
與此同時,民族的自治還有著效率的考量。民族自治的核心是保障民族文化權益,而它既有著特殊性,又有著資源配置優化的需要。從民族文化權益來看,既有物質性的一面,又有非物質性的一面。物質性的民族文化權益主要涉及民族文化中可物化、場景化保護的那部分,即不僅只是民俗村、博物館建設,或物質性、非物質性文化的資料搶救、收集、整理、研究、出版等,還涉及商業化開發民族文化的內容。非物質性的民族文化權益主要涉及少數民族文化中那些不能物化、場景化的文化及其權益,即文化參與權、文化受益權、文化認同權、文化保護權和文化發展權等。這些權利并非屬于民族族裔個體,而是歸屬于整個民族,因而它既有專業性的一面,又有整體性、復雜性的一面,而現有法律體系的效率不可能讓人滿意。
此外,民族的文化權益既有經濟性的一面,又有非經濟性的一面。但無論是經濟性的還是非經濟性的,都需要資源的優化配置。從外國立法經驗來講,主要有以下三種方式:公權保護模式規定政府或國家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方面的職能或行為,如普查、建檔、保存、研究、傳承、弘揚等,以及為實現這些保護行為而提供的政策、技術和財政等措施,不涉及平等主體就某一財產的歸屬、利用和轉讓等產生的權利義務關系;[39 ]194知識產權保護模式是指采用知識產權法律來規范、調整文化在其利用、傳播過程中所發生的社會關系,主要解決非物質文化遺產利用中產生的問題,旨在保障相關知識產權人精神權利和財產權利的實現;[19 ]綜合保護模式則關注到傳統文化的復雜性,強調對它的保護需要依賴綜合性措施,融公法、私法于一體,多種手段相配合的綜合性法律保護制度。[40 ]114
就此而論,民族既有自治的需要,又有效率的需要。
2. 民族的公法人類型
在公法人的三種類型中,民族屬于公法社團,即兼具地域性公法社團和屬人性公法社團特征的非典型公法社團。
公法社團是指“基于公法而設立,由社員組成并自治,在國家的法律監督下以公權力行為執行國家任務的具有權利能力的組織體”[34 ]。該概念的內涵有三:一是根據公法設定,二是作為社員自治的組織,三是以公權力執行國家任務。首先,民族并非是公法的結果,而是自然形成的特殊群體,但是它在政治國家中卻需要國家的承認。在我國,民族身份需要根據1990年的《關于中國公民確定民族成份的規定》來確定。其次,民族享有自治的權利,即便在不同的國家自治有不同的制度安排,也并不否認它是族裔成員自治的組織。中國的少數民族根據《民族區域自治法》享有民族地區的自治權利。最后,民族以公權力執行國家任務,這是法律規定的結果。從目前我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實踐來看,民族自治地方確實是以公權力在執行國家任務。即便不是在民族地區實行區域自治,就民族權益保障的內涵和措施來看,它作為公法規定的組織也必然是在執行國家任務。因此,從外觀上講,民族可以是公法人。
事實上,中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下的民族,既是地域性公法團體,又是屬人性公法社團。這里的民族自治是民族的區域自治,是民族地方的自治,就是在該民族所在地區實行的民族的地方的自治。它不同于地區自治,因為它涉及民族因素,要考慮民族的特殊情況;它是特殊的民族自治,因為它只是在該地區實行民族的自治。在地方自治的意義上,它是地域性公法團體,因為它以群體所在地的居民作為成員實行自治;在民族自治的意義上,它是屬人性公法社團,因為它在民族事務上以民族族裔作為成員實行自治。因此,它是非典型的公法社團。
3. 民族族格的法律意義
既然認為民族是非典型的公法社團,那它就是公法人,進而作為法人應當有其法律人格,暫且稱之為“族格”。因此,民族族格在法律意義上被證成。
根據公法人理論,作為公法人的民族應當根據法律的規定享有固定的任務、執掌、管轄與權限。就其管轄而言,它只應當在該民族聚居的地方。換言之,它可能在政治國家范圍內只有一個自治單位,也可能有幾個自治單位。只要達到一定的聚居規模,該民族就應當獲得自治。應當講,這種自治單位的設置,不可能達到省的規模,通常只是在縣一級。就其權限而言,民族是區域性的民族自治,是兼具民族自治與區域自治的公法人治理,上級與民族自治單位之間必然有權限的劃分,尤其涉及財權、事權、人事任免權等方面。同時,它必須受到上級的法律監督。就其任務與執掌而言,就是通過區域性的民族自治實現對本民族文化權益的保障:通過教育傳承本民族的文化,通過整理、修繕等措施保障本民族的物質性文化的延續,通過保護性開發促進本民族文化的社會影響力,通過文化傳播擴大本民族的文化影響力,通過研究本民族文化以加強同其他文化之間的交流,通過諸如公有付費制度或者社區知識產權等制度保護本民族文化的經濟利益等。
根據自治理論或分權理論,作為特殊地方自治單位的民族,它是在分享國家權力,因而它存在于主權之下,必須接受主權原則的限制。主權意味著不可分割,因而在國家統治之下的民族通常情況下都不能根據民族自決權提出民族自決的主張,更不可能根據民族自治提出民族獨立的要求。民族之所以享有此種自治權利,乃因為它不能夠獨立于國家之外,這是國家法律體系的客觀要求。但是,這種不能獨立是相對的,它必須以民族確實享有此項自治的權利為前提。換言之,民族自決權提出的根據正是這個,所以列寧指出,“民族自決權從政治意義上來講,只是一種獨立權,即在政治上同壓迫民族自由分離的權利。具體來說,這種政治民主要求,就是有完全的自由來鼓動分離、鼓動實行分離的民族通過全民投票來解決分離問題。因此,這種要求并不等于分離、分散、成立小國家的要求,它只是反對一切民族壓迫的徹底表現”[41 ]719。從法律哲學上來講,民族獨立是對既有法律體系的破壞,是對法律安定價值的否定,這種否定不可能在一般意義上完成。按照拉德布魯赫公式所言,“實證的、由法令和國家權力保障的法律有優先地位,即使在內容上是不正義或者不合目的性的,除非實證法與正義之間的矛盾達到了一個如此令人難以忍受的程度,作為‘不正當法的法律則必須向正義讓步”[42 ]232。質言之,民族獨立只有在國家壓迫達到本民族以及國際社會都不可忍受時,該民族才能獲得民族自決權。
應當講,國家賦民族予族格,是對民族法律地位的確認,同時也是國家法律秩序在民族問題上的起點,它標志著民族國家法律秩序的開始,不只是限制民族不能獨立,還在于保障民族的文化權益。
四、結語
通過對民族的公法人地位的研究,我們認為,民族自決權不過是民族文化權利在特殊情況下的表現,它是例外。因此,現代國家面對民族問題,在肯定民族主體地位的同時,實際上已經預設了對民族自決權的認同,它需要通過保障民族權益來消弭民族自決權對現實政治的張力;而將民族作為公法人,就是將民族納入國家法律體系當中,通過法律的制度設計來實現此目的。這表明,國家及其法律確認了民族有其族格。
參考文獻:
[1] 朱俊.族群平等的多元文化主義路徑分析[J].民族研究,2014(5).
[2] 馬俊毅,席乾隆.論“族格”——試探民族平等與民族自治、民族自決的哲學基礎[J].民族研究,2007(1).
[3] 朱俊.也論族格——從“天賦人權”展開[J].廣西民族研究,2016(3).
[4] 余建華.民族主義:歷史遺產與時代風云的交匯[M].北京:學林出版社,1999.
[5] 王軍.民族主義與國際關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
[6] [德]費希特.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M].梁志學,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7] [德]費希特.國家學說:或關于原初國家與理性王國的關系[M].潘德榮,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0.
[8] 江鈴寶.“國族”而非“族群”——試論民族自決權的適用主體[J].世界民族,2012(6).
[9] [蘇]列寧.列寧全集:第27卷[M].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0] 廉思,孫國華.民族自決權實現方式的法理研究——以全民公決制度為對象的分析[J].政治學研究,2008(3).
[11] 尚穎,張麗東.對國際法中民族自決原則的重新認識[J].浙江社會科學,2000(3).
[12] 張穎軍.國際法上的民族自決權原則:基于《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院的解釋[J].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5).
[13] [印]A·R·德賽.重新評價“現代化”概念[G]// 塞繆爾·亨廷頓,等.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王紅塵,譯.羅榮渠,編.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
[14] 馬偉華.沖擊與整合:城市化進程中民族社會的變遷與發展——基于民族文化、民族關系、民族權益三個視角[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6).
[15] 裴云.民族文化、國家權力與全球化[J].青海民族研究,2008(2).
[16] 葉遠鋒.淺析安順蠟染傳承與發展現狀[J].大眾文藝,2012(16).
[17] 劉亞玲.文化安全視域下民族文化認同的審視——以甲居藏寨為例的評述[J].中華文化論壇,2014(6).
[18] 柴陽,李貴紅.立法機制在少數民族文化保護與扶貧開發博弈關系中的建構[J].社會科學輯刊,2013(5).
[19] 田艷,王祿.少數民族文化風險及其法律規制研究[J].貴州民族研究,2011(4).
[20] 邱廣宏.傳媒化進程中民族文化及其主體的調適[J].貴州民族研究,2014(4).
[21] [加]金里卡.自由主義、社群與文化[M].應奇,葛水林,譯.上海:上海世界出版集團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
[22] 司馬俊蓮.論少數民族文化權利與國家義務[J].太平洋學報,2009(3).
[23] 夏新華.外國法制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24] 尹田.論法人的權利能力[J].法制與社會發展,2003(1).
[25] [意]彼得羅·彭梵得.羅馬法教科書[M].黃風,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
[26] 虞政平.股東有限責任:現代公司法律之基石[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27] [美]伯爾曼.法律與秩序——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M].賀衛方,等,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
[28] 尹田.論法人人格權[J].法學研究,2004(4).
[29] 薛軍.法人人格權的基本理論問題探析[J].法律科學,2004(1).
[30] [德]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M].邵建東,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31] 楊洋,劉曉敏.淺析公法人制度——我國公法人制度的缺陷及完善途徑[J].法制與社會,2012,04(中旬刊).
[32] Hendler, Selbstverwaltung als Ordnungsprinzip, 1984,s.8 ff:s.116.
[33] 李昕.論公法人制度建構的意義和治理功能[J].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09(4).
[34] 葛云松.法人與行政主體理論的再探討——以公法人概念為重點[J].中國法學,2007(3).
[35] 秦奧蕾.《德國基本法》上的公法人基本權利主體地位[J].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6).
[36] 周友軍.德國民法上的公法人制度研究[J].法學家,2007(4).
[37] [美]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M].鄧正來,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
[38] 朱倫.關于民族自治的歷史考察與理論分析——為促進現代國家和公民社會條件下的民族政治理性化而作[J].民族研究,2009(6).
[39] 王鶴云,高紹安.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律機制研究[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
[40] 張玉敏.民間文學藝術保護模式的選擇[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41] [蘇]列寧.列寧選集:第2卷[M].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2] [德]拉德布魯赫.法哲學[M].王樸,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ON NATIONAL CHARACTER ONCE AGAIN:STARTING FROM THE STATUS OF PUBLIC LEGAL PERSON OF NATION
Zhu Jun
Abstract:By analyzing problems in the protection of rights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and ethnic culture,we believe that there exists structural barriers to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minorities under the current legal system. The key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s to introduce the system of public legal persons and to give nation the status of the public legal persons. In this process, the state and its laws recognize the national character of ethnic groups.
Keywords:nation;the right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ethnic cultural rights;public legal persons;national character
﹝責任編輯:黃仲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