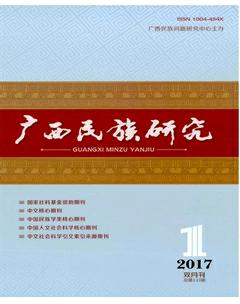漢象郡府治“臨塵縣”方位地址的文化人類學考釋
韋福安+么加利
【摘 要】龍州縣上金鄉政府所在地及周邊近年來考古發現有漢代墓葬、漢庭遺址以及青銅器和玉器,“岜傷”安置駱越將士戰死者靈魂的神話、民間傳說與秦漢時期駱越先民抗擊中原王朝或與相鄰族群爆發沖突史實的較為吻合,上金鄉的船街作為延續駱越先人船祭水神祈福的重要物證,以紫霞洞為中心的左江流域壯族民間以儂峝節、搶花炮等形式傳承古駱越生殖圖騰崇拜文化,上金鄉政府所在地周邊一些村落的古今地名信息存在高度重合,尤其是運用壯族語言思維模式對照分析發現“臨塵”與“上金”所指地名一致。這些文化遺存進一步肯定了“漢象郡治臨塵縣所在地在當今龍州縣上金鄉政府所在地,花山古都就是臨塵縣”的基本推斷。這對于構建民族文化安全有著極其重要的政治意義,也對我們準確把握花山文化的地脈和文脈進行科學規劃花山文化旅游產業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臨塵縣;上金鄉;花山文化源地;文化遺存;考釋
【作 者】韋福安,西南大學西南民族教育與心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廣西民族師范學院民族學教授;么加利,西南大學西南民族教育與心理研究中心教授、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重慶,400715
【中圖分類號】K928.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 - 454X(2017)01 - 0061- 011
關于“臨塵”,《漢書·地理志》記載:“臨塵,硃涯水入領方。又有斤員水,又有侵離水,行七百里。莽曰監塵。”[1 ]302酈道元《水經注》有與“臨塵”有密切關聯的“斤江水”和“侵離水”記載,即“斤江水出交趾龍編縣,東北至鬱林領方縣,東注于鬱。侵離水,出廣州晉興郡(郡,以太康中分鬱林置),東至臨塵入鬱。”[2 ]清代王先謙作《漢書補注》指出臨塵(莽曰監塵)在“今太平府崇善縣地”。[3 ]蒙文通先生在其《越史叢考》中依據王先謙之說及《清一統志》中“太平府崇善縣地為漢臨塵縣”的說法, 進一步認定“崇善為臨塵縣地”。[4 ]90-93 1982年出版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西漢時期“交趾刺史部圖”也將象郡府治“臨塵”標在崇善縣。[5 ]35-36這便是長期以來人們一直確信臨塵縣在崇善縣地的主要原因。然而,或許上述學者未曾親臨左江或廣西實地考察之故,文獻描述與實際多有不符。為此,筆者曾刊文對歷代學者述及“臨塵、硃涯水、斤員水和侵離水”的文獻或研究進行邏輯梳理和綜合分析,考辨結果認為“斤南水”“硃涯水”“驩水”“侵離水”分別對應當今的河流為廣西的“左江(包括左江上游平而河)”“水口河”“右江”“明江”,得出漢志記載的臨塵縣 “應該是在當今的龍州縣上金鄉政府所在地,而不是在崇善縣地” [6 ]的初步結論。而鑒于在古代歷史研究的學術論爭中“田野考古發現的事實具有第一位的決定性的意義”,[7 ]人類學田野工作所發現的和發掘的文化遺存對史籍記載資料的佐證也顯得尤為重要。在南方少數民族地區,很多考古證明了我們并不應該過多寄希望于考古出土任何文物和遺址,但正如德國著名文化人類學者米契爾·蘭德曼所說的那樣:“每一個文化創造總是包含著一種神秘的或隱藏的人類學。”[8 ]9古代社會某個民族的生產生活民俗、宗教信仰和語言文字,往往在當今的該區域民族社會中仍會留下文化印記。漢代雖在左江流域設臨塵和雍雞兩個縣,但仍“以故俗治”,唐宋以來朝廷也在這一地區采取羈縻制度和土司制度,直到清末民初才最終實現改土歸流,這就使得駱越部族的社會組織和包括圖騰儀式在內的原始生活習俗得以保留和延續。[9 ]這使得我們能夠運用左江流域民族文化語境還原駱越民族歷史現象時更具真實感。因此,考察今龍州縣上金鄉政府所在地及周邊近年來考古發現的古代墓葬及器物、民間神話傳說、宗教信仰民俗等文化遺存,以及借助壯語思維方式對照分析“臨塵”與“上金”及周邊村落古今地名信息的重合度,成為考實佐證文獻考辨得出漢象郡府治“臨塵縣”就是在“今龍州縣上金鄉政府所在地”的最重要路徑。
一、龍州縣上金鄉政府所在地周邊近年來考古發現有漢代墓葬、
漢庭遺址以及青銅器和玉器等文化遺存,表明古象郡治臨塵縣
應該是在明江和左江交匯的上金鄉政府所在地范圍
考古發現古人行為的遺跡和遺物,通常被看成是古代文化的見證和無聲的歷史,這在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當中已是毋庸置疑的共識。2008年,廣西考古隊對龍州縣棉江花山附近的古坡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出土了一批銅斧、銅矛、銅盆、銅碗、和陶器,考古專家鑒定這批出土的文物為漢代的兵器和生活用品,并進而推斷出這一帶存在漢代古墓群。考古學認為,古墓附近一般會存在較大規模的城市或鄉村聚落。2009年12月12日,廣西文物考古研究學者在上金鄉政府附近的“龍珠”臺地上的考察工作中,挖掘出不少碎瓦片,經鑒定,這批碎瓦片屬漢代的板瓦、筒瓦、陶罐等殘片,據悉,這是在廣西西南地區首次發現的一處面積約3600平方米的漢代遺址。據上金村里老人說,“龍珠”臺地在古時候稱為“庭城”,壯語又稱“夯城”(南壯方言讀作“湯城”,兩者均意為“尾城”),“龍珠”臺地對面的江岸稱“江城”。上金鄉政府所在地的左江半島(以下均稱為“上金半島”)一直以來都被當地視為“風水福地”,半島上還發現了清道光、光緒年間的土司官族墓群。在發現的漢瓦殘片中,最大的一塊為繩紋板瓦,約有2.2厘米厚,火候較高。據考古專家鑒定,這種形制的漢瓦是用于官署、衙署等建筑。而從其他的筒瓦、陶罐殘片也可判定,這里在漢代可能曾存在過大型建筑。考古專家因而將該遺址命名為庭城遺址。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壯族地區自古就有干欄建筑和崖洞葬的習俗。首先,與中原大型夯土建筑風格不一樣的干欄建筑,表明駱越先民所居住的生態環境不同于中原漢族,干欄建筑材料在經歷成百上千年風雨腐蝕之后,很容易破敗消失,因此,很難通過考古發現并還原古代的城邑原型;其次,由于駱越先民多選擇崖洞葬,故很難發現大型的古墓群。值得一提的是,古坡漢墓群和庭城遺址是左江流域首次發現的漢代遺址,它們都處在花山巖畫分布最密集的明江、棉江一帶,尤其是庭城遺址的發掘,可以認為這一帶曾經是古代人口聚落規模較大的區域。保存在龍州縣博物館的駱越時代重要的王族禮器——玉戈,是多年前從上金鄉那浪屯村民中征集到的,玉戈被征集前,曾作為當地師公的法事道具,據說是被征集人世代祖傳下來的物品。盡管玉戈的出土、制造地點已經不詳,但可以肯定玉戈的發現是在花山和紫霞洞附近的地域,因此可以推斷玉戈的古代使用人應當在上金鄉政府所在地的地域范圍以內。玉戈是古代駱越王權的標志,據《武鳴獨山巖洞葬調查簡報》介紹,獨山巖洞葬墓主有一把青銅戈隨葬,青銅戈是從新石器時代的權利重器玉戈演變來的有令牌功能的特別兵器,這一隨葬品的出土更證明了墓主的駱越將帥身份。[10 ]16由此可知,玉戈在上金鄉流傳,說明這一帶早在先秦時期就存在一個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此外,花山巖畫開始作畫的時間是戰國,這說明戰國時期花山巖畫附近已經有足以支持作畫人力、物力和財力的一座“城市”。古坡漢墓群及其出土的青銅和陶罐、漢代庭城遺址及遺物、花山巖畫群密集分布帶、玉戈的發現地均指向同一地域范圍的信息及花山作畫起始年代的信息表明,處于交通便利的明江和左江交匯的上金鄉政府所在地應當是漢象郡府治“臨塵縣”所在,也就是足以支撐花山作畫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的那座花山古都。此外,上金鄉政府附近的明江河岸發現的多座古代碼頭,以及通過河岸裸露出來的有著深厚的古文化層,可以看出,上金鄉政府所在地及其附近,古代曾是人口居住較為密集以及水上交通極為繁忙的地方。
先秦時期駱越有自己的方國,廣西武鳴縣馬頭鄉、陸斡鎮、兩江鎮在商周至戰國時期都是馬頭方國的轄地,而馬頭圩是方國政治、軍事、文化中心。[11 ]185馬頭方國的制銅鑄銅技術最早又從中原傳入,但該地域出土的春秋戰國墓葬的青銅器和制銅石范也說明了駱越先人有著發現和開采利用銅礦的悠久歷史。按照時間序列推測,龍州古坡遺址的銅器有可能是從駱越方國中心傳入,或者是漢軍從中原帶入。但不管怎樣,古坡遺址出土的漢代銅器也至少說明上金鄉及其附近曾在一定時期內駐扎有軍隊。近年來,有采沙船在花山巖畫附近的江中挖出高級青銅器和玉器出水,如平而河巖洞山巖畫附近出水的駱越王族出行使用的高級儀仗禮器鳥喙形青銅大戈,沉香閣巖畫附近出水的王族高級禮器青銅鎏金大戈,巢城山巖畫附近水域出水的繪有王族高級游船圖案的鳥頭船紋銅桶,花山巖畫附近水域出水的和花山巖畫上羊角紐鐘樣式相似的帶布痕的青銅羊角紐鐘,以及花山巖畫附近水域發現的珍貴鑲金玉塊等,有專家推測這些文物要么是王族沉船的遺物,要么是王族祭祀時投入河中的禮器。[12 ]162-165不管出于何種推測,高級青銅和珍貴玉塊等王族禮器出水的水域都主要集中在花山巖畫密集分布的上金鄉政府所在地的上金半島周邊,說明了秦漢時期在花山巖畫的中心區存在一座較大規模的“城市”——臨塵縣。
二、“岜傷”安置駱越將士戰死者靈魂的神話、民間傳說和秦漢時期
駱越先民抗擊中原王朝或與相鄰族群爆發沖突的史實存在吻合
人類學認為,任何民間傳說都被視為一定族群范圍的“族群性表述”和“譜系性記憶”,是特殊的歷史敘述與記憶關系。上金鄉民間有駱越古城和安置駱越將士戰死者靈魂的傳說記憶。據上金鄉河抱村老人說,上金鄉中山村與隔著明江相望的河抱屯一帶曾是駱越兵駐守的古城寨,青銅長鏈橫貫明江河上連接兩村,后來官兵攻打駱越兵城寨,駱越兵死傷很多。那些戰死的駱越兵都安葬在紫霞洞山附近,因此紫霞洞山壯語叫“岜傷”,即戰死者山。廣西寧明縣民間流傳《勐卡造反的兵馬》[13 ]233-234傳說,其大致梗概為:
從前,寧明那利有一個力氣很大的名叫勐卡的青年想造反打皇帝,但是因為他沒有兵馬,所以只能在紙上畫兵馬。所畫的兵馬經過一百多天便可以變成真兵真馬,但前提是他不能讓任何人知道他畫兵馬之事。秋收季節到來的時候,勐卡連續畫兵馬已經有90多天了。但不幸的事情發生了,他母親發現他這些天白天待在家里不外出做工,一天,他母親趁他外出后偷偷打開箱子看個究竟,誰知道那些兵馬都飛出去了。沒有人知道勐卡的兵馬到底飛到了哪里。后來,寧明岜耀屯有一個窮人到山上砍柴,不小心將柴刀掉在崖邊,并且柴刀很快滑落下去。砍柴人便順著陡崖爬到山腳下的明江邊,突然聽到一陣陣敲鑼打鼓的聲音從一個巖洞里傳出來,原來洞里的兵馬正是勐卡的畫飛來變成的。
不久,皇帝便派大部人馬來攻打打巖洞里的兵馬,勐卡的兵馬寡不敵眾而全部被殺光。遍地的鮮血和尸體映到明江邊的巖壁上,形成了現在的花山巖畫。從此以后,凡是陰雨天,人們走到明江邊的巖畫下,能隱約聽到哭聲。當地的人們痛惜勐卡兵馬的不幸遭遇,自發請道公仙婆打醮,祈禱他們英靈升天。老人們說花山巖畫上的人獸圖形就是當年勐卡的兵馬的形象。對于一些在刮風、打雷和大雨中剝落的巖畫圖形,老人們說:他們投生去到別的地方繼續他們還沒有做完的事了。
與《勐卡造反的兵馬》同樣的內容在《寧明縣志》和《龍州縣志》也有記載,除此之外,《寧明縣志》還有《黃巢大敗朱溫于明江》和《巖洞兵馬搬上崖壁住》的民間傳說,《龍州縣志》還有《紙人》和《馬伏波將軍作畫》。[14 ]700-701上述傳說大都是古代戰爭的內容,或是駱越將士反抗朝廷官兵,或是馬援率軍打敗交趾兵。戰爭難免有大量死傷,而戰死的駱越將士的靈魂則要在能溝通人神的巫師的超度下并經由一定的路徑才能到達它們的歸宿地——“天”,“中越跨界的壯、岱、儂族群與泰國的泰族一樣,都信仰‘天,壯、岱、儂族群‘天的發音為‘then,‘then發音與‘神相同,泰國的泰族‘天的發音‘thεm,跟‘仙的發音也相近。因此在布傣人心目中,信仰‘天,即是信仰神仙,是創世神或保護神,神仙住在天宮。布傣人‘做天即是請天宮的天神下凡,為人們消災祈福。” [15 ]壯族遠古神話《天地分家》中有旋轉著的一團大氣變成一個三黃蛋爆炸成三片分別成為天上、人間和地下“三界”之說,這反映了壯族先民的宇宙三界觀。“三界”說在壯族師(道)公經書里多有記述,如一些經書開頭都有“三蓋(注“蓋”即“界”,“界”在狀語方言中讀“蓋”)三王置,四蓋四王造”的經文。壯族先民的三界宇宙觀的象征意蘊也體現在壯族銅鼓的造型中,銅鼓上下突棱將鼓身分為三節,鼓面是天上,有象征太陽崇拜的太陽紋和象征雷神崇拜的云雷紋,鼓身有魚紋、羽人等景象寓意地上人間,鼓足是水波紋,是人間和地下的分界,銅鼓因此成為壯族先民溝通人間與天上地下的神器。古代壯族村社“寨老”往往是由技術高超的巫師來主持擊鼓溝通人神的儀式,今天的壯族民間仍有師公擊鼓祭祀的痕跡,喪葬習俗中師公主持的亡魂超度儀式。我們可以據此推斷,左江流域古代壯族先民認為高聳的崖壁是亡魂登天的理想通道,在崖壁上繪制代表著戰死的駱越將士的人像,巫師通過特定的巫術禮儀將這些戰死的駱越將士的魂靈通過高聳的崖壁送入永生的天界。
花山巖畫的作畫是從戰國早期到東漢的前后持續600多年的時間,這一時間推定早已被學術界廣泛認同。這一時期,生活在華南的壯族及其先民時有抗擊中原王朝或與相鄰族群爆發沖突的史實,史籍也有記載。如《史記·吳起傳》和《后漢書·南蠻列傳》都記載了楚悼王在公元前401年至公元前380年啟用吳起“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可知這一時期楚越之間發生的軍事沖突屬于強迫兼并。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秋冬,秦始皇命尉屠睢率50萬大軍兵分五路揮師嶺南,遭到越人頑強的抵擊。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統一嶺南,置桂林、象郡和南海三郡,而左江流域屬象郡所轄范圍。事實上,秦始皇統一嶺南戰爭中,第一階段幾乎沒有遇到太大的阻力,很快就打下廣東地區,而在廣西則打了6年之久,并且是秦軍以“伏尸流血數十萬”的代價才統一廣西及越南地區。[16 ]公元前207年,南海尉趙佗擊并桂林、象郡而據嶺南建南越國,拒絕歸漢。公元前112年,漢武帝遣20多萬軍隊攻伐南越。公元前111年,漢軍攻占南越國都番禺,存續93年的南越國滅亡。《后漢書·馬援傳》記載交趾女子征側及其女弟子征貳叛亂并自立為王,光武帝(劉秀)于建武十七年(41年)“于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為副,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趾。”次年,馬援大破二征部眾并斬首數千人。建武十九年(43年)正月,馬援擒獲二征,將其斬首,并將其首級傳至京都洛陽。以上所列歷史大事件為正史所記載,而這期間壯族及其先民與中原王朝或相鄰族群所爆發的小沖突亦應不少。盡管史籍沒有記載漢代馬援將軍率軍經過上金、龍州入交趾征伐二征,但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記載明正德年間太平府的威震關提到,威震關“志云舊在衣甲山下,一名伏波關,相傳馬伏波征交趾時所筑。”[17 ]4954龍州有班夫人投江傳說和龍州城建有伏波廟,響水(在今龍州至崇左江州區的麗江中段)與三叉交匯處有規模不小的古代造船碼頭遺址,可提供馬援部將的補給及交通工具的制造與維修,加上古坡遺址考古發掘出土的一批古代兵器的銅斧和銅矛。我們可作這樣的推測:漢代馬援任伏波將軍奉命兵分兩路前往交趾鎮壓征側、征貳時,一路溯郁江、邕江、左江而上,經今龍州縣城并在龍州一帶屯兵籌糧,從平而關和憑祥入交趾,乃因上金、龍州的地理環境及其在桂西南的重要地位有關。可見,左江巖畫作畫與發生在嶺南地區的戰亂事件和民族沖突在時間年代和地理位置上基本可以相對應。有學者一再聲明并非有意將這一時期的左江巖畫作畫與嶺南地區的戰亂事件對號入座,卻因兩者之間如此的吻合絕非偶然,故而推斷“左江崖壁畫上繪制的巫術舞蹈,主要就是超度那些在戰亂年代里為民族、氏族利益而戰斗犧牲的烈士英魂。”[18 ]150至今,壯族師(道)公在超度亡靈的法事中仍有“開路瓦”儀式,即在瓦頂開天窗,架上木梯,在木梯上鋪上白布匹,死者的靈魂就會經由梯子通過天窗升入天堂。廣西龍州金龍壯族布傣支系有人生必須經歷“三座橋”(■橋、渡橋和天橋)之說,其中的“天橋”就是法師將亡魂送上天堂的搭橋儀式。從花山巖畫上反映的駱越巫術儀式,再到當今左江流域壯族民間的原生態民間宗教信仰,絕不會是一種孤立的偶然的信仰現象,而是一個綿延不斷的信仰傳承體系。神話感知在近現代科學的光芒下不得不逐漸消失,“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的觀相學經驗的事實本身被摧毀和消滅了。它們雖然失去了一切客觀的或者宇宙論的價值,但是它們的人類學價值繼續存在著。”[19 ]130換言之,上金鄉民間傳說并非空穴來風,它折射了左江流域駱越群落對古代兵家必爭之地——左江駱越古城的歷史敘述和記憶。
三、上金鄉的船街是駱越先人船祭水神祈福的重要文化遺存
船在近代公路通車之前,是人類出行所依賴的最為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其名稱來源于“舟”字。甲骨文和金文的“舟”字的構形都象一只木船,篆文則承續金文字形。秦始皇推行書同文之后,隸書“舟”字始與現在的文字相近。關于舟的用途,《說文解字》解釋道:“舟者,船也。古者共鼓、貨狄刳木為舟,剡木為楫,以濟不通。象形。”早期的字形像獨木船的形狀,來表達舟主要是作為人們渡河的交通工具。駱越先民沒有自己的文字,故常以直觀形象的寫實圖像表達物體以及人們的行為,如左江巖畫上的渡船形圖像,表達了駱越自古是親水而居、靠船出行的民族。學界大致認同了花山巖畫的內容凸顯的是駱越人原始宗教祭祀的主題,因此可以斷定,“舟”在壯族人心目中除了表達人們生產生活的重要交通工具之外,祭祀祈福也成為了其重要的功能。
祭祀水神是駱越人重要的宗教儀式,每到灘險水急處,駱越人都要舉行祭祀水神的儀式,以求旅途平安或招撫遇險的亡魂。左江流域自古以來就是洪水多發區,而且災情都極其嚴重。據《寧明縣志》記載:明江河下游,河道迂迥狹窄,泄洪欠佳,水災顯得特別嚴重。大洪水或特大洪水一般發生在7-9月,絕大部份是由臺風雨形成。倘若左江上游其他支流同時爆發洪水,左江洪水產生頂托,則后果更為嚴重。如明永樂六年(1408年)農歷7月,淫雨水漲環城;清光緒七年(1881年)農歷8月15日大洪水致明江兩岸形成縱橫50-60里汪洋,溺死58人,牲畜、財物等損失甚巨;民國29年農歷8月14日洪水,思樂沿河各村街牲畜被淹沖走不計其數;1980年7月25日的明江大洪水淹死、沖走耕牛35頭、豬36頭、鴨1160只、雞250只,死亡5人。[20 ]61-64相同或相近時間段因洪水爆發導致家毀畜死人亡的記載在龍州、崇左(今江州區)和扶綏等地縣志俯拾皆是。近現代的人們在抵御洪水能力遠超古代,但面對洪災尚有諸多無奈,更何況早期生產力極為低下的駱越先民,他們只能因畏懼而將洶涌而來的洪水視若大自然神靈,并且加以虔誠祭拜,可見洪水對駱越先民的影響是巨大的。洪水災害在壯族神話中也有很多描述,如兄妹結婚繁衍后代的神話流傳于廣西各地,講述的是在從前的一場洪水劫難中,人類只有兄妹兩人幸免于難,為了繁衍后代,兄妹只能沖破傳統倫理結為夫妻繁衍后代的故事。左江花山巖畫作畫地點的選擇反映了壯族先民希望將死去親人的靈魂送去天堂的強烈心愿。有學者認為,花山巖畫有6個地點都發現了舞人在船上和岸上歌舞的隆重場面,是駱越人祭祀水神禮儀所跳巫舞的反映。[21 ]149-150在調研時聽到上金鄉一些老人有這樣的說法:左江流域在古代經常發洪水,沿河居住的村落也經常被大水沖毀,村落里的牲畜甚至是一些來不及轉移的人被大水沖到河里淹死。當地人將在外遭受意外傷害的非正常死亡的人稱為“披傷”,“披”是鬼的意思。洪水過后,被沖走淹死的“披傷”一般在河流急彎處的漩渦中浮上來。為了避免“披傷”的鬼魂回來禍害人間,人們便在河流彎道的巖壁上作畫祭祀,“披傷”鬼魂便可以經由巖壁升入天界找到安身的地方。該說法或許帶有附會之嫌,但在左江流域發現的79個巖畫地點中確有70個地點是臨江的,占總數的88.6%,這其中又有54個作畫點是位于水流湍急的江河的拐角處,約占地點總數的68.3%,約占臨江地點總數的77.1%%。[22 ]21此外,壯族民間至今仍有請師公為“披傷”招魂的法事,接回在外意外死亡的“披傷”尸體不能進家門,所做的超度法事儀式只能在屋外進行,甚至有些村落擔心驚擾祖宗神靈而不允許“披傷”進村安葬。為了實現引魂升天,巫師還需要借助一定的工具,其中花山巖畫中的渡船形圖像便是指駱越巫師引魂升天的工具。駱越人也有死后用船形棺安葬的習俗,如1976年廣西貴縣(今貴港市)羅泊灣一號漢墓挖掘出土的葬有7名殉葬者的棺材,形如獨木舟,均是將圓木中間刳空以葬尸骨;右江沿岸的平果、田東、田陽等地巖洞葬中發現的棺木,也都是用圓木制成獨木舟形狀。此外,在廣西各地出土的銅鼓上也會有大量的羽人劃船紋。法國學者V·戈鷺波認為,東南亞婆羅洲達雅克人超度死者亡靈到云湖中央的“天堂之島”用的“金船”,其作用與廣西銅鼓上羽人劃船紋相類似,其本質都是運送靈魂升天的“靈魂之舟”;另一位法國學者鮑克蘭也認為,達雅克人用犀鳥的頭和尾作裝飾“金船”的船頭和船尾,其功用也是“引魂”,將“亡魂”送到云海中的“天國”;左江巖畫中也有不少頭上插有羽翎的人形圖像,我們也可以稱之為羽人,巖畫中站在船上的也多為羽人,他們則是運送靈魂升天這一儀式的參加者,這和銅鼓船紋上的羽人圖案具有同樣的文化功能。由于銅鼓在古代西南少數民族中被視為神物,具有溝通人與神的功能,顯然,用船“送魂”圖案出現在銅鼓上是不難理解的,因此,左江巖畫中的羽人劃船紋同樣表示的是“送魂”。[23 ]
現存的建于1928年的上金鄉中山村的船街(因這條街酷似一艘船,故稱船街)。從船頭穿過牌坊連接明江古碼頭,見證了民國初年邕龍公路通車和崇左馱盧至天等龍茗公路路基建成前這里曾是亙古以來左江流域最重要的交通中心。船街兩邊共有民房76間,均為蓋小魚鱗瓦的騎樓式兩層磚瓦木架結構的樓房,街道全長172.3米,其中船頭、船身長105.8米,船尾長66.5米;船頭寬12米;船身最寬處25米;船身與船尾交界處寬8米。船街曾是民國上金縣政府公署所在地,房屋除了用于縣府用房外,絕大多數都是商鋪,船街54號大門右側青石墻上有一幅石刻的行業對聯:“土能生白玉,地可產黃金。”說明當時住在這里的人多數是官員、商賈、富人等。船街前身為建于清咸豐元年(1851)的有名的窯頭圩,清道光年間,由南寧水運至左江的大宗食鹽都以窯頭為轉運站。窯頭到沿明江上溯上思、經平而河和水口河進入越南,因河灘險阻或河道窄小,須用小船轉運,因而各地船只都停泊窯頭,所以窯頭又有鹽埠之稱。可見,明江和左江交匯處的上金鄉政府所在地作為古代左江最為旺盛的商貿集散地之一。
由于船街街道形狀酷似一條平躺的大魚,魚嘴連著碼頭,當地人因而也將船街稱作“魚街”,后人因附會“鯉魚跳龍門”之義,故又稱“鯉魚街”。關于以魚為圖騰崇拜對象的氏族部落或民族,世界各地均有不少,據統計,澳大利亞從沿海到內陸的96個氏族部落中,共有798個圖騰,其中魚圖騰有102個;美洲印第安人的110個氏族中14個氏族以魚為圖騰;非洲土著民族巴希馬(或稱巴欣達)部落中的所有氏族,以及奧克蘭科人和南卡尼斯等部落也有以魚為圖騰的氏族。在中國,傈僳族、白族、滿族、侗族和部分布依族等少數民族也有以魚為圖騰的民間神話傳說。[24 ]駱越民族自古親水而居,關于越人的魚圖騰崇拜問題之研究,早有刊于《古代文化》1937年第15期蔣玄佁先生的《吳越魚圖騰考》一文;關于壯族、瑤族等先民的魚圖騰崇拜,閔敘輯的《粵述》有記載:“……而鬼魚則出蠻洞中,似靈。猺獞(瑤壯)取而禱之。食,人即死,這種‘鬼魚即是被人視為圖騰禁忌的魚。”但是與同是越人后裔的瑤、苗、侗族、布依等民族相比,壯族的魚圖騰崇拜的痕跡比較淡。[25 ]盡管現在左江地區民間仍有用“三牲”(豬肉、魚、雞)祭祖的習俗,并且桂西龍津壯族農村曾流傳有民間故事《白鴿姑娘》說鯉魚乃龍太子的化身。[26 ]51但并不意味著這就是該地區的人們以魚為圖騰崇拜對象的文獻記載。民間傳說盡管可以被視為歷史研究的史料來源之一,但倘若缺乏其他文獻史料的佐證和考古物證的支撐,民間傳說往往就會失去有證明效力。況且在廣西出土的銅鼓上沒有刻有魚形(魚紋)圖案,出土的漢代墓葬也沒有與魚相關的物證,甚至在記錄幾千年前駱越先民大型巫術儀式的左江花山巖畫中,也都沒有看到任何魚或魚紋的圖案。因此,左江流域壯族先民自古以來應該沒有以魚作為圖騰崇拜對象的習俗。由此可以斷定,當地人將船街稱作“魚街”進而附會“鯉魚跳龍門”之義而稱“鯉魚街”,這與民間利用“魚”與“余”同音而以魚祈盼生活“富余”“吉慶有余”或“連年有余”等吉祥語一樣,只是具有象征的意義,而并非是駱越先人將魚作為圖騰崇拜對象的遺風。相反,從古至今,船在左江流域人們的生產生活中和生意往來的重要作用不可替代,直至今日,該地區一些地方因自然山水阻隔的人們,日常出行仍主要靠小木舟作為交通工具。
由此,我們認為花山巖畫上的渡船形圖像、崖洞葬中的船形棺材和船槳及船街之間有著密切的關聯,而壯族船祭水神祈福觀念的重要文化遺存的船街就在上金鄉政府所在地。我們因此可以勾畫出上金鄉政府所在地曾經是非常繁華的“古都”和“商埠”,至少是相當繁華的古駱越人部落。
四、古駱越生殖圖騰崇拜文化在以紫霞洞為中心的左江流域壯族民間
以儂峝節、搶花炮等喜聞樂見的形式代代傳承
母系氏族公社的原始人,將某種動植物、無生物或自然現象視為氏族的親屬、祖先和神,這種現象稱為圖騰崇拜。幾乎所有的氏族都經歷原始社會制度,圖騰崇拜因此是世界各民族先民共有的自然習俗。經歷漫長的社會發展,伴隨人們抽象思維的產生,人們開始意識到自己的祖先并非動植物而是人的時候,圖騰祖先崇拜便逐步過渡到人祖先崇拜了。在花山巖畫場景中,我們看到太陽、象征雷神的銅鼓、蛙形舞、男根、男女交媾等圖案,加之巖畫所處的山川、河流等自然生境,儼然展現的是一幅壯族先民由圖騰崇拜到人祖先崇拜的宏大歷史畫卷,而象征生命繁衍的生殖崇拜則無疑地成為巖畫的主題。有學者根據史籍記載和壯族的雷王神話傳說中認為:“左江流域崖壁畫中的人物圖像以青蛙的形狀為模擬對象,除了要向青蛙祈求生殖和豐饒外,則主要是通過青蛙與雷神的溝通,以得到雷神的來自生殖和豐饒方面的保佑。……銅鼓在左江流域崖壁畫中出現,與人們祭祀雷神有一定的聯系。”[27 ]167-169花山巖畫上的雷公(銅鼓上的云紋)、銅鼓、青蛙同時展現,反映的是左江流域壯族先民祈求生育和集團繁衍圖騰崇拜的抽象思維。楊燖認為,“蛙”是“媧”的原型,女媧是蛙圖騰氏族的女氏族長,女媧氏的由來,原是一個通名而非專名,是指生育人類的原始祖母而言。[28 ]499-502葉舒憲也贊同此觀點,并進一步指出:“蛙與人類比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嬰兒出生與蛙相類似,嬰兒哭聲也酷似蛤蟆叫,所以漢語稱小兒為‘蛙,發音恰恰與‘蛙相同,兩者皆為摹聲詞。根據音近義通的語用原則,蛙與娃、蛙與人也就自然聯系起來了。”[29 ]149鄧偉龍指出,左江流域花山崖壁畫中的青蛙圖騰是女性生殖崇拜的體現,而從影像的整體來看,腹部凸起的明顯具有女性特征的并不多,更多的是正面的人像幾乎男性化的雙手向前曲肘上舉,兩腿下屈呈現半蹲式的影像,人物側影中特別突出代表男性的陽物,把代表女陰象征的掌形附諸在他們身上而不是真正的女性身上。夸張表現男根至少表明男性在社會中的主宰地位,因而女性生殖崇拜讓位于陽物崇拜,本來屬于女性生殖的特征和功能,也被讓渡到男性的身上,圖騰已由女性生殖崇拜蛻變為男性生殖崇拜。[30 ]花山巖畫上不少畫面所展現的正是駱越人從蛙圖騰崇拜漸進到人祖先崇拜、從女性生殖崇拜過渡到男性生殖崇拜的幾千年文化累積的歷史動態變化進程。石頭一向在人類原始文化中具有特殊的生殖意義,其在壯族文化中亦有獨特表現。廖明君先生認為:“石頭在壯族先民的原始思維中不僅是一般的自然物,而是具有神秘生殖力的東西。這就是壯族先民選擇石頭來制作女陰和男根象征物以及石鏟的文化基礎。”[31 ]44在上金鄉中山村附近的清代土司官族墓群中,發現了許多用石器鑿刻成的男性生殖圖騰,盡管這些男性生殖崇拜圖騰石器屬于清代,但遺留石制生殖器圖騰殘件之多亦表明了當地沿襲著駱越先民對于男根的強烈崇拜的文化遺存。
駱越人對于巖洞的崇拜,除了早期駱越人作為“住在山洞的人”情結之外,更是因為從世居巖洞的歷史衍生出了巖洞生人的女性生殖器崇拜。壯族地區如今仍有巖洞生人的神話,如“駱越始祖女神乜洛甲的生殖器變成一個大巖洞給人類和鳥獸遮風躲雨”[32 ]3-4和“乜洛甲把自己孩子送進山洞寄給蘭太(娘家)撫養管教”[33 ]13的神話。孩子們從哪里來?“當乜洛甲創造了山川大地,河水沖擊巖石出現一個洞,布洛陀就從洞里走出來,和他一同出現在世界上的是四兄弟——老大雷王(壯語叫Duz byai),老二是蛟龍(壯語叫Duz ngieg),老三是老虎(壯語叫Duzguk)。”[34 ]783上述神話寓示著人類和鳥獸都是生自乜洛甲的生殖器,因此,女性生殖器與巖洞在此獲得了明顯的結合。有壯族研究學者認為:“巖洞生人的神話體現出壯民族對自然界中巖洞的崇拜,通過生殖崇拜(巖洞隱喻女陰)的橋梁走向祖先崇拜(布洛陀、乜洛甲)的頂點。”[35 ]左江流域是駱越人洞穴居和巖洞葬分布較為密集的地區,他們與巖洞有不解情緣,如該地區盛行的“儂洞節”歌圩習俗。“儂洞”是壯語音譯,古壯字讀作“■峝”,“儂”即“■”,“下來”的意思,“儂洞”即是從洞里下來的意思。為什么要從洞里下來?在農耕時代,人們已把對巖洞生殖的崇拜,轉化為祈雨及保佑農作物豐產的祖先崇拜,祭祀活動才從洞中轉到平地;而從洞里下來到哪里呢?只能選在“峝”(后標準漢語讀作“峒”,即山間比較開闊的地方)。“儂洞”因而也可寫成“儂峒”,即“儂洞節”演變成為駱越人集中在山間開闊的田野上求雨、祈福消災和祈求駱越人繁衍生息的祭祀活動。歌圩與祭祀合一乃源于遠古駱越的習俗,左江流域“儂峒”歌圩必唱頌祖先,如今這一習俗仍然流傳于左江流域一些地方。崇左市大新縣寶圩街農歷二月十九日歌圩節那天,在當地師公的主持下,當地群眾先在紫云洞舉行隆重的祭神活動,祭神活動結束后,師公將事先制作好的神像裝進轎子,由當地群眾選出四名代表從洞中抬著神像下山沿街巡游,以表示請天神下凡保佑百姓五谷豐登、生意興隆和四季平安,在眾多的巡游方隊中,有兒童組成的方隊緊跟在神像之后,這顯然寓示著人們請求祖先保佑子孫繁衍昌盛的意義,而沿街居民每家每戶則在門口擺上魚、肉、水果、糖餅等供品供奉。請神下山巡游結束后,舉行隆重的山歌大賽活動,龍州縣不少山歌手驅車前往參加山歌大賽。同在農歷二月十九日那天,崇左市江州區左州鎮金山“花炮節”,當地的師公、巫婆以及眾多善男信女除了請天神沿街給各家各戶送福外,人們還自發組織山歌對唱,搶花炮也是當地人喜愛的活動,金山搶花炮還有特殊的寓意:“頭炮求子,二炮求財,三炮求平安”,顯然,左州金山歌圩節和搶花炮蘊含著濃厚的拜祖求子祭祀印記。龍州的麗江和明江都曾有一種古老的祭祀水神白母娘的習俗,游修齡先生《龍舟、端午節和屈原》一文記載廣西寧明縣當地的傳說,古時候的蛟龍叫“圖額”,是壯族的雌性水神,五月五舉行龍舟的活動不是紀念屈原,而是白娘。……在(龍舟)競賽時,還要放鞭炮和地炮,炮聲和吶喊聲此起彼應,十分熱鬧。與他們祖傳的《端陽節歌》所唱的一致:“劃船恭敬白母娘,鞭炮地炮響連天。”壯族地區龍舟的演變,更為明顯地說明端午紀念屈原是后來受到漢族的影響,他們最初祭祀的白母娘(蛟龍圖騰)才是與古百越族同源。[36 ]白母娘就是左江流域駱越祖母神,花山巖畫密集分布的明江和棉江地帶是駱越祖母神白母娘的祭祀中心,而這個中心的中心就是紫霞洞。相傳古代每年的農歷五月初五,越南北部紅河流域、左江流域等地各地數萬群眾匯集紫霞洞祭祀白母娘,并舉行隆重的搶花炮和歌圩活動。因龍州有漢代“班夫人”傳說,后人遂將駱越祖母神白母娘附會為“班夫人”,近代又把“班夫人”附會為觀音神,白母娘祭祀日因而變為農歷二月十九的觀音誕,寶圩街和左州鎮的農歷二月十九觀音誕才因此得來。“一個文化在某地發源,如果這個文化長期發展,中途沒有消亡,那么它的源地會以傳說的形式、史詩的形式、族譜記載的形式,被長期保留在群體記憶中。”[37 ]
五、上金鄉政府所在地周邊一些村落的古今地名信息存在高度重合,
尤其是運用壯族語言思維模式對照分析發現“臨塵”與“上金”
所指地名一致,這更進一步說明了近代的“上金縣”縣治
最有可能是漢象郡府治“臨塵縣”之所在
漢代對其經略嶺南時所設的行政區名與當時當地民族語言的密切關系已眾所周知,如壯族地區以“那”“板”“峒”等壯語語音起頭的“齊頭式”命名的城鎮和村寨頗為常見,故借助壯族語言思維模式分析漢字表達古代壯族語言所指的地名,或許不失為民族地區考古工作值得關注的一種思路。龍州縣上金鄉政府附近的中山村河抱屯,與紫霞洞同處明江的一面河岸,距離紫霞洞約兩公里,三面環山,一面沿江。該屯居民房屋沿河而建,在居民區與環山之間,分布著幾百畝水田地,當地人稱這片水田為“那岜”,意即山下的水田,很顯然,這里以前就曾存在過一個較為富裕的農耕部落聚居區。據當地人說,該屯原稱“滿藤堂”(“滿”是南壯方言中“村”或“屯”的意思,而北壯方言則讀“板”),“藤”的意思是鏈子,“堂”是壯語中“銅”的轉音。傳說古時在河抱屯曾鑄有一條銅制粗鏈橫過江水連接左江半島,方便人們交通和物資的過往。如若秦漢時期當地確實存在過“藤堂”(銅鏈),那么可以想象:在生產力極其低下的年代,駱越人建造一條渡河銅鏈,得需要花費巨大的人力物力,說明當時人員、兵員及其物資的流通會是量大且頻繁;如果沒有一個擁有相當人口規模的“城市”在附近,就沒有必要也不可能有那么大的人力物力支撐渡河銅鏈的鍛制。也有人將“藤堂”稱為“等蕩”,“等”字壯語意思是“豎立”,“蕩”字借助南部壯語方言發音為“銅”,則“等蕩”連讀意思是“豎立銅柱”,這就意味著,河抱屯就是“豎立銅柱的村莊”,這似乎也可以推測漢代馬援率漢軍攻下這里的駱越城邑后曾在這里豎立過銅柱記功。不管當地民眾將河抱屯稱為“藤堂”還是“等蕩”,其隱含的駱越古地名的信息自不待言。漢志記載的“臨塵”顯然是壯族古地名的漢字表達,“臨”字在壯語方言中有兩種讀法,即“lam4”或“nam4”。“lam4”是北壯方言讀法,有“水”和“河邊”的意思,“nam4”是南壯方言讀法,也是“水”的意思;壯語方言“大”是江河的意思,“臨”就是“大”。“塵”在壯語中讀“khan2”,是“河邊、岸上、上面”之意。這樣“臨塵”所表達的意思是水邊、河邊的地方。由于漢志將“臨塵”與“硃涯水”、“斤南水”和“侵離水”等三條河流并列記載,由此推斷“臨塵縣”就應該是建在“斤南水”“硃涯水”和“侵離水”匯合處岸邊的縣城。史籍記載的“斤南水”是指包括左江上游越南段的奇穹河在內左江干流全段,“斤南水”在一些不同版本的古籍中也寫成“斤湳水”或“斤江水”。“斤南”在南壯方言中是指“吃水”或“喝水”的意思。不管是“南”“湳”還是“臨”,其壯語讀法都是表示水或江的意思;“塵”與“斤”在古漢語中讀音相近,由此可推斷“臨塵”就是“塵江”或“斤江”。從現存的地名看,龍州縣上金鄉的左江邊有確實一個名字叫“勤江”的村落,“勤江村”過去曾用名“芹江村”。“塵”“斤”“勤”“芹”都是壯語的音譯,表示“上面”或“天上”之意。勤江村的地名信息表明“臨塵”(即“左江”)所指的具體河段就在龍州縣上金鄉地界。[6 ]另外,筆者在調研中偶爾聽到當地有“象郡”即“上金”的民間說法,由于受到壯語方言發音習慣的影響,操南壯方言的一些人至今仍有將“像”字讀作“上”和將“郡”字讀作“盡”或“金”的現象,故將“象郡”讀作“上金”便是很自然的現象。事實上,“象郡”和“上金”在南壯方言的讀法也是極其相近的。由于“象郡”即“上金”之說在歷史上沒有任何文獻記載,故其音近或許只是巧合而為民間茶余飯后之閑談而已。然而,“一個民族的語言,是有其傳統性的。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當然有所演變,但許多詞匯因與人們生產、生活有著密切關系。為人們所常用而有較長的生命力。”[38 ]9-10此外,值得關注的是,古臨塵縣在漢代王莽主政時改為監塵縣,壯語“監”和“金”音近,“監”在壯語中是山洞的意思,“監塵”即是“巖洞上面”的意思,“上金”的壯語意思也是巖洞上面。在語言思維模式中,壯語是“中心詞(A)+修飾詞(B)”的順行結構,側重于事物的本體和第一性,具有類別化、整體性的思維特征,形成“A+B”型的思維模式;漢語是“修飾詞(B)+中心詞(A)”的逆行結構,側重于事物的形體和第二性,具有情態化、具象性的思維特征,形成“B+A”型的思維模式。[39 ]“監塵”是壯族語言思維模式,“上金”是漢語語言模式。如果將“上金”轉換成壯族語言思維模式,即“金上”,則“金上”顯然與“監塵”如出一轍,由此可以推斷,近代的“上金縣”縣治最有可能是古代“臨塵縣”之所在。查上金鄉,既濱臨左江且附近又有重要巖洞的當屬紫霞洞文化遺址,因而左江流域只有近代的“上金縣”稱得上是巖洞上的縣。
六、結語
文化地理學認為,文化的產生與自然地理環境息息相關,某種文化的產生必定有它的發源地。換言之,花山文化必有它的中心地,這個中心地或許就是左江流域的駱越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這個中心究竟在哪?要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得從左江流域巖畫分布最密集的區域考察入手。左江流域巖畫多沿江分布,表明駱越人多沿江聚族而居,每處畫點就是一個氏族或部落的祭祀點,其附近必有古人的聚居點。巖畫分布點的密集程度和大小,可以斷定古代氏族部落分布的密集程度和人口的密度。巖畫分布點以龍州縣上金鄉為中心,向兩邊沿河伸展。上金鄉周邊巖畫分布最為密集,可以推斷,這一區域當是駱越時期桂西南人口最為密集的地段。就規模宏大的寧明花山巖畫而言,梁庭望教授認為:“沒有強大的政權和相當雄厚的財力是做不到的。得有大量的顏料,大量的木料,繁雜的后勤保障,嚴密的安全措施,手法的高超畫師,缺一不可。”[40 ]換言之,明江花山巖畫附近必定曾經存在一座持續幾百年繁榮昌盛的具備支撐寧明花山作畫的人力和物力的駱越“城市”,這個“城市”應該就是漢志記載的“臨塵縣”。
雖然左江流域古代社會發展史一直還沒有被系統寫出來,但追溯這一發展的每一步驟對于每一位人類學者而言,都是充滿吸引力的事,它足以使人們對于該區域的駱越民族文化生活圖景獲得真知灼見。畢竟建立在真實史料基礎上的文化人類學方法正是把馬克思提出的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科學方法落到實處。從漢志記載的臨塵、硃涯水、斤員水和侵離水等地理信息看,要明確漢象郡府治臨塵縣的方位地址,需要符合以下條件:一是臨塵縣濱臨左江,且位于左江與其重要支流硃涯水、斤員水和侵離水交匯處,水上交通便利;二是該處及其附近漢代以前的青銅器、玉等遺物;三是有豐富的壯族民間神話、民間傳說記憶遺存及其相關聯的史實;四是有豐富的古駱越祭祀水神、生殖圖騰崇拜等民間信仰文化遺存;五是有壯族古地名的證據支撐。盡管一些學者仍持有臨塵縣所在地為太平府志崇善縣的觀點,而令人遺憾的是,目前在崇善縣地缺乏足夠支撐這一觀點的考古遺物和與“臨塵”密切關聯的駱越古地名,這恰恰證明了漢象郡府治臨塵縣并非在太平府治崇善縣。相反,整個左江區域只有龍州縣上金鄉政府所在地符合“臨塵縣”作為左江流域古駱越地中心的條件,加之上金半島和龍州城作為古代郁江流域與紅河流域兩大駱越區域之間的交通樞紐,以及龍州縣自古以來一直是桂西南重鎮的歷史地位。由此,本文進一步斷定:漢象郡治臨塵縣所在地在當今龍州縣上金鄉政府所在地,花山古都就是臨塵縣。
當2016年7月15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舉辦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0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上確定“左江花山巖畫文化景觀”成功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之際,左江花山巖畫便已開啟了它的后申遺時代,追尋左江花山的文化源地便將不可避免地引起人們的更大關注。因此,上述關于花山文化源地(即文化中心)的推斷若能成立,這將毫無疑問地對于構建民族文化安全有著極其重要的政治意義,同樣也對我們準確地把握和分析左江花山文化的地脈和文脈進行因地制宜地科學規劃花山文化旅游產業,推動廣西西南邊疆地區旅游及相關經濟產業發展,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 班固.漢書:卷二八·下 [M].北京:中華書局,2007.
[2]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M].清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卷四十.
[3]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地理志[M].清光緒刻本,第八(下).
[4] 蒙文通.越史叢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5]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M].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
[6] 韋福安.漢象郡府治“臨塵縣”方位地址的文獻法考辨[J].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3).
[7] 郭立新.考古對象對考古學研究的影響[J].華夏考古,2000(2).
[8] [德]米契爾·蘭德曼.哲學人類學[M]. 張天樂,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
[9] 潘其旭.花山崖壁畫——圖騰入社儀式的藝術再現和演化[J].民族藝術,1995(5).
[10] 羅世敏.大明山的記憶:駱越古國歷史文化研究[M].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2006.
[11] 鄭超雄.壯族文明起源研究[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5.
[12] 楊炳忠,藍鋒杰,劉勇等.花山申遺論壇[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10.
[13] 過偉.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廣西卷[M].北京:中國ISBN出版中心,2001.
[14] 龍州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龍州縣志[Z].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
[15] 韋福安.布傣天琴文化的跨國界傳承認同[J].廣西社會科學,2013(6).
[16] 鄭超雄.從古國到方國——壯族文明起源的新思考[J].廣西民族研究,2003(4).
[17]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第十冊)[M].賀次君,施和金,點校.中華書局,2005年,卷一百十.
[18] 黃桂秋.巫磨信仰:廣西左江崖壁畫新探[G]//宗教與民族(第七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
[19] [德]恩斯特·卡西爾.人論——人類文化哲學導論[M]. 甘陽,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
[20] 寧明縣志編纂委員會.寧明縣志[Z].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8.
[21] 陳遠璋.左江巖畫舞蹈圖像初探[C]//中國銅鼓研究會第二次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22] 廣西壯族自治區民族研究所.廣西左江流域崖壁畫考察與研究[M].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87.
[23] 肖波.左江巖畫幾個問題的思考[J]. 三峽論壇(三峽文學·理論版),2013(3).
[24] 何星亮.半坡魚紋是圖騰標志, 還是女陰象征?[J].中原文物,1996(3).
[25] 黃達武.劉三姐與魚圖騰崇拜[J]. 貴州民族研究,1990(2).
[26] 胡仲實.壯族文學概論[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2.
[27] 唐華.花山文化研究[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6.
[28] 楊燖.楊燖民族研究文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
[29] 葉舒憲.千面女神——性別神話的象征史[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 .
[30] 鄧偉龍.歷史性別視角下的壯族青蛙圖騰[J].文藝理論研究, 2009 (4).
[31] 廖明君.性器崇拜與生殖崇拜——壯族生殖崇拜文化研究(上)[J].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1).
[32] 藍鴻恩文集編委會.藍鴻恩文集:故事卷[M].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2004.
[33] 農冠品,過偉,等.女神·歌仙·英雄[M].南寧: 廣西民族出版社, 1992.
[34] 《中國各民族宗教與神話大詞典》編審委員會.中國各民族宗教與神話大詞典[M].北京:學苑出版社,l999.
[35] 黃桂秋.壯族“巖洞情結”的人類學分析[J].河池學院學報,2006(6).
[36] 游修齡.龍舟、端午節和屈原[J].尋根,2001(4).
[37] 唐曉峰.文化源地崇拜[J].中國西部,2013(1).
[38] 黃現璠,黃增慶,張一民.壯族通史[M].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88.
[39] 潘其旭.壯語詞序順行結構的A+B型思維模式與漢語詞序逆行結構的B+A型思維模式的比較研究——壯族文化語言學研究系列論文之一[J].廣西民族研究,2000(2).
[40] 梁庭望.遺落崖壁間的壯族古駱越文明[J].中國文化遺產,2007(6).
THE CULTURAL ANTHOP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N LOCATION OF THE LINCHEN COUNTY,SEAT OF XIANG PREFECTURE OF THE HAN DYNASTY:SERIES PAPERS II OF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N THE LINCHEN COUNTY,THE ANCIENT CAPITAL OF HUASHAN
Wei Fuan,Yao Jiali
Abstract:There has been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of tombs,courtyards,bronze wares and jade wares of the Han dynasty at the locat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Shangjin Town,Longzhou County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in the recent years. The Bashang myth and folklores of placing the souls of Luoyue officers and soldiers are identical with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Luoyue ancestors fighting against government from central plain of China or conflict with neighboring ethnic groups in the period of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e boat street of Shangjin Town is a critical physical evidence of water god worshipping on boats of Luoyue ancestors. The Nongdong Festival and firework-grabbing activities that is popular in folk society of the Zhuang in the Zuo River valley centered with the Zixia Cave inherit the totemic reproduction culture of the ancient Luoyue. The names of some villages around the location of Shangjin Town government coincidence highly with that of the ancient times,especially the contrastive analysis in the thinking model of Zhuang language finds that both “Linchen”and“Shangjin”point to the same location. These cultural relics further affirm the basic deduction that the location of the capital of“Linchen County”,Xiang prefecture of the Han dynasty is at the seat of current Shangjin Town government,Longzhou County and that the ancient capital of Huashan is actually Linchen County. Not only is this affirmation of great political significance to construct ethnic cultural security,but it is also of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precisely grasping the geographical position and context of Huashan culture to plan the tourist industry of Huashan culture scientifically.
Keywords:Linchen county;Shangjin Town;Huashan cultural hearth;cultural relic;interpretation
﹝責任編輯:羅柳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