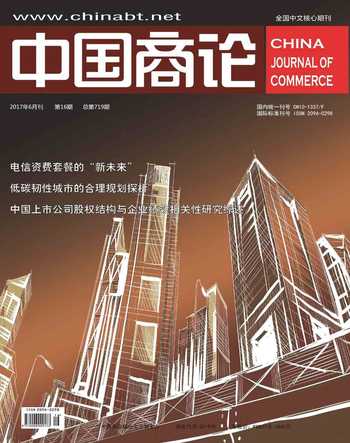基于利益相關者的草原旅游生態補償機制分析
付向陽
摘 要:內蒙古草原生態系統脆弱性和環境資源再生能力較弱等特征,要求在草原旅游發展過程中實施合理的生態補償。本文根據草原旅游活動中各直接利益相關者對草原生態環境的影響分析,從草原旅游可持續發展的生態補償主體、補償對象、補償標準和補償方式等方面,構建了內蒙古草原旅游可持續發展的生態補償機制。
關鍵詞:內蒙古 草原旅游 可持續發展 生態補償機制
中圖分類號:F59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0298(2017)06(a)-049-03
草原生態系統是陸地生態系統的重要類型之一,在我國不同類型的草原生態系統總面積約為4億hm2,約占我國國土面積的41.7%;內蒙古草原屬地處亞洲大陸腹地典型的北方天然草原生態系統,具全國五大草原之首,也是我國北方草原生態系統的主體。北方的氣候特征和草地資源的特性,使得內蒙古草原生態系統具有脆弱性和環境資源再生能力較弱等特征。近年來,依托草地生態系統開展的草原旅游得到了迅速發展,但也給草原生態環境帶來了諸多嚴重的負面效應,草原退化、草原生態系統失衡、生態環境承載超負荷等,使得草原旅游吸引力逐漸衰退。因此,需要在依托草地資源發展內蒙古草原旅游的過程中,明確利益責任,構建合理的草原生態補償機制。
1 內蒙古草原旅游發展中的生態環境問題
內蒙古自治區地處祖國北疆,土地總面積118.3萬平方公里,草地總面積約8700萬公頃,占全區國土總面積的74.4%,占全國草地面積的14.3%。內蒙古因其地域狹長的特征,使得其由東向西各地氣候差異較大,草地類型分別為溫性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草原化荒漠和荒漠五大類[1]。隨著草原旅游的不斷升溫,旅游目的地的生態環境問題日漸顯現。旅游活動的開展不可避免的對旅游區內乃至區外的生態環境產生多層次、多方面的負面作用,如造成地下水、地表水、土壤、空氣以及景觀的污染和破壞,使野生生物種群發生變化等[2]。當前,草原旅游發展對生態環境的威脅,主要表現在旅游活動對草原植被及土壤的影響、對草原動物的影響、對草地水體的影響和廢棄物污染的影響等四個方面[3]。
1.1 對草原植被及土壤的影響
草原旅游對草原植被的影響主要是由于開展各類旅游活動時人畜踩踏、建設各類旅游接待設施造成的。草原旅游的一項重要活動就是騎馬,隨著人們對草原旅游需求的日益強烈,每年5月份就開始接待旅游團隊,而此時內蒙古正處于氣候干燥、降水稀少的時期;加上草原旅游點的馬匹集中使用,騎馬旅游線路也相對固定,使得騎馬活動所涉及的草場被反復踩踏,植被密度、高度都受到了損害,嚴重的造成土地板結、草地退化。同時,隨著旅游人數的增加,不斷擴建旅游設施,也造成了草地地表土壤裸露面積擴大,導致草原沙化。
1.2 對動物的影響
草地資源是發展畜牧業的生產資料,馬、羊等草原地區草食動物是草原動物的主體;同時,草地資源也供養著黃羊、狍子、野兔、狐貍、狼等種類繁多、遺傳性狀各異的野生動物。據不完全統計,我國北方草原地區人工放牧馴養和管理的主要草食家畜遺傳資源共有253個[4]。隨著草原旅游活動的開展,游客的大量涌入,使得動物賴以生存的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外來物種的入侵也給草原畜牧業帶來人畜共患病的傳播隱患;更有甚者,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有些野生動物遭到殘酷獵殺,成為一些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這些都嚴重破壞了草原生態系統和野生動物生態鏈的原有平衡。
1.3 對水體的影響
內蒙古草原由于北方氣候和地形條件等因素,有著季節性雨熱同期、氣候多樣化等特征,降水量從東向西遞減,水資源總體相對匱乏。隨著旅游開發規模的逐步擴大,大量生活垃圾、廢水、廢渣的產生,對草地水質產生污染;此外,地表植被破壞、地表垃圾的沉積也會影響到地下水源,造成水質的富營養化。同時,過度開發也造成了水源供給和地表徑流補給不足,湖泊萎縮。20世紀末,位于內蒙古中部地區的希拉穆仁草原有著星羅棋布的小湖泊,而到2016年原來最大的“天鵝湖”也幾近干涸。
1.4 對廢棄物污染的影響
自然、綠色、生態是草原旅游的主要標簽。草原上蒙古族的生產生活方式都體現著與大自然的高度和諧統一,比如居住的蒙古包、放牧實行的四季游牧、人死后的天葬等習俗,都體現著尊重自然這一最樸素的生態觀念。但伴隨著草原旅游的快速發展,部分旅游企業只看重眼前利益,甚至沒有污染物處理設施,對提供旅游服務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沒有進行合理處置;游客的環境保護意識也不夠,生活用品包裝等塑料制品的廢棄物到處亂扔,草原旅游點附近和騎馬旅游線路上各類垃圾隨處可見,超出了草原生態環境的承載力,嚴重污染環境。
2 內蒙古草原旅游生態補償各利益相關者的影響分析
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從1963年斯坦福研究所提出其定義,到1984年Freeman的《戰略管理——一個利益相關者方法》認為“利益相關者是任何能夠影響組織目標的實現或者受組織目標實現影響的團體或個人”[5],其是管理學理論研究中產生的概念,利益相關者理論逐步被應用到相關研究。國內學者在20世紀90年代也開始了關于利益相關者的研究,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楊瑞龍的觀點[6]。按照利益相關者理論,宏觀上可以將其分為直接利益相關者和間接利益相關者,就草原旅游發展的利益相關者亦是如此。草原旅游發展的生態環境保護主要取決于直接利益相關者之間的相互影響和協調關系,本文主要對地方政府、旅游者、旅游企業和當地農牧民等四類利益相關者進行生態補償影響分析。
2.1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需要考慮草原旅游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有機融合,從統籌草原旅游活動主客體和草地資源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出發,緩和和消除各種矛盾與沖突,推動草原旅游的健康持續發展。因此,在發展草原旅游的過程中,地方政府首先要統籌草原旅游經濟的宏觀發展,制定明確的發展規劃,堅持可持續發展的原則,最大限度的實現潛在環境和經濟利益,同時將可能造成的環境破壞降到最低點;其次要加強管理,嚴格準入制度,遏制草原旅游的過度開發;最后要出臺相關配套政策,對發展草原旅游經濟、倡導生態保護、均衡社區發展、規范市場管理等方面提供政策保障,從而實現對草原旅游生態補償的宏觀管理。
2.2 旅游企業
旅游企業通過向市場提供草原旅游產品和向游客提供服務來實現經濟效益,其獲取經濟效益的基礎是草原旅游資源,包含的企業有組團旅行社、餐飲企業、住宿企業、旅游商店、旅游交通公司、旅游景點、娛樂場所等。旅游企業作為草原旅游的經營主體,一方面為當地帶來了收益,促進了當地經濟發展、居民生活富裕;另一方面,在企業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目標下,對維護草原生態環境的高成本投入等方面明顯不足,造成對草原生態環境的損害,進而破壞了發展草原旅游的資源基礎。因此,要實現草原旅游的可持續發展,就需要旅游企業正確處理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的關系,合理開發、控制規模,注重在考慮區域草原生態環境承載力的基礎上,滿足游客日益旺盛的草原旅游需求,從而保障草原旅游經濟在資源基礎上的可持續性。
2.3 旅游者
一次完整的草原旅游活動由旅游企業、旅游產品和旅游者組成,其中旅游企業銷售旅游產品與服務,旅游者購買旅游產品與服務,旅游產品與服務價值的實現,需要旅游者的購買行為來完成。旅游者在草原旅游活動中主要關注的是通過旅游體驗獲得的知識、愉悅和滿足感。但是,受旅游者自身收入、職業、年齡和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響,體現在對旅游活動與生態環境的問題、人與自然的關系等方面也各不相同,存在部分旅游者為滿足自身求知、獵奇的愿望,造成對草原資源核心區及野生動植物的破壞。旅游者的大量涌入也不可避免的帶來了與旅游地不同的文化觀念,對原有的文化生態造成了沖擊。因此,旅游者應在旅游需求得到滿足的同時,要在保持和維護草原旅游地自然生態、文化生態和社會生態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2.4 當地農牧民
草原旅游的發展與當地社區的發展緊密聯系、相輔相成,當地農牧民既是利益相關者,也是草原旅游資源的另一載體。草原牧區原有的當地農牧民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在發展草原旅游帶動當地經濟發展和增加收入方面,當地農牧民能夠基本認可并支持開展草原旅游;但隨著環境的破壞、本地傳統文化習俗的失真變味,特別是多數農牧民的參與基本停留在較低級的階段,如租賃蒙古族服裝、提供馬匹等,且從中獲取的收益很少,經濟收益的分配及利益分享的不公,使得當地農牧民對發展的現狀感到不滿。當地農牧民作為草原旅游系統中構成社會環境的重要部分,也是對旅游環境影響的直接承受者,其對發展草原旅游的態度、與旅游者之間的關系等,都直接關系到能否實現草原旅游的可持續發展。因此,應當通過草原生態補償機制的建立,來實現當地農牧民在發展草原旅游中得到實惠,實現草原牧區總體利益的提高。
3 內蒙古草原旅游生態補償機制的構建
實現草地永續利用的生態環境補償包括畜牧業、草業等多方面內容,本文僅從發展草原旅游所獲得利益的分配方面,構建內蒙古草原旅游可持續發展的生態補償機制,實質上就是形成一種協調草原保護者與草原旅游受益者之間的制度安排;其目的是要實現發展草原旅游與實現生態環境保護的和諧統一,通過經濟手段調節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分配。按照“誰開發誰保護,誰受益誰補償,誰破壞誰賠償”的原則,構建內蒙古草原旅游可持續發展的生態補償機制框架,主要由以下四方面內容組成。
3.1 草原生態補償主體
明確草原生態補償主體,即界定實現內蒙古草原旅游可持續發展的生態補償責任和如何承擔責任。根據草原生態補償的原則,但凡從發展草原旅游中受益的個人和團體都應該是補償主體;理論上講,內蒙古發展草原旅游的各主要利益相關者都是直接或者間接的受益者,都依托草地資源不同程度地實現了各自的利益訴求,因而都應該是草原生態補償的主體。地方政府通過開發草地資源,拉動交通、景區、酒店等一系列基礎設施投資,從而實現地方GDP的高增長和稅收的增加;旅游企業利用草地資源吸引游客,從而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實現企業利潤增加;旅游者通過形式多樣的草原旅游活動,滿足了旅游需求,通過體驗實現身心愉悅,但也不同程度地對草原環境造成了破壞;當地農牧民也在開展草原旅游活動過程中,獲得了部分的經濟收益,提高了收入、改善了生活。但根據目前內蒙古發展草原旅游產生的生態補償實際情況來看,當地農牧民作為開展草原旅游的載體,與草地資源不可分割,理應參與利益分配;旅游者所獲得的體驗及愉悅,主要包含在其購買的旅游產品及服務中;因此,內蒙古草原旅游發展的生態補償主體主要是地方政府和旅游企業。
3.2 草原生態補償對象
明確補償對象,即要確定內蒙古發展草原旅游導致的合理權益受到損害、應該對其做出補償的對象。發展草原旅游的基礎是草地資源,同時開展草原旅游活動的核心是人,在草原上生活的居民也是草原旅游的重要載體;草原旅游即對草原生態環境造成一定的破壞,也對當地居民原有的生活造成了影響。因此,生態補償的對象不僅包括對自然的補償,也包括對人的補償;對自然的補償指對因開展旅游活動造成草原生態破壞的補償,重點指草原生態的保護、恢復與重建;對人的補償即對以草原為生產資料的當地居民因利益受損的補償,也又對為保護和恢復草原生態環境而付出工作的個人和團體的補償。
3.3 草原生態補償標準
確定補償標準,即針對草原旅游所產生的經濟效益,結合草原生態環境價值評估的有關方法對草原生態價值進行量化;是構建草原生態補償機制的核心問題。明確了“誰補償、補償誰”之后,“補多少”即補償標準就成為構建補償機制的關鍵,它也直接影響到實施草原生態補償的最終效果。目前,從具體的生態補償實踐來看,國外比較認同Castro(2001)[7]在研究哥斯達黎加的流域水環境服務收費對生物多樣性保護和坡地生態系統恢復中提出的機會成本法;在國內,蔡邦成等(2005)[8]將生態補償中資源環境價值評價方法歸納為評估效果評價法、收益損失法、旅行費用法、隨機評估法等四種方法,其中旅行費用法是利用旅行費用來計算由于旅行而造成的旅游地環境質量變化,并估算其造成的經濟損失或收益。結合草地資源及草原旅游的實際,通過旅行費用法和草地資源的機會成本法,來計算草原生態補償標準較為可行,通過旅行費用和草地資源保護成本及草地價值損失的比較,來確定單位面積的草原生態補償標準。
3.4 草原生態補償方式
選擇補償方式,即確定內蒙古發展草原旅游的生態補償采取何種方式,常用的方式可以分為有形補償和無形補償兩種。有形補償包括資金補償和實物補償,其中,資金補償首先涉及到資金來源,現在內蒙古各地在發展草原旅游過程中,都普遍收取了草原牧區服務費,但卻存在著各自為陣、資金使用效率低下、管理不規范等問題,當地政府應依托草原資源成立專門機構,設立草原生態保護基金,統一管理相關費用。同時,要加強對旅游企業生態補償稅費的征收和管理,所征稅費也統一納入當地草原生態保護基金,一部分用于草原生態保護和恢復的資金補償,一部分用于當地農牧民當前生產生活條件改善及未來生活保障等。實物補償是針對因發展草原旅游造成的部分農牧民賴以生存的草地資源的破壞,采取異地置換草地、生態移民等方式進行補償。無形補償主要是針對利益受損的農牧民進行補償,通過提供畜牧養殖技術指導、旅游服務職業技能培訓、農牧民轉移再就業、項目對口精準支援等無形的方式,提高草原牧區農牧民的生產生活能力,進而為其提供因草地資源權益受損的適當補償。
4 討論分析
構建內蒙古草原旅游可持續發展的生態補償機制,首先考慮的是基于發展草原旅游的基礎,即草原資源,核心是草原旅游的可持續發展和草原資源的有效保護相協調,就某一草原旅游地內的草原生態補償。因旅游業對其他相關產業有著較強的關聯性和帶動性,其經濟屬性和市場化運行等特征,有助于改變草原牧區因傳統畜牧業對草原資源過度依賴的生產生活方式,緩解草原生態環境保護壓力;所以,在科學規劃、合理開發和有序管理的基礎上發展草原旅游,并對草原旅游系統內各利益相關者的權益訴求進行分析,構建草原生態補償機制,對實現發展草原旅游與草原資源良性循環著重要意義。
5 結語
本文僅從內蒙古草原旅游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對草原旅游系統內的草原生態補償機制進行了探討。在具體的實踐中,草原生態補償機制的補償標準是核心問題,補償標準既要考慮草地資源的經濟成本,更要考慮其生態價值,需要利用經濟學、地理學等多學科理論,科學計量草地資源的經濟及生態價值,從而確保補償機制的有效性。因此,要提高草原生態補償機制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就仍需對具體的補償標準計算做進一步研究,從而為地方政府制定保護草原生態環境等相關政策提供參考。
參考文獻
[1] 呂君,劉麗梅.草原旅游發展的生態環境影響研究[J].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05(03).
[2] 黃發平.西部地區的旅游業發展與生態環境建設[J].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00(02).
[3] 衛智軍,楊靜,韓國棟.草原旅游對草地影響與管理[J].內蒙古草業,1999(03).
[4] 章力建.關于加強我國草原資源保護的思考[J].中國草地學報, 2009(06).
[5] 賈生華,陳宏輝.利益相關者的界定方法述評[J].外國經濟與管理,2002(05).
[6] 楊瑞龍,周鑿安.一個關于企業所有權安排的規范性分析框架及其理論含義——兼評張維迎、周其仁及崔之元的一些觀點[J].經濟研究,1997(01).
[7] Castro E,Costa Rican.Experience in the charge for hydro environmental services of the biodiversity to finance conservation and recuperation of hillside ecosystems[Z].Paris:OECD,2001.
[8] 蔡邦成,溫林泉,陸根法.生態補償機制建立的理論思考[J].生態經濟,20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