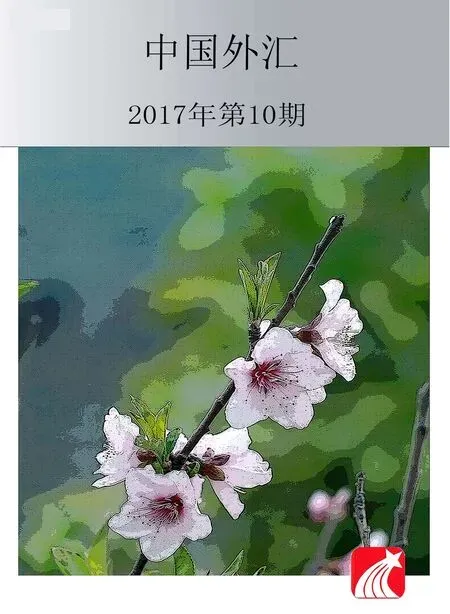人民幣國際化再出發的時機來臨
人民幣國際化再出發的時機來臨

沈建光瑞穗證券亞洲公司董事總經理、首席經濟學家
當前,人民幣大幅貶值與資本大規模外流的壓力有所減輕。在此背景下,重拾人民幣國際化改革進程恰逢其時。
4月,中國外匯儲備增至3.03萬億美元,連續3個月呈回升態勢,表明在人民幣匯率穩定的背景下,資本外流壓力已經明顯減輕。這也符合筆者在今年1月發表的《保外儲還是保匯率是個偽命題》一文中的判斷。文中,筆者堅持認為,保匯率與保外儲二者擇一是個偽命題:外匯儲備下跌與人民幣匯率大幅貶值預期密切相關,3萬億美元外儲并非生命線,確保匯率穩定有助于防范大規模資本外流和金融風險。
對于近一段時間人民幣匯率與外匯儲備的齊升,筆者認為有以下兩方面的原因。首先是與外部環境變化導致美元觸頂回落密切相關。歐元區政治經濟轉好,法國大選未再次上演黑天鵝事件以及特朗普新政不及預期,導致美元升值態勢逆轉。預計今年美元或將出現拐點,可緩解人民幣貶值與資本外流壓力。其次,也得益于中國經濟企穩、貨幣政策收緊以及前期資本管理政策的實施。今年年初以來,為緩解人民幣貶值壓力,央行采取了包括加大直接參與外匯買賣的力度、提高離岸市場做空人民幣的成本,以及加強跨境資金流動管理等諸多穩定匯率的措施。
對此,曾有部分觀點質疑:中國是否要重拾部分資本管制,并認為這是人民幣國際化與改革的倒退,會重挫投資者的信心。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在今年3月底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就此做出了回應。他指出,去年ODI增速井噴40%,比往年增幅提高了20%—30%,其中不乏非理性和異常的投資行為,有的是借對外直接投資之名行轉移資產之實。
對于市場擔憂的外商企業利潤無法正常匯出,潘功勝也做出了解釋:外商企業資金匯出需要滿足一些條件,一是按照中國相關法律要求,要彌補以前的虧損;二是有董事會的利潤分配決議;三是有經審計司審計的財務報表;四是有在中國的完稅證明。滿足這些要求,企業利潤匯出沒有障礙。
筆者在早前《中國資本管制利弊之辨》一文中也曾提到,資本管制的利弊并非涇渭分明,關鍵在于“度”的把握。雖然資本管制短期或會挫傷投資者對改革的信心;但長期看,如果以一定的資本管制避免了幣值大幅貶值的預期以及大規模資本流出的沖擊,則反而有助于贏得投資者對中國經濟穩定的信心,并為推進改革贏得緩沖時間。實際上,IMF在亞洲金融危機后也對資本項目完全可兌換進行了反思,并提出資本項目基本可兌換的目標。
可以肯定的是,當前人民幣大幅貶值與資本大規模外流的壓力已有所減輕,這對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改革進程而言,是有利時機。近期,多位央行人士也就人民幣國際化做出了積極表態。如央行副行長潘功勝就指出,“打開的窗戶不會再關上”,但“改革不能僅有目標,還要有達成目標的策略”;央行副行長易綱也表示,“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中長期戰略,要保持定力,穩步實現目標”。
筆者認為,在跨境資本流動風險降低的背景下,決策層有必要更加細致地對項目進行甄別:一方面,對一些已認定為非理性的投資加強監管,并打擊地下錢莊等非法行為;另一方面,對于符合資金匯出條件的利潤以及個人合理的換匯需求也應予以滿足。
今年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提出,準備今年在香港和內地試行債券通,這是加大資本項目開放、促進資金雙向流動的舉措。近期有報道稱,央行在4月初做出的窗口指導,不再要求商業銀行跨境人民幣結算收付業務嚴格執行1﹕1的限制規定,表明短暫停滯的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或再次加快推進。
綜上,筆者認為,雖然政治局會議將“維護國家金融安全”作為今年中國經濟工作的重要任務,各監管機構也紛紛采取行動以防范金融風險,但顯然,今年防范金融風險的重點在內而非在外。預計今年國內金融去杠桿會持續深入,并有望加快推進資本項目開放與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這也是對質疑資本項目開放與人民幣國際化倒退的回應,有利于重拾投資者對中國改革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