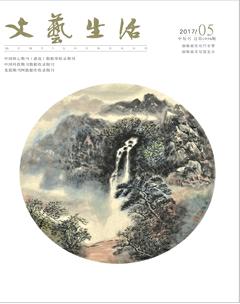淺談紫砂陶刻裝飾藝術
譚海鷗
摘 要:紫砂陶刻藝術,是紫砂陶制品裝飾藝術范圍內的一個門類。它是在清代西泠八家之一的陳曼生帶動下,逐漸完善起來的。紫砂陶與中國的多種文化有著關聯,是一門比較不易隨便介入的藝術。
關鍵詞:紫砂;陶刻;裝飾藝術
中圖分類號:J5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7)14-0032-01
宜興紫砂工藝品是一種民族性較強的傳統工藝品,自北宋以來經千年的藝術春秋,以她釋放而悠久、古樸而端莊、敦厚而大方的豐富多彩的壺體造型,及傳統工藝的性格特征、神似的表現手法,自立于世界陶瓷藝苑之中,成為人們陶冶情操,提高文化素養的良師益友。
宜興紫砂陶藝術根據其造型藝術可以分為光器、花器與筋紋器三大類,針對不同的造型形式,紫砂陶刻裝飾藝術的運用也略有不同。書法陶刻,一般裝飾于紫砂光器與筋紋器,而繪畫陶刻除了紫砂光器造型之外,一些紫砂花器也有采用。這是因為紫砂光器一般整體構圖畫面“干凈”,與國學書法的“高古之風”相宜,而繪畫藝術就不存在這樣的藝術適宜性的“狹隘”,無論光器還是花器,只要造型藝術增添藝術內容。
陶刻文化是金石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國文化的重要載體。離開中國文化的陶刻創新,必定是無本之本,無源之水。
首先,要深入領會中國文化的內涵。儒家的“仁政”“王道”“禮制”,道家的“順應天道,無為而治”,法家的“法”“術”“勢”,雖區分明顯,但內在又有一定的聯系,只有深刻領會這些文化的要旨,方能在陶刻中信手拈來,創新設計。如在《鐘壺》上進行陶刻創作,不論是方形器還是圓形器,若是給予花草蟲魚等自然物象裝飾,不僅該壺的內在味道盡失,該壺所傳遞出的文化品位盡失,而且陶刻與壺本身也顯得格格不入。此時的創新,更需要融入中國的古代文化,雕刻以小篆銘文,內容以《過秦論》、《小石潭記》、《六國論》等古代相關文章的全文為佳。
其次,要深入領會古典詩詞的要旨。中國的古典詩詞,本就與儒、道、法諸家一脈相承,但在傳承的過程中,又融入了詩詞創作者自己的獨特理解和個人的情感傾向。筆者曾在市場上偶見一把《西施壺》,該壺做工精細,設計優雅,可稱這類壺中做工上的上品,可惜在陶刻裝飾上雕刻上了“一片冰心在玉壺”的字樣,大煞風景。
究其原因,是陶刻者錯誤理解“玉壺”與“紫砂壺”的內涵,該詩句中的“壺”,是用以裝酒的,而紫砂壺的“壺”,是用來泡茶的,酒與茶的內涵,截然不同,前者濃烈,后者淡雅,前者是李白式的豪飲,后者是陸羽般的慢品。同時,就所刻就的這首詩歌的內涵看,與《西施壺》的內涵也完全不同。反之,若能緊扣該壺的內涵,以“為伊消得人憔悴”來雕刻裝飾,效果立馬彰顯。同樣,在《蓮心壺》的陶刻創作中,可以用“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來予以裝飾。
“在陶刻中彰顯書法的魅力,在書法中襯托陶刻的韻味”很好地概括了書法與陶刻的關系。陶刻藝人常常以書法來表現紫砂陶藝作品的個性和氣質。將書法作為紫砂陶藝的主體,來表現該作品的思想、感情、風格以及豐富的內涵。作品或古樸端莊、或高貴典雅、或霸氣十足,很多方面都是通過書法藝術來展示的。
在紫砂陶藝中變現書法藝術,最主要的一方面就是通過書法的線條與紫砂作品的造型、色彩、材料等有著內在的一致與融合。因為每一件陶藝作品其實都是包含著一種感情、一種思想、一種境界的,不管是刀法、刻法還是表現內容都需要與作品所呈現出來的感情、思想一致,那么作品中所融入的書法藝術也應該與陶藝作品的正題造型、感情相吻合。
紫砂陶刻裝飾手法獨特,以刀代筆,將中國的書法、繪畫、金石、篆刻諸藝術融于一體,神韻怡然,彰顯了筆墨藝術與工藝技巧高度結合的高雅風貌,形成了具有民族工藝特色的藝術。陶刻藝術的題材極為廣泛,形式更是豐富而多樣,舉凡山水、人物、花鳥、博古諸圖案均可作為入畫素材。
陶刻作品特別講究各種書法,利用正、草、隸、篆、鐘鼎、石鼓等各種不同的書法來表現于各式形體,或圖文并茂,或情趣皆有,表現出作品的構圖嚴謹、參差有致,體現了陶刻藝術的精髓。
只是,陶刻藝術不應只是把書法、繪畫、金石、圖騰等在紫砂器上的搬移再現,即使最成功的轉移摹寫也只能算是上乘的工藝裝飾;不管是哪一位書畫名家有飾壺時,倘若不加刻意經營,只以自己習慣于內容與形式去裝飾,忘卻了舞臺不同應各有各的深度與空間要求,就算是筆墨技法高超,也只能說是壺上留下某某名家的墨跡,不能算是一件成功的陶刻藝術品。
陶刻是一項技術性和藝要性很強的工作,它不但要示作者要有一定的書法功度,還要有繪畫基礎等,主要是要有一定的刀法功力,在完美的構圖排布下,內容合理的安排下,將這幾者有機的結合起來,融詩、書、畫、刻于一體,才能表現出陶刻的精髓和裝飾的藝術性。
參考文獻:
[1]于川.紫砂壺把玩與鑒賞[M].北京:北京美術攝影出版社,2007.
[2]卞宗舜.中國工藝美術史[M].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