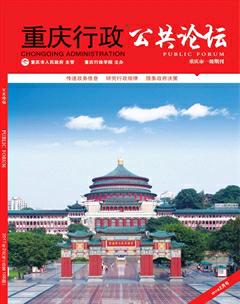重慶市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評價
任思潮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以下簡稱“四化”),為新時期的區域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國內學者將“四化”的關系概括為“工業化是農業現代化的基礎和動力;信息化加快了工業化的發展進程;城鎮化是工業化的成果,是農業現代化的直觀體現;農業現代化與工業化相互促進,是實現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途徑”(張琳,2014)。
重慶“直轄體制、省域面積,城鄉區域差異大”是全國的一個縮影,“四化”的協調發展對全國具有示范性。因此,國家將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賦予重慶,先試先行,探索統籌城鄉發展道路。
為此,本文依據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概念和內涵,構建“四化”綜合發展評價系統,識別重慶地區“四化”協調發展中的問題,提出統籌區域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的發展戰略。
一、數據與方法
(一)數據
本文數據主要來源于《2013年重慶統計年鑒》和38個區縣的《2013年統計公報》。
(二)評價指標構建
“四化”協調發展是一個復雜的經濟系統,該系統由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4個子系統構成,在綜合比較國內外研究“四化”指標的基礎上,依據“四化”協調發展的機理,在考慮科學性、系統性、層次性、可比性的原則上,本文建立包括工業產出比重、人口城鎮化率、郵電業務指數、農業勞均經濟產出等4類14項評價指標體系。
“四化”發展水平測度
G(g)=■aigi;X(x)=■βjχj;C(c)=■γkCk;
N(n)=■δlgl(1)
公式中工業化發展指數G(g)、信息化發展指數X(x)、城鎮化發展指數C(c)、農業現代化發展指數N(n),進行“四化”發展水平測度,ai、βj、γk、δl表示權重。
工業化發展指數、城鎮化發展指數、信息化發展指數、農業現代化指數進行加權得到“四化”綜合發展指數:
T=[G(g)+X(x)+C(c)+N(n)]/4(2)
各系統之間相互作用、彼此影響的強度,為此本文綜合研究情況引入復合系統耦合度,耦合度是通過數學模型反映系統協調的狀態或程度(公式3)。
“四化”同步發展耦合度測算模型:
C=■(3)
耦合度C表征“四化”間相互作用、彼此影響的強弱,C介于[0,1],且其值越大,耦合程度越高。
本文將綜合發展指數T與協調耦合度C綜合為協調發展度,用以衡量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與農業現代化的協調發展水平(公式4):
D=■(4)
三、結果與分析
(一)“四化”發展水平測度及空間分布
為了更好的識別“四化”發展水平的空間分布規律以及區域差異特征,以各項指數的平均值,±0.5標準差、±1標準差確定圖例臨界值進行空間分析(圖1)。
1.工業化指數的平均值為0.2336、標準差為0.1 791、變異系數為0.766,最高值0.821(渝北),最低值為0.003(巫溪);高值的區域主要分布在重慶的主城區、璧山、江津、涪陵、萬州、黔江,低值區域主要分布在渝東北、渝東南地區(簡稱兩翼),與地區經濟發展格局基本一致;2.信息化指數的平均值為0.317、標準差為0.1 411、變異系數為0.448,最高值0.645(渝北),最低值0.002(彭水),高于平均值的區域主要分布在重慶的主城區、1小時經濟圈內,低值區域主要分布在渝東北、渝東南地區;3.城鎮化指數的平均值為0.228、標準差為0.225、變異系數為0.986,最高值0.950(渝中),最低值0.002(酉陽),城鎮化的空間分布明顯,以渝中區為高值核心向四周降低;4.農業現代化指數的平均值為0.415、標準差為0.089、變異系數為0.215,最高值0.648(永川),最低值0.139(巫溪),高值區主要分布在渝西地區,低值區主要分布在兩翼區域。
總體來看,城鎮化、信息化、工業化指數變異系數大,平均值較小,而農業現代化指數平均值較大,變異系數較小;空間分布上看農業現代化也與城鎮化、信息化、工業化分布規律不一致,相關研究中表明這是農業現代化一定程度滯后于其他三化的發展,與其他三化未能實現良性互動(吳旭曉,2012,袁曉玲,2013)。“四化”中工業化涉及產業結構問題;信息化是創新驅動,屬于要素投入結構問題;城鎮化涉及需求結構;農業現代化涉及產業結構問題(常修澤,2013),產業結構中應以主導產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相融合的產業集群模式,提升工業化的水平;要素投入應加大科技投入,提高勞動者的素質;需求結構依靠城鄉區域發展協調互動,人口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跟著經濟、產業走,形成人口和經濟相一致的格局;最終達到“四化”協調發展。
“四化”協調度將發展水平和耦合度進行綜合評價,更能刻畫“四化”的協調程度,具有更強的辨識度;“四化”綜合協調度的平均值為0.493、標準差為0.148、變異系數為0.299,最高值0.761(渝北),最低值為0.171(巫溪);高于平均值的區域主要分布在重慶的主城區、永川、江津、涪陵、萬州,低值區域主要分布在兩翼。
萬州、黔江是兩翼地區的核心城市,是帶領兩翼發展的關鍵點,在評價結果中兩城市都形成區域高地,但黔江的協調度在東南翼不夠高,表明人口和資源要素集聚不明顯,需要進一步加快發展,形成渝東南中心城市和武陵山區重要經濟中心。
總體而言,“四化”的空間分布兩翼較低,都市區內較高,以墊江、豐都、武隆為界線,西高東低;界線是武陵山與大婁山結合部,大都市區與兩翼的重要接點,表明“四化”區域格局與城市自然地理背景、交通區位條件、經濟發展水平、政府規劃等有關。
(二)基于“四化”發展狀態的問題區域識別
為了更好地識別“四化”發展的問題區域,以“四化”指數、綜合指數、協調度低于全市平均水平的60%準則,進行綜合分析,得出4種滯后全市發展水平的類型:1.工業化滯后型2個。大渡口工業產值只占都市區總產值2.3%,人均GDP為39570元,低于都市區的62930元,也低于城市發展新區的48478元,只比全市38914元略高。大渡口在重鋼主業搬遷后,經濟總量相對較小,增長速度慢,發展的內生動力仍然不足,支撐區域發展的大項目、好項目少,培育新的產業支柱尚待時日。南川工業實力不強,工業產值只占城市發展新區總產值3.9%,人均GDP為32612元,資源加工占主體的傳統行業持續虧損,主導產業仍處于起步階段。大渡口、南川區位優勢較好,經濟提速增效空間大,應發揮優勢,加快產業升級轉型,與周圍區縣形成集群發展。2.城鎮化滯后型2個。榮昌(44.50%)、銅梁(44.87%)。銅梁、榮昌在城市發展新區城鎮化滯后發展,涪陵、長壽、江津、合川、永川、南川、綦江的城鎮化率均高于50%(永川高于60%)。根據賽爾奎因和錢納里模式關于工業化進程判別標準(安虎森,2012),銅梁和榮昌人均GDP和產業結構屬于工業化中期,城鎮化率應高于50%,兩區應實現人的城鎮化,達到產城融合。3.工業化城鎮化滯后型2個。潼南工業化率24.08%,城鎮化率42%;豐都工業化率25.88%,城鎮化率37.91%。兩縣處在工業化初級階段,工業化帶動城鎮化,隨著工業化的提升,城鎮化也會隨之匹配。4.綜合滯后型12個。奉節、彭水、城口、巫山、巫溪等主要分布在兩翼地區,是生態脆弱區域,是國家限制開發區。
總體上看來,“四化”滯后型主要分布在兩翼地區,渝東北和渝東南的經濟總量僅為都市區的21.1%、7.1%,人均GDP為都市區的49.1%、48.4%,兩翼與大都市區““四化”差距大。如何統籌兩翼地區的發展,是重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破解的重大命題。
(三)“四化”協調發展的意義
如表2所示,人均GDP作為反映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農民人均純收入作為衡量農村發展水平,城鄉居民收入比反映城鄉收入差異,進行相關性分析:協調指數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極顯著正相關(0.804),與城鄉居民收入比極顯著負相關(-0.503),表明“四化”協調發展程度越高,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城鄉收入差異越小,也表明“四化”協調發展,歸根結底是為縮小城鄉二元差異,促進勞動生產率趨于一致,使城鄉人民獲得同等的福利待遇(馮獻,2013)。
(四)區域協調發展
為統籌區域協調發展,市委在根據資源稟賦、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現有開發強度所形成的發展潛力,按區域分工和協調發展的原則,在四屆三次全會中將全市劃分為都市功能核心區、都市功能拓展區、城市發展新區、渝東北生態涵養區、渝東南生態保護區(五大功能區域)。五大功能區域是重慶對區域發展失序問題、促進區域協調、統籌城鄉和可持續發展而提出的重要舉措。
由表可知3,1.都市功能核心區工業化指數0.324,城鎮化指數0.663,工業化指數低于都市功能拓展區,根據英國經濟學家克拉克和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茨研究,工業化初期到后工業時代,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將經歷一個由上升到下降的“∩”型變化,第三產業經歷上升、徘徊、再上升的發展過程,最終成為國民經濟中最大的產業。都市功能核心區正處于后工業時代,第三產業正處于再上升階段,該區域應重點發展現代服務業如金融、商貿等。2.都市功能拓展區是工業化的領頭羊,城鎮化指數0.413,仍有提升空間,需合理布局規劃,集約用地,人口居住地,是未來新增城市人口的宜居區。3.城市發展新區工業化指數0.267、城鎮化指數0.188,與都市功能區相比仍有不少差距,是重慶工業化、城鎮化的主戰場,集聚新增產業和人口的重要區域,“四化”發展的示范區。4.兩翼“四化”發展程度不高,屬于限制開發區,主要任務是生態涵養與保護,提供農產品和生態產品,堅持“面上保護、點上開發”,因地制宜發展特色產業,有序引導農村人口有序就近向縣城、萬州、黔江集聚,重點引導區域內超載人口向都市功能拓展區和城市發展新區轉移。
四、結論與討論
一是重慶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協調度均存在不協調。農業現代化一定程度滯后于其他三化的發展,與其他三化未能實現良性互動,應調整產業結構,合理規劃城市布局,達到產城融合,加大創新要素投入,縮小城鄉二元差異,促進勞動生產率一致,形成1+1+1+1>4的功效,最終使得城鄉人民獲得同等福利待遇。
二是重慶“四化”發展水平均存在明顯的區域不均衡。“四化”的空間分布以墊江、豐都、武隆為界線,西高東低,差異明顯,已形成發展鴻溝。為此市委劃分五大主體功能區域,進行區域非均衡協調發展的重大實踐,強化五大功能區建設,發揮比較優勢,充分集聚各自發展資源,實現錯位競爭、差異發展,形成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新格局,最終實現全面小康。
參考文獻:
[1]張琳,邱少華.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評價研究[J].山東社會科學,2014,(4):124-129.
[2]俞立平.工業化與信息化發展的優先度研究[J].中國軟科學,2011(5):21-28.
[3]劉濤,曹廣忠,邊學等.城鎮化與工業化及經濟社會發展的協調性評價及規律性探討[J].人文地理,2010,(6):47-52.
[4]袁曉玲,景行軍,楊萬平,班斕.“新“四化””的互動機理及其發展水平測度[J].城市問題,2013,(11):54-60.
[5]吳旭曉.我國中部地區城市化、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三化”協調發展研究——以贛湘鄂豫四省為例[J].農業現代化研究,2012,(1):1-7.
[6]安虎森,周亞雄,劉軍輝.濱海新區產業發展路徑分析——與浦東新區的對比[J].經濟與管理評論,2012,(3):131-136.
[7]馮獻,崔凱.中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內涵與同步發展的現實選擇和作用機理[J].農業現代化研究,2013,(3):269-273.
[8]吳旭曉.我國中部地區城市化、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三化”協調發展研究——以贛湘鄂豫四省為例[J].農業現代化研究,2012,(1):1-7.
[9]常修澤.中國新型““四化””之探討——以“京南第一縣”為案例[J].改革與戰略,2013,(7):13-25.
作者單位:中共重慶市璧山區委宣傳部
責任編輯:馬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