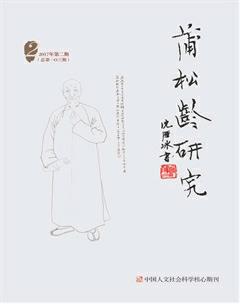真幻流轉:《聊齋志異》的壁間世界及佛道之思
王一雯
摘要:《聊齋志異》中有多篇涉及異界空間書寫,其空間敘事美學一直為學界所關注,但對于《聊齋志異》中的真幻敘事藝術仍有可書之處。蒲松齡通過多層空間的構造,將人物與敘事轉圜于真幻之間,營造出“真中有幻”、“幻中有真”的氛圍,且在真幻的不同思辨中流露出人生最深刻的矛盾。這種空間構造以及真幻虛實糾纏的敘事模式展現了蒲松齡對現實與理想的復雜心態,以及其思想背后儒道佛三教的文化背景。本文擬將以《聊齋志異》中的《畫壁》與《寒月芙蕖》為主要的分析對象進行管窺,輔之以《聊齋志異》的其他篇章或其他志怪筆記篇章作為對照。
關鍵詞:聊齋志異;空間;真幻;敘事;三教
中圖分類號:I207.419 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中國古代相當重視空間感,異界書寫傳統古已有之。異界相對于常界被構筑,某些情況下和常界形成對舉的關系,也構成了一個永恒的主題,即真與幻、實與虛在文本中的不斷流轉。在此傳統下,他界敘事藝術亦不斷趨于成熟。
以葉慶炳歸納的中國古代他界結構的構筑特點來觀察《聊齋》中《畫壁》《寒月芙蕖》等涉及壁上他界空間的篇章,可發現多數故事應歸類在幻境經歷的大框架下。
中國小說的敘事,空間結構是先于小說的時間邏輯的,及至清代《聊齋志異》,空間思維已由一種模糊的痕跡演變成為作者有意識的目的,空間也成為一種敘事對象。他界空間敘事中,這種在一壁之間構造仙鄉幻境的作品類型的出現,呈現出真幻變換的特點,表現了筆記小說敘事藝術的進一步成熟;同時,作者藉助儒道佛的異術和教義,將原始神話歷史中遙遠的仙鄉和幻境空間挪移到壁間他界,顯示了一種世俗化趨勢下對人生終極意義之思索考量。
本文所論的墻壁世界往往呈現與眾不同的“異象”、“怪相”,墻壁內外由此構筑出一種差異空間。此類“異象”一般以圖畫為媒介。這實際受多個母題影響。首先是民間的“畫中人”傳統,由于人所作之畫像的真實與虛假性帶來多重辯證,同時,亦有佛道宗教母題的滲透。如《畫壁》是人入畫境,朱孝廉幻由心生,進入壁畫中并與畫中人物發生一段愛戀,是佛家傳統。《勞山道士》的壁上世界則涉及道家方術。類似的壁畫故事傳統,在《太平廣記》中即有類似故事,卷七十四道術四陳季卿條載竹葉舟故事中,“陳季卿思鄉心切,睹寺院壁畫而生歸意,異人將竹葉放于圖中渭水中。此故事為袖里乾坤,道家當行的典型。” [1] 40
壁上有畫,或壁上作畫,亦或壁間如畫,以畫這種媒介來分割壁外和壁內兩種空間最常見,當然本文討論的此類媒介不一定全為畫像或是人物像,廣義上也包含了在壁間貼上的一些物品或是壁間出現的某種變異的現象。現實與他界僅僅相隔于薄薄的一壁之間,跨越了虛空與實在、真實與幻想、可見與不可見,實為現實與理想間的分割,背后包含了對于宗教想象和現實生活的深沉思考。
學界以往很少注意到此種他界空間。論及《聊齋》真假敘事藝術的學者,并非僅聚焦于他界空間書寫,且往往是針對單篇展開論述,如臺灣學者賴芳伶的《擬真敘事,如夢抒情——細讀〈聊齋志異〉〈寒月芙蕖〉與〈翩翩〉》,即詳細分析《聊齋志異》的真幻相攝的敘事手法,以及幻境敘事背后深沉的人間情感。而涉及壁上空間書寫的篇章大多集中在《聊齋志異》的道家法術特色研究中,歷來對《勞山道士》《寒月芙蕖》的研究也是放在此框架下的。《畫壁》的討論焦點在情與理法關系上,學界意見也一直無法統一,大概分成“主情”、“主悟”兩種派別,即其主旨究竟是“幻由人生”,還是只是一個描寫生動的美好愛情幻想。
目前,研究者也很少講他界空間書寫和其背后所表達的教化含義相聯系。臺灣學者陳翠英曾經討論過《聊齋志異》的仙凡流轉,以此總結蒲松齡的“劉、阮再返之思與情緣道念之辨”。本文亦想借由對壁間空間的書寫梳理蒲松齡故事背后的教化意義。
二、仙鄉的追求與成仙的渴望:《聊齋》壁間幻境的內向書寫
《聊齋》中的仙幻故事,有不少是主人公置身異界,并以此為契機展開空間敘事。故事書寫壁間的異狀,往往暗示此為幻境,或難為常人所把握的仙境,總體呈現內向型的空間構造特色。
蒲松齡處理此類墻壁的異象,往往藉助比喻手法。如《羅剎海市》里的馬龍媒游歷海中仙境,他看到海市蜃樓般的龍宮,“方至島岸,所騎嘶躍入水。生大駭失聲,則見海水中分,屹如壁立。俄睹宮殿,玳瑁為梁,魴鱗作瓦,四壁晶明,鑒影炫目。” [2] 此處,作者將墻壁比喻成鏡子。“鏡”對實體照映亦如“畫”一般,呈現真實與虛幻共存之二重性。不同的是,畫的模擬雖然是假,但因其能模擬真實,畫像可朝實物發展,因而六朝起即有“畫中人”;即使最終結果可能是幻夢一場,不可再得,但總能留下真的證明,似六朝仙鄉傳統中,與神女遇合而獲得信物。而鏡子可清楚地映鑒真容,真得極致卻是無法觸摸到的假;“但鏡子作為宗教上的法器和寶物,又能突破所有的假,照見萬事萬物的真面目。” [3]
《聊齋》中如鏡般的墻壁,也聯系著宗教,既是道家方術或仙境空間,也蘊含佛教的色空觀與大千世界的觀念。此處,墻壁作為常界和他界的界線,正是仙鄉所需分界線的隱喻。墻壁像鏡子一樣閃閃發光,這是道家的寶物傳統的描寫,實際上是通過這種異常的潔凈明亮特征來暗示這個內向的封閉空間的非常性。人已處在他界之中,被這樣的墻壁四面包圍,就如同是被這樣光亮的鏡子所包圍,理應產生一種奇異感和神圣感。
再如《余德》中的地上龍宮。尹圖南將一幢別墅租出,后來碰到了叫余德的秀才。一日,尹到余家,“見屋壁俱用明光紙裱,潔如鏡”。這是一種比喻,亦是一種暗示,尹圖南和余德兩個人在這個空間中,四周的裝飾華美奢侈,有“金狻猊爇異香,一碧玉瓶,插鳳尾孔雀羽各二,各長二尺余。一水晶瓶,浸粉花一樹,不知何名,亦高二尺許,垂枝覆幾外;葉疏花密,含苞未吐;花狀似濕蝶斂翼;蒂即如須。筵間不過八簋,豐美異常。” [2]
這是功名失意的蒲松齡幻想的地上龍宮,塵世仙境。余德后來去向不明。最后,一個道士告訴尹圖南,那只丟在后院的石缸是龍宮的蓄水器,缸雖破而水不泄是因缸有魂魄,用缸的碎片合藥有長生不老之效,可以推測余德與龍宮有關:
忽有道士踵門求之。尹出以示。道士曰:“此龍宮蓄水器也。”尹述其破而不泄之異。道士曰:“此缸之魂也。”殷殷然乞得少許。問其何用。曰:“以屑合藥,可得水壽。”予一片,歡謝而去。
他藉助尹宅在地上塑造了一座龍宮的鏡像,但那畢竟不同于龍宮,這種奇異的景象最終還是要消失的,但留有一些證據,來證明幻境真得存在過,這和過去遇仙留下證物是異曲同工。但這個物品不是簡單的紀念品,道士還告訴他,如何利用遺留下來的物品以增陽壽,尹生給了道士一片,道士歡喜而去。但故事沒有點出尹圖南最后是不是因為服用了藥物而長生,但按常理推測,選擇服用這種藥物的結果應是可想而知。總的看來,這是道家、仙境相結合的幻境。但幻境的消失所帶來的“空”觀又因長生之藥的獲得而被消解了許多。可見,此種幻境是作為長生的機緣而存在的。
又如《褚遂良》中的狐仙,為報答唐朝褚遂良的恩情,治好了他的轉世趙生的病,還愿意嫁給他為妻。而故事中趙生所住茅屋,是:“某自慚形穢,又慮茅屋灶煤,玷染華裳。女但請行。趙乃導入家,土莝無席,灶冷無煙。……曰:無論光景如此,不堪相辱;即卿能甘之,請視甕底空空,又何以養妻子?”可見趙生十分窮困。而“女但言:‘無慮。言次,一回頭,見榻上氈席衾褥已設;方將致詰,又轉瞬,見滿室皆銀光紙裱貼如鏡,諸物已悉變易,幾案精潔,肴酒并陳矣。遂相歡飲。” [2] 狐仙又構筑了一個相似的鏡像壁間。
等到端陽時節,白兔躍入,狐仙說這是“春藥翁來見召矣!”,于是二人共登云梯,趙生成仙而去,后眾人:“共視其梯,則多年破扉,去其白板耳。群入其室,灰壁敗灶依然,他無一物。猶意僮返可問,竟終杳已。”狐仙最擅幻化之術。破舊的茅屋被施以幻術。凡人往來其間由實入幻而無所覺,直等到狐仙攜趙某登梯上天之后,人們才看到那梯子只不過是多年的一張破門去掉了白板而已,走進房子,依然是灰壁敗灶,別無他物。仙境雖然在此消失,但趙生已經獲得了成仙的機遇。
諸如《余德》和《褚遂良》這種塵世幻境,以呈現異象之壁作一個簡單的區隔,墻外世界一如往常。鏡壁既暗示神奇感,又消融了墻壁帶來的他界空間和外部的界限感,將幻趨于真;同時它本身具有的特性又強烈暗示其虛幻特性。
這一類的內向型壁間世界的構建大抵都是用來消除塵世富貴念,進一步暗示仙界永恒的。這些故事里,成仙是實有,蒲松齡通過這種壁里世界的變換,所透露的意涵,是人間世界的幻境,必將是富貴繁華,到底成空,卻又將仙境攝于幻境的背后;這些故事中,幻境消失,卻指引了一條真正存在的成仙之路。
三、道士的虛假幻境:《勞山道士》與《寒月芙蕖》的平行空間
《勞山道士》,也有道家在壁上分酒貼月法術的展演。因道士有穿墻之仙術,于是,墻壁就不是內向封閉的限制,而具有了通道的功能和意義。王生是求道者學穿墻之術,道士答應傳授給他:
呼曰:“入之!”王面墻不敢入。又曰:“試入之。”王果從容入,及墻而阻。道士曰:“俯首驟入,勿逡巡!”王果去墻數步,奔而入;及墻,虛若無物;回視,果在墻外矣。
這僅僅是現實空間中物理上的移動。而《勞山道士》里還有另一個法術,王生“一夕歸,見二人與師共酌,日已暮,尚無燈燭。師乃剪紙如鏡,粘壁間。俄頃,月明輝室,光鑒毫芒”。這是貼紙于壁的法術,類似于《寒月芙蕖》中道士在門上繪畫。座中客人想要呼喚嫦娥到來,道士“乃以箸擲月中”,于是“見一美人,自光中出。初不盈尺;至地,遂與人等。纖腰秀項,翩翩作‘霓裳舞”。但是,嫦娥最后又復為箸,消失無蹤。
此時,客人還想移步月宮。在道士的法術中,“三人移席,漸入月中”,“眾視三人,坐月中飲,須眉畢見,如影之在鏡中。”此處,弟子的視角暗示了他們似乎是通過了那個貼在墻上的紙片,進入到一個虛幻的仙境當中。“須眉畢見”,表現得十分真實;而又如“影在鏡中”,暗示了全為虛假。當“月漸暗”,“門人然燭來,則道士獨坐而客杳矣。幾上肴核尚存。壁上月,紙圓如鏡而已”,似乎剛才的一切就是幻覺,只有肴核可以證明有客人存在過,其余的異界之物都是道士的法術虛構的,弟子所見三人于月宮中的經歷也應為虛,呈現出真與幻的交織。仙境是道士的幻術,而非仙人的法術。成仙之事也因此而變得更加虛無縹緲,不可捉摸。
但《寒月芙蕖》的真幻藝術更加高明,通過墻壁上手繪之門扉較清晰地看到同時存在的真幻兩個世界。
《寒月芙蕖》的真幻空間構造,與袖里乾坤及壺天勝景不同。《寒月芙蕖》用閘門連接兩個獨立空間,因此異托邦和烏托邦平行投影模式得以開啟。
不同于《桃花源記》中,武陵人進入仙境,勾連兩個獨立時空;《寒月芙蕖》的兩個空間,其呈現出獨特性,即無限貼近,卻又絕無交集。是一種空間上的平行投影。形成反影的藝術。“門”雖然存在,兩個世界之間,食用物品雖然可以被傳遞,但是這兩個空間之人卻不能互相往來,甚至不能說話,更不能跨界。兩個空間的疊合,一定程度的交叉,表現在佳肴美色,都是較為低階的物品能夠傳遞,這是變異的袖里乾坤。若將壁內看作是仙境,壁外此時則為幻境。這幻境是壁內仙境的平行投射;而壁內世界和現實的連接,壁上閘門消失了,壁外世界自然回歸現實。
《寒月芙蕖》中,空間的交互以及平行投影的特性,主要體現在兩個空間是否存在彼此交集的關系。而壁外的空間中,除了第一層物品的傳遞之外,還有第二層“寒月芙蕖”的盛開,仿佛改變了壁外空間的時間。這時,壁內的世界已經從文本中隱去,但是并沒有像《勞山道士》那樣直接描寫法術褪去的真實世界,而處于一種被敘述者忽略的狀態。
一官偶嘆曰:“此日佳集,可惜無蓮花點綴!”眾俱唯唯。少頃,一青衣吏奔白:“荷葉滿塘矣!”
寒月芙蕖,實際上是墻內理想世界的投影,理想世界隱去,其實是將自身投影在現實空間中,依靠現實的空間得以展現。兩個空間的關聯性,從物品的添加,進一步變為景致轉變,也就是時間的轉變。這種展現,亦持續維持了現實世界的虛幻性。但壁外的空間雖然是開放空間,在理想世界的投影下卻是沒有方向感的;甚至是有邊界而無法突破的,所以必定是帶有虛幻色彩的。
同時,這也說明,異界空間的變動,亦會勾連時間的變動。《聊齋》中的異界時間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仙界一日,人間千年,即寫某一凡人偶入仙境,回家時已是時過境遷,人事全非。如《仙人島》中的王勉,隨道士至仙人島上,仙人以女妻之。逾數月,王以親老子幼回到家鄉。至家,始知母與妻早已亡故,惟有老父尚存。另一類型是仙界百年,人間片刻。道教的追求,讓愚迷者在頃刻間經歷人生百年所能經歷的一切,夢醒以后,幡然醒悟,于是求仙悟道而去。如《續黃粱》寫曾孝廉只是小睡了一會兒,在夢中卻已歷兩世。” [4] 11
蒲松齡拋棄傳統游歷仙境中常有的“仙凡”時間差的觀念,即仙境一日人間數十年甚至百年,以幻境時間對比人間時間的反諷性為基本結構的時間處理方式。《寒月芙蕖》中的兩個世界,時間是一起流逝的,從壁內世界拿出來的食物是熱的,食客沒有長短變化而帶來的感嘆。這正代表了內外時間的關系也是平行投影,沒有時間的反差,而是相續若流水,真幻相成。較之壁外現實世界滿溢的虛幻感,門內的世界則昭示一種異界理想。相對現實而言,它是充滿虛幻色彩的空間,但這個虛幻的空間在超越性的意義上代表了一種真實存在,同時又影響了現實空間。它讓壁外真實世界染上虛幻的色彩的過程,正是它自身的虛幻投射在真實上產生影子,反讓自身平添幾分真實。
敘述者已經認識到,這種仙境亦為幻境。《寒月芙蕖》中沒有“異史氏曰”,沒有任何證據留存,只有:“道人笑曰:‘此幻夢之空花耳。無何,酒闌,荷亦凋謝;北風驟起,摧折荷蓋,無復存矣。”這意味著虛幻世界的崩塌,真實只能被限縮到人心這樣的一個抽象支點上。支撐這種幻境的是壁內空間,但這種仙境亦為一個不可復得的洞穴通道,或者是不能常駐的。且這種不可復得的地點,邏輯上并不能夠推出它就是絕對的真實,因為幻境也是不可復得的。道士的話是在變相點明這是門內的仙鄉亦是一個幻境,是烏托邦,即虛假的空間,是沒有真實內容的存在。
即使壁內世界為真,但這種真就如幻一樣不可得之。但作者體現了,人們對仙鄉有一種渴望,這是真實的。然而這種渴望的結局是,仙鄉是幻,夢一樣的經歷是幻,只剩下當前的自己是真實。這就是作者的道念辯證,他拋棄對功名的眷戀,實際上也不是真得完全相信成仙之路,認為那也只是道教所作的幻化之術而已。故事的焦點人物,是作為異人的道士,由他最后點明夢幻的空花意旨。故事最后,亦從道士暗示個人層面的選擇,即“空”要在常界中去追尋。
四、佛教的戒色主題:《畫壁》的多層空間
《畫壁》的幻境設置沿用仙鄉艷遇的模式,及佛教以美人考驗他人的傳統,構成了“嵌套型”的壁間空間。故事發生的場地具有十分明顯的宗教性:“江西孟龍潭,與朱孝廉客都中。偶涉一蘭若,殿宇禪舍,俱不甚弘敞,惟一老僧掛搭其中。”寺廟被視作凡界與仙冥二界的鏈接處,以一種“過渡空間”的形式存在。以壁畫為界,建立了兩個截然不同的空間維度。空間結構由兩個獨立的空間的串聯而成:第一空間,寺廟與第二空間,幻境。第一空間是以現實世界為參照的古寺廟,寺廟的選擇除了其自身所蘊含的文化意義外,也具備了為后續情節鋪墊的作用。第二空間,壁畫世界,作為一個獨立的空間同時也是一個密閉空間存在。以壁畫為界,建構了一個異空間,這個異空間的出入口都是壁畫,從物理層面達到了封閉的效果。而且,壁畫世界內部,在作者安排下,也以第三人稱有限視角去展開敘述,將空間直接限制在朱生的經歷中。他主要的經歷都在壁畫中的世界發生:“使者反身鶚顧,似將搜匿。女大懼,面如死灰。張皇謂朱曰:‘可急匿榻下。乃啟壁上小扉,猝遁去。”即相對于朱生而言,他所游覽的壁內空間,自成一個體系。
同時,《畫壁》在時間上也呈現傳統仙鄉幻境模式,敘事時間晚于故事發生時間,被割裂成為兩個獨立體。由此看來,寺廟中的一面墻壁,墻壁有畫,朱生進入壁畫中游歷,每一個空間相對封閉而呈現嵌套疊加模式。其共通性在于聯通兩個空間的是兩個關鍵人物,即老僧與天女。
老僧涉足了真與假的世界。而天女也可以在真實存在的壁畫上改變形態。如文中所述,朱孝廉進入佛寺首先映入眼簾的景象是:“殿宇禪舍,俱不甚弘敞,惟一老僧,掛褡其中。”而他進入幻境時的第一印象是:“一老僧說法座上,偏袒繞視者甚眾。朱亦雜立其中。”兩個老僧形象互相呼應。
在游寺的開始,朱生賞識壁畫中神女的審美感受,與其在壁畫中賞識神女的容貌以一種錯亂的方式分散在兩個空間中,這種有意無意的重復使第二空間的出現更具真實感。
神女的形象就如一般艷遇故事,不過蒲松齡的筆法更為細膩生動。在壁畫世界中,朱生一開始在聽法。這位神女主動上來“暗牽其裾”,并且對他囅然一笑,進而引他“過曲欄,入一小舍”,最終成就“狎好”之事。其間小說還特意寫了朱孝廉的疑慮、膽小:“過曲欄,入一小舍,朱次且不敢前”;這時,“女回首,舉手中花,遙遙作招狀”,以手勢招引,而后“舍內寂無人;遽擁之,亦不甚拒,遂與狎好。”女伴察覺到了這點,于是給神女改了發型,“髻云高簇,鬟鳳低垂,比垂髫時尤艷絕也。”
等到朱生從壁間返回現實世界,他們“共視拈花人,螺髻翹然,不復垂髫矣”,這說明這種變化并非朱生一個人看見,神女也通過畫像在現實中出現。朱生在幻游期間,形象也是在壁畫上顯現:“旋見壁間畫有朱像,傾耳佇立,若有聽察。”而“少時,以指彈壁而呼曰:‘朱檀越何久游不歸?”其間,聲音也是相通的:“僧又呼曰:‘游侶久待矣。”最后就像游歷仙鄉返回一樣,朱生“遂飄忽自壁而下,灰心木立,目瞪足耎。孟大駭,從容問之,蓋方伏榻下,聞叩聲如雷,故出房窺聽也。”這樣的敘述更加模糊了現實與異界真幻的界線。
同時,《畫壁》的主題涉及女色考驗。成仙考驗是道教仙話的四大母題之一,是神仙對度脫對象的心性的考驗,通過考驗的修道教徒才能進一步修行成仙,佛教小說也用這種考驗方式。《畫壁》故事中的神女是一個散花天女,也是佛教典型警醒式故事。天女散花的故事來源,現只有一種說法,主要認為來自《維摩經·觀眾生品》。此故事以天女所散之花是否著身驗證向道之心,如果塵俗未盡,花即著身。
于是,神女和老僧一起完成對于眾生之一的朱生的考驗與開悟。而故事最后,“異史氏”現身進行主題的深化,曰:“幻由人生,此言類有道者。人有淫心,是生褻境;人有褻心,是生怖境。菩薩點化愚蒙,千幻并作,皆人心所自動耳。老婆心切,惜不聞其言下大悟,披發入山也。”作者通過“異史氏”之口,再次強調了點化眾生的目的。幻由心生,所化之境是以色欲為先驗的世界,此處正展現了佛家的“色空”觀念。
在此主旨下,讀者一般都視《畫壁》內部世界為幻境。與《寒月芙蕖》意指人間富貴不同,《畫壁》中老僧說,“幻由心生”,似意指這個幻境是由朱生的色欲而引起的,因為他看到“東壁畫散花天女,內一垂髫者,拈花微笑,櫻唇欲動,眼波將流”,所以“注目久,不覺神搖意奪,恍然凝想。身忽飄飄,如駕云霧,已到壁上”。
但這個幻境本身卻呈現出真實性。首先,朱生入畫,則寺中無人,所以朱生的游歷非僅僅是神游:“時孟龍潭在殿中,轉瞬不見朱,疑以問僧。僧笑曰:‘往聽說法去矣。問:‘何處?曰:‘不遠。”故事中確實發生了空間的移動。
雖然越界經驗模糊,但對于這個幻境,朱生自己是有所覺的:“見殿閣重重,非復人世。”和人世的區隔和不同是明顯的。后文也提到,金甲使者來搜尋下界之人,“朱伏,不敢少息。俄聞靴聲至房內,復出。未幾,煩喧漸遠,心稍安;然戶外輒有往來語論者。朱局蹐既久,覺耳際蟬鳴,目中火出,景狀殆不可忍,惟靜聽以待女歸,竟不復憶身之何自來也。”反向證明了一開始他對于自己的來處還是有意識的。
同時,這個金甲使者的言語,似乎也暗示了壁畫中的世界是勾連仙界或者說佛教的異界的:“忽聞吉莫靴鏗鏗甚厲,縲鎖鏘然。旋有紛囂騰辨之聲。女驚起,與生竊窺,則見一金甲使者,黑面如漆,綰鎖挈槌,眾女環繞之。使者曰:‘全未?答言:‘已全。使者曰:‘如有藏匿下界人,即共出首,勿貽伊戚。又同聲言:‘無。”由此來看,這是一個不同于人界,而高于人界的地方,但是就此空間內故事內容的展演而言,自然還是依據朱生心意而動。
因此《畫壁》的嵌套藝術,就在于壁畫內外區隔了真幻世界的同時,又讓這兩個空間保持了真實的交流,空間得以交叉。現實的寺廟是實有;由真入幻的感覺、過程也是實有;壁畫內部的仙鄉式幻境亦有實存,以改變了發型的神女圖像為證。這固然有畫中人傳統的影響,但是若要證明壁內世界完全虛,應該反其道而行,為何刻意留有三人都能“共視”的證據?這樣的設置也透露了佛教的思想。壁內空間,是人心之幻,卻又都是真實存在。這種真一方面是有宗教極樂世界的需要;另一方面,是需要用“實”有來襯托虛無。
故事的最后,是:“朱驚拜老僧,而問其故。僧笑曰:‘幻由人生,貧道何能解。朱氣結而不揚,孟心駭而無主。即起,歷階而出。”而其實老僧沒有明確回答朱生的提問,只是說“幻由人生”,最后是由“異史氏”進行補充而點明主題的。老僧對“幻”的領悟,和朱生對“幻”的體驗是不同的。老僧之所以以“幻由人生”點化朱生,但老僧自己是更高層面上的覺悟者,對應著蒲松齡借“異史氏”之口,對眾生的教化。
朱生由心而起的幻境,只是在這樣的實存的空境當中,又由心創造了眾多因緣而和合存在的壁間世界,但這個世界的因緣依舊是剎那生滅。這和《寒月芙蕖》中,用仙界否定人界,繼而又否定了仙界,所展現出的虛幻的含義有所區別。兩者救贖的主題雖然一致的,救渡的對象和方法不同。就個人層面而言,有內向的心和外向的生活;同時又有相對個人而言的眾生,《畫壁》就是被籠罩在更龐大的救贖主題當中的。
五、儒家的戒色訓教:《閱微草堂筆記》的畫壁故事
《閱微草堂筆記》對應的是子部筆記小說的傳統,是離不開儒家的教化觀念的。《聊齋·畫壁》中天女是悟道,充滿佛教智慧的靈動形象,抒發了“身死神不喪、寓群形于大夢,實處有而同無,豈復有封于所愛,有系于所戀哉” [5] 的佛家色空觀念。但紀昀《閱微草堂筆記》中的畫壁故事就充滿血腥,有更明顯的民間的“畫中人”傳統,這種民間性的恐怖也許更利于教化人心。《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三《灤陽續錄》(五)二十六則,記載的畫壁故事,同樣的佛寺,懸掛了一幅美人畫,而非壁畫,這更貼合民間志怪中的“畫中人”。同樣有美一人,形容如生,又是同樣的天女散花圖。而士人和僧人的身份與他們的表現更加耐人尋味。
士人問僧人,美人畫難道不會干擾禪心;而僧人不是因為修煉到了“不動如山”的境界,只是因為沒有空細細地觀看。而有一天士人觀畫。這時畫中女想要到現實空間中,士人卻嫉惡如仇,想要將畫付之一炬。僧人聞聲而來,說起之前的弟子在此間生病死去,且可能所殺之人不止一個。間接說明僧人也是抵抗不住誘惑。整個故事都是由士人進行主導,并且要“除惡務盡”,僧人不但沒有成為點化者,反而受到士人的幫助。由此可見,紀昀對于士人身份的認同是遠高于科舉不中,半生潦倒的蒲松齡。
而從藝術特色來看,《聊齋·畫壁》中的女子形象始終美好,而非面目可憎的鬼怪,沒有令人敬畏乃至驚懼的感覺。同樣的神道設教立場,《聊齋》的點化更加生動,這是學界公認的。紀曉嵐筆下的狐鬼更多地是起著一種無形的監察作用,多義正言辭,威嚴龍鐘之態。這樣的書寫或許有類似佛家的怒目金剛的勸誡效果,但顯然,他處理真與幻的方式是將某一個特點放大到極致,如“西洋界畫”概念的提出。這表現出《閱微草堂筆記》有更嚴謹正統的筆記小說“資考證、廣見聞、寓勸懲”的特點。因為這種畫多用以表現造型嚴謹,結構精密的宮殿樓閣,亭臺廊榭等,甚至有立體的效果;由此可見,這種畫是淋漓盡致的真實表現。于是將整個畫中女人幻化進入佛寺禪房害人的故事表現得相當具有真實恐怖的效果。而且其對鬼怪故事的逼真描寫并沒有指向形而上的人生意義,反而透露出濃重的面向現實社會的趨向。
六、結語
中國小說中,往往呈現出以空間關聯和表現時間的趨勢,《聊齋志異》的壁間空間書寫也呈現這一特點。而這種仙鄉幻境,他界空間,由古小說中的神山、海洋與洲島等遙遠的神圣空間轉移到人世相關,隨處可見的壁間空間或者更加具有俗世意味的宗教場所,寺廟來展現。這與晚明以來思想的激蕩應該不無關系。而“壁上”空間的開發,有對中國古代遇仙以及仙鄉桃花源母題的繼承,一方面是六朝以來民間以及佛道畫像變異母題傳統展演的顯現。而對這些母題的繼承,更加豐富了蒲松齡塑造的他界空間的真假流轉的藝術表現能力,使其作品能夠承載更加豐富的思想內涵,更具詩性的表現張力。但這些創作風格還是為其神道設教的目的服務的,而一些篇章末尾的“異史氏曰”的存在更是鮮明地揭示了他這一目的性的存在。
由《聊齋志異》中類似《寒月芙蕖》和《畫壁》的壁間世界中,可看出蒲松齡對于他界空間的描繪藝術中表現了釋道的思想以及以儒家立場出發的教化意涵,與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相比,雖然文風不一,且思想不同,但都無法擺落儒家教化世人的立場。但因三教合一的影響,蒲松齡的《聊齋志異》記述鬼怪,亦運用了濃厚的宗教元素。這些思想的交織運用,都指向作者本人對于超越性思考的關懷。但《聊齋》對于天道是在信任與懷疑之間的,對于出世的理想亦然,所以在他的作品中的他界空間想象難免出現真假復雜交織的特色。同時在個人對于超越性的向往與否定的擺蕩的同時,他的教化立場讓他的教化表達對象也在個人與社會大眾之間搖擺。因而《聊齋》呈現出來的是“馳想天外,幻跡人間”的藝術特色,其敘事手法變化豐富,縱橫捭闔。他的敘事重點則落于凡人對仙境的向往與企求,卻又不止是“人生如夢”的旨趣。
當然蒲松齡《聊齋志異》他界空間的敘事藝術以及其背后三教思想十分復雜,此處僅以零星篇章來觀看他書寫藝術以及思想傾向的一隅。
參考文獻:
[1]李蕊芹,許勇強.借鑒與反思:《聊齋志異》與道藏仙傳關系論略[J].蒲松齡研究,2016,(2).
[2]蒲松齡.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M].張友鶴,輯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趙福生.Heterotopi:“差異地點”還是“異托邦”?——兼論福柯的空間權力思想[J].理論探
討,2010,(1).
[4]寧旭東.神話思維在早期中西文化中的留存及差異性研究[D]//中南民族大學文藝學碩士學
位論文.武漢,2007.
[5](梁)僧祐.弘明集(卷五)[M].北京:中華書局,2011.
(責任編輯:譚 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