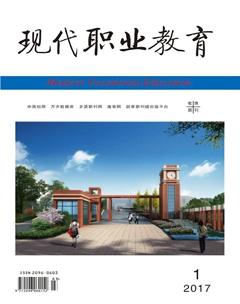簡論地方高校寫作課的“導”與“寫”
潘文峰 蘇潔梅
(廣西民族師范學院,廣西 崇左 532200)
[摘 要] “導”和“寫”,是高校寫作教學中的關鍵環節。寫作理論引導和啟發要敢于突破舊的模式,可選取經典文本、建構系列的案例,并把理論的講解融合在經典文本揣摩、分析中;“寫”則應據實情在“主體性”和“應世”模式之間找到最佳契合點,把“自主性”和壓力結合起來,讓寫作的工具性和人文性較好地融合起來。
[關 鍵 詞] 高校寫作課;理論引導;工具性;人文性
[中圖分類號] G642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 2096-0603(2017)03-0022-02
“導”和“寫”,是高校寫作教學中的關鍵環節。二十多年來,國內寫作界對“導”與“寫”做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相關專著和訓練體系層出不窮。福建師大林可夫教授建構的以寫作主體智能訓練為主的體系,上海大學李白堅教授的“快樂大作文”,福建師大潘新和教授“能寫、能講、能教”的“高等師范寫作三能教程”,信陽師范學院金長民教授建構的“現代寫作教學與寫實踐訓練”系統,廣西民大容本鎮教授的“寫作學可操作性訓練的研究與實踐”課題等都曾產生過積極的影響。不過,從目前地方高校寫作教學的整體狀況來看,“導”與“寫”之間的不協調仍相當普遍,主要表現在:講授者為“導”付出巨大的努力,而學者卻“受之不恭”,寫作課成了被嫌棄的雞肋。不僅是地方高校的寫作課面臨如此尷尬的處境,就是一些著名學府也在所難免。北京大學甚至長時間不開設寫作課程,“寫作”成了個體的自我修煉。對于地方高校寫作教學缺乏活力,難以得到學生的認可,一些論者認為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1)大學寫作課教材的理論陳舊,與中學寫作課教材在內容上重復較多,內容仍是“主題、材料、結構、語言、文章的起草與修改、標點符號”等傳統的“八大塊”,寫作訓練大都是基礎教育階段寫作課教學內容的機械重復。(2)理論與實踐脫節,課堂與生活脫節,教學形式化,部分大學生寫作才智被埋沒,學生的主體作用和創造精神并未得到充分發揮。可以說,以上兩點分析抓住了當前地方高校寫作教學的薄弱之處。
從教學規律來看,“導”與“寫”之間的對立矛盾會永遠存在。但如何更為有效地處理這一矛盾以期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
一
寫作課程中的“導”,主要是指教師啟發、引導和氛圍的創設。某種意義上,評價也屬于“導”的范疇。
在地方高校寫作課教學過程中,“導”仍非常關鍵。地方高校大多數學生的寫作素養比較一般,甚至部分學生筆下還出現“字不成句、句不成段、段不成章”及“應試”八股文的現象。這與《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提出的“寫作是認識世界、認識自我、進行創造性表述的過程。要學會對自然、社會和人生有自己的感受和思考。要以負責的態度陳述自己的看法,表達真情實感,培育科學理性精神”,仍有較大的差距。大學寫作課仍需對學生進一步加強引導和啟發。
當然,大學寫作課的引導、啟發和訓練,要敢于突破教材的束縛,并力戒重復中學寫作課的內容,把理論認識提升到新的高度。
理論包括了理念、思想、規律、原理、方法和技巧等。不得不承認:一個具備了良好的理論素養的寫作者,其眼光、思維、胸襟、視角、技巧等,會優于那些欠缺理論素養的人。藝術大師羅丹的論斷“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美的眼睛”,在文藝理論、美學界彌久恒香,早說明理論的重要性。這進一步說明,具備了良好的理論素養者,其創作更有后勁。
然而,本文所強調的“把理論認識提升到新的高度并落到實處”,并非要向學生灌輸高深的理論,而是要把理論的講解融合在經典文本揣摩、分析之中或通過經典案例分析上升為深切的理論體味。
理論乃寫作教學中的一個大難點,是因為其屬于抽象的范疇。然而,理論畢竟是從已有的創作實踐中探索、總結、歸納和提煉出來的。因而,在小說、詩歌、散文等方面選取經典文本,建構系列的案例供學生揣摩和研討,并最終上升為理論的認識,那么,學生對各類文體的寫作特征和技巧運用的認識勢必更為深切。選取經典文本建構系列的研討案列,與學生共揣摩和研討,可以獲得一石多鳥的效果。以小說為例,如沈從文《丈夫》在語言、人物心理變化與環境、視角的內在聯系、小說結尾留下的深長意蘊等方面可謂是短篇藝術典型的一個代表。換言之,語言、手法、視角、結構、意境或主題等要素以及這些要素之間的內在聯系往往在經典文本研讀中,經過學生的思考,再經過教師的點撥、總結,更容易形成總體的藝術感知,并可上升為對藝術規律和美學原則的把握。樂黛云教授回憶青年時代所上的寫作課時,曾說:“我最喜歡的課是沈從文先生的大一國文(兼寫作)和廢名先生的現代文學作品分析。沈先生用作范本的都是他自己喜歡的散文和短篇小說,從來不用別人選定的大一國文教材。他要求我們每兩周就要交一篇作文,長短不拘,題目則有時是一朵小花,有時是一陣微雨,有時是一片浮云。現在回想起來,這種類型的講課和聽課確實少有,它超乎于知識的授受,也超乎于一般人說的道德的‘熏陶,而是一種說不清楚的‘感應和‘共鳴。”
二
“寫”,即學生基本的寫作訓練和創作實踐。
以教師為主導的傳統教學和訓練模式存在很大的不足。在探索新的教學和訓練方式過程中,出現了兩種趨勢:一是遵循主體性原則,即尊重學生主體的自主性、審美性、創新精神,淡化文本目標,追求“無意為文”;另一個則強調“應世”(契合社會發展對人才的要求),分文體進行模塊訓練。
遵循主體性原則,講究“有為而作”——積累一定的生活經驗及生發較深刻的情感體驗,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寫作實踐。“有為而作”,實際上正是中國歷代眾多文人秉持的創作理念,如班固所講的“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白居易所說的“大凡人之感于事,則必動于情然后興于嗟嘆,發于吟詠而形于歌詩矣”等。圍繞確立主體“有為而作”的寫作實踐——力圖把課堂、生活與創寫緊密聯系在一起,一定程度上糾偏了早前的工具主義寫作,讓寫作課具有一定的活力、自由與美。然而,現實讓我們看到:圍繞“主體性原則”的教學實踐設計未免過于“理想化”。地方高校的生源大都來自鄉鎮中學,閱讀量偏少,見識窄,作文以應試為目的,而且中學階段幾乎過著與世隔絕的學習生活(學校實行封閉式管理),這使得學生寫作基礎不扎實,加之人本身的惰性和大學生涯短暫,因而圍繞“主體性原則”的教學實踐設計不利于整體提高學生的寫作水平。
而強調“應世”和模塊訓練,雖可讓學生了解各類文體的結構和特點,但在一定程度抑制了學生的創作激情。
筆者認為,應根據教學實際情況在“主體性”教學和“應世”模式之間找到最佳契合點,很好地把“自主”和壓力結合起來,創設良好的創作氛圍,讓寫作訓練貫穿學生的整個大學生涯。目前高校的基礎寫作課程設置基本上僅為一年(大都在大學一年級開設),課程結束后常規的寫作訓練也隨之結束。“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這話雖有一定的道理,但不符合當今社會對人才的要求。在電子媒介傳播時代,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生態等各個領域對人才都有素養方面的要求,寫作才能就是其中的一項重要指標。而對于地方高校而言,培養應用型人才是其主要任務。熟練各類文體的寫作,是文科生必備的一項基本技能。因此,寫作訓練應貫穿在大學四年的日常學習之中。
同時,我們也應看到:寫作是一門融中介和途徑為一體的課程,即其不僅是一種對技能的掌握,也是一種精神的創造(個體把自己的所聞、所見、所思、所學由內向外地轉化為一種表述)。當寫作邁向高層次便屬于一種創造性的思維活動,是對人生、社會的思索及進行藝術探索的過程,所以它既是一種獲得技能的途徑,也是形成較高綜合素質的過程。
目前,許多高校為創設良好的創作氛圍,激發學生的寫作積極性,進行了諸多的探討和實踐,如聘請作家入駐校講學,加強文學社團建設,改革課堂教學和課程成績評價標準等。這雖有利于寫作課程的建設和提高教學效果,但如著眼于提高整體學生的寫作水平而言,仍需更為有力的措施。筆者認為,除了按常規把寫作課設置為專業必修課外,還可把創作實訓列入校本課程,要求學生在四年學習生涯中按計劃較好地完成一定的創作任務,而這些創作任務是靈活和多元的,如讀書筆記、小型論文、社會調查報告、散文、小說、詩歌、新聞報道等等。這不僅有利于學生克服惰性和培養興趣愛好,又把讀書與實踐和對人生與社會的思考融入其中。
另外,在教學過程中應根據對象的能力和學習目的,結合課程總目標,明晰多層次的教學目標及這些層次之間的關系。多年來,授課者更為注重課程教學總目標的設置,或者依據教學總目標來開展教學和引導,而忽視了在教學過程中根據不同能力或不同興趣的群體來建構多層次的教學目標和具體的實施步驟。當不同能力和學習傾向的群體一旦明了近期和遠期的學習目標并獲得恰當的引導,會迸發出學習和訓練的熱情。
當寫作成為一種有效的學習和研究方式(技能和智慧相融合),成為一種深刻感知和把握世界的方式(讓人更用心地品味生活、反思人生與社會),也就把工具性和人文性完美地融合起來了。
參考文獻:
[1]李曉華,朱希祥.高校迫切需要開展對寫作實踐教學與效果的研究[J],應用寫作,2007(12).
[2]李曉華.高校寫作教師宜非專職化:北大中文系不開設寫作課思考之二[J].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04(2).
[3]王平.論大學寫作課的教學改革[J].教育理論與實踐, 2014(12).
[4]肖寧.大學寫作課程教學改革的思考[J].黃石教育學院學報,2000(2).
[5]樂黛云.四院·沙灘·未名湖:60年北大生涯1948-2008[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①本文系2016年度廣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學改革工程立項項目“導、寫、評一體化教學模式在高校寫作課中的實踐研究”(項目編號:2016JGA363)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潘文峰(1970—),男,廣西上林人,文學博士,廣西民族師范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地方文化研究。
蘇潔梅(1974—),女,廣西賓陽人,廣西民族師范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副教授、教育學碩士,主要從事語文課程與教學、教師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