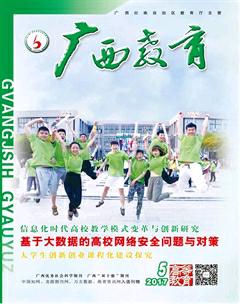人性的閃光 生命的體驗
【摘 要】本文通過對話劇《薩勒姆的女巫》背景、內容的基本介紹,引出該劇表演風格、臺詞風格和舞美設計三個方面的分析與評介,以此來提高觀眾對該話劇的理解與認識。
【關鍵詞】《薩勒姆的女巫》 人性 風格 自然 細膩
【中圖分類號】G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50-9889(2017)05C-0134-03
《薩勒姆的女巫》是由被譽為繼尤金·奧尼爾之后的美國最杰出的戲劇大師、著名的文化批評家之一的阿瑟·米勒創作的。《薩勒姆的女巫》創作于1953年,當時美國出現了恐怖的麥卡錫主義,自由和人權遭到踐踏。故事取材于美國建國前一個真實的案子“薩勒姆女巫案”:事情發生在1692年馬薩諸塞州的薩勒姆小鎮。以牧師薩繆爾·帕里斯(Samuel Parris)9歲的女兒和11歲的侄女突然痙攣,發出尖叫,渾身抽搐為開端。從馬薩諸塞州小鎮薩勒姆到整個埃塞克斯郡,再到周邊的米德爾塞克斯、塞弗科,開始了獵巫活動。從最開始,處于社會底層的奴隸、乞丐和窮人,發展到大量市民被審判、關押,人人自危,紛紛控訴身邊可能危及自身的人。最終1693年5月,以州長菲利普全面赦免被關押者而告終。此時已有19人被絞死,近200名服刑者,還有數人死在監獄里。
該劇內容如下:“魔鬼”造訪了薩勒姆小鎮,整個鎮子上充滿了嫉妒、污蔑、陷害和報復。很多無辜的人被送上絞刑架。牧師帕里斯的侄女艾比·蓋爾原是普洛克托家的女傭,因與普洛克托發生了不正當關系,被女主人伊麗莎白趕出了家門。她便利用指控女巫的機會誣陷伊麗莎白是女巫。普洛克托為拯救妻子的性命,說服了家中女仆瑪麗,來到法庭作證。在法庭的威逼下,關鍵時刻瑪麗卻推翻了自己的證詞,并反誣普洛克托是魔鬼代言人,普洛克托因此入獄。法官托馬斯誘逼普洛克托在懺悔書上簽字。在生與死之間,普洛克托終于撕毀了認罪書,選擇了絞架……
在談到創作《薩勒姆的女巫》的體會時,阿瑟·米勒說道:“如果《全是我的兒子》和《推銷員之死》所受到的褒獎使我感到這是一個充滿友好的世界的話,5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事件則使這種感覺一下子化為烏有……我吃驚地看到,那些多年的老相識從我身邊走過時連頭也不敢點,而且更使我震驚的是,我了解到存在于這些人中間的恐怖氣氛是有人蓄意策劃的,以致人們心里感到的盡是恐怖。”《薩勒姆的女巫》正是一場能使人心靈受到洗禮的社會悲劇。
云南藝術學院于麗紅老師(表演專業教授、學科創始人)、唐偉老師(云南話劇院,國家一級導演)指導的本科生畢業大戲《薩勒姆的女巫》,以自己獨到的藝術見解和較好的演技技藝,創造性地將大洋彼岸的藝術之花,成功地引種到中國的土地上,使之成為當地話劇舞臺上一出和諧生動統一完整、韻味無窮的藝術精品。此劇如此成功,筆者認為這和師生之間配合默契、辛勤勞動是分不開的。兩位老師以縝密的藝術構思、嚴謹的工作作風、通領全局的導演風范、各有千秋的教學方法,引領學生在一種團結、奮進、活潑、緊張的氣氛中將這一力作鮮活地呈現在觀眾眼前。本文從該劇的表演、臺詞、舞美三方面來闡述。
一、表演風格
(一)樸實、自然。《薩勒姆的女巫》講述的是小鎮上的故事,主要人物是村民們與法官、牧師。不像以往的戲劇,比如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宮廷味十足,講述貴族與貴族之間的糾紛;也不像羅伯特·托馬斯寫的《八個女人》描述著貴族與平民之間的紛爭。該劇沒有貴族們身上那種特有的氣息:虛偽和做作。演員們容易與角色相契合,像生活一樣去行動、去思考。
約翰·普洛克托是本劇的男主角,一個曾經犯下奸淫罪的農夫。在審巫案件發生之初面對邪惡,他也曾屈服、動搖過。但正直、善良的本性終于使他回到正義的一邊,捍衛自己做人的尊嚴,勇敢地面對死亡。
謝宇飾演的約翰·普洛克托對角色整體的認識還是把握得比較準確的。他牢牢地抓住了該角色是最明顯的特點:一個強壯的莊稼漢。既然是一個種地的農民,不可能飽讀經書,學富五車。在他與普特南的談話間,手中還在不停地削尖著用來種地的木棍。與黑爾牧師的對話中頓了一下斧頭并利索地握在手中等沒有一點做作之感。在戲劇表演中,一個人隨身攜帶、佩帶、使用什么樣的物件,常能夠表現這個人物的地位、身份以至所從事的職業。在這種樸實、自然的表演中,觀眾很容易感受到約翰·普洛克托在特定情境中的典型性格。
肖晶同學嬌飾演的蒂圖芭,筆者認為她較好地把握住了人物的特點。該角色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村婦,同樣也說明了她沒有多么高深的思想,沒有優雅的舉止,沒有甜美動人的嗓音,正是個無比樸實的女仆人。該角色的本質是一個善良忠誠的好人,但在艾比·蓋爾的誣陷、眾人的嚴刑逼供下使得她也不禁害怕、退縮,最后不得已站在邪惡的一邊。但她內心卻受著良心的指責、痛苦的煎熬。最終,她選擇離開這個充滿烏煙瘴氣的地方,走之前她邊借酒消愁,邊大聲喊:魔鬼啊,帶我回到我的家鄉巴巴圖斯,我的家鄉可沒有地獄……精彩之處就在于:肖晶嬌同學沒有故意去裝,去表演情緒、表演結果。能感覺得到演員是用真誠的心去體會該人物的復雜的內心情感,把“我”與角色合二為一、融為一體。否則為了痛苦而痛苦,這是非常可怕的。
張振宇同學飾演的詹理斯是一個60多歲的老頭,無論是在外形還是聲音上對他來說都是個極大的挑戰。但他還是努力克服了這一切,使得他被公認為塑造角色能力最強。例如:在第二幕中,詹理斯得知自己的老婆被人抓走了,他匆匆忙忙地來到約翰·普洛克托家,由于心里太著急,說話都吞吞吐吐,喘不上氣兒來。這時,不需要更多的行動和語言,觀眾們已經能體會到詹理斯對老伴深深的愛。良好的感知力使他的表演沒有一絲雕琢的痕跡,整體看來都比較流暢,把詹理斯這種身老而心不老、勇敢正直的倔老頭形象刻畫得令人久久難以忘懷。
(二)細膩、準確。劇中的女主角艾比·蓋爾在小的時候,親眼看見她父母的頭顱被印第安人砸碎在枕頭上。童年時期經歷的悲慘遭遇,使她的人格發生嚴重的扭曲。當她碰見人生中第一個男人,并且這個男人同樣給了她渴望已久且急需的溫暖時,結果可想而知:她強烈而執著的愛與她的占有欲,導致了她的自私和兇殘。特別是在艾比·蓋爾詛咒伊麗莎白的那一幕:她喝著雞血,而后把死去的動物往地上一扔,惡狠狠地說:“我要伊麗莎白死。”真是可怕到令人毛骨悚然。人性絕不是簡單的好與壞,人不會為壞而壞。劉嘉南同學飾演的艾比·蓋爾沒有一味地露出她兇殘的一面,這個女人也有柔情的一面,不過只是對約翰開放。這正是塑造該角色最艱辛的地方。給筆者觸動最深的是在第一幕中,劉嘉南同學把艾比·蓋爾的純情、癡情演繹得淋漓盡致。當她突然從背后深情的擁抱著心愛的人,說出的那段肺腑之言讓人不由覺得艾比·蓋爾并不是一個十惡不赦的女子,她只是愛約翰到了一種近乎癲狂的地步,其中透露出來的種種無奈和凄美之感都是通過演員細膩的表演呈現出來的。“我”不能否認她的愛,但是“我”也不能原諒艾比·蓋爾要別人付出生命作為代價來滿足她的愛。這與話劇《雷雨》中的蘩漪:交織者最殘忍的愛與最不忍的恨有著異曲同工之處。
另一位女主角是由劉佳同學扮演的伊麗莎白同樣使人印象深刻。該角色好像是為她量身定做的。首先,劉佳同學對此人物理解得非常透徹:伊麗莎白雖然對丈夫(約翰·普洛克托)與艾比·蓋爾有私情頗為不滿,但她還是深愛著丈夫(她為丈夫養育了三個孩子。為了保全丈夫的名聲,她在法庭被審中平生第一次說謊:否認普洛克托在外和別的女人通奸)。劉佳同學的外表好似天然的就有著一種高雅與莊重的氣質,十分吸引人。由此可見,指導老師在演員的選擇上獨具慧眼。在最后一幕中,她明知丈夫不簽字就會死,但她還是沒有去勸他,因為她一直相信丈夫是個好人,他的決定應該由他心目中的上帝來評判。在與丈夫訣別的時候,伊麗莎白輕撫著丈夫的臉,淚流滿面的與他深情相吻。這一刻,使得觀眾都禁不住淚濕衣襟。這正符合了作為演員應該具有的深刻、真摯的體驗,和細膩、生動的體現,達到內外的完美統一,才能調動觀眾的情緒并深深地打動著他們。
(三)節奏感強。優秀的演員在創作的整個過程中會根據角色的發展狀態和心理變化來調整表演方式。在對角色的性格展現上,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靠準確的戲劇節奏。在戲劇中,作為舞臺節奏,它的范圍要比音樂、美術等要廣泛豐富得多,因為它是時與空統一的藝術,是動和靜結合的藝術,是直觀性和過程性統一的藝術,是再現與表現的結合的藝術。戲劇中的人物性格豐富多彩,劇情發展相當復雜,內容涉及面比較寬廣,舞臺節奏也相應地更為復雜。蘇民導演曾說:戲劇節奏是舞臺藝術創作者把各方面的創作因素都完美的綜合起來,才獲得一個新的舞臺藝術的,既有整體又有局部的完美統一的結果。《薩勒姆的女巫》的節奏掌握比較到位。從序幕的艾比·蓋爾施巫術:把血淋淋動物仍向地上時就揪緊著觀眾的心。接著另一個興奮點就在眾人審問蒂圖芭時(大家有節奏的一個個圍繞著她):有的拿鞭子,有的說出惡毒的語言,有的用兇狠的目光逼向她。第二幕前期雖然表面上沒有什么大的沖突,其實人物內心節奏還是強烈的。直至后來的一個場景:普洛克托沖上去用手狠狠地抓住契佛的肩膀阻止他帶走妻子,此刻節奏非常緊湊。因為動作性也是節奏感的一部分,舞臺上沒有可有可無的形體動作和語言動作。在最后一幕的高潮中,普洛克托捏著認罪書大喊道:“因為那是我的名字,因為我這一輩子不會再有第二個名字了……我已經把靈魂交給你們,你們就把名字留給我吧。”在類似于這種沖突較激烈的情節中,演員們的肢體動作和舞臺語言都處理地較干凈,利索,既符合生活邏輯,又符合舞臺創作規律,從而加強了整部戲的節奏感。
二、臺詞風格
于麗紅老師特別注重臺詞的表現力。在排演中,老師不放過每一句甚至每一個詞的語音、語調、語氣、邏輯重音、情感色彩的細致處理,從而使該劇的臺詞也成為一個亮點。
(一)自然鮮明的口語化色彩。劇情雖然發生在1692年的美國,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地域,但至今觀眾看起來都容易理解并接受。這歸功于作品的現實主義風格,作者不是以論述或說教的方式敘事出來,而是通過人物形象化、細節化、生動化、故事化的語言展現出來。指導老師在排演中一再強調要說人話,用心去說話,也就是用貼近、接近生活中的人物語言,而不是去演、去刻意展現聲音的優美性。
(二)清晰悅耳。大部分演員的臺詞都能做到重音明確、抑揚頓挫、停連得當,使觀眾在觀看精彩表演的同時也能享受到圓潤飽滿、穿透力較強的聲音。但部分演員對于潛臺詞的掌握還有待加強。
(三)獨特的性格色彩。體驗派表演大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經斷言:“沒有性格特征的角色是不存在的”。德國哲學家黑格爾也曾說過:“演員應該滲透到藝術作品里整個人物性格中去,連同他的身體形狀、面貌、聲音等等都了然于心,它的任務就是把自己和所扮演的人物融合成一體。”這也就是說演員要突出角色的性格特征,不僅靠外貌和動作,臺詞也是塑造人物重要的手段之一。
該劇的臺詞很好地體現出人物的不同性格:
丹福斯總督:“在我們這個時代,是個邪惡分明的時代,無論是什么人?要么就和法庭站在一邊,要么就只能被認為是反對法庭,決沒有中間道路。感謝上帝,上帝啊!我們現在生活的這個世界已經不再邪惡和善良,混雜難辯了。”蘇杰用他那低沉、渾厚的男中音把一個妄自尊大、專橫武斷,自認為是上帝的代言者的丹福斯總督刻畫得栩栩如生。
呂蓓卡:“這是謊話,這是謊話,我怎么能詛咒我自己呢?我怎么能這樣欺騙自己。”“約翰,什么也不要害怕,另一次審判在等待著大家呢!”張玉臻通過壓低聲音,放慢說話的語速,很好地表現了一個心地善良、堅韌不拔、不向邪惡勢力低頭的呂蓓卡。
普特南太太:“噢!這真是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情,這一定是有魔鬼在和你搗亂。”“她能飛多高?她能飛多高?是魔鬼鉆到她們身體里去,臉上,背上,都鉆進去了都鉆進去了。肯定是的。”趙春燕通過故意拔高聲音、氣息上提、改變話語節奏的方式來調整音色,把該人物反復無常、神經兮兮的特點扮演得惟妙惟肖。
三、舞美設計
舞臺上的整體設計都運用了象征手法。臺上樹立著一根一根的大柱子,預示著人們被重重的謊言與陰謀包圍著。中間掛著一個大大的十字架,表明宗教勢力密不透風似的籠罩在薩勒姆鎮上。當總督對女孩子們說到她們一個個將被處以絞刑時,臺頂上突然降下幾根絞索繩,讓人觸目驚心,毛骨悚然,仿佛當年那種殘忍的刑法就將發生在眼前。主旋律的反復出現與舞臺燈光恰到好處的運用更加深了該劇的舞臺藝術魅力。
在演出當中,當臺頂的幾根絞索繩“倏地”降下來時,筆者覺得可以再放低點,使得投影在背景墻壁上的繩子正好處在墻上人影的脖子上。這樣更能凸顯統治者的暴烈和殘酷。在第一幕中,普洛克托說完這句話:“幫派?他說我們這兒有一個幫派?”節奏沒有把握好,走得太快,以至于普特南叫他的時候,演員已經在場下了,演員的提起預知反應會使觀眾瞬間跳戲。有個別演員的表演過于激動,顯得有點過火。不過,瑕不掩瑜,整體良好的演出效果,使得這些問題略顯得微不足道。筆者認為,這是在所難免的,畢竟是一場學生的演出,相信畢業后通過社會上的磨煉,他們會愈加優秀。
【參考文獻】
[1]Robert A.Mart in,ed.The Theater Essay s of Arthur Miller,New York:The Viking P ress,1978:153-154
[2]張仲年.戲劇導演[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3:7
[3]葉濤,張馬力.話劇表演藝術概論[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98
[4]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員自我修養:第二部[M].北京:藝術出版社,1956:54
[5]黑格爾.美學:第三卷下冊[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276
【作者簡介】唐衍歡,廣西師范學院新聞傳播學院,研究方向:播音與主持和戲劇表演。
(責編 黎 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