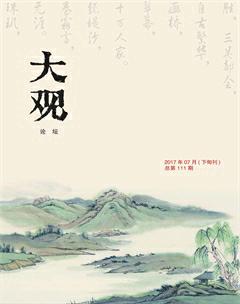“詩意的棲居”
摘要:現象學是關于現象的科學,是一種觀察世界的新方法與新思維。建筑現象學試圖以現象學來探究建筑的本質。建筑為人的生存提供居所,現象學指導建筑讓人生存的更加詩意。本文重在梳理現象學“場域“觀念與后現代主義建筑風格的關系,運用閱讀文獻資料與建筑圖片對比等方法,粗略探討人如何“詩意的棲居”。
關鍵詞:現象學;筑思潮;居住
一、簡述現象學中“場所”概念
現象學即關于現象的科學,探討西方哲學中個別與普遍,現象與本質的關系問題。目的是改變西方哲學的方法,即割裂現象與本質、客體與主體的思維方式。創始人胡塞爾強調在現象中直接把握本質,主張“讓事物回歸事物本身”。除了著名的懸置概念與意向性概念,“視域”概念對海德格爾以及后來的建筑提供更為直接的思想基礎,它意味著一種原本的可能性,每個經驗都有它自己的視域范圍,比如建筑師在設計住居時應考慮周圍的視域并順應其風格進行創作。
如果說胡塞爾在先驗現象學與發生現象學階段對建筑的影響較為微弱,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現象學為建筑提供主要思想來源。他在《筑·居·思》中闡釋棲居與筑造、存在的關系。人依憑筑造棲居于世界,這也是人存在與大地的方式,將筑造與存在相聯系。建筑不僅是人存在于世界的手段,建筑本身就是棲居,人居住即習慣于在大地上,某一環境中習慣的生存。將“天、地、神、人”同一于一體,所以運用于實際建筑中我們要考慮建筑與周圍環境的關系是否符合他所說的四重整體性。為之后的建筑理論家舒爾茨的“場所精神”提供重要思想來源。
挪威哲學家諾伯格·舒爾茨繼承并發展了海德格爾關于建筑與四重整體的關系,提出“場所(place)精神”概念。通過對于身體、知覺、感觸的關注,舒爾茨認為建筑應該關心人的心靈感受,而非僅僅注重客體自身忽略人的需要。他認為存在空間是生活空間的建筑化,建筑是存在空間的具體化形式。人居住與建筑物中,獲得安穩的生活方式與思維方式,即心理上對建筑物或場所精神的認同感與方向感。
此外,斯蒂文·霍爾的建筑現象學也在70年代風靡紐約,他比舒爾茨更注重知覺的力量,認為建筑與其所存在的特定場所經驗交織在一起,并影響到阿爾瓦·阿爾托、路易·康、貝聿銘等建筑家。
二、簡述西方現當代建筑流派
現代主義建筑在20世紀20年代伴隨現代主義思潮、藝術、文學逐漸興盛。20年代—50年代的建筑注重功能使用,以包豪斯為代表。工業化所帶來的機器美學崇拜、左派與保守派意識形態的斗爭、俄國構成主義為包豪斯提供堅實的政治后盾、荷蘭風格派繪畫中所體現出的幾何化、理性思維成為建筑師追求的目標。現代主義建筑具有六面體、材料裸露無裝飾、室內墻體的減少、功能性等特性,柯布西耶設計的“薩伏伊別墅”、“馬賽公寓”,格羅皮烏斯為德紹時期包豪斯設計的校舍都是其代表。功能主義建筑的高潮隨著格羅皮烏斯退出包豪斯學院告一段落,密斯接手包豪斯設計學院,整改政治風氣控制藝術設計的局面,追求藝術的純粹性,形成另一條道路—國際主義風格。二戰后,密斯在美國的極少主義影響廣泛,他的名言less is more和“玻璃盒子”觀念受經濟快速發展的美國社會推崇,代表現代化、大企業、大政府和權力。戰后美國所需要的不再是質樸實用甚至粗野風格的柯布西耶式建筑,而是典雅的、追求細節與形式美感的風格,如密斯設計的“范斯沃斯別墅”與1952年SOM設計所設計的立華大廈。
現代主義發展到1940年代,自身的弊端不斷暴露,建筑烏托邦理念的初衷無法達到。后現代主義建筑反對過分的功能主義與形式主義,抵制刻板的幾何外形,更加注重建筑的地域性與文化性,要體現為多元化風格,在同一所建筑中可以看到古典與現代及后現代的糅合,看到建筑物對自然的利用與順應,看到建筑師對人的心靈感受的關注。代建筑家如阿爾托·阿爾瓦、賴特、貝聿銘。
三、案例:建筑中的場所精神
在西方,自然總是被放在與文化對立的位置上來看待,因此建筑史也可被看作人類與自然進行斗爭的發展史。但在20世紀下半夜的后現代主義運動中,建筑與自然盡力達到和諧共生的關系。
弗蘭克·勞德埃·賴特所作建筑的獨特之處在于大膽的將其與自然結合,把自然的本性凸顯在建筑中,為人服務,進而發展成為有機建筑學原理,成為新地域主義建筑的代表,在意元素間的融合與延續性。他的有機建筑觀點比較明確的體現在芝加哥的“羅比住宅”、匹茲堡的“流水別墅”、“西塔里埃森建筑群”中。流水別墅追求形式的自由,把自然環境尤其是“流水”考慮在內,將別墅建于瀑布之上更有獨創性與共生性,這正是“場所”意義所體現的建筑與環境的“天人合一”。西塔里埃森的環境適合游牧民族的生存石塊、紅木與帆布的組合形成粗獷特性,賴特被沙漠的美、干凈的空氣以及山脈的幾何輪廓所大宋,他挑選不同形狀不同色彩的石塊,墻面顯現沙子涂抹的痕跡,使用巨大的天然紅木框架,帆布營造出光線交錯的室內,整個建筑群與山川交相輝映,從而形成與幽靜的“流水別墅”不同風格的建筑。
貝聿銘作為跨越現代與當代建筑風格的大師,其作品無法被歸為一個流派或者固定的模式,他自己對于標簽化的判斷不屑一顧,建筑中他并不過分強調建筑的風格問題,而在意建筑的嚴肅性與社會性。在盧浮宮廣場所設計的玻璃金字塔是典型的“密斯”風格,將玻璃與鋼材以及古代埃及的金字塔形式挪用進行古代與現代的組合,使得以古典藝術聞名的盧浮宮具有現代化韻味。但是在“文脈主義”一派中,貝聿銘于1982年設計的北京香山飯店是重要代表。雖然貝聿銘是堅定的現代主義者,卻并未因此而局限于現代主義風格。香山飯店兼容了現代建筑元素與中國傳統文化特色,比如白色的墻壁和窗子周邊仿木裝飾借鑒徽派建筑風格,墻壁下部的窗子顯而易見的借鑒蘇州園林,使得空間開闊并且借助自然形成藝術趣味,這在李漁的《閑情偶寄》一書中稱為“借景”,體現出貝聿銘對中國古代設計樣式的繼承與遵循。香山飯店已然成為展現中國精神的元素之一,它在設計時所考慮的環境、文化、政治性元素都是“場所精神”的再現。他所參與設計的蘇州博物館同樣是中國傳統與后現代建筑風格的融合。建筑結構體現出幾何形樣式,利用當地的園林、山石、樹木以及人們對于園林文化的理解,加之后現代流行玻璃、鋼架作為天頂框架,在外形上保持中國特色,細節處體現前衛與流行,這同樣是符合地域與文脈的場所精神。
四、結語
現代人在購買房子時,總會考慮到周圍的環境因素。比如愛清靜的學者會把樹木、花草、公園、學區作為參照物;上班族或者白領會考慮住房與公司之間的距離以及交通是否方便;老年人會選擇熱鬧的市區或者廣場附近等等,這些選擇都反映了建筑與環境、生理、心理等方面的關系,隱含的反映“場所”精神。由于現象學的引入,建筑設計開始由關注自身轉向關注人、關注環境、關注文化與歷史傳統等因素,為人類詩意的棲居提供一個落腳點。
作者簡介:劉娜娜,四川美術學院 美術學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美術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