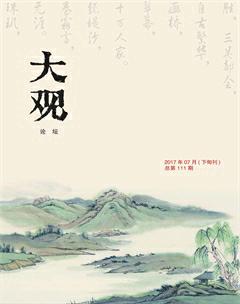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政體思想和治國原則之差異比較
古希臘的政治思想家對于政治學的一些基本問題比如政體的分類、理想國家的原則等進行了充分的討論和論證,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懷揣改造社會的熱忱,在政體思想和治國原則上構建美好藍圖,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政治學遺產。
一、政體思想之比較
柏拉圖在尋找心目中理想政體的時候,依據執政者的人數及每種政體的內在精神和原則,首先考察了存在于現實政治生活中四種不當的政體形式,即榮譽政體、寡頭政體、民主政體和僭主政體,四種政體內在原則分別是榮譽、財富、自由和專制,與柏拉圖心目中的理想政體大相徑庭,他認為最理想的政體形式應該是以法律輔之,推行“賢人政治”,即由“敏于學習、強于記憶、勇敢、大度”的哲學王掌握國家的最高權力,柏拉圖充分肯定了哲學王的地位,“除非哲學家成為我們這些國家的國王,或者我們目前稱為國王和統治者的那些人物,能嚴肅認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權力與聰明才智合而為一;那些得此失彼,不論兼有的庸庸碌碌之徒,必須排除出去,否則的話……對國家甚至我想對全人類都將禍害無窮,永無寧日。”這一政體思想體現了知識和權力的結合,但這里所指的知識是與“意見”相對的范疇,帶有神秘色彩,柏拉圖將國家權力的權杖賦予哲學王,其實質是維護奴隸主階級尤其是極少數壟斷知識的貴族的利益,反映了極少數奴隸主的要求。
亞里士多德首先給出了他對政體的定義:“一個城邦的職能組織,由以確定最高統治機構和政權的安排,也由以訂立城邦及其全體各分子所企求的目的。”這一定義帶有明顯的功能主義取向,也滲透在其劃分政體的標準中。依據政府的宗旨與目標即統治者照顧利益人數的多寡和掌握城邦最高治權的人數的多寡,亞里士多德細分出了六種政體,即君主政體,貴族整體,共和政體,僭主政體,寡頭政體和平民政體。亞里士多德認為眾人的智慧優于一人的智慧,“誰說應該讓一個個人來統治,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獸性的因素,雖最好的人們也未免有熱忱,這就往往在執政的時候引起偏向。”這一點與柏拉圖的賢人政體出現了分歧,顯然在對人的價值預設中,他是人性惡者,認為人的天性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即使是最優秀的人執政,也不可能全然不帶任何感情色彩和利益立場。由于共和政體旨在照顧城邦的公共利益以及在此政體的運行中,多數人掌握最高權力,因此亞里士多德認為在現實政治中最理想的政體是以中間階級為主體的共和政體,“就一個城邦各種成分的自然配合說,唯有以中產階級為基礎,才能組成最好的政體。中產階級比任何其它階級都較為穩定。他們既然不像窮人那樣希圖他人的財物,他們的資產也不像富人那么多得足以引起窮人的覬覦。既不對別人抱有任何陰謀,也不會自相殘害。”這一主張是其中道思想在政治哲學上的體現,中間階級作為中庸的化身,由其主政有利于抗衡極富和極貧階級兩股階級勢力,有如公正的天秤,防止政體的砝碼向僭主政體或平民政體的任何一端傾斜。
二、治國思想之比較
在治國思想上,柏拉圖以社會分工論為基礎,推崇由哲學王一人執政治理國家。在論證的邏輯中,柏拉圖首先對哲學家的內涵和品質做出了特殊的界定,認為只有哲學家才具有“知識”,這種“知識”源于對理念的把握,“他不會停留在意見所能達到的多樣的和個別事物上的,他會繼續追問…直至他心靈中…生出了理性和真理…”哲學家由于掌握了“知識”,因而能認識事物的本質,區分實在、本質和現象,保持清醒的頭腦。進而,哲學家能把握國家理念,知道如何治國理政,這一界定為哲學家治國提供了合理性。在具體執政過程中,國家在哲學家的治理下是朝著“劃一”的整體框架被治理的。一方面建立森嚴的等級制度,提倡在哲學家和軍人等級中廢除私產,實行共產制、公餐制,廢除家庭和婚姻制度,另一方面推行文化專制主義的教育制度,貶低法律的地位、主張由哲學家執政的人治。整個國家發展的軌跡朝著“整齊劃一”的方向發展,呈現出柏拉圖極端整體主義的思想。
基于共和政體的政體思想,亞里士多德在治國思想上放棄了柏拉圖過于純粹、過于理想化的治國理念,在城邦治理中強調法律的作用,反對柏拉圖以人治取代法治的思想,“法律失去其權威的地方,政體也就不復存在了。”在城邦的制度設計和政體選擇上,亞里士多德推崇民主政治,法律作為管理運作規則,為城邦的制度設計保駕護航。接著,亞里士多德對法治做出了明確的界定,“法治應包含兩重含義:已經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是制訂得良好的法律。”即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法治不單單只是存在法律,關鍵是在法治中應包含價值的考量,即存在的法律是良法,是得到普遍遵守的,好的法治是實行好的法制。此外,亞里士多德也看到了柏拉圖構建的理想社會分工制度的缺陷,“過度企求一致的結果…友誼猶如水那樣淡泊”,認為“賢人政體”下追求的終極劃一不但不能達到國家統一的預期,反而因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不分、利益范圍不明,最終導致城邦走向消亡。因此他提倡加以限制的“私有公用”私有制,即承認財產私有,但前提是保障它用于公共的目的,在整體主義的大框架中加入了個人主義的色彩。
三、結語
總體上說,柏拉圖的政體思想和治國原則傾向于理想化,對于社會階級的劃分,在等級森嚴的預設前提下,階級間存在堅不可摧的流動壁壘,基本上排除了流動的可能性。極端的集體主義與人的本性相違背,最終導致的是個人個性的泯滅,在此分工基礎上,賢人政體將權力束之高閣,集中在哲學家一人之手,哲學家被置于權力金字塔的頂端,其他各等級則完全被排斥在城邦權力體系之外,底層階級的意志一級級往上集中,統一到哲學家的意志中,形成一種精英政治。
不同于老師對理想城邦的規劃,亞里士多德將研究重心轉向對現實城邦的經驗和歷史性的描述與分析,在社會階級的劃分上,他務實地看到經濟結構和黨派力量的實際因素,在承認各階級存在界限的同時,提出階級間存在流動性,將道德倫理注入到城邦政治中,認為城邦存在的本質是追求善,因此其政治觀追求多元、自由、平等,亞氏還肯定了民主制和法治的作用,實行以中間階級為主體的共和政體,展現了超越柏拉圖思想的風采。
無論是柏拉圖的一元賢人政體觀還是亞里士多德的多元共和政體觀,實際上都有其時代的局限性,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都是為了維護奴隸主階級的利益,但是二者為古希臘的社會前景勾勒出了振奮人心的社會藍圖,為政治學的研究做出了獨特的貢獻,給后世留下了寶貴的遺產。
作者簡介:周瑩(1995-),女,漢族,廣東汕頭,華南師范大學在讀本科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