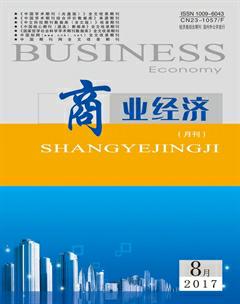農業企業社會責任層級模型研究
馬少華
[摘 要] 受農業企業產業特性的影響,農業企業社會責任行為被打上了“三農”的烙印,其社會責任層級結構區別于一般企業。根據資源基礎觀理論,構建了“倒金字塔”CSR層級模型,即第一層級為經濟責任與法律責任,第二層級為倫理慈善責任,第三層級為泛慈善責任,且倫理慈善責任與泛慈善責任呈現“差序格局”的特點。在面對多元利益相關者的目標和關系時,農業企業完全有可能通過推行CSR戰略獲得其合法性以及獲取某些發展資源的先機。
[關鍵詞] 社會責任;層級模型;農業企業
[中圖分類號] F27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6043(2017)08-0012-04
Abstract: Influenced by the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behavior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has been branded as three rural, and its social responsibility hierarchical structure is different from the ordinary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BV (Resource-Based View), the study builds the CSR hierarchy model of inverted pyramid. The first hierarchy is the economic and legal responsibility; the second hierarchy is ethical charity responsibility; the third hierarchy is general charity responsibility, and the last two hierarchies present differential pattern. Facing the goals and relationships of multiple stakeholders, it is entirely possible that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can obtain the legitimacy and development resources by means of CSR strategy.
Key words: social responsibility, hierarchy model,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一、農業企業社會責任的提出
為了生存和發展,作為經濟組織,農業企業無異于其它類型的企業,盈利是其主要目標。但是,由于目前國內大多數農業企業都發跡于農業,成長于農村,無論這些企業當前的狀態(規模、經營范圍、收入結構、國際化程度等)怎樣,都始終無法割裂與農業、農村和農民的天然聯系[1]。多數農業企業在享受一些額外權益(例如免稅、優惠信貸等)的同時也被賦予了更多的使命(如農業技術推廣、帶動農戶等),因此很難將農業企業定位為單純的經濟組織。受農業企業定位、農業產業及農產品特征的影響,農業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勢必會被打上“三農”的烙印。就此而言,農業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以下簡稱:CSR)的層級結構無疑區別于一般意義上的企業。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企業社會責任在不自覺中被公眾賦予了較多的期望和內容,而農業企業自身則存在著產業競爭力不強、對CSR認識不夠等問題。由此看來,研究農業企業獨特的社會責任層級模型并尋求在轉型經濟背景下農業企業的應對策略,已經成為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現實問題。鑒于此,在對現有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回顧的基礎上,本文以資源基礎觀等為理論依托,結合農業企業的特性,試圖構建農業企業社會責任層級模型,為后續論證企業社會責任是否具有層級性等命題研究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二、CSR層級模型文獻回顧
自1924年Sheldon提出CSR的概念以來,不同學者從不同的視角對CSR的內涵和外延進行了界定。目前,被廣泛接受和應用的是Carroll(1979)對CSR的定義。Carroll(1979)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在給定的時間內社會對組織所具有的經濟、法律、倫理、慈善方面期望的總和[2],據此Carroll(1991)將CSR劃分為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和慈善責任四個層次[3]。其中,經濟責任是最基本的責任,是企業履行其它三種責任的基礎,如果沒有經濟責任,其它責任則無從考慮。四種責任對于企業而言并不是無主次輕重之分的,不可等量齊觀,而是呈現一個“金字塔”層級結構(如圖1所示),從下往上依次是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和慈善責任,從第一層到第四層是按4:3:2:1的比例分布,呈現層層遞進的關系。Carroll的CSR“金字塔”層級模型是后來其它CSR層級模型發展和創新的基礎。
另一個具有代表性的CSR層級模型則是由美國商會(2004)提出,其對Carroll金字塔模型進行了拓展,提出了包含四個層級的CSR層級模型,其中,第一層次涵蓋了Carroll模型第一和第二層次的內容;第二層次涵蓋了Carroll模型的第三和第四層次的內容;第三層次的社會責任主要是要求企業要對社會需求變化具有前瞻性并做出反應;第四層次的社會責任是期望企業在建立企業社會表現的新標準上擔任領導者角色。
同樣,國內學者結合利益相關者理論,借鑒Carroll金字塔模型,也構建了CSR層級模型。黎友煥[4]構建了CSR三層次模型,其中把經濟責任和法規責任放在第一層次,倫理責任和自愿性慈善責任放在第二層次,但把倫理責任和自愿性慈善責任明確分開,把未來可能出現的責任或新出現但還沒有明確的責任定為“其它相關的責任”放在第三層次。陶曉紅和曹元坤[5]參照Carroll的金字塔模型,利用利益相關者理論,構建CSR層級模型,包括三個層次:一是基本社會責任即企業的必盡責任,包括對股東、員工負責;二是中級社會責任即企業的應盡責任,包括要對消費者負責,按時納稅,與社區關系融洽,有可持續發展的眼光,對環境負責;三是高級社會責任即企業的愿盡責任,包括主動承擔社會公益責任,積極進行慈善捐助。陳彥勛[6]按照責任內容的性質把企業社會責任劃分為不侵害責任和扶助支持責任二層級。其中,第一層級是不侵害責任,即企業負有不侵害利益相關者正當權利的責任,這一層包括法律責任和基本道德責任,針對利益相關者而言,是企業應當負有的基本責任;第二層級是扶助支持責任,這一層級包括高層次道德責任和企業慈善,高層次道德責任的履行對象仍然局限于利益相關者,企業慈善則針對更廣泛的對象;而企業的經濟經營行為處于社會責任范圍之外,作為層級模型的基底。
無論是Carroll的CSR“金字塔”層級模型、美國商會拓展了的四層次模型,還是國內學者改良的層級模型,都強調CSR包括多個維度和內容,且經濟責任是根本,是其它社會責任履行的基礎,沒有經濟責任的履行,一切都無從談起。然而Schwartz & Carroll[7]的實證研究指出實際上沒有任何一個層次的社會責任在CSR的概念中的作用是最基本的或者說是最重要的,它們絕大部分內容是相互獨立的,只有很少一部分有著并不明顯的聯系。
當前,關于CSR層級模型還存在較大的爭議,CSR各組成部分之間是否具有等級性還有待進一步的論證和探索。Cottrill認為不同行業的特點決定了行業間社會責任的重點不同,社會責任的研究應該更加注重特定行業[8]。現有的CSR層級模型是在把所有類型的企業放在同一層面上進行構建的,而沒有針對某一特定行業進行分析和探討。因此,從某一特定行業入手,構建CSR模型或許是論證CSR各部分等級性的一個切入點。
三、農業企業社會責任層級模型構建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業企業則是農業產業化經營的重要組織形式。作為在基礎性行業生存和發展的農業企業,是發揮農業基礎性支撐功能的有效載體;作為農產品的生產者或流通載體,農業企業扮演著“維穩者”的角色;作為農業產業化的主要運營者,是國家農村經濟政策貫徹實施的工具。結合我國農業企業的特性,基于對現有CSR內涵的思考,本文將農業企業社會責任定義為:農業企業社會責任指農業企業通過合法經營實現自身的經濟效益外,基于契約治理和關系治理,對債權人、政府、農民等利益相關者以及農村所必盡、應盡或是愿盡的責任。簡言之,農業企業社會責任是農業企業為實現農業產業化、促進農村發展以及帶動農戶增收而負有包括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和慈善責任等在內的一種綜合責任。
資源基礎觀(RBV)是現代戰略管理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主要觀點是企業控制的獨特資源乃是企業贏得持續競爭優勢的關鍵,這為企業建立、發展和維持競爭優勢提供了嶄新的視角。企業的要素投入包括影響企業和被企業生產經營影響的各種隱性、顯性和潛在的要素資源。企業的生產要素不僅包括傳統的財務資本、人力資本等顯性生產要素,還包括政策法律、知識與技術、顧客資源等隱性要素,以及社區環境、自然環境、人以外的其他生命物種與人類后代等潛在的要素[9]。Derichx & Cool指出企業內各種資產的整合是企業持續競爭優勢的關鍵,但是并非所有的要素都可在公開市場上交易,如產權未明確界定的資源、商譽、信任及高度專有性的資產等[10]。因此戰略資產由于時間壓力的非經濟性、資產累積的效率、資產存量協同性、資產消蝕性、原因不明等因素可以產生持續競爭優勢。顯然,無論是有形的資源抑或是無形的資源,對企業的成長壯大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Penrose認為,企業是建立在管理性框架內的各類資源的集合體,其功能則是“獲取和組織人力與非人力資源以贏利性地向市場提供產品或者服務”,“企業的成長則主要取決于能否更為有效地利用現有資源”[11]。Collis & Montgomery[12]也強調公司部分優勢是建立在公司所擁有的獨特資源及它在特定的競爭環境中配置這些資源的方式基礎之上的。農業企業為了取得長足的發展,必須獲得充分的資源并合理配置資源。
作為經濟組織,為了生存與發展,實現自身的盈利,是農業企業的主要目標。毋庸置疑,實現經濟責任是農業企業最基本的責任。然而,農業是一個弱質的產業,農業企業的生產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自然資源,受自然因素影響較大,具有生產周期性和季節性,資金周轉率較慢,其經濟效益相對較低。正是受農業企業的產業特性的影響,農業企業為了獲得競爭優勢,實現經濟目標必須獲得與其產業特性互補的戰略資源。企業是社會性的經濟組織,欲獲取戰略資源、實現持續競爭優勢的關鍵在于得到外部環境的認可,因此,合法性是企業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條件,是實現經濟目標的前提。韋伯認為合法性是指符合某些規則,法律只是其中一種比較特殊的規則,合法性的基礎可以是法律程序,也可以是一定的社會價值或共同體所沿襲的先例[13]。農業企業是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又一產物,其建立的初衷在于實現農業產業化經營,實現“保供給、保民生”的政策目標。農業企業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多數能夠享受政府的一些額外權益(例如免稅、優惠信貸以及財政支持等),獲得各種戰略資源,但前提是農業企業能夠遵紀守法,依法經營,即合法性。因此,農業企業只有在法律框架內實現經濟目標,即履行法律責任,才能獲得企業發展所需的外部資源(例如政府的扶持優惠政策、公共設施的建設)。由此,不難看出,對于農業企業而言,履行CSR的第一層級不僅要履行經濟責任,同時也要履行法律責任。經濟責任與法律責任并重,如果沒有經濟目標的追求,履行法律責任沒有意義;而沒有法律責任的履行,企業不具有合法存在的基礎和前提,無法獲得外部資源的支持,更談不上發展和盈利。農業企業的經濟責任和法律責任沒有先后順序之分,處于同一層級,是其基本的社會責任。
農業企業的發展需要各種不同資源要素的投入,包括土地、資本、勞動力和技術等生產要素資源,還包括社區和自然環境等外部資源。鄉村社會是一個資源載體,其資源非常豐富,既有自然資源,也有社會資源;既有有形資源,也有無形資源。農業企業除了對股東履行經濟責任獲得財務資本外,絕大多數的生產資源能夠通過社區和自然環境獲得,不但可以從農村獲得所需的生產資料(例如土地、初級農產品等),也能夠吸納農民成為股東或是員工。此外,社區居民也是農業企業產品的消費者或是潛在的消費者。農業企業發跡于農業,根植于農村,獲利于農民,與農村社區和農民保持著始終無法割裂的天然聯系。與城市比較,傳統文化對農村的滲透更嚴重,后者對市場感知和理解還有很大的局限性,因而更缺乏對規則的尊重[14]。這意味著,農業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內外環境與其他類型的企業比較可能存在較大的差異,為了能夠融入農村社區,獲取各種資源(例如土地資源、人力資源等),農業企業的經營和發展必須堅持社會道德標準和規范,遵循農村社區的價值觀念、信任結構以及慣例等,以贏得更加廣闊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同時,農業企業還應積極參與農村社區建設,如支持社區基礎設施的建設;積極參與社區的公益事業、慈善捐款等活動;保護環境,通過改進技術或是構建生態循環體系等消除環境污染等。
不可否認,農業企業對于農村及農民履行倫理和慈善責任,是為了獲得企業發展所需的各種資源,有形的抑或是無形的。同時,這也是農業企業與農村社區所構建的一種特殊的關系模式,是農業企業的產業特性與農村的鄉土文化融合的結果。我們的社會格局是一種“差序格局”,這種格局“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差序格局”存在于血緣和親緣關系中,也存在于地緣關系中[15]。同樣地,個體的差序格局被延伸到組織結構中。農業企業根植于農村的鄉土社會之中,其行為模式不可避免地受到鄉土特點的影響,鄉土社會的“差序格局”特點深刻地影響了農業企業的社會責任行為,其倫理責任和慈善責任呈“差序格局”局面,農業企業根植于農村,其生存和發展與農民息息相關,尤其是企業家與農村社區存在著傳統的血緣、親緣和地緣關系,將農村與農民視為企業的擴展。因此,無論是出于經濟利益的考慮或是鄉土情結的影響,農業企業將對農村履行倫理和慈善責任視為自身必盡和應盡的責任。隨著市場競爭的激烈及農業企業發展的進一步需要,農業企業逐步突破狹隘的“圈子里的人”限制的文化基因,為了實現從社會獲得更多的稀缺資源或是回饋社會的愿景,對社會履行倫理和社會責任。至此,依據資源的可得性及關系的親疏程度,農業企業形成了以農村社區為中心,并逐步向外層泛化,并形成社會層面的倫理慈善責任的“差序格局”。為了區分這兩種不同層級的倫理慈善責任,鑒于作用范圍和邊界較為多元和廣泛,將其對社會履行的倫理慈善責任稱為泛慈善責任。
綜上,農業企業社會責任的層級結構如圖2所示,農業企業履行CSR的層級模型從下往上依次是由經濟責任和法律責任構成的基本責任、倫理慈善責任以及泛慈善責任。為什么其結構呈“倒金字塔”呢?一方面,由于農業企業的定位及產業特性,三種責任對于農業企業獲得戰略資源贏得競爭優勢都是至關重要的,盡管并不是等量齊觀,但是對其進行輕重之分并沒有太大的意義。然而,三種責任的作用對象范圍則是逐漸擴大,從少數的主要利益相關者,到次要利益相關者,再到整個社會,農業企業社會責任的層級結構具有縱深性,呈類“差序格局”。另一方面,受鄉土社會“差序格局”的影響,農業企業的倫理慈善責任呈“差序格局”結構,以農村社區為中心的內圈層倫理慈善責任,逐步向外擴展,外圈層為泛慈善責任。顯然,農業企業社會責任的層級模型不同于Carroll的CSR“金字塔”層次模型,這是由農業企業特殊的產業性質所決定。
四、結論
關于CSR層級模型的研究是學術界討論的熱點問題,且存在較大的爭議,企業社會責任各組成部分之間是否具有等級性還有待進一步的論證和探索。不同行業的特點決定了行業間社會責任的重點不同,因此,從某一特定行業入手,構建CSR層級模型,以論證CSR各部分之間的等級性具有可行性。
發跡于農業、根植于農村、獲利于農民的農業企業,宏觀層面上受政府方針政策的影響,微觀層面上受農業企業的產業特點所制約,其發展所需的有形資源抑或是無形資源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農村和農民。在面對多元利益相關者的目標和關系時,農業企業完全有可能通過推行CSR戰略獲得其合法性以及獲取某些發展資源的先機[16]。根據資源基礎觀理論,結合農業企業的特殊地位及產業特性,構建了“倒金字塔”CSR層級模型,即第一層級為經濟責任與法律責任、第二層級為倫理慈善責任、第三層級為泛慈善責任,且倫理慈善責任與泛慈善責任呈現“差序格局”的特點。
[參考文獻]
[1]歐曉明,汪鳳桂.社會資本、非正式制度和農業企業發展:機制抑或路徑[J].改革,2011(10):116-125.
[2]Carroll A.B. A three-dimensional Conceptual Model of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79, 4(4): 497-505.
[3]Carroll A.B.The Pyramid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ward the Moral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al Stakeholder[J]. Business Horizons, 1991(4):39-48.
[4]The USA Chamber of Commerce Center for Corporate Citizenship and the Centre for Corporate Citizenship at Boston College. The State of Corporate Citizenship in the U.S: A View from inside 2003-2004[R]. Chestnut HillMA, 2004.
[5]黎友煥.企業社會責任理論[M].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10.
[6]陶曉紅,曹元坤.企業社會責任的層級理論及其應用[J].江西社會科學,2011(9):240-244.
[7]陳彥勛.企業社會責任層級劃分與提升策略[J].理論探索,2012(1):76-80.
[8]Cottrill M. 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Marketplace[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990, 9(9): 723-729.
[9]蘇蕊芯,仲偉周,劉尚鑫.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效率關聯性分析——以深市上市公司為例[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0,32(11):75-85.
[10]Derichx,I and Cool,K. Asset Stock Accumul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J].Management Science, 1989(35):1505.
[11]Penrose E. T. The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2]Collis D. J and Montgomery C. A. Competing on Resources: Strategy in the 1990s[J].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5, 73(4): 118-128.
[13]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61-67.
[14]姜廣東.非正式制度約束對農村經濟組織的影響[J].財經問題研究,2002(7):35-40.
[15]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16]Matthias, H. and Ludwig, T. Legitimating Business Activities Usi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there a Need for CSR in Agribusiness?
[17]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110th EAAE Seminar ‘System Dynamics and Innovation in Food Networks Innsbruck-Igis, Austria, 2008:175-187.
[18]Schwartz M. S. and Carroll A. B.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three-domain approach[J].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 2003, 13 (4): 503-530.
[責任編輯:高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