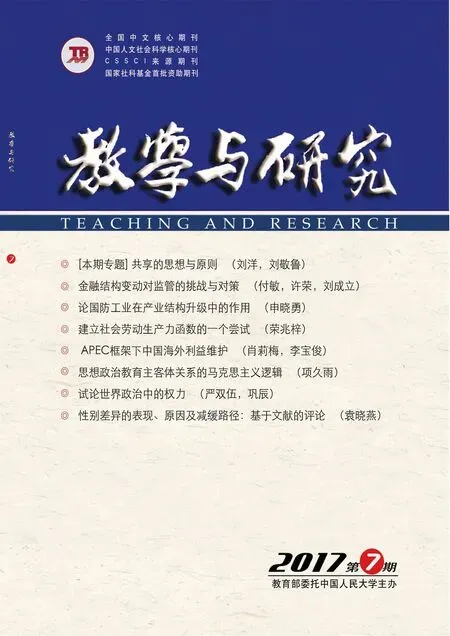試論世界政治中的權力
——基于馬克思主義和女性主義的比較分析
,
試論世界政治中的權力
——基于馬克思主義和女性主義的比較分析
嚴雙伍,鞏辰
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世界政治;政治權力
在世界政治情境中,對政治權力這一核心變量的重新解讀,并不能完全依靠已有的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來詮釋,已有研究揭示出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的目標,卻也框定了理論效度,即僅限于解讀國內政治,因而需要注入新的內涵。綜合運用馬克思主義和女性主義來考察世界政治中的權力,可能拓寬理論框架的運用范圍,有助于推動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同時,也可能有益于適應世界政治的現實發展,揭示政治權力運行的內在矛盾、基本規律和權力分布現狀等,從而也凸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持久生命力,既涉及性別政治,又觀照世界政治的現實發展。
引 言
馬克思主義理論,對諸如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結構、特定職業結構的產生以及居于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的本質等進行了全面分析,從而有助于我們深入剖析和全面理解資本主義社會的方方面面。而且,馬克思主義理論還嘗試對無產階級的生長和資產階級的滅亡進行科學預測。同時,馬克思主義也是一種社會分析和歷史(辯證唯物主義的)分析方法。那么,作為社會歷史中的難以規避的性別議題,自然也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不得不予以分析解答的重要領域。何況反而觀之,比如在資本主義社會當中,女性在經濟活動乃至家務勞動中的角色、作用等等,可以借助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概念進行深度剖析。
1789年開始的法國大革命是歐洲史乃至世界史上的里程碑,對歐洲社會經濟文化等帶來了巨大沖擊,女性主義(Feminism),或曰女權主義,也是受法國大革命影響而產生的一大社會思潮。女性主義的發展,意味著人類社會開始邁向一個旨在實現性別平等的新時代,顯然這一時代轉變意義堪比母系時代向父系時代的過渡,在轉變的過程中遭遇挑戰的,自然是曾視為“天經地義”的父權制;伴隨女性自身追求平等和權利的意識增強,女性主義運動不僅在實踐當中推進,而且還上升到理論建構的高度,拓寬了與女性相關的學術思考,在這一進程中出于對女性在社會各個領域的經歷、角色和利益進行考察的需要,并對性別壓迫和不平等根源進行追問,各種形式的女性主義理論應運而生*Mary Brabeck and Laura Brown, “Feminist Theory and Psychological Practice”, in Judith Worell and Norine Johnson, eds., Shaping the Future of Feminist Psychology: Edu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997, pp.15-35; 另參見鞏辰:《政治權力的反思與重構——基于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視角》,《太平洋學報》,2014年第5期。。女性主義標志著女性有意識研究自身的開端,作為一種社會思潮和社會運動,女性主義還嘗試探索解放自己的可能性和具體路徑。女性主義的核心議題在于討論性別不平等以及男性主導地位形成之起因。
那么,問題在于,如何既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又豐富有關性別議題的相關討論?不少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女性主義的重要性至多也仍無法超越階級分析,況且其局限性還可能分化工人階級。這種觀點希望將女性主義納入階級分析框架之下,而且馬克思主義對資本權力的精彩論析,也自然使女性主義的光芒相形失色,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仍有待發展的性別政治分析之重要性,也因之受到遮蔽。可見,在為我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行動指南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自身發展亦不應陷入“性別盲區”(sex-blind);反而觀之,女性主義分析路徑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和女性政治實踐發展可能面臨的困境,也一度源于唯物史觀的缺失。[1](P172)
顯然,在世界政治情境下,現有的研究不論馬克思主義還是女性主義,都有過多討論。但是,大多是在割裂二者的情形下所作的孤立分析。就理論共性來看,馬克思主義和女性主義的核心論述均圍繞著權力及其分配(不公平)而展開,何況(政治)權力也是世界政治的核心變量。馬克思主義和女性主義所共有的一大理論品性,在于二者都批判性地看待世界、斗爭矛頭都直指資本主義社會、都主張社會變革以改變不平等*參見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eds., Materialist Feminism: 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p.65-70; 秦美珠:《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思想歷程、理論特征及其意義》,《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評論》,2008年第1期。。可見,我們可以結合馬克思主義和女性主義來分析世界政治中的權力。
一、相關研究述評
誠如恩格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所言,“根據唯物主義,歷史的決定因素在于生產和再生產。一方面,對于生存所必需品的生產(包括食物、衣著、住所的生產以及生產這些必需品所用的工具);另一方面,人類自身的生產,即人類的繁衍。社會組織由人在特定歷史時期下的這兩種生產所決定。”[2](P71-72)也就是說,女性需要從家務勞動當中解放出來,即回到公共生活和勞動領域,并且消除資本主義的剝削(包括對男女雙方的剝削),實現真正的男女平等,如此才有可能實現女性的解放。
具體到“世界政治”,馬克思主義對世界政治的深刻論析,散見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經典作家對他們所處特定歷史時空的一些精彩論述之中,如馬克思的《十八世紀外交史內幕》、恩格斯的《俄國沙皇政府的對外政策》、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等經典文獻*參見馬克思:《十八世紀外交史內幕》,人民出版社,1979年;陳樂民:《歐洲與中國》,三聯書店,2014年;《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351-394頁,人民出版社,2009年;《列寧專題文集·論資本主義》,第97-213頁,人民出版社,2009年。。這些論著對18至19世紀,乃至20世紀的國際關系進行了外交史、政治學和經濟學上的綜合解讀,如今讀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大國行為的根源追蹤,理論與實踐分析緊密結合,其深刻洞見性相比所謂地緣政治理論和均勢理論等,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同時,與本文所選主題緊密相關的已有研究,還主要體現在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及其實踐上,這方面的國外研究汗牛充棟,國內研究也處在快速起步階段。比如,女性主義研究方面的國內權威——“北李南胡”,即北京外國語大學的李英桃教授和上海外國語大學的胡傳榮教授,兩位學者基本代表了女性主義研究方面的國內最高研究水準,在引介女性主義理論流派并將其嵌入世界政治研究視野方面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她們在對國別個案、區域問題乃至國際和平這一宏大主題的討論上,系統引介和運用了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并思考相關的女性政治活動與實踐,甚至嘗試在社會性別分析中切入中國視角*參見李英桃、林靜:《女性主義和平研究:思想淵源與和平構想》,《世界經濟與政治》,2009年第8期;李英桃:《及笄與志學——中國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研究》,《國際政治研究》,2011年第3期;李英桃:《婦女與外交:個人的即是外交的》,《國際觀察》,2013年第6期;李英桃:《和平進程中的非洲婦女安全——以布隆迪和利比里亞為例》,《國際安全研究》,2014年第3期;李英桃:《奧巴馬政府第一任期的“女權外交”評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5年第1期;李英桃、金岳嵠:《婦女、和平與安全議程——聯合國安理會第1325號決議的發展與執行》,《世界經濟與政治》,2016年第2期;李英桃:《婦女不提要求?——西方談判學中的社會性別議題》,《婦女研究論叢》,2016年第4期;李英桃主編:《女性主義國際關系學》,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李英桃:《女性主義和平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胡傳榮:《批評 拓展 改造——西方女權主義運動與婦女參政的發展》,《國際觀察》,1998年第6期;胡傳榮:《日益壯大的職業娘子軍——西方國家婦女的經濟活動》,《國際觀察》,1999年第4期;胡傳榮:《個體本位、現實主義與社會性別歧視》,《國際觀察》,2010年第6期;胡傳榮:《有關和平與性別政治的中國視角——評李英桃的〈女性主義和平學〉》,《國際觀察》,2012年第6期;胡傳榮:《全球經濟治理中的社會性別議題》,《國際觀察》,2013年第6期。。之所以必須首先肯定國內學界對女性主義理論的引介,主要是因為在某種理論(包括女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西學東漸”的過程中,諸如譯作、書評等的確為我們了解國外原創理論打開了一扇窗。隨后,國內學界往往可能有意或無意地開啟兩種理論研究進路:其一,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西方理論的既有框架來分析帶有“普適性”的議題,如女性參政議政、和平與安全等;其二,將西方理論付諸中國實踐,并努力構建本土的、中國化的理論。
近年來,與世界政治的變遷相同步,女性主義國際政治學也得到了進一步發展:一方面女性主義國際政治學似乎仍從屬于政治學,另一方面女性主義也位列有關全球化的跨學科敘事當中。可以說,興起于20世紀末對現實主義尤其理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批判浪潮,女性主義研究如今已開始呈現多樣化發展,包括不同的理論路徑、經驗分析和研究方法,并大致分流為三大領域,即女性主義安全研究、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女性主義全球治理。[3](P111-116)其中,以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為例,認為主流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國家與市場”互動以及公/私二元劃分忽略了女性所創造(如無償家務勞動)的價值,必須將性別議題納入全球化和發展研究,并重新思考國家、市場和社會之間的辯證關系。[4](P93-115)至于女性主義的中國本土化理論討論,則將性別視角引入社會主義文化/實踐的考察,形成了一些與女性主義理論反思色彩頗為貼近的學術共識:第一,作為以暴力革命為基礎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當代中國以其強大的社會動員力和組織力著稱,女性從來不是以自身的角色和身份被安置在革命序列中,婦女運動也從來不是以單純的婦女解放口號為唯一的目標,那么女性顯然是“依附于”且被整合進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實踐;第二,女性走出家庭而參加公共勞動,實際上仍然不過是國家的勞動力“蓄水池”或曰工具“征用”,女性的主體感和尊嚴感,是一種被建構之物,因而走向社會、走向公共空間仍然可能落入父權制陷阱;第三,“男女平等”與“婦女解放”顯然是兩個不同概念,并不能等同對待*相關代表作,參見左際平:《20世紀50年代的婦女解放和男女義務平等》,《社會》,2005年第1期;金一虹:《“鐵姑娘”再思考》,《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1期;董麗敏:《“歷史化”性別:以“十七年”中國婦女解放為場域的考察》,王玲珍、何成洲主編:《中國的性/性別:歷史差異》,第115-116頁,三聯書店,2016年。。也就是說,當代中國女性所遭遇的現實與文化困境似乎是一種邏輯的謬誤,一個頗為荒誕的怪圈與悖論:一個在五四以后艱難浮出歷史地表的性別,卻在她們終于和男人共同擁有了遼闊的天空和伸延的地平線之后,失落了其確認、表達或質疑自己性別的權利與可能;當她們作為解放的婦女而加入歷史進程的同時,其作為一個性別的群體卻再度悄然地失落于歷史的視域之外;中國女性主義理論的實踐介入,卻迥異于非社會主義國家,不是以男女平等而是以對性別差異的強調為開端,其直接的對話對象,無疑是建構在階級論基礎上的、否認性別差異的社會結構*對中國女性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深刻反思,參見戴錦華:《緒論:可見與不可見的女性》,《涉渡之舟:新時期中國女性寫作與女性文化》,第2-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戴錦華:《兩難之間或突圍可能?》,陳順馨、戴錦華選編:《婦女、民族與女性主義》,第34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
國內外相關研究仍構成本文的研究基礎。因此,需要在世界政治的性別話語中嵌入馬克思主義分析,以確保女性主義理論的科學性。同時,性別觀照也有利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豐富和發展。
二、政治權力、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
在復雜的世界政治情境當中,聯合馬克思主義和女性主義分析,可以為我們全面揭示復雜的世界政治圖景、認清世界政治的現實提供思想武器和理論工具。政治權力是世界政治的核心變量,對政治權力的一般界定往往受到西方政治哲學和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現實主義)的影響,因之帶有深刻的不平等、霸權和男權象征色彩。馬克思主義和女性主義,分別建立在對政治權力再認識的基礎上,并相應對政治權力的載體、目標和話語進行了深刻反思,進而重構政治權力的內涵、認知和目標。換言之,馬克思主義和女性主義對世界政治中的權力這一參考系的共同“解構”式反思,以及“破舊立新”式重構,為我們全面理解和認知世界政治現實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
然而,有關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的“聯姻”尚且存在爭議,爭論無非聚焦于“二者該不該聯合?”這一問題。一些女性主義者反對這種聯合,并把現有的“聯姻”(如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稱之為“不幸的聯姻”,認為所謂聯姻的依據是歷史唯物主義,這忽略了父權制對婦女的壓迫;“不幸”的表現在于“將婦女受壓迫看成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一種單純的補充”、“聯姻過程中存在程度不同的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性別化’改造的傾向(這可能在理論出發點或理論觀點上偏離甚至歪曲馬克思主義)”、“所進行的意識形態修補過程中參雜了不少后現代主義話語(這可能顛覆經典的唯物主義或在政治權力討論中淡化女性受迫害等問題)”*參見王宏維:《論西方馬克思主義在社會性別視域中的演進與拓展》,《馬克思主義研究》,2006年第8期;秦美珠:《女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婚姻幸福嗎?——關于西方女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結合的反思》,《學術交流》,2009年第4期。。于是,海迪·哈特曼(Heidi Hartmann)等學者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認為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仍忽略了性別歧視和性別壓迫的現實,因此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主張必須與階級分析相結合對父權制提出進一步的批判,并嘗試在公共領域討論性別分工問題,從而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這一點,感謝匿名評審專家的指導與啟發。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很大程度上正是由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衍生而來,且在20世紀80年代達到了一定的理論高度,相關代表作參見Heidi Hartmann,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 Capital & Class, Vol.3, No.2, 1979, pp.1-33; Heidi Hartmann and Ann Markusen, “Contemporary Marxist Theory and Practice: A Feminist Critiqu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12, No.2, 1980, pp.87-94; Nancy Fraser, Unruly Practices: Power, Discourse, and Gender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Nancy Fraser, “Talking about Needs: Interpretive Contests as Political Conflicts in Welfare-State Societies”, Ethics, Vol.99, No.2, 1989, pp.291-313; Iris Marion Young, “Polity and Group Difference: A Critique of the Ideal of Universal Citizenship”, Ethics, Vol.99, No.2, 1989, pp.250-274.。
無論是在政治學,還是國際關系學當中,政治權力(political power)*按照權力運行的形態及其結果而言,至少可以細分為政治權力、經濟權力、社會權力和文化權力等。然而,筆者以為,從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的共有理論邏輯,乃至世界政治這一敘事情境來看,政治權力較為典型,它既是經濟權力的集中表現,又是社會權力和文化權力等其他權力形態中的應有之義,同時也是影響世界政治變遷與發展的核心變量。因此,本文所討論的世界政治中的權力,一般專指政治權力(特別說明除外)。何況,政治權力本身其實就已基本涵蓋了權力的其他表現形態,如約瑟夫·奈(Joseph Nye)的“軟權力”論,參見Joseph Nye,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No.80, Autumn 1990, pp.153-171.有關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等的相互關系討論,參見Lester Salamon and John Siegfried, “Economic Power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The Impact of Industry Structure on Public Poli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71, No.3, 1977, pp.1026-1043; Marian Lee, Tammy Jorgensen Smith and Ryan Henry, “Power Politics: Advocacy to Activism in Social Justice Counseling”, Journal for Social Action in Counseling and Psychology, Vol.5, No.3, 2013, pp.70-90.始終都是一個出現頻度較高的重要概念,借助這一概念,不僅可以用于政治系統分析,而且還可能進一步助益于理解廣義上的政治學(比較政治、世界政治)命題。
1.政治權力的一般界定。
一般來說,倘若某個政治行為體具有讓其他行為體不得不服從自己的能力,這種能力就可以稱為政治權力,政治權力施動者的利益目標亦有望借助政治權力而得以實現。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Robert Dahl),抑或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他們的思維當中都傳達了一種這樣的信念,即權力有可能推動既定目標的實現,哪怕權力主體/載體追逐該目標時遭遇社會關系中的重重阻力*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translated by Ephraim Fischoff et al.,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53; Robert Dahl, “The Concept of Power”, Behavioral Science, Vol.2, No.3, 1957, pp.202-203.。應當承認,有關政治權力的界定,始終都面臨著爭議,但無論是在國際關系學、政治學、社會學還是其他社會科學領域,政治權力都不可或缺。
從詞源上不難發現,政治權力這一術語當中的核心詞匯是“權力”,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認為權力是一種控制關系(power-over relations),這種控制關系不僅指涉“控制”本身,還強調權力的鏈條或系統——如斗爭(struggles)、對抗(confrontations)、變革(transforms)、強化(strengthens)或逆轉(reverses)等“關系過程”方面的內容*“Afterword: The Subject and Power”, in Hubert Dreyfus and Paul Rabinow, eds.,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217;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An Introduction, translated by Robert Hurley, New York: Vintage, 1979, p.92.。其中,權力的“關系過程”似乎顯得更為重要,因為這種動態的過程往往再造/強化了權力結構本身,并使權力凸顯政治性。[5](P63)
或許出自理論抽象的需要,又或者源自各學科領域不同的研究偏好和假設前提,政治權力的概念和界定自然也眾說紛紜,其原有的經典的政治哲學意蘊和社會文化內涵,也總避免不了遭遇批判和質疑。如此一來,政治權力似乎也成了一個既“信手拈來”又“隨意填充”的模糊概念。不過,基本可以確定的是,政治權力的載體和施動者往往是國家,從而由國家所派生出來的政治權力思考,基本也足以滿足國內政治(政治權力的內向流動)和國際政治(政治權力的外向拓展)對政治權力的想象。本文從世界政治的寬廣情境考察政治權力,事實上也涵蓋了這兩大領域,即囊括了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相互交織、彼此互動的客觀事實,下文將重點討論的馬克思主義和女性主義,正是從各自理論邏輯和視角出發,對政治權力進行了深層剖析。
2.馬克思主義對政治權力的認識。
馬克思主義對政治權力的認識,深刻地揭示了政治權力的科學內涵、特性和構成要素。
有關政治權力的科學內涵,如果單純從經濟與政治的關系來看,政治權力對于經濟利益來說,只具有工具性意義,亦即政治權力旨在推動經濟利益的實現。考慮到政治權力主體與政治權力客體之間的關系,特別是剝削社會中階級對立,帶有剝削性質的政治權力往往以全社會的名義來行使,變成私有權力。
有關政治權力的特性,即使是在人類社會初始階段,政治權力都具有至高地位,使得個體的人不得不屈從于這種權力。到了階級社會,“每一個企圖取代舊統治階級的新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就是說,這在觀念上的表達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6](P552)而且,恩格斯還認識到了政治權力具有能動性,即政治權力對經濟發展可能具有推動作用或者阻礙作用,要么使得經濟發展實現飛速增長,要么損毀經濟本身。
根據馬克思主義尤其唯物史觀,不難理解政治權力的構成要素,客觀上應至少包括生產資料、物質財富、暴力、自然資源、地理條件、文化傳統和社會心理等方面。其中,權力的構成成分不僅包括人(如警察),還包括各種國家機關(如監獄)。
3.女性主義對政治權力的認識。
如前所述對政治權力的一般界定當中,強調了政治權力的“控制”色彩和“關系”過程。那么,對于女性主義而言,無論哪種流派,都將性別這一變量加入到對政治權力的考察當中,亦即性別與政治權力原有的屬性(如社會結構和權力關系)之間存在互構,并且賦予男性和女性的意義各不相同。[7](P47)在女性主義者看來,主流理論所強調的高級政治議題當中往往忽略了女性的作用,而就女性個體經歷而言甚至都能極大影響國家體系的運轉。[8](P265)
遺憾的是,高級政治中的核心議題,比如戰爭與沖突,其巨大的代價往往由女性來承擔,戰時波黑和剛果等地對婦女的迫害現象嚴重,更遑論常規戰爭90%傷亡數據都由婦女構成。[9](P2)鑒于此,主流理論所珍視的政治權力意義和價值,難免遭到女性主義的質疑和批判,政治權力應當意識到女性的重要性,而非固化男權價值,既然現有的所謂公共私人、國內國際等二元分類都是建立在男權價值基礎之上并通過政治權力來夯實,那么政治權力這一重要媒介就必須被解構,對政治權力的再認識和重新界定也相應提上議程。[10](P75-77)
我們知道,具體到國際關系學當中的經典和主流理論,則包括古典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代表人物分別是漢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和肯尼思·沃爾茲(Kenneth Waltz),二者的代表作分別是《國家間政治》和《國際政治理論》。而且,不論是摩根索還是沃爾茲,都將政治權力視為世界政治的核心變量(《國家間政治》的副標題甚至就是“權力斗爭與和平”),主要差別似乎僅在于究竟將權力視為國際行為的結果還是原因*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5th edn,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73, pp.69-82; Kenneth N.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p.109.。只不過,兩位現實主義大師所討論的政治權力其實仍為男性專屬,因為女性很難或者說很少能夠占有權力;至于“無政府狀態”這一看起來似乎極為“客觀”的前提假定,也不過是一種為父權制搖旗吶喊的怪誕托辭,從而以謊言的形式來維系男權制度和秩序*參見J.Ann Tickner, Gend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Achieving Global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37; Mary Daly, Gyn/Ecology, The Metaethics Radical Feminism, Boston: Beacon Press, 1978, pp.19-20.。
因此,需要對政治權力進行再認識,就馬克思主義和女性主義理論視角而言,主要體現在對政治權力的反思和重構這兩大方面:對政治權力的反思,為馬克思主義和女性主義提供了聯合契機;對政治權力的重構,則為馬克思主義和女性主義提供了聯合進路。換言之,正是建立在對政治權力進行反思與重構的共有批判性話語基礎上,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存在某種聯合的可能。而且,通過下文論證我們還將看到,這種聯合并非簡單地將兩種理論視角加以比較或“拼湊”,而是希望通過對政治權力這一世界政治中的核心變量進行再認識,豐富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議程,汲取女性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正能量,克服女性主義的不足,實現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的進一步發展。
三、馬克思主義和女性主義對政治權力的反思
1.馬克思主義對政治權力的反思。
馬克思主義對政治權力的反思,是以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來全面展開的,主要體現在政治權力的載體、目標、話語等方面。
首先,反思政治權力的載體。從歷史發展的邏輯演繹來看,政治權力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起初是以公共權力表現形式如氏族單位為載體的。進而,政治權力的載體由氏族發展到國家這一過程中,利益沖突和對抗無可避免,恩格斯認為,“國家是以一種與全體固定成員相脫離的特殊的公共權力為前提的……”;列寧也指出“如果沒有一種似乎駕于社會之上并一定程度脫離社會的‘權力’,它便無法存在”*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110頁,人民出版社,2009年;《列寧選集》,第2卷,第600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可見,就政治權力的載體而言,它與某種有組織的暴力緊密相關,而且這種權力的表現與關系過程總是難以避免充滿著沖突色彩。
其次,反思政治權力的目標。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這是政治權力的本質目標。可見,利益是政治權力的目標,為了實現統治階級的經濟利益,必須占有、控制和維系政權。鑒于此,不論是無產階級在與資產階級的斗爭中,還是馬列主義與機會主義的較量中,都應當努力“掌權”,才有望打破資產階級的統治、瓦解機會主義投機謀利的可能性。[11](P303)而且,在社會主義國家,政治權力的載體最終歸屬于人民,因為“歷史活動是群眾的活動,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6](P287)
再次,反思政治權力的話語。對于當時世界政治正處于歐洲革命的歷史背景而言,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于政治權力的反思,表現在對其剝削性的洞察上。如此一來,政治權力的逐利性決定了其捍衛的是統治階級的話語,包括意識形態工具、法律、政治思想等,無一例外是代表著主導地位的統治階級話語及利益訴求,而且政治權力話語的傳播仍是通過國家機器這一載體來實現的。
2.女性主義對政治權力的反思。
與馬克思主義對政治權力的反思相類似,女性主義對世界政治中的權力的反思,主要也體現在政治權力的載體、目標、話語等方面,通過對這些內容的批評,女性主義得以對政治權力進行再認識,并為政治權力的重構提供必要的觀念基礎。
首先,反思政治權力的載體——國家(the state)。因為政治權力的載體主要由國家來承擔,故而女性主義首先對國家這一載體進行了深刻反思,且認為自西方政治思想史對公私分離的討論以來,國家的道德標準和角色意義往往通過男性公民(citizen)的政治活動來加以實踐;女性的意義在國家的運行和公民身份政治過程中都被極度弱化、淡化,妻子和母親對于國家延續的重要意義也可能同樣被漠視;國家的政治行為當中也充滿著性別歧視,且還以立法和法律的形式,使帶有性別歧視的“既定事實”獲得合法性并加以延續。[12](P35-36)
其次,反思政治權力的目標。在女性主義看來,主流理論尤其現實主義所追逐的政治權力目標,往往過多強調軍事和安全,亦即政治哲學傳統有關政治權力界定的“控制”色彩。事實上,權力不僅表現為“控制”,還可能存在“共享”,而女性主義則對權力的共享更為看重,即強調全新的合作權力觀。[13](P246)就21世紀以來的世界政治現實而言,傳統的政治哲學和主流理論對政治權力目標的界定顯然已經無法詮釋轉變中的安全意義,如上提到的政治權力的載體即國家的身份其實也在經歷重塑。換言之,從理論發展及其現實實踐之間的聯系來看,政治權力的目標,尤其有關安全的意義評估,也的確需要依據轉變中的世界政治現實進行再思考。
再次,反思政治權力的話語。政治權力的運行和動態延續,往往離不開其話語基礎。一定程度上,正是關乎政治權力的話語和文本敘事,使得政治權力的關系結構和社會秩序得以延續。那么,從語言學上來看,現有的分類在女性主義看來都是具有明顯局限性的,因為其話語基礎往往指涉的都是男權價值或父權制意義,所謂的等級、霸權話語政治無非是加劇了性別不平等和壓迫。鑒于此,政治權力的話語,尤其性別間不平等的話語權狀況引發了來自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和精神分析女性主義等流派的激烈批評。[14](P5-6, 44-50)
通過比較分析不難發現,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對政治權力的載體、目標和話語進行了深刻反思。這其中的論證邏輯具有明顯的差異性,但也存在聯合契機。也就是說,結合馬克思主義和女性主義理論,可能為反思政治權力的內涵提供一個較為完整的分析思路,有助于我們全面理解和認知政治權力。
總起來看,結合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有望更為全面地認識政治權力的本質。如果說,女性主義為我們揭示了政治權力所帶有性別壓迫和偏見的話,那么馬克思主義則為我們更進一步分析這種壓迫和偏見所賴以存續的經濟社會根源提供了思想武器。就世界政治中的權力而言,需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對政治權力的深刻洞見,同時批判借鑒女性主義從性別話語上對政治權力所進行的反思,有助于我們全面理解當前變化中的世界政治及其權力現狀。
四、馬克思主義和女性主義對政治權力的重構
1.馬克思主義對政治權力的重構。
馬克思主義對政治權力的重構,從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出發,批判繼承了政治哲學傳統中的合理內核,并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權力論。
政治權力的內涵方面,馬克思主義認為,出于社會公共生活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公共權力應運而生,且這種公共權力本質上體現了社會公共意志;權力的價值追求應是為人民服務,權力為人民而存在;權力的價值取向,其重要表現在于對民主集中制原則的堅持;要努力實現權力與權利之間的平衡,就必須要以權利來限制權力,并通過保障公民權利的方式來實現。[15](P18-22)
有關政治權力的認知和目標,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尤其國家理論,較為強調政治權力的階級性和對抗性。而且,人類社會發展演繹自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以來,政治權力的這種為少數人統治所占有的工具色彩始終無以淡化,其目標自然也是維系剝削階級的利益。可見,政治權力的載體,即無論奴隸制國家、封建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無外乎都充當了剝削階級的統治工具。那么,作為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對于這些政治權力“劣根性”的克服,自然是希望通過包括社會變革和革命的手段,打破剝削階級的政治權力鏈條,瓦解剝削制度賴以維系的國家機器,從而構建真正意義上的、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服務的政治權力。換言之,無論是政治權力的內涵,還是政治權力的認知和目標,不在乎這種權力運行的方式路徑或曰手段的差異,而在于政治權力為誰所掌控、為誰服務。顯然,馬克思主義對政治權力的重構,具有時代發展和歷史進步意義。
為了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馬克思主義者提出了有別于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主義新型制度體系之構想,列寧為代表的布爾什維克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體系理論,進而,中國共產黨逐步建構的共產黨執政體系,形成了“權為民所賦、權為民所用、權為民所控”的馬克思主義政治權力。[16](P43-48)
2.女性主義對政治權力的重構。
基于前文所述對政治權力的反思,女性主義主要從資源、支配、授權等路徑嘗試對政治權力進行重構,并直接指向政治權力的內涵、認知和目標等。
表1古典現實主義政治權力vs.女性主義政治權力*資料來源: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pp.4-15; J.Ann Tickner, “Hans Morgenthau’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Realism: A Feminist Reformulation”,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17, No.3, 1988, pp.437-438.

古典現實主義政治權力女性主義政治權力政治的“客觀性”政治由客觀法則支配,而客觀法則根植于人性和自然狀態。政治權力現實主義之“客觀性”,是與男性所謂“男子氣概”相聯系的。以權力界定利益依照權力來定義的利益,將理性秩序注入政治的主體,使理論上的解釋因之成為可能,現實主義強調合理的、客觀的、不帶感情色彩的判斷。利益的界定,不能完全依照權力來定義,而應該是一個多層面且不斷因地因時而變化的概念。權力控制論依照權力來定義的利益是一種客觀的范疇,該利益范疇是普遍有效卻并非一成不變的定義,它把權力當成是人對人的控制。權力的統治和控制,體現了男性體能上的優勢,卻忽略了集體,而事實上權力可能與女性的再生產力相聯系。道德與政治一般的道德原則不適用于政治領域。政治行為必然有其道德后果,應當對政治權力的道德性給予更多的重視,因為這種道德有利于社會穩定和再生產。普遍道德法則依照權力定義的利益概念,保護人們不受道德干擾和政治愚昧的沖擊,某國的道德激勵不能等同于普遍的道德法則。某國的道德激勵不能等同于普遍的道德法則,但女性主義力求發現共同道德因素,以緩和國際沖突、構建國際共同體。政治的自主性政治現實主義保持政治領域的自主性,政治現實主義應建立在人性的多元主義概念基礎上,一個人(man)若僅僅是“政治人”(politicalman),則將是十分野蠻的,因為他完全沒有道德約束,為了建立有關政治行為的自主理論,必須將“政治人”從人性的其他方面抽象出來。政治的自主性被女性主義否定,因為所謂人性多元主義仍是一種片面的和男性的視角,排斥了女性的關切和貢獻,新的政治理論應重新評價和思考性別的影響及女性的作用。
其一,重構政治權力的內涵。女性主義對政治權力內涵的重構,與古典現實主義政治權力觀之間可謂“針鋒相對”,尤其對摩根索的政治現實主義六原則進行逐一批駁,從而在政治權力的內涵中體現女性政治地位和性別平等觀念,直接挑戰主流理論的政治權力觀(見表1)。這里,女性主義重構政治權力的內涵,有可能顛覆長久以來似乎“不言自明”的一個偏見/思維慣性,即認為相比男性,女性對“政治”并不感興趣——事實上,重構的“政治權力”內涵,說明女性和男性的政治議題關注范圍并不相同,但不能因此而武斷地下結論認為女性缺乏政治參與熱情。[17](P323-338)
其二,重構政治權力的認知。由于冷戰的終結,原有的歷史、啟蒙和正義的意義被放大,女性主義對政治權力認知的重構,體現在對“世界政治”的倡導和理解基礎之上,認為這樣的表述優于“國際政治”范疇,更能反映冷戰后以來的世界現實。[18](P181-182)而且,國際政治學之所謂經典的層次分析,即“人、國家、國際體系”這三大意象劃分在女性主義看來也是有缺陷的,顯然世界政治的現實認知并不局限于這些層次或單一層次。[19](P348-350)如果說世界政治研究正是建立在對權力非對稱關系的認知基礎上,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理論亦在此基礎上持久生長,那么必須承認這一“政治權力”傳統影響到了性別和女性主義研究的發展——畢竟從認識論上來講,男性和女性在身份、社會、文化、經濟和政治等各方面也存在著這種類似的“權力”非對稱關系;作為分析視角的女性主義,通過重構政治權力的認知,將諸如人的安全等容易被忽視的因素納入對外政策和決策考量,有望以更為審慎的態度面對世界政治現實。[20](P45-61)對于女性主義者而言,性別角色絕非世界政治的子集,而應當是本質所在,存在于世界政治的方方面面。換句話說,女性主義理論為我們拓展了研究視野,開啟了新的研究理路,并致力于影響人們的生活,或者反過來,為人們的生活所塑造。
其三,重構政治權力的目標。在女性主義看來,主流理論對政治權力的目標追逐往往以傳統安全為對象,這不符合當代世界經濟與政治的形勢發展。何況,非傳統安全風險抬升,例如環境問題,女性主義認為在這一非傳統安全領域不能無視女性的作用,否則全球環境治理的成效將大打折扣,因為“女性比男性更親近于自然”。[21](P118)需要指出的是,女性主義理論并非僅僅關注女性。事實上,男性同樣受到性別政治的影響,女性主義者時常將世界政治描繪為男性王國專屬領地,但必須承認這種領地通常僅為少數男性精英群體所掌控。而且,我們還應當嘗試著去了解,究竟世界政治的哪些領域和議題對某些群體(包括男性)存在歧視或敵意?例如,戰時的男性,不論他們是戰士還是平民,都極有可能淪為暴力攻擊的直接目標。[22](P83-103)可見,女性主義研究的最新進展,已經開始嘗試更為全面、包容地思考性別角色和世界政治議題,同時不少男性學者也加入到女性主義理論研究陣營當中,從事性別話語政治和女性主義研究*參見Kathy Ferguson, The Man Question: Visions of Subjectivity in Feminist The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Marysia Zalewski and Jane Parpart, “Introduction: Rethinking the Man Question”, in Jane Parpart and Marysia Zalewski, eds., Rethinking the Man Question: Sex, Gender and Viole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Zed Books, 2008, pp.1-20.男性學者研究世界政治女性主義的最新相關代表作,參見Terrell Carver, “Sex,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Jill Steans and Daniela Tepe-Belfrage, eds., Handbook on Gender in World Politic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6, pp.58-65; Paul Kirby and Marsha Henry, “Rethinking Masculinity and Practices of Violence in Conflict Settings”,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Vol.14, No.4, 2012, pp.445-449; Paul Kirby, “Refusing to be a Man?: Men’s Responsibility for War Rape and the Problem of Social Structures in Feminist and Gender Theory”, Men and Masculinities, Vol.16, No.1, 2012, pp.93-114; Paul Kirby, “How is Rape a Weapon of War? Femin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odes of Critical Explanation and the Study of Wartime Sexual Violenc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9, No.4, 2012, pp.797-821; Paul Kirby, “Ending Sexual Violence in Conflict: the Preventing Sexual Violence Initiative and Its Crit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1, No.3, 2015, pp.457-472; Paul Kirby, “Acting Time; or, The Abolitionist and the Feminist”,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Vol.17, No.3, 2015, pp.508-513; Paul Kirby and Laura Shepherd, “The Futures Past of the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Agenda”,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2, No.2, 2016, pp.373-392; Paul Kirby, “Gender”, in John Baylis, Steve Smith and Patricia Owens,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269-284.。
可見,重構政治權力,為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提供了某種聯合的具體路徑。在對政治權力的內涵、認知與目標等維度的共同解構與重構過程當中,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存在“共同語言”。不過,這種聯合,仍然需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方可能克服女性主義視角單純強調社會性別分析的局限性。換言之,世界政治的具體議題方面而言,女性主義可能為重構政治權力并導向更為公正的權力關系過程而提供性別視鏡,但在更為深遠和更具有歷史進步意義的角度來看,需要在比較政治和歷史等“國別”意義上進一步探索人的價值,這方面的路徑,只能通過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權力實踐(如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來實現。
五、結語和啟示
政治權力是某個政治行為體所具有的讓其他行為體不得不服從自己的能力。有關政治權力的界定,不論是西方政治哲學傳統,還是國際關系理論,都明顯帶有男權色彩和性別歧視。那么,馬克思主義和女性主義,反思政治權力的載體、目標和話語,重構政治權力的內涵、認知和目標,這種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對世界政治中的權力所進行的聯合考察,不妨稱之為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權力女性主義。通過綜合運用馬克思主義和女性主義理論,政治權力的本質(階級、歷史、性別意義)得以完整還原,如此一來,有助于我們全面地、審慎地理解和認知世界政治現實的復雜圖景。
此外,從政治權力的主體、目標、權力作用方式和權力分布等方面來看,世界政治的權力構成狀況發生了新變化。不僅提升了女性對政治權力的參與,非國家行為體的作用凸顯,因之也使得國際政治邁向世界政治——“超越威斯特伐利亞”的跡象成了冷戰后世界政治權力新常態。也就是說,女性非政府組織等非國家行為體,再加上其他如區域國家(這方面以超國家性的歐盟為典范)和全球公民社會等形式,這些都使得政治權力呈現多元化發展趨勢;政治權力目標的新變化,則體現在非傳統安全議題的重要性抬升,包括恐怖主義和氣候環境問題等等議題導向,這些可能與政治權力的傳統安全目標如軍事沖突和戰爭等等形成相互交織,從而使得政治權力的目標相應復雜化;政治權力的作用方式新變化,即作用方式由單一轉向多維——不僅包含硬權力,還涉及軟權力和巧實力;政治權力分布新變化,則明顯表現為權力的流散態勢,即這種權力分布不再如冷戰兩極集團政治對立那般主導人們的認知觀,而相反所謂“霸權更迭”、“霸權式微”、“霸權之后”等焦慮和聒噪,其實恰恰反映了權力分布一再處于動態的流散狀態中,可能不再局限于流向舊有的權力中心。
言而總之,世界政治的權力構成現狀,可以說是一種仍處于演化中的政治權力變化進程。在這種背景或曰敘事情境下的女性主義,具有應然意義(表達女性話語權)并取得了些許實然效果(以實踐推動社會性別平等)。馬克思主義和女性主義對政治權力的反思與重構,具有深遠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既對政治哲學和國際關系理論傳統構成了挑戰,又為我們邁向一個更為和平、公正和具有包容性的世界政治遠景提供了有益啟發。
[1] Heidi Hartmann.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A]. in Alison M. Jaggar, Paula S. Rothenberg (eds.). Feminist Frameworks: Alternative Theoretical Account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Women and Men[C].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78.
[2] Eleanor Burke Leacock. 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A]. in Frederick Engels.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C].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2.
[3] Elisabeth Prügl. Femin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J]. Politics & Gender, Vol.7, No.1, 2011.
[4] 曾怡仁,李政鴻. 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發展與挑戰[J].世界經濟與政治,2013,(1).
[5] Steven Lukes, Power: A Radical View,[M].London: Macmillan, 2005.
[6]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Jill Steans. Gend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Introduction[M].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8] J. Ann Tickner. Gender in World Politics[A]. in John Baylis, Steve Smith, Patricia Owens(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9] Cynthia Enloe. 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10] Huibin Amelia Chew. What’s Left? After “Imperial Feminist” Hijacking[A]. in Robin L. Riley, Chandra Talpade Mohanty, Minnie Bruce Pratt(eds.). Feminism and War: Confronting US Imperialism[C].London, New York: Zeb Books, 2008.
[11] 鄧小平文選[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2] 鞏辰. 政治權力的反思與重構——基于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視角[J].太平洋學報,2014,(5).
[13]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Contributions of a Feminist Standpoint[J]. 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18, No.2, 1989.
[14]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M].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9.
[15] 王建新. 馬克思主義權力文明思想論綱[J].社會科學家,2008,(10).
[16] 唐亞林. 馬克思主義權力觀:共產黨執政體系的制度基礎[J].探索與爭鳴,2010,(10).
[17] Hilde Coffé. Women Stay Local, Men Go National and Global? Gender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Interest[J]. Sex Roles, Vol.69, No.5, 2013.
[18] R. B. J. Walker. Gender and Critique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in V. Spike Peterson (ed.). Gendered States: Feminist (Re)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C].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1992.
[19] Jean B. Elshtain. Feminist Them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in James Der Derian (ed.). International Theory: Critical Investigations[C].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20] Mauricio Lascuarín Fernández and Luis Fernando Villafuerte Valdés.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Under A Feminist Approach[J]. Revista de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Estrategia y Seguridad, Vol.11, No.1, 2016.
[21] Lynda Birke. Women, Feminism and Biology: The Feminist Challenge[M].New York: Methuen, 1986.
[22] R. Charli Carpenter. Recognizing Gender-Based Violence Against Civilian Men and Boys in Conflict Situations[J]. Security Dialogue, Vol.37, No.1, 2006.
[責任編輯劉蔚然]
OnPowerinWorldPolitics——AComparativeStudyBasedonMarxismandFeminism
Yan Shuangwu, Gong Che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nd Maritime Right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Marxism; Feminism; world politics; political power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within world politics cannot be fully rest on Marxist Feminism which has its own destination and theoretical validity, and its limitation on interpreting domestic politics so as to input updating connotations. The comparative studies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could well be worth to investigate the power in world politics, meanwhile the theoretical frame could be broadened from which would be helpful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theory. Simultaneously, it would be good for adapting to the reality development of world politics, revealing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basic rules and current distributions of political power, etc. Therefore, the permanent validity of Marxism theory could be emerged, referring to not only gender politics but also the reality of world politics.
嚴雙伍,武漢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鞏辰,武漢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法學博士研究生(湖北 武漢 43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