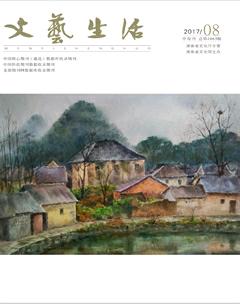從書法簡史中看三教融合
劉古雪
摘 要:書法是世界上所有繪畫類別中最為抽象的一門藝術,用抽象的線條表現造型,用形質表現氣韻,其中融合了太多無法言傳的審美精神內涵。而隨著社會、政治、經濟等大環境的變更,宗教在中國興起、發展,并相互融合,對文人書法的審美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本文欲以書法發展的線索為脈絡,在儒、道、釋三方面分別進行闡述,試分析其融合發展的過程。
關鍵詞:書法;審美;精神;宗教融合
中圖分類號:I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7)23-0222-01
隨著三教最初融合至唐、宋、元、明、清泛泛觀之。唐代開明政策背景下三教融合進一步鞏固,在此背景下,書法藝術審美精神促使其書法藝術發展至尚法的高峰。由于儒家傳統經世治時的思想影響,唐人崇尚嚴謹法度,但在此儒家影響基礎上,眾暑假兼修道、釋兩教,如顏真卿信封道教,并以此作為仕途受阻的精神寄托。其書如《麻姑仙壇記》亦有儒、道兩教氣息,既有儒之嚴謹又不失道家率真自由之趣。佛教同樣在此得以廣泛融合,眾士人開始一心向佛,且國家大興佛風,于此背景下大批士人出身的經生開始涌現,隨即誕生了獨具佛家色彩的書法藝術形式——抄經體。
至宋,三教中佛教的深入融合令人咂舌,由于佛教的涅槃境界則是截斷眾流,在剎那的靜觀中獲得智慧上的覺悟和清明——萬事萬物都是智慧觀照的對象,因此感物是為了超越感物向智慧心回歸。其通過即色即空,回歸澄明本心,自覺、覺他,最終達至覺行圓滿。蘇、黃、米三家作為時代驕子,突破唐人樊籬闖出一條“尚意”新路,而幫助他們達到自由的思想武器既是禪宗。
禪宗,作為佛教的一個派別,起源于唐中期,發展到宋代,已成為士大夫的宗教。這一方面是因為宋朝統治者出于政治需要,倡導儒、道、釋三教并舉,而已居佛主流的禪宗,為建立進一步適應社會的完備理論體系,也吸收了較多的儒、道思想,使禪宗成為三教合一的最佳樣板。而北宋“尚意”書風的三位倡導者皆受禪宗影響,即便是米芾如此狂人與晚年痛失愛子米有知后,精神蒙受打擊,方深覺“幻法有如是,不以禪悅,何以為譴”。正是禪宗獨特的吸引力,使得以蘇軾為代表的“尚意”書法理論中追求“無法之法”“不工之工”,主張“放筆一戲”“信手自然”,仍然貫徹著禪宗“直至人心”“凡性成佛”“平常心是道”等觀念。同時,“宋四家”中蘇、黃、米三人又皆以行草擅長,這種書體也向“尚意”書風提供了縱橫馳騁的用武之地。
而時至南宋,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是南宋占主導地位的思想體系。理學最可看作是儒家的禪學化,發揮了禪宗的心性之學,但他們主張“存天理。去人欲”,對藝術的觀點還是力圖把他納入儒家以道德為先的規范中去,儒學正是在理學的發展中于南宋書法藝術審美精神中回歸主導地位,因此品評是非取舍的標準到南宋已完全顛倒,而這種所謂標準一旦借助學術正統的官方力量傳播,并深入人心,如此一來,書法的藝術生命力也不言而喻。
理學主導下的書法藝術的沒落悲劇下,趙孟頫作為元代代表,他主張并著意追溯晉人,取晉人逸趣,他的書法以遒麗秀逸為基調,以清新脫俗、高雅出塵開啟了一代新風,將文人書法繼北宋蘇、黃、米之后向前發展了一大步。恰巧元代是宗教大發展時期,除儒、道、釋三教外,多教并行,其中因佛、道兩教在蒙古統一中起到重要作用,因此二教力量最強,影響最大,如此一發不可收拾。這種審美精神的變化還得力于一大批當朝佛家、道家書法家,如中鋒明本,其書雖學王羲之,然用筆尖起尖出似“柳葉”自成家數,其書風對當時日本書法同樣影響甚大。
明代董其昌一生以超越趙氏為目的,而董的意、法統一目標正是晉人的韻。觀董其昌一生在以二王為代表的文人流派書法傳統中扎根至深,并且董將禪宗的思想融入血液,形成獨特的談、秀、潤、韻的書法審美取向,用筆的虛和變化、結字和欹側反正、章法的疏空簡遠,用墨的濃淡相間,造成其書做白大于墨的視覺效果。用筆虛和而骨力內蘊,章法疏密而氣勢流宕,用墨淡潤而神韻反出,這種風格表現了禪意,所謂豐彩姿神、飄飄欲仙,這種風格反映了士大夫文人崇尚自然的率真之趣,即所謂書卷氣是也。
在儒、道、釋三教不斷融合并且于不同時期各占主導的相較中,碑學從帖學的反省和突破中生長出來,是書法藝術審美精神的又一次轉折,并且是書法藝術發展到新領域,并于清代風靡。高古、雄渾、壯偉、竣烈、沉郁、悲愴的碑學之所以能于清代茁壯成長,養潤、守護它,撥開它的正式儒家學說所陶養的士人之生命情調和人格氣象,而傅山正是明末清初碑學觀念的啟發者,對清代碑學建構產生直接深遠的影響。
也同樣因為儒學在明代的重大精神轉向——心學的崛起,使清代碑學形成獨特的精神氣象和審美選擇。心學強化了士人內心的道德信仰力量,激發出高亢豐沛的個體道德感情,同時也因其帶有宗教個人主義精神而極富個性色彩,表現出強烈的主體自由意識和特異才情。士人精神風骨之煥然直接誘發了審美理念和藝術形式的變遷。最重要的是清代儒學的內在傳統及變遷和經世致用傳統在清初的復歸、失落和潛移以及“道間學”傳統的復歸和興盛。這一切的一切便是使清代碑學得以發展,并且在此將儒學中傳統的“文”的一面發揮至巔峰和絕處。理論最終需服務于實踐,而實踐反哺于理論,二者相輔相承。若單修技法不習理論思考,或單空談理論不解技法,學生認為二者皆為無根之木,無源之水。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