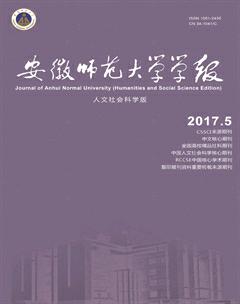關系理性:社會自主性生成的價值選擇及其實現
岳柏冰
摘 要:以國家和社會的關系為視角,反思個體理性導向下社會自主性的生成困惑,指出要以關系理性來引導社會自主性的生成。關系理性導向下的社會自主性在“治理身份的正確認知”“自治權力的科學詮釋”“治理的價值旨趣”等方面超越了個體理性思維,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治理觀的價值導向。關系理論導向下的社會自主性要在融合“國家與社會關系”“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個人與個人關系”的三個層次上逐步推進。
中圖分類號:D03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2435(2017)05056908
關鍵詞:個體理性;關系理性;社會自主性;治理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reflect on the confusion that arises during the generation of social autonomy, which is guided by individual rationality, and point out that its formation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relational rationality. Social autonomy guided by the relational rationality transcends the thinking misunderstanding of individual rationality in many respects, such as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identity of governance”, “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wer of autonomy” and “the value of governance”, and it accords with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cial autonomy guided by the relationship theory is to be gradually advanced in the three levels of integr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state and sociie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ch individual”.
一般而言,人們習慣于從“國家社會”二元關系中來理解社會自主性,并以社會自主性的生成來評價社會治理的意義所在。在這樣的言說語境中,“民主”“多中心”“善治”“主體”“權力”等話語總能凸顯出社會自主性的合理性,這的確是當代中國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應有之義。而當前盛行的“國家理性的狹隘性批判”“權力生產的線性思維”“治理系統的科學主義傾向”的思維,本質上是“個體理性”價值在社會治理中的運用。這種狹隘、排他性的主體性思維會將“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對立起來。“關系理性”導向的社會自主性則以“國家理性的正確認知”、“權力生產的單向度超越”以及“公共倫理的化育”為基礎,解決了個體理性的思維困境。以關系理性作為社會自主性發生的價值向導,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治理觀的價值要義,是我國實現社會治理現代化目標的必然選擇。
一、個體理性導向下的社會自主性思維及批判
“國家社會”關系是貫穿在社會治理實踐中的重要線索。事實上,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變遷對社會管理體制的存在形態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無論是國家控制社會模式、社會參與國家模式、國家社會合作模式、國家社會共生模式和社會自治模式,都涉及到“國家社會”關系的調整和變遷。在常規思維中,人們往往把國家和社會當作兩個獨立主體,并通過其結構關系特征來反思社會治理現代化問題。正如有學者提出的“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與國家特征,決定了中國國家與社會互動關系的主要議題與研究重點在于國家建設與社會發展,國家與社會組織、社區、基層自治、公民參與的關系,國家能力的強弱,社會組織的生存與發展策略等等”[1]。本文借助社會治理中“國家社會”關系來談論社會自主性這一問題。
社會自主性的實現是現代社會結構變遷、政府職能轉變的必然選擇,更是實現我國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它代表著“善治”理念的真正落實。社會自主性強調的是國家合理地對社會進行政治干預和行政管控,社會作為主體能夠進行自我管理、自我調控,在自治的過程中來實現其自主和獨立,即國家的制度安排所允許的社會組織自主性程度、社會主體能不受限制的表達自身的價值主張,“社會價值觀、自由結社、社團合作的成長,以及社會事件所呈現的社會動員和認同機制”[2],概要之,就是在政治社會學意義上,相對于“強國家”的社會有多少自主行動地空間。上述分析,我們會發現一個基本的脈絡——“國家社會”關系之于社會自主性實現的重要規定性。
什么是自主性?在規范性意義上,“自主”(autonomous)表現為“獨立自主”,不受他者控制。在古希臘城邦時期,“自主性”表現為城邦不受異邦干涉和統治,表現為“獨立自治”;近代以來,康德從“自我立法”的角度來倡導個體的自由,以此實現人真正的自主性。阿爾都塞曾以經濟對上層建筑的相對獨立性來論述國家獨立性,即國家相對于統治階級而言有一定的“自主性”。就現代意義而言,“自主性”意味著獨立、自治而不受管控和約束,它與主體性文化有著密切關系。
作為現代化進程中主體意識絕對化的產物,“個體理性”是指個體將自身實體化為絕對、單一“主體”,并將自身視為其他一切存在的最終依據,將一切外在于“自我”的他者都與“自我”對立起來、并由“我”來規定的個體化思維。在個體理性的倡導下,個體與他者的關系都基于“主客二分”的取向而體現為“對象性關系”“統治化關系”。而個體理性導向下的社會自主性,其本質就是將社會和國家視為互斥個體,并從“個體理性”出發來為社會發展進行自我立法,它強調社會發展的獨立性、自我決定性,反對國家對社會發展的干預和調節,試圖將“國家社會”關系割裂開來。其實,個體理性導向下社會自主性的思維誤區不僅僅存在于理論辨析中,它也存在于我國社會治理的現實進程中,其思維取向和認知邏輯主要體現為以下方面:endprint
1.治理身份的合法性論證——國家治理身份的排斥
反對和掙脫傳統觀念中普遍主義的價值模式,以“自我”作為價值規范的奠基,是現代個體理性的價值追求。以“社會”為個體來看,掙脫國家與社會混沌一體、國家凌駕于社會之上的現實,是個體理性導向下社會自主性實現的重要目標。而如何質疑并解構國家的合理性,進而“掙脫”國家的“管控”,這就需要對國家理性進行批判,當前盛行的批判論調主要體現為兩個層面:
其一,權力批判論調。主要強調國家自身的合理性僅僅局限于階級統治,即國家只是一種工具性存在。將國家理性僅僅看作是國家依靠政治技巧和技術進行對象化統治的過程,這種過程表現為一種純粹的權力沖動,正如有學者所言,“國家理性更多的是從國家權力的存續和效能的角度思考應以何種方式建構國家、實施統治……這與現代社會生活中社會單元主體化的要求顯然是背離的”[3]。可以看出,這種以權力批判來謀求社會自身治理主體的思維,儼然將政治生活狹隘地理解為違背道德規范的暴力行為,這顯然是不全面的。
其二,民主批判論調。從社會治理的“民主”價值出發,來批判國家權力行使中對民主價值的消解。正如有學者所說,在社會自主性實現的過程中,“通過合作、協調及對共同目標的確定等手段達致對公共事務的治理,這種治理方式就是民主化的治理”[4]。這種借社會自治過程中的民主價值來批判國家絆腳石形象的思維,其本質是以民主批判論來質疑國家治理權力。可以想象,如果以社會組織、團體、NGO等“少數民主”來質疑國家這一“多數民主”時,那么何種民主更具合理性呢?顯然,從形式上的民主來肯定社會自治的合理性,并以此質疑國家理性的思維必然會陷入民主悖論之中。
2.治理權力的獲得方案——權力生產的簡單化思維
“對象化”“統治化”的思維是個體理性的又一重要取向。對于社會而言,如何獲得自我治理、自我調適的權力,無疑是社會自主性實現過程中的必然邏輯。在這種對象化思維方式中,社會自主性的實現總是依靠權力獲取的實踐方案,即社會自治的權力生產主要取決于國家的實際放權。從現實來看,這種治理權獲取中的簡單化思維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其一,權力缺場的狹隘認知。這種論調承認權力生產對于社會自主性的意義所在,但僅僅將權力生產邏輯限定在國家和社會的狹隘關系層面,卻忽視了社會領域內部治理權力的自我生產,即權力生產場域的“社會”缺場。從現實來看,社會自治強調的是多中心治理,蘊含在多中心治理邏輯中的是多元價值觀,在這種價值觀背后可能會形成不同權力的此消彼長,這是權力生產的重要場域。治理權力的生成、落實、運行和實踐不僅僅在國家和社會相互空間中,社會內部場域的權力生產也是治理權生成的又一重要維度。所以,社會自主性的發生不僅僅是單向度地攫取國家權力,反思社會自身的權力生產更是一個重要方面。
其二,權力生成的簡單化邏輯。這種論調強調社會自治權力的獲得主要取決于國家的權力讓渡,總是將社會自治能力低下歸結于社會自治權的缺乏,即造成自治權缺乏的主要原因在于國家對于治理權的包攬和壟斷,使得社會缺乏自治權。正如有學者所說的:“在民主的旗幟下,可以冠冕堂皇的還權于民”[5]。于此,社會自主性實現的過程就是權力獲取的過程,對國家而言就是國家逐漸放棄權力的過程,進而言之,社會自主性中自治權的生成過程就是“讓渡權力”和“接受權力”的過程。這種簡單化的權力生產過程無疑是粗糙的,這種論調可能會產生以下價值導向,即在社會治理過程中,國家在任何時候都是強勢的,且將中國過去的社會治理結果完全歸結于國家權力作用的結果,而當前社會治理過程中“善治”的失落,國家是無可推脫的責任主體。另外,這種單向度的“權力轉移”思維,是否真正產生“無縫對接”的現實效應?這顯然沒有這么簡單。
3.治理邏輯的物本取向——系統化思維和工具性思維
擺脫“生活世界的統一性”、逃離同一性觀念,是個體理性又一重要價值訴求。從價值論的角度來看,隨著個體理性的確立,維系原有社會的“共同感”“倫理感”逐漸失落;取而代之的是“理性”“科學”“效率”“利益”等理念作為活動依據。基于此,個體理性導向下的社會自主性往往呈現出以下特征:
其一,“系統”性思維來指導社會自主性產生。這種論調將社會看作是一個系統,企圖依靠系統自身的調節來實現社會自主性,如“優化社會治理系統”“健全信息反映系統”“打造治理的信息系統”等各種關于治理系統的構建。政治行為主義的倡導者戴維·伊斯頓曾有過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他將政治生活的運行過程理解為系統本身的運行,并從系統與外部世界的互動、刺激、反應過程來闡述如何提高政治生活系統的穩定性和科學性。自從后帕森斯時代的到來,“系統論”的批判也是不絕于耳。就社會自主性而言,“系統論”導向僅僅依靠科學知識、治理技術、成本收益等指標來搭建一個“物本的”“科學主義”的信息系統,它僅僅將社會運轉理解為簡單化、抽象化、物質化的自然邏輯。以“效率”“理性”“科學”等思維來選擇治理方案和評價治理效果,它可能忽視治理中的“人本性”“公正性”等價值要義,也會因功利主義思想而阻礙社會自主性的產生。
其二,社會自主性實現中的“工具性”傾向。如何調動廣大人民參與到社會治理中,形成組織化、有序化、科學化的自治組織,這當然是社會自主性產生的核心。而當前所流行的“利益共存”“風險承擔”等思維僅僅以功利視角來闡釋參與治理的必要性,將治理僅僅理解為化解風險的手段,它忽視了個體間既定“情感”“文化淵源”等共同體情感。可以說,廣大民眾在國家認同基礎上所產生的“我們感”“共同感”都是社會參與的最重要情感支撐。所以,僅僅以科學主義思想來闡釋社會自主性的必要性是不夠的。
二、關系理性導向下社會自主性的現實主張及超越之境
近年來的研究證明,基于“國家社會”關系對立的思維前提來解決社會自主性問題,是存在弊端的,如“市民社會”“法團主義”等理論缺陷就是直接體現。西方社會治理理論基于“國家社會”二分假設是否符合中國實際,即“國家”和“社會”在中國現實生活中是真正彼此獨立嗎?顯然,這一客觀現實是我們解決社會自主性問題前提條件。endprint
從理論上看,近代西方社會科學“國家回歸”理論也是說明“國家社會”的絕對劃分是難以實現的。米格戴爾指出,國家的邊界并非高度統一,而是“破碎的”“缺少協調性”的,國家與家庭、宗族、政黨、跨國公司等組織即沖突又重疊,他認為“國家處在社會中”[6]16,二者并非完全互相獨立;雷米克基于中國地方政權的現實指出,中國各個階層的“地方性政權”,在制度實踐中“把既定政治制度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視為一個統一體”[7]5-6;亞歷山大也指出“國家與社會”范疇中的 “社會”在現實中是多元和復雜的"[8]19,我國學者也從“制度生活” “過程事件” “多元話語分析”[9]等范式說明來中國現實生活中“國家社會”并非是完全分離,而是相互交融、互相作用的。
可以說,當代中國社會自主性的實現并非基于“國家社會”二分的前提,而是在“黨的領導下,多元治理主體共同發展”為前提下互相影響、互相嵌入的實踐邏輯,即“關系理性”就價值層面來看,與關系理性對應的是公共理性,其核心理念是:在承認主體地位的前提下,注重公共生活中價值主體之間的平等性、互惠性與合作性,認可反思價值的基礎上的交流與批判機制,公共理性實際功效也指向來現代社會主體性難題。然而,作為一種理論倡導,無論是康德還是羅爾斯意義上的公共理性,其適用的前提是現實多元主體之間相互分離的客觀現實,即主體間存在鮮明的分界線,其實踐徑路是“從分離到融合”。就中國“國家社會”關系的現實來看,其二者關系現實并非互相分離,而是相互交融的。基于此,本文選用“關系理性”而非“公共理性”。
導向下社會自主性的實現邏輯。“關系理性”是以超越原子化個體、實體化思維為前提,在保留“個體理性”積極效應的基礎上,注重從關系維度來理解個體生存意義、存在依據和生活模式的理性。賀來認為“關系理性”主要表現為兩種旨趣,即“從交互性關系來理解個體存在的意義、從互依性關系理解個體生存條件”[10]。從價值論上看,“關系理性”是以對他者自由人格的承認和尊重出發,以此來構建“共同感”“共在性”“相互性”等普遍價值觀。關系理性導向下的社會自主性拆除了“國家”與“社會”二元對立的藩籬,它倡導國家與社會不可分離的依賴關系,并把社會主義“社會”自身的建設與“國家”聯系起來。與個體理性導向下的社會自主性相比,關系理性導向下的社會自主性體現了“社會”發展的價值自覺。以關系理性為導向來推動社會自主性的產生,這絕非是一種理論假設,它更貫穿于中國社會治理的現實過程中,是融合國家和社會關系的價值準則,更契合了當代中國社會治理的現實。
1.治理身份的正確認知——以國家之于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為前提
“社會”這一治理身份的回歸與重構是社會自主性產生的前提。與個體理性導向下治理身份的解釋邏輯不同,關系理性導向下的社會治理身份重構,絕非是以排斥“國家”治理身份為基礎的,相反,這種治理邏輯能客觀認知、承認國家理性在社會自治中的合理之處,并在國家與社會優勢互補的現實中增強社會自治能力。
在個體理性導向下,社會總是從國家理性的“邪惡”面相來質疑國家治理的合法性。馬克思在論證國家屬性時,不僅僅揭示了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也強調了國家的社會服務職能,即國家的“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在一切要由許多人彼此協作才能完成的工作中,都必須出現對管理的要求,靠它的幫助,社會生產活動和其它活動才能達到一定的統一”[11]532。邁內克也講到,國家理性總是徘徊于政治與道德之間的二元張力中,即“二元性的行為原則”,他強調了國家理性中的“價值王國”意涵,他說“權力(Kratos)和道德 (Ethos) 一起建造國家,塑造歷史”[12]55。可以看出,國家理性表現為服務社會和政治統治兩個方面。而就社會自主性的產生而言,不僅僅要杜絕和防范“統治權力”泛化而引起的理性偏執,也要承認并依靠國家在服務、引導社會自治中的重要職能。
也有學者提出,國家的善治理念更新了傳統“國家理性”的知識。在傳統思維中,主要存在兩種知識方案,即經由廣大人民同意的民主、符合公平原則的民主,而上述“同意型民主”和“公平型民主”[13]自身的理論困境也昭示出對國家理性的理解必須在知識上有所更新。于此,以國家在治理中的“善治”來更新國家理性的知識話語,也是關系理性的必然產物。國家理性的“善治”之維,再現了國家在人權保障、依法治理、提高效率、追求正義的“善治”效應。所以,正確看待國家理性、更新國家理性的知識話語,在承認、接受國家治理權的基礎上才能真正實現社會自主性。
2.自治權力的科學闡釋:簡單化思維的超越
社會如何獲得“自治”權力,并鞏固其自治權,這是社會自主性產生的又一重要方面。關系理性導向的社會自主性始終會以國家和社會的關系來應對自治權力的再生產問題,它將考察權力再生產的場域拉回到社會場域本身。這種權力再生產的邏輯表現出兩種規范性要求:既滿足關系理性下權力的生產邏輯,又要確保個體理性下社會自治權的規范和鞏固。所以,按照上述兩種規范性要求,關系理性導向下社會自治權力的生產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其一,承認社會自身固有的治理權力,還原自治權在社會場域中再生產的邏輯脈絡。這種理念下的權力生產邏輯能打破長期以來的錯誤思維,即社會自治權力的再生產完全在于國家治理權力的讓渡,社會權力的再生產被簡單化為“讓渡獲取”方案。顯然,承認社會自身固有的治理權力,能使我們認知到社會自治權力再生產脈絡也存在于社會場域自身。事實上,基于歷史原因而存在的地方自治力量就能證明這一點,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其實說明了社會自身的固有權力正不斷消解、阻礙了國家的權力行使。正如有學者所說的“內生性制度”“適應性非正式制度”描述的就是社會自身權力運作的現實。所以,社會自主性不應該忽視社會自身所固有的權力。
其二,社會自治權的規范化行使,鞏固了權力生產邏輯。在微觀層面,社會自治權往往以“合情性”來取代“合理性”,比如在諸多場合,個人、社會團體會使用“情感共鳴”“惻隱之心”“價值共通過”等情感邏輯,達到“無權者”獲得“權力”的目標。“使行動者傳遞的符碼不能被互動對象接受,但只要被旁觀者特別是大眾媒體接受并傳播,輿論力量和一般觀眾在道德上的同情就得以生產,其訴求和行動就具有了合情性,互動對象就得承受一定的情感和道德壓力,無權者的權力由此生產出來”[9];也有學者通過實證研究,發現社會團體“有組織的抗戰”,會對國家行政制度產生消解和抵觸(如地方有聲望者的權威遠遠超過行政機關官員,而社會治理的實現往往需要行政機關人員向地方有聲望者求助),這也說明社會自治權力絕非是在國家讓渡基礎上產生的。相反,社會自主性的實現需要反思社會自治權在運行中的“人情化”“不規范化”“非制度化”傾向,要促進社會自治權力再生產的制度化、理性化和法治化。endprint
其三,在融合國家和社會關系中實現權力生產的現代化。關系理性導向下的自治權力再生,不僅僅強調國家與社會通過協商、對話、合作等抽象實踐來實現權力的再生產,更強調了國家和社會二元主體治理權力的規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即國家通過行政權力,如法律、政策規則來引導社會組織治理理念的現代化,改變社會自治過程固有的習慣性、人情化等傾向,國家也要基于社會這一主體的需求不斷進行制度革新、提高服務水平,實現國家和社會權力生產中的雙重現代化。
3.治理價值的升華:治理過程中公共倫理的化育
實現“共同性”“普遍性”的價值理念是關系理性的根本旨趣,關系理性反對“原子式”存在方式和“主觀理性”思維,主張在交互性關系中體驗生存的根本意義,這種“共同感”在現實中就表現為“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各方全面參與”。
其一,關系理性下“共同感”的重建。從社會自治的價值導向來看,關系理性導向的“共同感”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國家和社會共同存在、共生互促;另一方面是對國家倫理實體的“普遍性”價值認同。“共同感”倡導國家和社會的共在,“共同感”的達成也事關廣大人民形成對國家倫理實體的價值認同。黑格爾將國家倫理實體的產生看作是解決市民社會中個體“原子式”生活困境的可能方案,“現代國家的本質在于,普遍物是同特殊性的完全自由和私人福利相結合的,所有家庭和市民社會的利益必須集中于國家”[14]261,國家也被黑格爾稱為“地上的精神”“神自身在地上的進行”[14]258-259。反觀現實,公民為什么積極參與到社會治理中,社會組織為何能在不計利益的情況下參與其中?我們應該以何種價值來倡導廣大組織和個體參與到社會治理中來?很顯然,這種價值導向絕不能僅立足于“共同利益”“危機防范”這一功利土壤中,而是應該以公民對國家最高倫理實體的認同性來培育這種價值理念。正是基于“個人國家”關系中國家認同前提下的“我們感”“共同感”,才能真正生長出適合中國特色的公民意識和公共精神,這才是社會自主性形成的終極指向。
其二,人與人的關系中實現治理“人本性”。社會自主性并非指向“機械化”“物本化”“科學化”的治理系統,而是指向人與人和諧交往中下的社會有機體。“系統性”思維是社會自主性實現的方案,這種方案顯然不能成為其價值所指。關系理性是營造了生活中信任、尊重、公正、倫理、交往、溝通等倫理氛圍,解決了現代個體“原子式”生存困惑的重大問題。可以說,關照人的生存困境——這才是社會自主性的價值所在。
三、關系理性導向下社會自主性形成的路徑選擇
以關系理性來指導社會自主性的形成,需要在“國家與社會”“組織與組織”“人與人”之間的多重關系上來推動社會自主性的形成,以此來豐富和發展當代中國的治理觀。
1.宏觀層面的關系:在國家與社會之間
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融合是社會自主性形成的前提。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要堅持系統治理,加強黨委領導,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在關系理性的引導下,社會自主性的形成不會以排斥國家治理身份為前提,相反,它是承認社會和國家在社會治理現實意義的基礎上,以提高公共生活質量為目標,注重國家和社會在治理能效上的優勢互補,以此來融合國家和社會的相互關系。
首先,要以馬克思主義國家觀來審視國家之于社會自主性的意義。馬克思指出國家有“包括執行由一切社會的性質產生的各種公共事務,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眾相對立而產生的各種特殊職能”[15]432,馬克思從階級性、社會性、服務型來闡釋國家的意義所在,任何對國家意義作狹隘理解的觀念都會背離馬克思主義國家觀的“總體性”思想。以馬克思主義國家觀來審視國家之于社會自主性的意義,才能在承認國家的治理意義和防范權力異化的雙重路徑上融合國家和社會的二元關系。
其次,國家與社會雙向承認中要避免“個體理性”思維。一般來講,人們總是以國家和社會的現實意義來論證國家和社會的融合可能,如“自我功能”“他者局限”等來證明“自我”的意義,這就很容易再次落入“個體理性”的窠臼中。所以,要以“受約束的”“有限性的”價值思維來回歸國家和社會這二元主體之于“自我”意義的理解,才可能在相互承認的基礎上融合其二元關系。避免“個體理性”思維,既要防止關系處理中的“工具性”思維,又要避免落入絕對自我的價值窠臼中。
2.中觀層面的關系:社會組織之間
社會領域內組織間的關系融合是社會自主性形成的關鍵。“多中心治理”“多元治理主體”等意涵決定了各類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合理性,但社會自主性的產生絕不僅僅等同于“多中心”和“多主體”,社會自主性更在于強調多元治理主體在治理過程中的有序性、規范性和自覺性。當前,人們總是以“反中心”“反權威”的思維來解釋組織參與治理的合理性,這種后現代的思路可能使組織在參與社會治理中碎片化、離散化。從關系理性來看,社會組織間的關系融合是組織公共性產生的關鍵,否則,參與治理過程中組織之間的對峙、排斥自然不利于社會自主性的產生。
首先,要以“責任”來更新社會組織參與治理社會的話語邏輯。個體理性導向下的社會組織總是以“權力”話語來闡釋治理邏輯,如“權力再生產邏輯”“治理權回歸”等,然而這種以“權力”為核心的話語邏輯往往不利于組織間的關系融合。隨著我國社會組織的不斷發展,社會組織所帶來價值觀也是多種多樣、甚至相互排斥,而在以“權力”為核心的話語邏輯中,權力生產過程中可能導致價值觀的沖突,以此引起社會組織在治理過程中公共性的中斷。“社會組織因其價值的合理性而遮蔽失范行為的事件損害的不僅是公共秩序,這對于組織自身的發展亦有不利。組織的價值理念雖然會引起共鳴,但對于自身價值訴求‘原教旨式的實踐則會導致公眾的反感。”[16]以“責任”來補充和更新社會組織參與治理中的話語邏輯,其實是從“責任”維度來實現不同社會組織價值的可公度性,即“公共責任”達成。可以說,在“責任”的話語邏輯中來劃分組織的“責任承擔”邊界,這即可以厘清組織在社會治理中責任歸屬問題,也能避免組織活動中“原教旨主義”傾向。另外,在追求公共責任的過程中,組織之間的協商、對話、溝通、尊重,都將推動社會組織之間關系的融合。endprint
其次,以制度化方案來規范組織的活動方式,在組織規范化發展的前提下融合組織間的關系。制度化方案的運行主要是借助于一定的權力保障,來管束、支配、調節組織的行為規則、程序,使得組織行為方式和交往關系規范化、有序化。一般而言,制度的運行總是按照既定的程序通過資源的配置和整合來調節組織行為,即將資源和利益的分配和組織的行為方式緊密結合起來,以此來引導組織按照規則辦事。當前中國社會組織的發展必須法治化、規范化、制度化,在加強組織立法的基礎上規范組織行為;同時,要完善社會組織自身的立法,社會組織的注冊、準入、退出和運行機制等都應規范化、法治化。基于此,才能避免組織之間的價值沖突,融合社會組織間的相互關系。總之,組織規范化發展就是要實現組織發展的價值共識,避免組織之間的價值沖突,融合社會組織間的相互關系。
3.微觀層面的關系:現實個體之間
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融合是社會自主性產生的根本。無論是從社會自主性發生的依據還是從社會自主性的現實意義來看,人與人良好交往關系的產生都是根本性的。馬克思曾這樣描述未來的人類社會,“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地調節”[17]77,所以,真正有序的未來社會必定體現為人與人交往關系的融合,社會自主性的產生也必定要以人與人的關系融合為根本。
首先,在公共倫理認同的基礎上推動“普遍性”價值的產生,這是融合人與人關系的起點。從個體角度來看,社會自主性表現為廣大人民基于共同的、普遍性的價值認同而產生的社會凝聚力。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會發現,個人自愿、積極、無私地參與社會治理往往是因為對他者的人道關愛,而這種人道關愛產生的基礎就是基于個體對國家認同而產生的“普遍性”倫理情懷,如我們常說的“同胞之情” “手足之情” “炎黃子孫”等,這些人道情感都是個體對國家這一普遍性實體認同而產生的主觀體驗。美國學者R.G.佩弗在總結馬克思道德觀時指出,“與他人相異化通常是令人排斥的,因為它表明缺乏一個真正的共同體,于是就失去了實現人的潛能的機會,這些潛能的實現是以真正的人類共同體為前提條件的”[18]55,很顯然,以共同體為依托的公共倫理確實是融合人與人關系的前提,這也是當前社群主義在解決社會發展時一再強調“社群”“共同體”的原因所在。而當前我國公共倫理產生的基點只能是基于對“民族國家”這一倫理實體的認同。
其次,要在加強公民道德培育實踐中融合人與人的相互關系。從個體化角度來看,人與人交往關系和諧也需要個體層面的道德修養,即公民道德的養成。公民道德從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角度闡釋了現代個體必須具備的道德素養,這些道德素養又是個體參與社會治理的精神支柱,可以說,社會自主性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個體素養的提升。公民道德的培育能推動個體友善、信任、互助、平等關系的養成,而這些也是融合人與人關系的基本道德要求。當前中國公民道德的養成必須著力于規則意識、契約意識、公共責任、公共關懷等層面來引導人們參與公共生活,在公共倫理中的化育中生成人與人之間的良好關系。同時,公民道德的培育也需要個體加強道德自律,在各類道德實踐中產生道德認知、提高道德能力,在關愛、團結、互助的道德行為中融合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
參考文獻:
[1] 郁建興.從社會管控到社會治理——當代中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新進展[J].探索與爭鳴,2014(12):7-16.
[2] 高丙中,夏循祥.社會領域及其自主性的生產[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5):120-127.
[3] 周謹平.社會治理與公共理性[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6(1):160-165.
[4] 鄭杭生.“理想類型” 與本土特質——對社會治理的一種社會學分析[J].社會學評論,2014(3):3-11.
[5] 張康之.現代社會治理中的權力依賴及終結[J].河南社會科學,2015(1):16-22.
[6] 米格代爾.社會中的國家[M].李楊,郭一聰,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
[7]Elizabeth J. Remick. Building Local States[M].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2004.
[8]Jefrey C.Alexander. The Civil Sphere[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9]肖瑛.從“國家與社會”到“制度與生活”:中國社會變遷研究的視角轉換[J].中國社會科學,2014(9):89-99.
[10] 賀來.“關系理性”與真實的“共同體”[J].中國社會科學,2015(6):22-44.
[11] 中央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 弗里德里希·邁內克.馬基雅維利主義——“國家理由”觀念及其在現代史上的地位[M].時殷弘,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13] 姚大志.善治與合法性[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5(1):46-55.
[14] 黑格爾.法哲學原理[M].范揚,張企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15] 中央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 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6] 崔月琴,袁泉.轉型期社會組織的價值訴求與迷思[J].南開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3):117-125.
[17]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8] R.G.佩弗.馬克思主義、道德與社會正義[M].呂梁山,等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責任編輯:陸廣品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