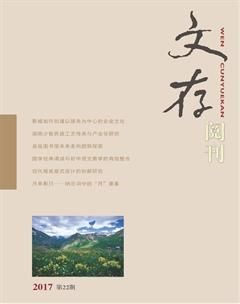心理彈性作用機制:“人”主體性的漸顯
張鑫
摘要:心理彈性作用機制研究有助于人們更加深入地了解個體的心理彈性,同時對相關的心理彈性干預也具有重要指導意義。本研究在梳理四種心理彈性作用機制的理論模型基礎上發現:心理彈性作用機制在價值取向上越來越關注“人”的主體性,重視從個體內部出發,積極主動尋求保護性因素,以達到良好適應的狀態。
關鍵詞:心理彈性;作用機制;主體性;積極主動
心理彈性作用機制是當下發展心理學研究的熱點,而構建心理彈性作用機制的理論模型有利于我們更加深入地理解心理彈性產生所需要的因素及作用過程,同時也將有助于我們在實踐中對處于壓力/逆境中的個體施以援手,并幫助他們重拾自信自尊,積極面對。縱觀已有研究發現,心理彈性作用機制主要包括四種理論模型,這些模型在價值取向上表現出:愈發關注“人”的主體性,而這種價值取向上的變化將為我們提供一個新的研究視角。
一、心理彈性:被“關注”的個體
(一)心理彈性
學界對心理彈性的界定一直處于爭論階段。如,Rutter將心理彈性定義為:處于高危環境中的個體表現出的積極發展性適應結果。[1]Connor則認為“心理彈性是個體在面臨挫折和壓力、經受創傷痛苦等消極情境時表現出的應對能力。但此種界定透漏著些許將心理彈性靜態化和固定化的意味,認為一旦個體獲得心理彈性,心理彈性便會對處于壓力/逆境中的個體產生持久的保護作用,不會增加亦或減弱。美國心理學會將心理彈性定義為個體在面對創傷、逆境等重大壓力時展現出的良好適應過程。該定義結合了系統論的觀點,將心理彈性作為一個連續變量,強調心理彈性具有動態性、交互性。
從結果性定義到能力性定義再到過程性定義這一變化過程可以看出:研究者們越來越關注個體能力和品質在壓力/逆境中的作用;個體在壓力/逆境中具有主動性,而非被動接受“挑戰”;心理彈性是個體展現出的積極適應的動態過程。
(二)心理彈性作用機制
目前大部分研究者比較認可將“保護性因素”視作心理彈性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中介。保護性因素是相對于危險因素而言的,當個體處于壓力/逆境中時,保護性因素可以適度緩解危險因素產生的消極影響。這些保護性因素既來自外部環境,也來自個體內部。通過對過去25年研究成果的總結,Masten等人提出了相似的保護性因素,包括個體良好的智力機能、自我效能感、信念等;來自家庭方面的支持性家族網絡、親社會家庭價值觀等;以及家庭外因素等。[2]可以看出研究者們已經開始關注保護性因素,并將其作為心理彈性作用機制的研究重點。
二、心理彈性作用機制的理論模型:被“遺忘”與“珍視”的個體
對心理彈性作用機制理論模型的研究不僅需要關注個體適應的結果,更需要重視發揮個體主動性的重要作用。本研究列舉了四種主要的心理彈性作用機制的理論模型:
(一) Garmezy等人的三種理論模型
1985年Garmezy提出三種理論模型。(1)補償模型:保護性因素直接作用于結果,抑制消極影響。(2)挑戰模型:某種程度上危險因素也可被視為一種“潛能”,較低或中度水平的壓力,可能會增強個體的心理能力;相反過度的壓力情境可能會導致個體能力下降或“奔潰”。(3)保護因素模型:該模型與補償模型相反,保護性因素可以直接作用于危險因素,同時減低消極結果發生的可能性,在這個模型中保護性因素起著類似于調節器的作用。
這三種模型描述了危險因素和保護性因素之間的關系以及在交互作用時如何對處境不利中的個體產生影響。該理論一經提出便得到廣泛的認可,受Garmezy的影響,許多研究者引用了該模型或在此模型基礎上做進一步完善。
(二)Rutter的發展模型
1990年,Rutter在總結了大量文獻的基礎上,提出了四種心理彈性發展的作用機制模型:(1)危機因素沖擊的減緩。個體對危險因素的高認知程度可以幫助個體避免或降低與危險因素的直接性接觸。(2)負向連鎖反應的減緩。長時間持續的危險因素可能會造成一系列的消極反應,保護性因素則可以適度降低這一消極影響。[3]例如,長期生活在父母沖突中的兒童,由于得到親密朋友的關心也可以減緩該兒童父母沖突帶來的消極影響。(3)促進個體自我效能感與自我尊重的獲得。(4)機會的開發。保護性因素與危險因素的交互作用可能會促使危險因素向“危險+機會”的轉變,從而增加個體獲得成功適應的可能性。
Rutter的發展模型表明,心理彈性保護機制的產生過程并非單純地避免外在消極環境,更重要的是通過個體內在資源、利用外部環境資源,打破連鎖的負向影響效應。[4]發展模型承認個體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且更重視個體內部力量,這一進步為以后探討心理彈性作用機制指出了重要方向,產生價值取向上的變化——重視“人”的主體性,將心理彈性看作一個動態過程。
(三) Kumpfer的心理彈性綜合模型
Kumpfer結合社會生態模型和“個體-過程-情境”模型,提出了一個全新的心理彈性綜合模型。(1)已有環境特征,包括外部環境中既存的危險因素和保護性因素,其中保護性因素起著類似調節器的緩沖作用。(2)個體心理彈性特征,如認知、情感、精神等。(3)個體心理彈性的重組,以及調適個體和環境以及個體和結果之間的動力機制。值得注意的是,Kumpfer指出:選擇性覺知、認知再建構、與親社會人群的交流溝通、個體對環境做出的積極主動的交互影響,可以幫助個體將危險環境轉變為保護性環境。[5]
Kumpfer的心理彈性綜合模型價值在于關注了個體與環境的交互作用,將其視作一個整體系統。在該系統下,一方面兒童可以接受他人的幫助或是在成人的良好照顧下來獲得心理彈性;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自身努力去達到心理彈性重組的可能。可見,該模型延續了關注個體主體性的價值取向。
(四)Richardson的身心動態平衡模型
Richardson的身心動態平衡模型同樣結合了生態系統論和發展系統論。該模型描述的是個體的身體、心理、精神等方面對環境適應的平衡狀態。但此平衡狀態可能會遭受內部和外部各種因素的影響,假如保護性因素無法抵御高危環境的沖擊,就會引發個體既有系統的失衡,個體將會進行意識或無意識的機能重組,從而出現以下情況:心理彈性重組,指個體生物心理精神系統在原有水平上進一步的提高;回歸性重組,指個體生物心理精神系統重新恢復到先前狀態;缺失性重組,指個體解構了一部分原有的想法和信念以此達到一種新的平衡狀態;機能不良重組,指個體通過一些危險途徑來應對高危事件。
Richardson在Kumpfer的基礎上將可能性重組當中的“適應”細分為“回歸性重組”和“缺失性重組”。二人同時關注了“人”的主體性,即任何一種可能性重組都取決于個體內部是否能夠成功應對,這一理念繼續堅持了 Rutter對個體力量關注的重要方向,為此后心理彈性的研究探出了新路徑——從單純的減少危險因素走向個體積極主動尋求保護性因素以獲得成功適應。
三、心理彈性作用機制的評析:逐步突顯的“人”的主體性
心理彈性作用機制的演變過程表明,研究者們的關注點逐漸從危險因素轉向保護性因素,而這一轉變更加突顯出“人”的主體性,強調個體自身力量在心理彈性過程中的重要作用。進一步分析發現,Garmezy等人的三種理論模型和Rutter的心理彈性發展模型同屬于早期心理彈性作用機制成果。Garmezy等人的三種理論模型從保護性因素與外在危險因素之間的關系出發,探討保護性因素在三種不同情況下起作用的機制,遵循的是“保護性因素—外在危險因素”這一直線模式。只分析了兩種因素交互作用的關系,缺乏對可能存在的適應結果的對應分析。更重要的是,Garmezy的理論模型缺乏對“人”作為主體的思考,個體并非是被動地接受外在危險因素的挑戰。與 Garmezy相比,Rutter更進一步地劃分了保護性因素起作用的四種不同情況,但該發展模型是他基于大量文獻的基礎上總結出來的,缺乏對心理彈性的新探索,不過,值得肯定的是,Rutter發展模型中“促進個體自我尊重和自我效能感的獲得”和“機會的開發”,不僅開始認識到個體的重要性,還開始關注外部環境能給個體提供的機會和資源,這些機會和資源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能夠促使個體采取積極的態度向外界尋求幫助,即從“危險”向“危險+機會”的轉變,增加成功適應的機率。
Kumpfer和Richardson的心理彈性作用機制模型屬于整合的心理彈性模型。站在更宏觀地視角思考心理彈性如何對個體產生影響,結合了生態學理論將心理彈性的機制問題看作一個整體系統,即從孤立的個體轉向生態系統中的個體。透過這個整體系統我們能夠發現個體處于核心地位:Kumpfer的綜合模型中,內部心理彈性因素、心理彈性過程同時強調了個體在經歷壓力/逆境時會調動內部各因素(認知、情感、行為等)與環境進行交互作用,而不是被動地接受環境的影響;Richardson的身心動態平衡模型中,身心精神的平衡、系統調整、機能重組都強調個體在壓力/逆境下的內在調整和重組,同樣體現了個體主動與環境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說,這一階段心理彈性作用機制研究已經關注到了“人”的主體性,強調個體的主動積極適應已經成為心理彈性作用機制研究的發展趨勢。
四、啟示
當今各種壓力的沖擊,讓人們備受心理問題的困擾。榮格就曾提醒,要防止遠比自然災害更危險的人類心靈疾病的蔓延。[6]尤其是兒童青少年更容易“暴露”在壓力/逆境之中,若只關注危險因素對兒童青少年的影響,便會忽略了他們的自我生長力和向上力。因此,正如心理彈性作用機制價值取向的轉變,家長和教育工作者應該將目光著眼于兒童青少年自身的內部力量,將“危險”轉化為“危險+機會”,幫助兒童青少年通過積極主動尋求保護性因素來協助自身成功適應壓力/逆境。
參考文獻:
[1]Flores E, Cicchetti D, Rogosch F A. Predictors of resilience in maltreated and nonmaltreated Latino children[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2005,41(2):338-351.
[2]Masten A S, Coatsworth J D. 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ence in favorable and unfavorable environments: lessons from research on successful children[J]. American Psychologist,1998,53:205-220.
[3][5]林雅芳.心理彈性[M].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2014:10-30.
[4]馬偉娜,桑標,洪靈敏.心理彈性及其作用機制的研究述評[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08,26(1):89-96.
[6]陳妙.臺灣地區大學生人格與心理健康現況研究[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