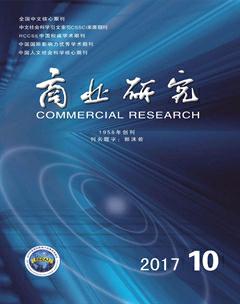論綠色生活對(duì)人類(lèi)需要的全面滿足
楊昌軍+吳明紅+嚴(yán)耕
內(nèi)容提要:綠色生活不是人類(lèi)面臨生態(tài)危機(jī)的被動(dòng)選擇,而是值得人類(lèi)主動(dòng)追求的美好生活;其本質(zhì)在于更全面地滿足人的需要,其中,既包括人的物質(zhì)需要、精神需要和社會(huì)需要,也包括逐漸凸現(xiàn)出來(lái)的生態(tài)需要,在有效增進(jìn)人們福祉的同時(shí)促進(jìn)人與自然和諧發(fā)展。為此,綠色生活就必須具備三大特征,分別是適度的物質(zhì)消費(fèi)、不斷豐富的精神消費(fèi),更加充裕的自主時(shí)間、基于興趣的創(chuàng)造力釋放,作為生活主體的人從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索取者變成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增益者。我們當(dāng)前生活的綠色程度欠佳,人類(lèi)應(yīng)從價(jià)值觀、政策法規(guī)、發(fā)展方式上逐步實(shí)現(xiàn)綠色轉(zhuǎn)型。
關(guān)鍵詞:綠色生活;全面需要;生態(tài)文明
中圖分類(lèi)號(hào):F062.2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B 文章編號(hào):1001-148X(2017)10-0133-06
工業(yè)文明以來(lái),生態(tài)環(huán)境破壞日益嚴(yán)重,逐步升級(jí)成為全人類(lèi)共同面臨的生存危機(jī)。為此,人們不斷探尋新的發(fā)展之路,從20世紀(jì)60、70年代的環(huán)境保護(hù)與末端治理,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提出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戰(zhàn)略,再到近年來(lái)由中國(guó)率先行動(dòng),并逐漸在國(guó)際社會(huì)取得較大影響的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無(wú)一不要求對(duì)傳統(tǒng)的生產(chǎn)與生活方式進(jìn)行變革。生產(chǎn)上,要求轉(zhuǎn)變粗放型的發(fā)展方式,破除GDP崇拜和無(wú)質(zhì)量的增長(zhǎng)迷信;生活中,則要求生活方式綠色轉(zhuǎn)型,推行綠色生活。顯然,如果生態(tài)文明是超越工業(yè)文明的一種新的文明形態(tài),綠色生活則是與生態(tài)文明相適應(yīng)的人類(lèi)新的生活方式。
一、綠色生活是更值得追求的美好生活
一提到綠色生活,人們?nèi)菀仔纬梢环N錯(cuò)誤的印象,認(rèn)為綠色生活僅僅是簡(jiǎn)樸生活,要求大家盡可能節(jié)制消費(fèi)、節(jié)約資源能源,甚至不惜以犧牲自我福利為代價(jià)。這種生活確實(shí)不會(huì)對(duì)自然造成太大損害,卻對(duì)生活主體有較高的道德要求,廣泛推行面臨一定的困難和阻力,就如巖佐茂所說(shuō)的“完全依靠人們的良心和道德的這種道德主義是不能解決環(huán)境破壞問(wèn)題的”[1]。同時(shí),也有人認(rèn)為,綠色生活是被迫的,是人們?cè)谏鷳B(tài)危機(jī)前不得不做出的選擇。這種說(shuō)法同樣有一定道理,卻也將人放到了一個(gè)消極、被動(dòng)的位置,忽略了人本身是生態(tài)系統(tǒng)的一員,可以通過(guò)合乎自然規(guī)律的生產(chǎn)生活活動(dòng)積極參與到生態(tài)循環(huán)之中,促進(jìn)自身與自然同步發(fā)展。
綠色生活是一種美好的、值得不懈追求的、能全面增進(jìn)人們福祉的生活。人們深切向往美好生活,并為此而付出了不斷努力,綠色生活就是這種努力的當(dāng)代目標(biāo)。不同的時(shí)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歷史與文化背景,人們對(duì)什么是美好生活有不同的看法。如在古希臘人看來(lái),美好生活就是符合宇宙秩序的生活,“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乃至斯多葛派哲學(xué)家都理所當(dāng)然地認(rèn)為美好生活以意識(shí)到自己從屬于一個(gè)‘外在于并‘高于我們每個(gè)人的現(xiàn)實(shí)秩序?yàn)楸匦钘l件”[2]。在中世紀(jì)的人看來(lái),美好生活在于“因信稱(chēng)義”,增加上帝的榮耀;在古代中國(guó)人看來(lái),“天人合一”的,能實(shí)現(xiàn)道德理想人格的生活是美好生活。這些看法中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禁欲主義,源于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生產(chǎn)力較為低下,物質(zhì)產(chǎn)品整體上較為匱乏,故人生幸福更多寄托于精神境界的提升或信仰的彼岸世界。文藝復(fù)興使人重新被發(fā)現(xiàn),“凡人的幸福”成為關(guān)注的中心。凡人的幸福也就是俗世的幸福、享樂(lè),其“根本內(nèi)容便是物質(zhì)生活的富足和感官欲望的滿足”[3],這是對(duì)封建神學(xué)長(zhǎng)期壓抑人們物欲的糾偏,在當(dāng)時(shí)有比較大的進(jìn)步作用。但是隨著科學(xué)革命和啟蒙運(yùn)動(dòng)張揚(yáng)了人的理性,開(kāi)啟了現(xiàn)代生產(chǎn)力,人類(lèi)社會(huì)進(jìn)入工業(yè)文明時(shí)代,在資本主義和科學(xué)技術(shù)的雙重刺激下,人的物欲就一發(fā)不可收拾。尤其是20世紀(jì)以來(lái),人類(lèi)社會(huì)進(jìn)入加爾布雷斯所說(shuō)的“豐裕社會(huì)”之后,物質(zhì)產(chǎn)品已相對(duì)豐富,同時(shí)消費(fèi)主義成為社會(huì)主流價(jià)值觀,將消費(fèi)塑造成獲取人生意義的唯一方式,因而在多數(shù)人看來(lái),幸福的、值得追求的美好生活就是,而且也只能是消費(fèi)充足、物質(zhì)豐盈、金錢(qián)財(cái)富越來(lái)越多的生活,這樣,人們就不斷地消費(fèi)、購(gòu)買(mǎi),又不斷地拋棄,造成物質(zhì)資源的極大浪費(fèi),也遮蔽了人的真實(shí)需要。在生態(tài)危機(jī)日益惡化的今天,這種生活顯然難以說(shuō)是值得追求的、美好的生活,綠色生活正是對(duì)它的超越。
要超越工業(yè)文明的生活方式,綠色生活就要求人的物質(zhì)和精神協(xié)調(diào)發(fā)展,人與自然和諧發(fā)展。一方面,現(xiàn)代社會(huì)之中,物質(zhì)匱乏問(wèn)題已基本解決,絕大多數(shù)人已能較為容易地滿足衣、食、住、行等生存需求,但精神空虛、人際失范、社會(huì)失信等問(wèn)題卻越來(lái)越嚴(yán)重,影響人的生活體驗(yàn)和對(duì)幸福的感知;另一方面,科學(xué)技術(shù)飛速發(fā)展,極大地增強(qiáng)了人們改造自然的能力,豐富的物質(zhì)產(chǎn)品也能養(yǎng)活越來(lái)越多的人口,促成人口爆炸,于是人類(lèi)發(fā)展終于走到了與自然根本性沖突的臨界點(diǎn)。這個(gè)臨界點(diǎn)如此重要以至于一旦處理不好就會(huì)威脅到整個(gè)人類(lèi)的生存,將人類(lèi)社會(huì)推向崩潰的境地。因此,綠色生活既要是能切實(shí)增進(jìn)人們幸福的生活,更要是低風(fēng)險(xiǎn)、不受威脅的生活,這才可以說(shuō)是美好的,真正值得追求的。
二、綠色生活是對(duì)人的需要的更全面滿足
對(duì)美好生活的追求具體表現(xiàn)為一系列的社會(huì)實(shí)踐行為,而正是人的需要為行為提供了內(nèi)在的、自發(fā)性的動(dòng)機(jī)。馬克思恩格斯認(rèn)為,以往的哲學(xué)在理解人和社會(huì)活動(dòng)時(shí),“習(xí)慣于用他們的思維而不是用他們的需求來(lái)解釋他們的行為”[4],而“在任何情況下,個(gè)人總是‘從自己出發(fā)的,但由于從他們彼此不需要發(fā)生任何聯(lián)系這個(gè)意義上來(lái)說(shuō)他們不是唯一的,由于他們的需要即他們的本性,以及他們求得滿足的方式,把他們聯(lián)系起來(lái)(兩性關(guān)系、交換、分工),所以他們必然要發(fā)生相互關(guān)系”[5]。也就是說(shuō),需要是人的本性,“從自己出發(fā)的”人的需要,以及求得需要滿足的方式構(gòu)成了理解生活的基點(diǎn)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強(qiáng)大動(dòng)力。綠色生活涉及個(gè)人、社會(huì),也涉及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而歸根結(jié)底都與人的需要相關(guān),故只有詳細(xì)分析人的需要才能理解到底什么是綠色生活,為什么值得追求,如何有效推進(jìn)綠色生活等,從而避免道德主義式的強(qiáng)制,增強(qiáng)綠色生活的吸引力,促使人們主動(dòng)選擇和踐行。
(一)人本質(zhì)的豐富性和需要的全面性
從自己出發(fā)、從實(shí)際需要出發(fā)就要注意到人的需要的全面性,這取決于人本質(zhì)的豐富性。人的本質(zhì),就是關(guān)于“人是什么”的問(wèn)題。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的地方論述過(guò)人的本質(zhì),如“人直接地是自然的存在物”[6];“人的本質(zhì)并不是單個(gè)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xiàn)實(shí)性上,它是一切社會(huì)關(guān)系的總和”[5];“人的類(lèi)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覺(jué)的活動(dòng)”[6],“人的實(shí)質(zhì)也就是人的真正的共同體”[7]。總結(jié)起來(lái)看,在馬克思主義語(yǔ)境中,人的本質(zhì)至少包括三方面的內(nèi)容,即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的、有生命的人,這點(diǎn)與動(dòng)物是同一的,其次也是精神的人和社會(huì)的人,超越于動(dòng)物而存在。作為精神的人體現(xiàn)在自由自覺(jué)的活動(dòng)中,因?yàn)橹挥腥司哂幸庾R(shí),才能通過(guò)對(duì)象性活動(dòng)來(lái)把握世界和人自身,從而獲得自由與自覺(jué);作為社會(huì)的人則體現(xiàn)在人與人的交往中,是各種各樣的社會(huì)交往和社會(huì)關(guān)系造就了人、定義了人。endprint
人是自然的人、精神的人、社會(huì)的人,就意味著人有著物質(zhì)、精神和社會(huì)三重需要。學(xué)界一般認(rèn)為,物質(zhì)需要包括對(duì)象性的物質(zhì)生活資料需要及非對(duì)象性的生理需要,如睡眠、休息、鍛煉、性的需要等。前者通過(guò)自然界的物質(zhì)變換及人與人之間產(chǎn)品的交換來(lái)滿足,后者則是對(duì)自身的身體狀況進(jìn)行調(diào)整。精神需要基于人的意識(shí)而產(chǎn)生,主要包括兩方面內(nèi)容,一是人作為主體自由地施展自己的才能,二是對(duì)文化成果的享用。也有學(xué)者將其劃分為三個(gè)層次,認(rèn)為第一層次為精神基本需要,包括受教育、感情、交往、尊重等需要;第二層次為精神享受需要,包括娛樂(lè)、休閑、運(yùn)動(dòng)、大眾性文化成果的享用等需要;第三層次為精神發(fā)展需要,包括文化創(chuàng)造、個(gè)性發(fā)展、精神信仰等需要[8],這是對(duì)精神需要更為細(xì)致的論述。社會(huì)需要有生產(chǎn)生活兩個(gè)層面。生產(chǎn)層面的社會(huì)交往表現(xiàn)為人與人之間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交換關(guān)系。從生活層面說(shuō),社會(huì)需要就是人在交往過(guò)程中所產(chǎn)生和實(shí)現(xiàn)的對(duì)于交流的期望、理解的渴求、感情的依賴(lài)等,表現(xiàn)為親情、愛(ài)情、友情等各種情感,以及交往中所獲得的交流、理解、愛(ài)、自尊、認(rèn)同等。生產(chǎn)層面的社會(huì)交往、需要與物質(zhì)生產(chǎn)、物質(zhì)需要融為一體,而通常所說(shuō)的社會(huì)需要?jiǎng)t主要指生活層面,人際關(guān)系的和諧,家庭的溫馨,社會(huì)的穩(wěn)定、有序等基本上都是生活層面社會(huì)需要的價(jià)值規(guī)定。
(二)人的生態(tài)本質(zhì)與生態(tài)需要
除了物質(zhì)、精神和社會(huì)三重本質(zhì)外,人其實(shí)還有著生態(tài)本質(zhì),即指人作為大自然生態(tài)系統(tǒng)中的一員而存在著。這一本質(zhì)馬克思恩格斯雖然沒(méi)有直接論述,卻蘊(yùn)含于他們對(duì)人與自然關(guān)系的討論之中。在他們看來(lái),人既依賴(lài)于自然,也能動(dòng)地反作用于自然。依賴(lài)于自然表現(xiàn)為人需要同自然進(jìn)行物質(zhì)交換,人們衣、食、住、行等所有物質(zhì)生活資料都要從自然界中獲得;并且自然也為人提供精神食糧,“從理論領(lǐng)域來(lái)說(shuō),植物、動(dòng)物、石頭、空氣、光等等,一方面作為自然科學(xué)的對(duì)象,一方面作為藝術(shù)的對(duì)象,都是人的意識(shí)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無(wú)機(jī)界,是人必須事先進(jìn)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糧”[6]。能動(dòng)地反作用于自然則表現(xiàn)為人總是按自己的尺度來(lái)改造自然,無(wú)論是從自然界獲取物質(zhì)資源,還是向自然傾倒排放垃圾廢物,都會(huì)改變自然原本的形態(tài),使自然向人生成,成為人化的自然。因此,人與自然是一體的,二者融合成一個(gè)互動(dòng)的生態(tài)系統(tǒng),互相制約、互相促進(jìn)、共同發(fā)展,而人的生態(tài)本質(zhì)就表現(xiàn)為這種人與自然的一體性、系統(tǒng)性和不可分割性。
生態(tài)本質(zhì)產(chǎn)生生態(tài)需要。劉思華指出生態(tài)需要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生態(tài)需要是現(xiàn)代人類(lèi)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中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系統(tǒng)對(duì)自然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生態(tài)環(huán)境資源的需要,即人作為自然生態(tài)系統(tǒng)的一員,在生存發(fā)展之中對(duì)自然所產(chǎn)生的所有需要,包括從自然界獲取物質(zhì)生活資料,對(duì)自然環(huán)境質(zhì)量的要求等,狹義的生態(tài)需要?jiǎng)t僅指人類(lèi)生活對(duì)自然環(huán)境質(zhì)量的要求[9]。本文首先區(qū)分了最基本的物質(zhì)需要,故此處所說(shuō)的生態(tài)需要主要指后者。
人類(lèi)生活的生態(tài)需要,即狹義的生態(tài)需要,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gè)方面。一是對(duì)不威脅、損害人的身體健康,同時(shí)盡可能少地對(duì)環(huán)境產(chǎn)生負(fù)面影響的生態(tài)產(chǎn)品的需要。這里的“生態(tài)產(chǎn)品”是與“物質(zhì)生活資料”不同的概念,物質(zhì)生活資料僅強(qiáng)調(diào)對(duì)人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需要的滿足,不關(guān)心這一滿足過(guò)程中人與自然的和諧及產(chǎn)品的生態(tài)屬性、生態(tài)質(zhì)量,生態(tài)產(chǎn)品則要求提供給人的產(chǎn)品是生態(tài)的、綠色的、環(huán)保的、健康的,如干凈的空氣、清潔的水、充足的陽(yáng)光、安全健康的食物、低碳環(huán)保的衣物和交通工具等。另一個(gè)就是對(duì)優(yōu)美的自然環(huán)境的需要。優(yōu)美的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不僅使人享受大自然的豐厚賜予,能開(kāi)拓人的胸懷,陶冶人的情操,而且能啟迪人思維,發(fā)展人的智力、體力,大大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發(fā)展”[10]。它與人們對(duì)自然的審美有關(guān),是一種無(wú)功利性地對(duì)居住環(huán)境、生活環(huán)境、自然景觀的欣賞,以獲得心情的愉悅和精神的充實(shí),如海德格爾所說(shuō)的那樣詩(shī)意地棲居在大地之上。
值得說(shuō)明的是,生態(tài)需要近年來(lái)才得到人們的普遍重視,但這并不意味著在此之前人們就不存在這種需要。相反,漫長(zhǎng)的歷史階段中,人們的生態(tài)需要一直處于滿足狀態(tài),直到20世紀(jì)中葉之后,高速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侵蝕了自然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健康,人類(lèi)的生態(tài)本質(zhì)受到威脅,發(fā)展的生態(tài)屬性出現(xiàn)匱乏,生態(tài)需要才真正凸現(xiàn)于人們的視野之中。同時(shí),生態(tài)需要更多的也是一種享受和發(fā)展需要。馬克思恩格斯除了有物質(zhì)、精神和社會(huì)的需要類(lèi)型劃分,也有生存、享受和發(fā)展的需要層次劃分,物質(zhì)需要基本上是生存需要,是為了維持人的存在。精神和社會(huì)需要?jiǎng)t主要屬享受和發(fā)展范疇,是為了完善自身,使生活過(guò)得更美好。生態(tài)需要同樣屬于這一范疇,因?yàn)橹灰晃<吧藗冊(cè)趷毫拥沫h(huán)境中也能生存,而要保證、提升生活質(zhì)量,不威脅人健康、盡可能降低環(huán)境負(fù)面影響的生態(tài)產(chǎn)品和良好優(yōu)美的居住生活環(huán)境就不可或缺。可見(jiàn),生態(tài)需要既是人之需要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有效滿足是美好生活的必備條件,又是正確處理人與自然關(guān)系的天然的、最強(qiáng)大的動(dòng)機(jī),畢竟只有人與自然和諧發(fā)展,生態(tài)需要才有可能得到滿足。
總之,作為新時(shí)代的美好生活,綠色生活不只關(guān)注物質(zhì)需要,也關(guān)注精神、社會(huì)、生態(tài)需要。馬克思指出,共產(chǎn)主義是“通過(guò)人并且為人對(duì)人的本質(zhì)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會(huì)的(即人的)人的復(fù)歸,……這種共產(chǎn)主義,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zhì),對(duì)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gè)體和類(lèi)之間的斗爭(zhēng)地真正解決”[6]。終極的美好生活存在于共產(chǎn)主義社會(huì)之中,是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身的完滿和諧,受限于經(jīng)濟(jì)基礎(chǔ)和歷史條件,綠色生活還只能說(shuō)是共產(chǎn)主義美好生活的一種初級(jí)形態(tài),但無(wú)疑已包含著全面的要求,是對(duì)人的需要的更為全面的滿足。
三、綠色生活的三大本質(zhì)特征
綠色生活要求更全面滿足人的需要,但需要的滿足程度是相對(duì)的,尤其是享受和發(fā)展需要,沒(méi)有一個(gè)絕對(duì)的標(biāo)準(zhǔn)可以衡量。因此,綠色生活某種程度上也是相對(duì)的,只能歷史的或與他國(guó)相比較確定。但無(wú)論怎樣,只要四個(gè)方面的需要平衡發(fā)展、共同進(jìn)步,不以犧牲其他需要為代價(jià)片面發(fā)展某一需要,人們的生活就會(huì)越來(lái)越綠色、越來(lái)越美好。要促進(jìn)四方面需要的平衡發(fā)展,綠色生活就必須具備三大本質(zhì)特征,而從這三大特征來(lái)看,目前中國(guó)的生活方式還稍欠綠色,還有較大的進(jìn)步空間。endprint
(一)適度的物質(zhì)消費(fèi),不斷豐富的精神消費(fèi)
消費(fèi)是生活的主要內(nèi)容,指消耗由外界提供的物質(zhì)或精神文化產(chǎn)品以滿足自身的物質(zhì)、精神需要。作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人的物質(zhì)需要是有限的,因?yàn)槿耸怯猩膫€(gè)體,具有自然的有限性,對(duì)物質(zhì)的攝取也就存在著生物有機(jī)體所規(guī)定的限度,并且意識(shí)是人區(qū)別于動(dòng)物的本質(zhì)特征,人本質(zhì)的完善不在于消費(fèi)更多的物質(zhì),發(fā)展動(dòng)物性,而在于精神境界的不斷提升。這樣,對(duì)物質(zhì)產(chǎn)品的消費(fèi)也就存在著限度,當(dāng)超過(guò)這一限度之后仍進(jìn)行消費(fèi),不但不會(huì)增加任何利益和價(jià)值,還有可能導(dǎo)致嚴(yán)重的健康問(wèn)題,增加生理或心理負(fù)擔(dān)。據(jù)統(tǒng)計(jì),美國(guó)近幾十年的肥胖率逐漸升高,1962年才13%左右,而2014年就已有36.5%的成人和17%的兒童出現(xiàn)肥胖問(wèn)題[11],因此問(wèn)題在美國(guó)每年造成約十萬(wàn)至四十萬(wàn)人的死亡[12]。還有衣物、住房、汽車(chē)、用具等的過(guò)度消費(fèi),它們既沒(méi)有給人增加額外的幸福感,還帶來(lái)了資源能源的極大浪費(fèi)和嚴(yán)重的環(huán)境污染。
物質(zhì)需要有限,精神需要卻是無(wú)限的,而過(guò)度消費(fèi)恰恰是顛倒了人的這種有限性與無(wú)限性,綠色生活須將顛倒了的人扶正,合理化消費(fèi)行為。一是要將物質(zhì)消費(fèi)控制在恰當(dāng)、適度的范圍內(nèi),拒斥消費(fèi)主義的負(fù)面影響。過(guò)度消費(fèi)之所以產(chǎn)生就在于消費(fèi)主義通過(guò)廣告等手段將物質(zhì)產(chǎn)品賦予了文化和符號(hào)意義,使人將購(gòu)買(mǎi)當(dāng)成了幸福的源泉,將商品當(dāng)成了精神的寄托和社會(huì)身份識(shí)別的標(biāo)識(shí),刺激了人們對(duì)物質(zhì)產(chǎn)品的無(wú)限需求。這是對(duì)真正的精神需要、社會(huì)需要的異化和遮蔽,是使物質(zhì)產(chǎn)品承擔(dān)了過(guò)多的、不該有的功能,故綠色生活必須節(jié)制物質(zhì)消費(fèi),褪去消費(fèi)主義加在物質(zhì)產(chǎn)品頭上的神圣光環(huán)。二是要不斷發(fā)展和豐富精神消費(fèi)。精神消費(fèi)越充足,人們的精神世界就越豐富,就越能感受到自己與世界的聯(lián)系,消解由消費(fèi)主義和現(xiàn)代性帶來(lái)的心理失調(diào)、精神空虛、人生意義喪失等生存困境。同時(shí),精神產(chǎn)品是無(wú)形的,雖然有物質(zhì)載體,但消耗的資源能源畢竟相對(duì)較少,因此不斷豐富精神消費(fèi),促進(jìn)物質(zhì)消費(fèi)與精神消費(fèi)平衡發(fā)展,應(yīng)是綠色生活的基本要求。
當(dāng)前雖然我國(guó)整體上還消費(fèi)不足,但也已深受過(guò)度消費(fèi)等問(wèn)題的困擾。據(jù)世界銀行發(fā)布的數(shù)據(jù),2015年中國(guó)最終居民消費(fèi)率僅為37%,低于世界58.31%的平均水平,更低于美日歐等發(fā)達(dá)國(guó)家,甚至在金磚國(guó)家中排名墊底,說(shuō)明消費(fèi)還有待提升①。但與此同時(shí),我國(guó)浪費(fèi)、高消費(fèi)現(xiàn)象卻非常嚴(yán)重。有數(shù)據(jù)顯示,我國(guó)餐飲食物浪費(fèi)量為每年1700-1800萬(wàn)噸,相當(dāng)于3000萬(wàn)至5000萬(wàn)人一年的口糧[13]。2016年中國(guó)人在境外消費(fèi)的奢侈品高達(dá)6300億人民幣,連同國(guó)內(nèi)市場(chǎng),中國(guó)人一共買(mǎi)走了全球46%的奢侈品[14]。除上述便于統(tǒng)計(jì)的領(lǐng)域,日常生活中人們各種不合理的消費(fèi)行為,如頻繁地購(gòu)買(mǎi)衣物、電子產(chǎn)品,對(duì)大排量汽車(chē)、豪宅的過(guò)度熱情等,都彰示著我國(guó)的消費(fèi)文化、消費(fèi)方式急需變革。
(二)更加充裕的自主時(shí)間,基于興趣的創(chuàng)造力釋放
擁有充裕的自主時(shí)間并能積極合理地加以利用,這是人滿足自己全面需要,促進(jìn)全面發(fā)展的必要條件,也應(yīng)是綠色生活的基本特征和評(píng)價(jià)生活品質(zhì)之優(yōu)劣的重要標(biāo)準(zhǔn)。自主時(shí)間就是能自主進(jìn)行各種活動(dòng)的時(shí)間,基于馬克思的“自由時(shí)間”概念,但更強(qiáng)調(diào)在這一時(shí)間之內(nèi)人們主動(dòng)、積極的生活態(tài)度和創(chuàng)造性才能的充分發(fā)揮、釋放,以激發(fā)人的全面潛能,實(shí)現(xiàn)人最完善的本質(zhì)。
長(zhǎng)期以來(lái)自主時(shí)間都較為缺乏,或沒(méi)有得到積極合理的利用,造成了人的片面化。傳統(tǒng)社會(huì)中,人們的生產(chǎn)力還較為低下,一天中絕大部分的時(shí)間與精力都要花費(fèi)在生產(chǎn)活動(dòng)上,甚少有自主時(shí)間可供支配。工業(yè)革命和現(xiàn)代化的經(jīng)濟(jì)組織模式使生產(chǎn)力得到了較大發(fā)展,生產(chǎn)效率提高,人們的必要?jiǎng)趧?dòng)時(shí)間減少,自主時(shí)間當(dāng)越來(lái)越充足。但當(dāng)消費(fèi)主義成為社會(huì)的主流價(jià)值觀,消費(fèi)成為人們的主要活動(dòng),自主時(shí)間也就被過(guò)多的消費(fèi)及支撐這些消費(fèi)的生產(chǎn)所占據(jù)。一方面,為了消費(fèi)更多、消費(fèi)更好,人們只有拼命賺錢(qián),努力工作,另一方面,即使有一定的自主時(shí)間,也多在感官、物質(zhì)的庸俗享樂(lè)中度過(guò),既沒(méi)有真正地放松、休閑,更沒(méi)有精力發(fā)展其他方面的能力,使自己越來(lái)越物質(zhì)化、片面化、單向度化。
綠色生活就是對(duì)人之發(fā)展片面化的糾偏,生活時(shí)間既不能是整天被繁重的、為謀生而進(jìn)行的勞動(dòng)、工作所占據(jù),人們欠缺休息時(shí)間、無(wú)心休閑的生活,也不能是無(wú)所事事、自由散漫地消極生活。在馬克思看來(lái),人的解放的一個(gè)重要方面就是越來(lái)越擺脫自然的限制,繁重的勞動(dòng)卻只將人限制于自然屬性當(dāng)中,“把自己的生命活動(dòng),自己的本質(zhì)變成僅僅維持生存的手段”[6]。在滿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之外,還須有充裕的時(shí)間能自主進(jìn)行其他活動(dòng),如學(xué)習(xí)、審美、休閑、交往等,以真正從自身興趣出發(fā),發(fā)展自己的才能,實(shí)現(xiàn)自己的目標(biāo),主動(dòng)創(chuàng)造,積極生活,全面增進(jìn)人們生活的充實(shí)感、成就感、幸福感。
然而我國(guó)當(dāng)前的自主時(shí)間也相對(duì)缺乏,幸福感難以有效提升。有數(shù)據(jù)顯示,2013年我國(guó)勞動(dòng)者年工作時(shí)間達(dá)2000-2200小時(shí),相當(dāng)于西方發(fā)達(dá)國(guó)家20-50年代的水平,并且九成行業(yè)周工作時(shí)間超過(guò)40小時(shí),過(guò)半數(shù)行業(yè)每周加班超過(guò)4小時(shí),這還不包括上下班路上越來(lái)越長(zhǎng)的通勤時(shí)間[15]。加班已成為常態(tài),過(guò)度勞動(dòng)問(wèn)題突出,再加上如瘋狂購(gòu)物、越來(lái)越多的夜生活、沉迷手機(jī)與網(wǎng)絡(luò)等自主時(shí)間內(nèi)各種不健康、不積極的休閑活動(dòng),由此雖然物質(zhì)生活水平提高,人們的生活幸福感卻沒(méi)有相應(yīng)增長(zhǎng)。美國(guó)經(jīng)濟(jì)學(xué)家伊斯特林等指出1990年至2010年的20年中,中國(guó)GDP增長(zhǎng)了4倍,“但這段時(shí)期的生活滿意度總體上看起來(lái)沒(méi)的提升,或許還有所下降”[16]。這顯然離理想的生活狀態(tài)還相距甚遠(yuǎn)。
(三)從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索取者,變成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增益者
人既然是自然生態(tài)系統(tǒng)的一員,有著生態(tài)本質(zhì)和生態(tài)需要,人們的生產(chǎn)生活活動(dòng)也就是生態(tài)系統(tǒng)物質(zhì)能量循環(huán)的一個(gè)基本環(huán)節(jié)。進(jìn)一步說(shuō),在全球整體生態(tài)系統(tǒng)中,人是作為一個(gè)種群而占有一定的生態(tài)位的,生產(chǎn)生活都在這一生態(tài)位內(nèi)進(jìn)行,因此人不但不能因自己的活動(dòng)而妨礙生態(tài)循環(huán),破壞生態(tài)系統(tǒng),相反,還必須承擔(dān)起應(yīng)有的生態(tài)責(zé)任,支撐生態(tài)系統(tǒng)平衡發(fā)展。endprint
這就要求在綠色生活中,人的角色發(fā)生轉(zhuǎn)換,從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索取者、破壞者變成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增益者。工業(yè)文明的生活方式中,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和機(jī)械自然觀將人與自然割裂了開(kāi)來(lái),人作為萬(wàn)物之靈、作為自然的主體而存在,因此人的生活不是生態(tài)循環(huán)的一個(gè)環(huán)節(jié),而是凌駕于生態(tài)之上的,對(duì)生態(tài)系統(tǒng)只有無(wú)盡的利用和索取,偶爾的一些保護(hù)行為也主要是為了使自然倉(cāng)庫(kù)不至于過(guò)快枯竭,同時(shí),沒(méi)有參與生態(tài)循環(huán)的意識(shí),產(chǎn)生的垃圾和廢物也就很難再回到生態(tài)系統(tǒng)之中,就如馬克思在論述資本主義城市化時(shí)所指出的那樣“破壞著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zhì)變換,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費(fèi)掉的土地的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條件”[17]。物質(zhì)和能量離開(kāi)了原有系統(tǒng),在別處成為垃圾被集中堆放、填埋、焚燒,生態(tài)循環(huán)便受到阻礙。
要使人成為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增益者,綠色生活就必須親近自然,保護(hù)自然,助益生態(tài)永續(xù)發(fā)展。充足的生態(tài)產(chǎn)品、優(yōu)美的自然環(huán)境這些滿足生態(tài)需要,提升生活質(zhì)量、增進(jìn)幸福感的要素只有在與自然的親近接觸中才能被充分享有。因此應(yīng)不斷增加生活的生態(tài)色彩,如經(jīng)常走入自然中去,提高小區(qū)、城市綠化率,多購(gòu)買(mǎi)綠色有機(jī)食品等,在滿足生態(tài)需要的同時(shí)培養(yǎng)對(duì)自然的熱愛(ài),進(jìn)而,通過(guò)個(gè)人、社會(huì)、政府等的努力將這種熱愛(ài)轉(zhuǎn)化為實(shí)際行動(dòng)。一是節(jié)約高效利用資源,減少垃圾排放,使資源的耗費(fèi)、廢棄物的排放不超過(guò)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再生能力和自凈能力;二是要通過(guò)行為習(xí)慣改變、產(chǎn)品材料創(chuàng)新、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等各種措施最大程度地打通生活,尤其是城市生活的生態(tài)循環(huán)通道;而更高的要求就是生活徹底綠色化、生態(tài)化,人與其他種群一樣完全融入生態(tài)系統(tǒng)之中,并能發(fā)揮力量,促進(jìn)生態(tài)更好發(fā)展。
我國(guó)的人均國(guó)民總收入、恩格爾系數(shù)、人均最終消費(fèi)支出等能直接體現(xiàn)生活水平的指標(biāo)基本上還無(wú)法與發(fā)達(dá)國(guó)家相比,但消耗的資源和排放的污染物卻有逐漸趕上并超越部分發(fā)達(dá)國(guó)家的趨勢(shì)。如2014年我國(guó)人均生活用煤消費(fèi)量為36.21千克油當(dāng)量,超過(guò)絕大多數(shù)OECD發(fā)達(dá)國(guó)家;人均生活用石油消費(fèi)為23.01千克油當(dāng)量,人均生活來(lái)源二氧化碳排放量為242.97千克每人,也將部分OECD國(guó)家甩在身后②。這些雖然只是部分領(lǐng)域的數(shù)據(jù),但也體現(xiàn)了我國(guó)當(dāng)前的社會(huì)生活在低碳、環(huán)保方面的欠缺,更難以達(dá)到親近自然、助益生態(tài)永續(xù)發(fā)展的要求。
以上三大特征都是建立在人全面需要的基礎(chǔ)之上的。適度、合理消費(fèi)要求人們的物質(zhì)需要和精神需要協(xié)調(diào)發(fā)展,自主時(shí)間為精神需要和社會(huì)需要的滿足提供保障,而生活主體從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索取者、破壞者變成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增益者能更好地滿足生態(tài)需要、正確處理人與自然關(guān)系。只有具備這三大特征,人們的生活才可以說(shuō)是綠色生活,是生態(tài)文明時(shí)代背景中更值得追求的美好生活,也是更積極進(jìn)步的生活。但顯然,從對(duì)現(xiàn)實(shí)境況的分析來(lái)看,中國(guó)當(dāng)前的生活方式離綠色生活還有一定的差距,還需從各方面努力,推進(jìn)綠色生活的建設(shè)。
一方面,從價(jià)值觀入手,培育綠色生活理念。綠色生活理念是對(duì)消費(fèi)主義價(jià)值觀的超越,是在認(rèn)識(shí)到人本質(zhì)的豐富性、需要的全面性、大自然的有限性等基礎(chǔ)上形成的對(duì)生活的理解與看法。中國(guó)有先進(jìn)的社會(huì)主義核心價(jià)值體系,有深厚的傳統(tǒng)文化根基,在超越以西方文化為基質(zhì)的消費(fèi)主義方面有獨(dú)特的優(yōu)勢(shì),因此中國(guó)必須發(fā)揮這種優(yōu)勢(shì),對(duì)人們的生活觀念進(jìn)行重塑和革新,使綠色生活理念深入人心。
另一方面,從管理上著力,制訂相關(guān)政策法規(guī)。政策法規(guī)對(duì)政府、市場(chǎng)、企業(yè)的合理運(yùn)行,對(duì)人們的生活行為能起到直接的指導(dǎo)和規(guī)范作用。目前我國(guó)有關(guān)綠色生產(chǎn)的政策法規(guī)體系已較為成熟,綠色生活方面卻還有完善空間,如生態(tài)產(chǎn)品的生產(chǎn)、銷(xiāo)售、認(rèn)證,垃圾分類(lèi)與回收,人們自主時(shí)間的保證等相關(guān)政策法規(guī)都還需進(jìn)一步完善、細(xì)化和切實(shí)推行,為綠色生活提供制度保障。
最后,從發(fā)展上進(jìn)行統(tǒng)籌,在生態(tài)文明整體建設(shè)中促進(jìn)生活方式綠色轉(zhuǎn)型。生活方式的轉(zhuǎn)型,歸根結(jié)底還是發(fā)展方式的轉(zhuǎn)型。過(guò)去我國(guó)的發(fā)展以經(jīng)濟(jì)建設(shè)為主,生產(chǎn)處于中心地位,當(dāng)前,我國(guó)已是世界第二大經(jīng)濟(jì)體,物質(zhì)基礎(chǔ)已相對(duì)豐厚,民生福祉成為關(guān)注的重點(diǎn),這就更需生產(chǎn)與生活的平衡。十八大報(bào)告將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融入中國(guó)特色社會(huì)主義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中,既關(guān)心自然,也關(guān)心人,既關(guān)心經(jīng)濟(jì)、也關(guān)心政治、文化與社會(huì),相信只要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穩(wěn)步推進(jìn),綠色生活終將到來(lái)。
注釋?zhuān)?/p>
① 世界銀行數(shù)據(jù)庫(kù)(http://data.worldbank.org.cn)。
② OECD數(shù)據(jù)庫(kù)(http://stats.oecd.org/).
參考文獻(xiàn):
[1] [日]巖佐茂.環(huán)境的思想[M].韓立新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29.
[2] [法]呂克·費(fèi)希.什么是好生活[M].黃迪娜等,譯.長(zhǎng)春:吉林出版集團(tuán)有限公司,2010:19.
[3] 盧風(fēng).享樂(lè)與生存——現(xiàn)代人的生活方式與環(huán)境保護(hù)[M].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11.
[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16.
[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514,5.
[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7,96,95,120,96.
[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87.
[8] 李大興.社會(huì)轉(zhuǎn)型期人的精神需要問(wèn)題探析[J].北京社會(huì)科學(xué),2002(4):95-99.
[9] 劉思華.論生態(tài)經(jīng)濟(jì)需求[J].經(jīng)濟(jì)研究,1988(4):77-79.
[10]尹世杰.論生態(tài)需要與生態(tài)產(chǎn)業(yè)[J].湖南師范大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學(xué)報(bào),1998(5):2-6.
[11]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Prevalence of obesity among adults and youth: United States,2011-2014[EB/OL].[2016-09-10].https://www.cdc.gov/obesity/data/adult.html.
[12]Blackburn G L, Walker W A. Science-based solutions to obesity:What are the roles of academia,government,industry,and healthcare?[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2005,82(1):207-210.
[13]我國(guó)每年食物浪費(fèi)相當(dāng)逾3000萬(wàn)人口糧[N].經(jīng)濟(jì)日?qǐng)?bào),2016-12-07(014).
[14]人民網(wǎng).中國(guó)人買(mǎi)走全球46%奢侈品,消費(fèi)外流持續(xù)嚴(yán)重[EB/OL].[2017-03-10].http://lady.people.com.cn/n1/2017/0310/c1014-29135765.html.
[15]賴(lài)德勝.2014中國(guó)勞動(dòng)力市場(chǎng)發(fā)展報(bào)告:邁向高收入國(guó)家進(jìn)程中的工作時(shí)間[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4.
[16]Easterlin R A, Morgan R, et al. China′s life satisfaction, 1990-2010[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2,109(25):9775-9780.
[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52.
(責(zé)任編輯:李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