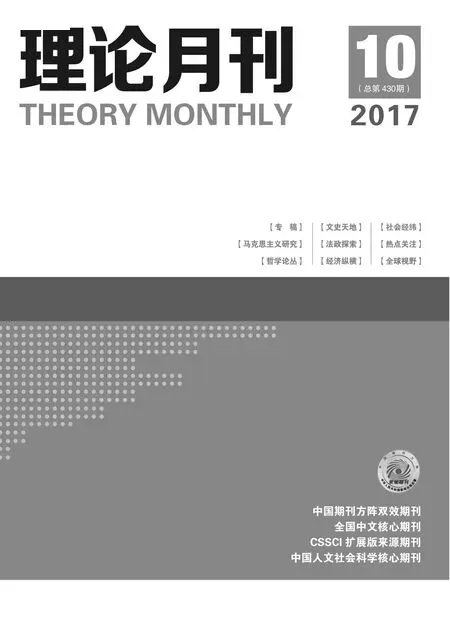我國大學(xué)章程執(zhí)行“腸梗阻”的病理解剖
——基于64所高校的數(shù)據(jù)分析
□陶光勝,付衛(wèi)東
(1.華中師范大學(xué) 學(xué)校治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漢 430079;2.華中師范大學(xué) 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湖北 武漢 430079)
我國大學(xué)章程執(zhí)行“腸梗阻”的病理解剖
——基于64所高校的數(shù)據(jù)分析
□陶光勝1,付衛(wèi)東2
(1.華中師范大學(xué) 學(xué)校治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漢 430079;2.華中師范大學(xué) 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湖北 武漢 430079)
對國內(nèi)64所不同辦學(xué)層次高校的調(diào)查訪談結(jié)果表明,章程文本的先天不足、利益群體的獲得感弱、監(jiān)督制約的機(jī)制不健全、法治文化的建設(shè)乏力、政策傳播的力度不夠是我國大學(xué)章程執(zhí)行“腸梗阻”的五大阻滯要素。進(jìn)一步解剖其致病機(jī)理,無章運(yùn)行的思維慣性、章程制定的程序缺失、權(quán)力配置的不盡合理是五大阻滯要素產(chǎn)生的深層次原因。正視這些阻滯要素及其滋生土壤,才能更好地祛病救疾,從體制機(jī)制上推動大學(xué)章程的貫徹實施。
大學(xué)章程;阻滯機(jī)制;實證分析
章程是學(xué)校的根本大法,是調(diào)節(jié)學(xué)校外部關(guān)系和內(nèi)部關(guān)系的基本準(zhǔn)則,是依法治校、自主辦學(xué)的基本依據(jù)。201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0-2020年)》發(fā)布后,章程建設(shè)進(jìn)入快車道。截至2015年6月30日,全國112所“211工程”高校率先全部完成章程核準(zhǔn)發(fā)布工作,大學(xué)章程取得標(biāo)志性成果,同時也迎來了拐點。高校章程面臨的緊迫問題從“有沒有”發(fā)展到了“用不用”。“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許多高校在章程執(zhí)行中遇到了這樣那樣的問題,章程推進(jìn)的效果不盡如人意。鑒于此,本研究采用實證方法,調(diào)查訪談了國內(nèi)不同辦學(xué)層次的64所高校,透過大量的訪談數(shù)據(jù),對阻礙章程執(zhí)行的各種要素進(jìn)行了梳理、歸納和分析,以從實踐和理論兩方面推動大學(xué)章程工作的順利實施。
1 調(diào)查的基本情況
2015年6 月至2016年12月,課題組以逐校拜訪、召開研討會等方式,發(fā)放調(diào)查問卷70份,回收有效問卷64份,有效回收率91.4%,并進(jìn)行了58人次的一對一訪談。
1.1 被調(diào)查高校的學(xué)校屬性
在有效回收的64份問卷中,從辦學(xué)層次上看,“985 工程”大學(xué) 26 所,“211 工程”大學(xué)(不含“985 工程”大學(xué))28所,其他普通高校10所,前兩類學(xué)校合計占此次被調(diào)查高校總數(shù)的84.4%(見表1)。調(diào)查樣本以“211工程”大學(xué)和“985工程”大學(xué)為主,是因為這些重點高校的章程制定和實施工作普遍開展較早,各方關(guān)注度高,社會影響力較大,具有較強(qiáng)的代表性。

表1:受訪高校的類別分布
1.2 被調(diào)查人員的身份性質(zhì)
64份有效問卷填寫者中,校領(lǐng)導(dǎo)有23人,中層干部35人,普通職員和教師有6人(見表2)。其中,直接參與了大學(xué)章程制定的有55人,占調(diào)查對象的85.9%。可以說,這部分群體是本校章程建設(shè)的直接參與者,乃至直接負(fù)責(zé)人,對章程的制定和執(zhí)行過程有較為深切的感受,他們的訪談結(jié)果可以較為準(zhǔn)確、全面地反映出該校章程建設(shè)的面貌及其背后邏輯。

表2:受訪者的身份性質(zhì)分布
1.3 被調(diào)查高校的章程頒布時間
參與調(diào)查的64所高校中,2013年及以前頒布大學(xué)章程的有13所 (吉林大學(xué)、華中農(nóng)業(yè)大學(xué)等高校2013年之前頒布過章程,后經(jīng)修訂核準(zhǔn)后重新發(fā)布),2014年29所,2015年22所,可見章程發(fā)布的高峰期在2014年和2015年 (見表3)。這可能與2014年5月,教育部辦公廳發(fā)文強(qiáng)制明確了各類學(xué)校的章程發(fā)布“時間表”有關(guān)。截止到本調(diào)查結(jié)束時,參與調(diào)研的所有高校均已發(fā)布并實施了章程,實施期最短的也有一年的時間,他們的數(shù)據(jù)和感受也就有了一定的參考性和說服力。

表3:受訪高校章程頒布的時間分布
2 章程執(zhí)行“腸梗阻”的要素分析
在依法治校的路上,高校章程的發(fā)布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落實章程的過程絲毫不比制定章程的過程輕松。經(jīng)過這幾年的實踐,大學(xué)章程的推進(jìn)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表4顯示,累計62.5%的受訪者對章程執(zhí)行情況持非常滿意或比較滿意的態(tài)度,但也有接近4成的受訪者對章程執(zhí)行情況持不樂觀的態(tài)度。開方先要號脈,只有找到阻礙章程執(zhí)行的那些要素,才能對癥下藥,祛病救疾。

表4:大學(xué)章程執(zhí)行情況的滿意度分布
2.1 章程文本的先天不足
章程的執(zhí)行力受制于章程文本的精確性,文本質(zhì)量的高低直接影響著章程的貫徹執(zhí)行。一部難以有效實施的法律,不僅無助于現(xiàn)實問題的解決,還會損害人們對法律的信仰和信心。由于受重視程度、投入精力、起草時間、辦學(xué)理念等多種因素的影響,章程之間的質(zhì)量差別很大,而且普遍存在如下問題:
2.1.1 部分高校章程內(nèi)容高度雷同。大學(xué)章程文本“千校一面”并非個例。例如有些大學(xué)章程對教職工權(quán)利規(guī)定幾乎一樣,對“黨委領(lǐng)導(dǎo)下的校長負(fù)責(zé)制”的內(nèi)容幾乎一樣,而在大的方向下,高校自己是如何做的,政治權(quán)力、行政權(quán)力、學(xué)術(shù)權(quán)力、民主權(quán)力是如何用富有特色的規(guī)定進(jìn)行區(qū)分和保障的,則缺乏高校個性化的制度設(shè)計。有訪談對象直言:“起草的時間很緊,沒精力對辦學(xué)理念、辦學(xué)經(jīng)驗等進(jìn)行提煉和升華,照著上位法抄一下算了。”這種想法比較普遍,有的為了應(yīng)付上級要求,盲目模仿其他高校已有文本。但壞處也很明顯,就是在執(zhí)行的時候與本校實際不相符,不接地氣的制度自然難以施行。
2.1.2 部分高校章程內(nèi)容簡單空泛。“有學(xué)者通過對美國大學(xué)章程文本的研究發(fā)現(xiàn),美國大學(xué)章程的篇幅普遍比我國長,詳盡程度也更高。以耶魯大學(xué)、密西根大學(xué)、康奈爾大學(xué)為例,三所大學(xué)平均的頁數(shù)為43頁,平均的條款為94條,平均字?jǐn)?shù)(英文)17 827字。而相比之下,我國首次頒布的六所大學(xué)章程平均頁數(shù)為 16 頁,字?jǐn)?shù)(中文)最多的只有 14 000 多字。”[1]從文本的具體內(nèi)容上看,有些章程言語空泛、大而化之,多半停留在框架性規(guī)定上,概念籠統(tǒng)、標(biāo)準(zhǔn)不清、責(zé)任不明,缺乏可操作性。比如某大學(xué)章程規(guī)定“學(xué)校尊重和愛護(hù)人才,維護(hù)學(xué)術(shù)民主和學(xué)術(shù)自由,為教師開展教學(xué)和科研活動提供必要的條件和保障”,具體提供哪些條件和保障,為此做出了哪些重大制度安排等在章程中沒有明確,致使章程缺乏指導(dǎo)性,失去了價值內(nèi)涵。正如有的學(xué)者所說:“缺乏后果模式不僅使得大學(xué)章程的義務(wù)性條款和禁止性條款形同虛設(shè),而且使大學(xué)章程在面對諸多爭議時形同廢紙。”[2]
2.1.3 部分高校章程文本要件缺失。通過對64所高校章程文本的分析,28.1%的章程存在要件缺失的現(xiàn)象。有些章程文本沒有載明章程修改的啟動、審議的具體程序及其基本規(guī)則,沒有明確黨委與行政的議事決策制度,沒有載明教師、學(xué)生權(quán)益的救濟(jì)渠道,沒有對可能產(chǎn)生的利益沖突的問題進(jìn)行救濟(jì)性措施的預(yù)設(shè)性規(guī)定等。這些先天不足的文本注定了“跛腳”的命運(yùn),使其缺乏可操作性,實施起來要花費(fèi)很大的成本進(jìn)行解釋和協(xié)調(diào),也使得大學(xué)章程容易被誤認(rèn)為是“花瓶”而被束之高閣。
2.2 利益群體的獲得感弱
“政策執(zhí)行理論認(rèn)為,政策執(zhí)行就是相關(guān)政策主體之間基于利益得失的考慮而進(jìn)行的一種利益博弈過程。”[3]2015 年,某“211 工程”大學(xué)在個性化智能辦公平臺發(fā)放了關(guān)于對本校大學(xué)章程基本看法的調(diào)查問卷,由于平臺可以確保每個教職工收到調(diào)查問卷,但回收率還不足1%。教職工對學(xué)校章程之所以持漠不關(guān)心、事不關(guān)己的態(tài)度,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學(xué)章程給予師生的獲得感不多,師生的權(quán)益無法通過章程得到較好的保障。這是因為一些高校章程對師生權(quán)益的保護(hù)和申訴表述相當(dāng)模糊,很多高校僅僅規(guī)定校工會是教職工權(quán)利救濟(jì)機(jī)構(gòu)及相應(yīng)權(quán)利保護(hù)機(jī)構(gòu)或者籠統(tǒng)地規(guī)定了要依法建立教職工和學(xué)生權(quán)益保護(hù)機(jī)制,但沒有具體載明師生權(quán)益受侵害后的受理組織、處理程序、議事規(guī)則等,導(dǎo)致大學(xué)章程實施后,涉及到師生的基本權(quán)益時,還是無章可循,執(zhí)行難度較大。
再以高校師生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監(jiān)督權(quán)利為例,幾乎所有的高校都把這一條寫進(jìn)了章程,但缺乏具體的保障措施。“這與我國20世紀(jì)50年代的大學(xué)章程相比,甚至顯得有些倒退。例如,1950年的《北京師范大學(xué)暫行規(guī)程》規(guī)定校務(wù)委員會有兩名學(xué)生代表,1951年的《湖北農(nóng)學(xué)院暫行規(guī)程》規(guī)定校務(wù)委員會中有2-3名學(xué)生代表,可見當(dāng)時的高校很重視學(xué)生參與學(xué)校決策和管理的權(quán)利。 ”[4]227
圖1的數(shù)據(jù)也基本佐證了這一分析,僅有累計34.5%的訪談對象認(rèn)為章程對落實師生權(quán)益的作用“非常大”和“比較大”,近七成的訪談對象并不看好大學(xué)章程對落實師生基本權(quán)益的作用。

圖1:章程落實對維護(hù)高校師生權(quán)益的作用
2.3 監(jiān)督制約的機(jī)制不全
對政策執(zhí)行進(jìn)行有效的監(jiān)督,是防止政策失控的有力手段。從校外監(jiān)督來看,專門針對大學(xué)章程的第三方監(jiān)督還基本沒有展開,甚至70.3%的高校理事會(董事會)都沒有把章程實施情況列入年度議題。而作為校外主要監(jiān)督主體的上級教育行政部門,對高校章程執(zhí)行情況的監(jiān)督也比較薄弱。圖2顯示,僅有16.7%的高校認(rèn)為上級教育行政部門對本校章程執(zhí)行情況進(jìn)行過監(jiān)督。教育部門監(jiān)督職能的缺位,既源于政府職能轉(zhuǎn)變和高等教育管理方式的變革尚不到位,也可能由于教育部門前期將主要精力放在章程核準(zhǔn)上,還沒有把工作重點轉(zhuǎn)移到章程執(zhí)行的督導(dǎo)上來。

圖2:上級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對大學(xué)章程執(zhí)行的督辦情況
從校內(nèi)監(jiān)督來看,也存在三個方面的問題:
2.3.1 大學(xué)章程執(zhí)行情況還沒有明確列入高校領(lǐng)導(dǎo)班子政績考核的范圍。他們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將章程執(zhí)行工作放在教學(xué)、科研之后的次要位置,還不足以引起足夠的重視或花費(fèi)足夠的精力。比如在調(diào)研的64所高校中,有39.7%的高校校長并沒有將大學(xué)章程執(zhí)行情況向教職工代表大會做年度報告。而2014年5月,教育部下發(fā)的《教育部關(guān)于加快推進(jìn)高等學(xué)校章程制定、核準(zhǔn)與實施工作的通知》中明確規(guī)定:“校長要作為章程執(zhí)行第一責(zé)任人,要把章程執(zhí)行情況,作為年度述職報告的內(nèi)容,向教職工代表大會作專門報告。”
2.3.2 部分高校還沒有設(shè)立獨(dú)立的監(jiān)督機(jī)構(gòu)來保障大學(xué)章程順利實施。《高等學(xué)校章程制定暫行辦法》(教育部令第31號)中規(guī)定,“高等學(xué)校應(yīng)當(dāng)指定專門機(jī)構(gòu)監(jiān)督章程的執(zhí)行情況,依據(jù)章程審查學(xué)校內(nèi)部規(guī)章制度、規(guī)范性文件,受理違反章程的管理行為、辦學(xué)活動的舉報和投訴。”然而,表5顯示,僅有10所高校設(shè)立了單獨(dú)的監(jiān)督機(jī)構(gòu)來監(jiān)督大學(xué)章程執(zhí)行,占被調(diào)查高校總數(shù)的15.6%。

表5:大學(xué)章程監(jiān)督機(jī)構(gòu)的設(shè)立情況
2.3.3 高校教職工和學(xué)生對大學(xué)章程執(zhí)行的監(jiān)督參與不夠。除了在制定章程時沒有預(yù)設(shè)有效的民主監(jiān)督渠道外,教職工代表大會、學(xué)生代表大會在學(xué)校的弱勢地位也使得其功能有限,像某些訪談對象所說:“教代會、學(xué)代會已經(jīng)成為‘走過場’和‘形式主義’的代名詞”。
2.4 法治文化的建設(shè)乏力
2013 年,知名學(xué)者馬陸亭就曾撰文指出,高校章程制定中存在“冷”“熱”不均問題[1]。 時至今日,章程從制定走向了實施,“冷”“熱”問題依然存在。訪談高校中,甚至還有26.6%的學(xué)校沒有做到章程文本人手一冊。有訪談對象說,章程實施是五熱五冷,即“教育部門熱,學(xué)校冷;分管領(lǐng)導(dǎo)熱,其他領(lǐng)導(dǎo)冷;主管處室熱,其他機(jī)關(guān)冷;校方熱,院方冷;領(lǐng)導(dǎo)熱,師生冷”。
盧梭說:“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的內(nèi)心里。”章程冷熱的背后是對章程“根本大法”地位的漠視,是法治文化的嚴(yán)重缺失,運(yùn)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來推動發(fā)展、化解矛盾、維護(hù)權(quán)益的習(xí)慣尚未養(yǎng)成。章程上承國家法律法規(guī),下啟校內(nèi)規(guī)章制度,可以實現(xiàn)法律原則規(guī)定與學(xué)校具體實際的結(jié)合,可以把大學(xué)的自主權(quán)具體化、制度化、法治化,為學(xué)校依法治校提供具體、可行的依據(jù)。但在實際運(yùn)行中,“重人情,輕法治”的社會氛圍對校園文化有較深的影響,大學(xué)里知法、用法、尊法的氛圍還不是那么濃厚。政府仍然習(xí)慣用指令和政策來領(lǐng)導(dǎo)和管理大學(xué),大學(xué)也習(xí)慣用各種繁雜的行政規(guī)定來保障學(xué)校的運(yùn)行。因此,培育社會和高校的法治文化顯得非常緊迫。只有在良好的法治文化建設(shè)中,政府才可能依法行政,大學(xué)才能依法治校[4]279。
2.5 政策傳播的力度不夠
“公共政策學(xué)認(rèn)為,政策有效傳播可以培養(yǎng)政策對象對公共政策的認(rèn)可、理解、信任和支持,從而減少對抗、抵制、抵觸、冷漠等不合作情緒,減少政策實施的阻力。”[5]部分高校章程執(zhí)行效果不理想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師生對大學(xué)章程具體內(nèi)容的知曉率太低。
2.5.1 從普及結(jié)果上看,我們此次調(diào)查專門抽取了13所高校,在師生中重點訪談?wù)鲁唐占扒闆r,僅有13.5%的教師和6.7%的學(xué)生“了解或大致了解”本校章程的基本內(nèi)容(見圖3),結(jié)果很不樂觀。

圖3:師生對本校章程內(nèi)容的知曉度
2.5.2 從普及方法上看,很多高校還是停留在“一份文件一冊書,發(fā)個通知管幾年”的階段,方法落后陳舊,宣傳推廣中沒有考慮師生對章程文本的特定需求,以做到針對性宣傳;較少利用新媒體新技術(shù)進(jìn)行交互性推廣,立體化、全方位宣傳的模式尚未建立;用生動活潑、易學(xué)易記的語言對學(xué)校章程進(jìn)行解讀釋義的工作也處于起步階段,64所高校中僅有48.4%的高校開展了章程解讀工作。
2.5.3 從普及機(jī)制上看,章程推廣的合力還沒有形成,工作機(jī)制還沒有建立,章程貫徹落實往往成為校內(nèi)某個部門一家的事,限于人力、財力和部門影響力,章程宣傳工作只能是蜻蜓點水、做做樣子。比如,新生入學(xué)教育、教師入職培訓(xùn)、干部任前培訓(xùn)等應(yīng)該是章程宣講的好時機(jī),但有訪談對象說:“我們學(xué)校發(fā)展規(guī)劃處跟學(xué)工部、人事處的領(lǐng)導(dǎo)有點不對付,這件事商量了幾次都沒搞成”。
3 章程執(zhí)行“腸梗阻”產(chǎn)生的深層原因探析
如前所述,章程文本、群體利益、監(jiān)督機(jī)制、法治文化和宣傳推廣是制約我國大學(xué)章程執(zhí)行的五大因素。但五大因素也有其滋生的土壤,只有正視這些更深層次的原因,才能更好地彌補(bǔ)不足,也才能供后來者引以為戒。
3.1 無章運(yùn)行的思維慣性
新中國成立后,絕大多數(shù)高校是先有學(xué)校,后補(bǔ)章程。大家覺得,幾十年過去了,沒有章程也照樣運(yùn)轉(zhuǎn)得很好,治校理政依靠經(jīng)驗和慣性就可以了。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這種想法非常有市場。這一輪章程制定浪潮中,有很多學(xué)校是被政府的潮水裹挾著往前走,制定章程是為了完成任務(wù)的想法不在少數(shù)。對章程意義和地位的認(rèn)識嚴(yán)重不足,章程制定的內(nèi)生動力嚴(yán)重不足,全校上下的思想甚至學(xué)校領(lǐng)導(dǎo)班子的思想都沒有統(tǒng)一。在這種情況下,想出臺一部“驚艷”的章程并將它付諸實施,可想而知是非常困難的。其實,制定和實施章程的過程,就是從經(jīng)驗到法治的轉(zhuǎn)換過程,這個過程很難,但一旦轉(zhuǎn)型成功,必將是無盡的紅利和燦爛的明天。
3.2 章程制定的程序缺失
章程制定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凝聚共識、規(guī)范權(quán)力、總結(jié)經(jīng)驗、體現(xiàn)特色、增進(jìn)和諧的過程,只有通過充分的溝通協(xié)商,甚至博弈,才能使章程得到最大程度的認(rèn)可,也才能減輕章程執(zhí)行的阻力。但由于部分高校對章程認(rèn)識上的不到位,以及盲目趕時間、趕進(jìn)度,章程制定并沒有嚴(yán)格遵循 《高等學(xué)校章程制定暫行辦法》(教育部令第31號)規(guī)定的各種程序,沒有經(jīng)過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多次反復(fù)、多次討論,沒有廣泛聽取和充分反映學(xué)校舉辦者、管理者、辦學(xué)者以及師生員工的要求與意愿,沒能找出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約數(shù),以至于為以后的執(zhí)行不順埋下了伏筆。因此,“章程制定不能缺少環(huán)節(jié),怕麻煩就是為以后找麻煩,想簡單就會讓以后更復(fù)雜,必須嚴(yán)格按照程序進(jìn)行。這樣的章程執(zhí)行起來,也會順暢很多。 ”[6]
3.3 權(quán)力配置的不盡合理
章程是建設(shè)現(xiàn)代大學(xué)制度的基礎(chǔ)性工作,“黨委領(lǐng)導(dǎo)、校長負(fù)責(zé)、教授治學(xué)、民主管理、社會參與”的現(xiàn)代大學(xué)制度體系作為權(quán)力配置的基本原則,理應(yīng)體現(xiàn)在章程制定和實施中。但從外部來講,政府對高校的管理職能和管理方式還沒有完全轉(zhuǎn)變到位,學(xué)校的辦學(xué)自主權(quán)也沒有經(jīng)過平等的協(xié)商、討論而體現(xiàn)在章程文本中。政府還需進(jìn)一步簡政放權(quán),改變直接管理學(xué)校的單一方式,“綜合應(yīng)用立法、撥款、規(guī)劃、信息服務(wù)、政策指導(dǎo)和必要的行政措施,依法行政、依法治教,支持和保障學(xué)校按照章程自主管理”[7]。
從內(nèi)部來講,學(xué)校的內(nèi)部治理結(jié)構(gòu)也不盡完善,很多學(xué)校的章程從制度設(shè)計上還沒有處理好政治力、行政力、學(xué)術(shù)力與民主力的關(guān)系,行政化色彩比較濃厚,行政權(quán)力遠(yuǎn)大于學(xué)術(shù)權(quán)力,沒有形成一種決策權(quán)、執(zhí)行權(quán)、監(jiān)督權(quán)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xié)調(diào)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和運(yùn)行機(jī)制。權(quán)力配置的不合理,放大了相關(guān)群體的利益剝奪感,增加了章程實施的協(xié)調(diào)成本,成為諸多執(zhí)行難題的源頭所在。例如,問卷調(diào)查結(jié)果顯示,64所高校中,有累計72.1%的高校認(rèn)為大學(xué)章程執(zhí)行對落實辦學(xué)自主權(quán)“作用一般”或“作用比較小”,有累計64.1%的高校認(rèn)為大學(xué)章程執(zhí)行對保證教授治學(xué)的 “作用一般”或“作用比較小”。
“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制定出一部好章程不容易,將之實施好則更不容易。在依法治校的新長征路上,只有相關(guān)各方積極行動起來,正視并破除阻礙章程實施的各種要素,把章程的內(nèi)容和精神真正貫徹落實到辦學(xué)治校之中,才能早日建立起中國特色現(xiàn)代大學(xué)制度,才能充分激發(fā)和釋放制度在規(guī)范辦學(xué)、保護(hù)權(quán)益、促進(jìn)發(fā)展上的巨大紅利。
[1]符瓊霖.對教育部首批核準(zhǔn)的六所大學(xué)章程分析與建議[J].高校教育管理,2015(1):45-50.
[2]陳立鵬,等.大學(xué)章程研究:理論與實踐的探索[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集團(tuán),2012:188.
[3]丁煌.利益分析:研究政策執(zhí)行問題的基本方法論原則[J].廣東行政學(xué)院學(xué)報,2004(6):27-34.
[4]朱家德.權(quán)力的規(guī)制:大學(xué)章程的歷史流變與當(dāng)代形態(tài)[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13.
[5]朱家德.大學(xué)章程實施比制定更重要[J].中國高教研究,2016(6):65-69.
[6]黃曉玫.加強(qiáng)大學(xué)章程建設(shè),發(fā)揮制度杠桿效應(yīng)[J].中國高等教育,2014(3):29-31.
[7]余敏,付義朝.走向法治:大學(xué)章程讀本[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6:112.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10.013
G647
A
1004-0544(2017)10-0070-05
教育部政策法規(guī)司重大委托項目(JYBZFS2015004)。
陶光勝(1983-),男,湖北襄陽人,華中師范大學(xué)學(xué)校治理研究中心講師,湖北省教育政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付衛(wèi)東(1973-),男,湖北浠水人,教育學(xué)博士,華中師范大學(xué)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信息化與基礎(chǔ)教育均衡發(fā)展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副教授、碩士生導(dǎo)師,湖北省教育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責(zé)任編輯 李利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