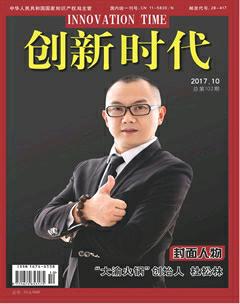淺談?wù)Z義指向理論及其對(duì)中學(xué)語(yǔ)文中歧義句教學(xué)的啟示
余麗華
摘要:在中學(xué)語(yǔ)文教學(xué)中經(jīng)常會(huì)遇到一些由語(yǔ)義指向引起的歧義,然而,利用傳統(tǒng)的中心詞分析法或?qū)哟畏治龇o(wú)法解決這種分歧。在西方尤其以美國(guó)描寫語(yǔ)言學(xué)為代表的各大語(yǔ)言流派的影響下,在20世紀(jì)80年代,我國(guó)漢語(yǔ)語(yǔ)法研究中出現(xiàn)了語(yǔ)義指向分析這種新的分析方法,這種方法對(duì)我國(guó)中學(xué)語(yǔ)文中歧義句的教學(xué)具有重大的指導(dǎo)意義。
關(guān)鍵詞:語(yǔ)義指向;語(yǔ)義指向分析;歧義句;中學(xué)語(yǔ)文教學(xué)
一、引言
以布龍菲爾德(L.Bloomfield)為代表的美國(guó)描寫語(yǔ)言學(xué)派的語(yǔ)法研究,重點(diǎn)在于對(duì)某一種語(yǔ)言或方言的語(yǔ)法規(guī)則作細(xì)微的、靜態(tài)的描寫;而喬姆斯基(N.Chomsky)所開(kāi)創(chuàng)的轉(zhuǎn)換生成語(yǔ)法學(xué)則重在從理論上探求人類的語(yǔ)言機(jī)制以及人類語(yǔ)言的普遍語(yǔ)法,并解釋這個(gè)普遍語(yǔ)法如何在一定的條件下生成為各種各樣的人類自然語(yǔ)言。前者可以說(shuō)是語(yǔ)言學(xué)研究中的開(kāi)山之作,對(duì)后來(lái)者進(jìn)行語(yǔ)言學(xué)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貢獻(xiàn)。后者在某種程度上說(shuō),意義則大于前者。他們代表的是兩種不同的研究方向,然而,這兩種研究不應(yīng)該是對(duì)立的,就研究對(duì)象來(lái)說(shuō),它們也有所交叉。因此,彼此應(yīng)該互相借鑒,相輔相成。在這里筆者特別要指出的是,不可忽視描寫語(yǔ)法學(xué)的存在和價(jià)值。描寫語(yǔ)法學(xué)還有它存在的價(jià)值,并有進(jìn)一步發(fā)展的必要,而在發(fā)展過(guò)程中,它也會(huì)不斷吸取其他語(yǔ)法理論的合理因素。應(yīng)該看到,在對(duì)某一具體語(yǔ)言的語(yǔ)法規(guī)律作深入、細(xì)致的挖掘和描寫上,它還會(huì)作出其他語(yǔ)法理論所無(wú)法完全代替的貢獻(xiàn)。目前我國(guó)的語(yǔ)法研究還是以描寫語(yǔ)法學(xué)為主,主要還是對(duì)漢語(yǔ)普通話或某一種方言的語(yǔ)法作細(xì)微的、靜態(tài)的研究、描寫,雖然現(xiàn)在也出現(xiàn)了對(duì)漢語(yǔ)普通話作宏觀的、解釋性的研究。本文所說(shuō)的語(yǔ)義指向分析就是描寫語(yǔ)法學(xué)里所運(yùn)用的一種分析方法。這是中國(guó)在20世紀(jì)80年代開(kāi)始出現(xiàn)的一種新的句法分析方法。
二、語(yǔ)義指向的含義、類型及其分析法的產(chǎn)生
1.語(yǔ)義指向的含義
語(yǔ)義指向分析法作為一種分析方法在語(yǔ)法學(xué)界雖已達(dá)成共識(shí),但對(duì)于語(yǔ)義指向的含義卻各有說(shuō)法。雖然學(xué)者們對(duì)語(yǔ)義指向的含義表述各異,但核心內(nèi)容是相同的,基本可以歸納為:語(yǔ)義指向就是句子中某個(gè)句法成分跟另外的句法成分之間的語(yǔ)義聯(lián)系,而這種聯(lián)系具有方向性和目標(biāo)性。成分所聯(lián)系的方向叫“指”,成分語(yǔ)義聯(lián)系所指向的目標(biāo)叫“項(xiàng)”。例如“我走累了”中的“累”所聯(lián)系的方向是“指”,所指的“項(xiàng)”是主語(yǔ)“我”。(李修尚,2009)
2.語(yǔ)義指向的類型
(1)從“指”和“項(xiàng)”的角度來(lái)看語(yǔ)義指向
大家互相幫助。(“互相”單指前面的“大家”)
南昌、景德鎮(zhèn)我們?nèi)チ恕#ā叭奔戎赶蚯懊娴摹澳喜⒕暗骆?zhèn)”,又指向前面的“我們”)
她們多半是英語(yǔ)系一年級(jí)的大學(xué)生。(“多半”既指向前面的“她們”,又指向后面的“英語(yǔ)系”和“大學(xué)生”)
(2)從句子成分的角度看語(yǔ)義指向
你砍快了,慢一點(diǎn)!(你砍+砍快了;補(bǔ)語(yǔ)的語(yǔ)義指向)
人也很多,圓圓地排成一個(gè)圈,不很精神,倒也整齊。(排成一個(gè)圓圓的圈;狀語(yǔ)的語(yǔ)義指向)
對(duì)于定語(yǔ)的語(yǔ)義指向,專門論述的不多,因?yàn)槎ㄕZ(yǔ)的語(yǔ)義一般都直接指向所修飾的中心語(yǔ)。盡管“語(yǔ)義指向一般是中心語(yǔ),但并不是所有的定語(yǔ)都指向中心語(yǔ)”。(李敏,1996)例如:
我要好好地逛一逛美麗的景德鎮(zhèn)。(美麗+景德鎮(zhèn))
(3)從語(yǔ)境影響的角度來(lái)看語(yǔ)義指向
根據(jù)目前漢語(yǔ)語(yǔ)法關(guān)于語(yǔ)義指向分析的研究情況考察,可以以分析中是否考慮語(yǔ)境因素的影響而使語(yǔ)義指向發(fā)生變化為依據(jù),把語(yǔ)義指向分為動(dòng)態(tài)和靜態(tài)兩大類型。我們?cè)诳疾煲粋€(gè)句子中某個(gè)成分的語(yǔ)義指向時(shí),孤立地從這個(gè)句子出發(fā),不考慮句外的語(yǔ)境等因素的影響,就可以直接分析出它的指向,而且這種語(yǔ)義指向一般是固定不變的,我們把這種語(yǔ)義指向稱為靜態(tài)語(yǔ)義指向。這種靜態(tài)語(yǔ)義指向包括沒(méi)有具體句外語(yǔ)境的所有句子,適合考察的句子成分是補(bǔ)語(yǔ)、狀語(yǔ)、定語(yǔ)、謂語(yǔ)動(dòng)詞等。如果我們考察分析某個(gè)句子成分的語(yǔ)義指向,需要考慮語(yǔ)境(主要是上下文)因素,那么語(yǔ)境不同,其語(yǔ)義指向也隨之改變,我們把這種語(yǔ)義指向稱為動(dòng)態(tài)語(yǔ)義指向,副詞的語(yǔ)義指向通常涉及動(dòng)態(tài)語(yǔ)義指向。
3.語(yǔ)義指向分析法的產(chǎn)生
現(xiàn)代漢語(yǔ)的語(yǔ)法分析法主要有成分分析法、層次分析法、成分層次分析法、變換分析法、語(yǔ)義指向分析法、語(yǔ)義特征分析法、配價(jià)分析法、語(yǔ)義成分分析法等。其中的語(yǔ)義指向分析法主要是從語(yǔ)義關(guān)系的角度來(lái)分析語(yǔ)法。語(yǔ)義指向分析法的產(chǎn)生與語(yǔ)法結(jié)構(gòu)自身的特點(diǎn)密切相關(guān)。任何一個(gè)句子的組成成分之間總是同時(shí)并存著兩種不同性質(zhì)的關(guān)系,即句法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和語(yǔ)義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但這種關(guān)系并非一一對(duì)應(yīng):其一,相同的句法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可以表示不同的語(yǔ)義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其二,不同的句法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可以表示相同的語(yǔ)義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語(yǔ)義指向分析產(chǎn)生的緣由首先在于結(jié)構(gòu)層次分析或者說(shuō)直接成分分析不足。格語(yǔ)法對(duì)語(yǔ)義分析是不完備的,因?yàn)樗谎芯恐^語(yǔ)動(dòng)詞同句中名詞性成分之間的關(guān)系,而不研究其他語(yǔ)義關(guān)系,例如偏正關(guān)系、述補(bǔ)關(guān)系等,因此要全面描寫、分析、解釋句法結(jié)構(gòu)的語(yǔ)義結(jié)構(gòu),還應(yīng)該進(jìn)行句法結(jié)構(gòu)的語(yǔ)義指向分析。語(yǔ)義指向分析不僅可以找出語(yǔ)義上有關(guān)系的成分,還能弄清句法結(jié)構(gòu)的語(yǔ)義網(wǎng)絡(luò),從而使人們正確理解語(yǔ)言片段。
三、語(yǔ)義指向分析法與歧義句教學(xué)
我們已經(jīng)知道語(yǔ)義指向分析法產(chǎn)生的緣由,那么到底什么是語(yǔ)義指向分析法呢?我們不妨先看幾個(gè)實(shí)例。例如“砍光了”的補(bǔ)語(yǔ)“光”在語(yǔ)義上指向“砍”的受事(雜草砍光了);“砍累了”的補(bǔ)語(yǔ)“累”在語(yǔ)義上指向“砍”的施事(我砍累了);“砍鈍了”的補(bǔ)語(yǔ)“鈍”在語(yǔ)義上指向“砍”的工具(這把刀砍鈍了);“砍快了”的補(bǔ)語(yǔ)“快”在語(yǔ)義上指向“砍”這一動(dòng)作本身(你砍快了,得慢點(diǎn)兒砍);“砍疼了”的補(bǔ)語(yǔ)“疼”在語(yǔ)義上有時(shí)可指向“砍”的受事,如“把他的腳砍疼了”,有時(shí)可指向“砍”的施事的隸屬部分,如“砍了一下午,我的胳膊都砍疼了”,因此這是一個(gè)有歧義的結(jié)構(gòu);“砍壞了”的補(bǔ)語(yǔ)“壞”在語(yǔ)義上有時(shí)可指向“砍”的受事,如“別把桌子砍壞了”,有時(shí)可指向“砍”的工具,如“他那把刀砍壞了”,因此這也是一個(gè)有歧義的結(jié)構(gòu)。歧義現(xiàn)象是指一個(gè)語(yǔ)言片段可以作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語(yǔ)義理解。歧義又叫作“同形”,一個(gè)著眼于內(nèi)容,一個(gè)著眼于形式,這是一個(gè)問(wèn)題的兩個(gè)方面。深入鏈接歧義現(xiàn)象,將有助于我們加深對(duì)漢語(yǔ)句法結(jié)構(gòu)復(fù)雜性、精細(xì)性的理解,同時(shí),對(duì)掌握句法結(jié)構(gòu)的分析方法也很有幫助。以上所說(shuō)的區(qū)別,就是補(bǔ)語(yǔ)語(yǔ)義指向的不同,即補(bǔ)語(yǔ)在語(yǔ)義上指向哪兒各不相同。可見(jiàn)所謂語(yǔ)義指向就是指句中某一成分在語(yǔ)義上跟哪個(gè)成分直接相關(guān)。通過(guò)分析句中某一成分的語(yǔ)義指向來(lái)揭示、說(shuō)明、解釋某一語(yǔ)法現(xiàn)象,這種分析手段就稱為語(yǔ)義指向分析法。endprint
語(yǔ)義指向最有效的領(lǐng)域就是對(duì)狀語(yǔ)和補(bǔ)語(yǔ)的分析,特別是對(duì)以下這些詞類或結(jié)構(gòu)的研究較為充分:表示范圍、程度或否定的副詞,如“最”“只”“就”“也“都”“才”“全”“不”“互相”“分別“又”等;作狀語(yǔ)的某些介同短語(yǔ),如“在”字結(jié)構(gòu)、“跟”字結(jié)構(gòu)等;復(fù)雜謂語(yǔ),如動(dòng)補(bǔ)結(jié)構(gòu)、連動(dòng)結(jié)構(gòu)等;特殊句式,如“比”字句、主謂補(bǔ)語(yǔ)句等。(楊紅,饒祺,2009)這里也主要以狀語(yǔ)和補(bǔ)語(yǔ)的語(yǔ)義指向?yàn)槔齺?lái)探討語(yǔ)義指向理論在中學(xué)語(yǔ)文教學(xué)中的應(yīng)用。在中學(xué)語(yǔ)文教學(xué)中經(jīng)常會(huì)碰到一些由語(yǔ)義指向引起的歧義,如果引入語(yǔ)義指向理論就會(huì)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
①戰(zhàn)士們?cè)跇琼斏习l(fā)現(xiàn)了敵人。
②戰(zhàn)士們?cè)跇琼斏峡吹搅碎L(zhǎng)江。
例①中的“在樓頂上”既可以指向“戰(zhàn)士們”(指“戰(zhàn)士們”在樓頂上,“敵人”不在樓頂上),又可以指向“敵人”(指“敵人”在樓頂上,“戰(zhàn)士們”不在樓頂上),還可以同時(shí)指向“戰(zhàn)士們”和“敵人”(指“戰(zhàn)士們”在樓頂上,而且“敵人”也在樓頂上),由于“在樓頂上”語(yǔ)義的多指性造成了歧義。例②則不同,一般情況下不可能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即長(zhǎng)江在樓頂上,也就是說(shuō),“在樓頂上”的語(yǔ)義一般不會(huì)指向“長(zhǎng)江”,只可能指向“戰(zhàn)士們”,這樣就不存在語(yǔ)義的多指性,因而例②沒(méi)有歧義。在一個(gè)句法結(jié)構(gòu)里,當(dāng)某一成分可以同時(shí)與其他幾個(gè)成分相關(guān)時(shí),就產(chǎn)生了語(yǔ)義多指性,因而會(huì)造成歧義,再看下面兩個(gè)例子:
③五個(gè)小學(xué)生就抬起了一百斤。
④五個(gè)小學(xué)生才抬起了一百斤。
例③“五個(gè)小學(xué)生就抬起了一百斤”有歧義,既可指這“五個(gè)小學(xué)生”,了不起—人不多,而且還是小學(xué)生,就可以抬挺重的一百斤,也可指這“五個(gè)小學(xué)生”不怎么樣,五個(gè)才抬起了一百斤。“就”的語(yǔ)義指向既可前指,又可后指。“就”的語(yǔ)義性質(zhì)是用來(lái)限定范圍的,這一語(yǔ)義性質(zhì)在語(yǔ)用蘊(yùn)含上的意義是“量少”。對(duì)這個(gè)例子兩種截然不同的理解就是從這兩方面派生出來(lái)的。當(dāng)“就”的語(yǔ)義前指時(shí),自然蘊(yùn)含著“人少”的意思;當(dāng)“就”的語(yǔ)義后指時(shí),自然蘊(yùn)含著“重量小”的意思。“五個(gè)小學(xué)生才抬起了一百斤”中的“才”的語(yǔ)用蘊(yùn)含義和“就”雖然相同,都有“量小”之意,但由于“才”的語(yǔ)義指向只能后指,不能前指,因此“五個(gè)小學(xué)生才抬起了一百斤”在語(yǔ)義指向上沒(méi)有歧義性,只能指這“五個(gè)小學(xué)生”不怎么樣,五個(gè)才抬起了一百斤。
在中學(xué)語(yǔ)文教學(xué)中,為了讓學(xué)生更好地掌握漢語(yǔ),經(jīng)常使用句式變換的方法,讓學(xué)生通過(guò)句式變換掌握其中的規(guī)律,如讓學(xué)生把“把”字句變成“被”字句(把酒喝光了—酒被喝光了),把肯定句變?yōu)殡p重否定句(我一定要努力學(xué)習(xí)—我不能不努力學(xué)習(xí)),把動(dòng)補(bǔ)結(jié)構(gòu)變?yōu)橹貏?dòng)結(jié)構(gòu)(喝醉了酒—喝酒喝醉了),等等。有時(shí)候?qū)W生的變換很順利,但有時(shí)候會(huì)比較麻煩,這其中有些麻煩就與語(yǔ)義指向有關(guān)。這里以句首受事轉(zhuǎn)換為句尾受事和重動(dòng)句變?yōu)榘炎志渑c被字句為例來(lái)說(shuō)明語(yǔ)義指向理論在句式變換中的應(yīng)用。(楊紅,饒祺,2009)首先看句首受事轉(zhuǎn)換為句尾受事的例子:
⑤這些地方我去過(guò)—我去過(guò)這些地方
⑥這些地方我都去過(guò)—我都去過(guò)這些地方(不能作此變化)
⑦這些地方我們都去過(guò)—我們都去過(guò)這些地方
上面幾個(gè)例子都是把受事位于句首的句子變?yōu)槭苁挛挥诰湮驳木渥樱徊贿^(guò)例⑤和例⑦能夠變換,而例⑥不能作相應(yīng)的變換,原因就在“都”字的語(yǔ)義指向上。“都”的語(yǔ)義一般是前指的(只有在后指對(duì)象含有疑問(wèn)代詞的時(shí)候才能后指,如“都誰(shuí)來(lái)了”中的“都”指向“誰(shuí)”),當(dāng)“這些地方”后移后,“都”前面的成分只有“我”,而“我”又是單數(shù),和表“總括”的“都”在語(yǔ)義上不相匹配,“都”的語(yǔ)義指向也就是落空的,所以不能成立。如果把“我”替換為“我們”,那么這樣的變換就成立了,因?yàn)檫@時(shí)的“都”的語(yǔ)義仍可指向表復(fù)數(shù)的“我們”。再看重動(dòng)句變?yōu)榘炎志浜捅蛔志涞睦樱?/p>
⑧劉老師喝醉了酒
劉老師喝酒喝醉了
劉老師把酒喝醉了(不能作此變化)
這點(diǎn)酒就把他喝醉了
⑨劉老師喝光了酒
劉老師喝酒喝光了(不能作此變化)
劉老師把酒喝光了
這點(diǎn)酒就把劉老師喝光了(不能作此變化)
上面兩組例子,第一組既可以變?yōu)橹貏?dòng)句,也可以變?yōu)榘咽苁绿岬骄涫椎摹鞍选弊志洌荒茏優(yōu)槠胀ǖ摹鞍选弊志洌坏诙M卻可以變?yōu)槠胀ā鞍选弊志洌荒茏優(yōu)橹貏?dòng)句和受事提到句首的“把”字句。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第一組中的補(bǔ)語(yǔ)“醉”指向前面的主語(yǔ)“他”,這時(shí)就可以變?yōu)橹貏?dòng)句和受事提到句首的“把”字句,因?yàn)檫@兩種句子都要求補(bǔ)語(yǔ)“醉”用來(lái)指向“他”,類似的例子還有如“他吃膩了香蕉”等;而后一組的補(bǔ)語(yǔ)“光”指向后面的賓語(yǔ)“酒”,這時(shí)就可以變?yōu)槠胀ǖ摹鞍选弊志洌驗(yàn)槠胀ǖ摹鞍选弊志渲械难a(bǔ)語(yǔ)“光”要求用來(lái)指向“把”的賓語(yǔ)“酒”,類似的例子還有如“他打破了玻璃”等。
在中學(xué)語(yǔ)文教學(xué)過(guò)程中還會(huì)遇到許多諸如此類的歧義結(jié)構(gòu),它們都具有各自的性質(zhì)和特點(diǎn),我們可以運(yùn)用不同的方法去分化它們,如層次切分法、成分定性法、變換分析法等。但是有些句子的歧義結(jié)構(gòu)無(wú)法用這三種方法加以分化。例如“你別鋸壞了”。這個(gè)句子有歧義,既可以表示為(a)“你別把木頭鋸壞了”,也可以表示(b)“你別把鋸鋸壞了”。對(duì)于這種歧義,我們無(wú)法用上述三種方法加以分化,無(wú)論是從層次構(gòu)造、句法關(guān)系上看,還是從句式變換上看,在表示這兩種意思的時(shí)候,都是一樣的,其格式都是“NP+別+V+A+了”。分析這種歧義結(jié)構(gòu),可以用語(yǔ)義指向分析法。根據(jù)語(yǔ)義指向分析法,我們認(rèn)為產(chǎn)生這一歧義的主要原因是補(bǔ)語(yǔ)A(壞)的語(yǔ)義指向不同。表示(a)的意義時(shí),補(bǔ)語(yǔ)A(壞)語(yǔ)義上指向V(鋸)的受事“木頭”;表示(b)的意義時(shí),補(bǔ)語(yǔ)A(壞)語(yǔ)義上指向V(鋸)的工具“鋸”。這樣就分化了“你別鋸壞了”這一歧義結(jié)構(gòu)。(李修尚,2009)
四、結(jié)語(yǔ)
語(yǔ)義指向理論及語(yǔ)義指向分析法對(duì)于語(yǔ)文教學(xué)具有重要的指導(dǎo)意義,我們可以在教學(xué)中適當(dāng)運(yùn)用它們來(lái)指導(dǎo)我們的教學(xué)實(shí)踐,或許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但是對(duì)這一理論的研究目前還未形成一個(gè)完整的結(jié)構(gòu)框架,還需加深研究的力度和深度,以便更好地服務(wù)于語(yǔ)言研究和語(yǔ)言教學(xué)。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