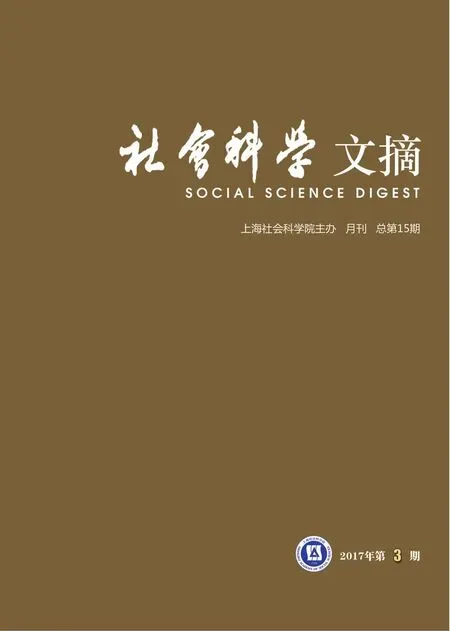當代中國的“私人信仰”陷阱
文/李向平
當代中國的“私人信仰”陷阱
文/李向平
關于信仰問題的社會學研究,國內(nèi)學術界尚屬少見。西方宗教學或宗教社會學對于信仰的研究比較豐富,但大都基于宗教類別而集中于某一種宗教信仰的研究,或者是把信仰置于宗教領域來加以研究。至于對中國人信仰方式的社會學研究,則更加不足了。本文所論之信仰,既有源自于儒教“天地君親師”、“天地圣親師”的信仰結構,亦有基于佛道教乃至民間信仰的傳統(tǒng)信仰,及其以宗法家族關系為基礎的祖宗祭祀,進而從其“私人信仰”方式及其當代影響出發(fā),梳理中國社會中自古迄今“私人信仰”的傳統(tǒng)模式及其現(xiàn)代實踐特征,探討中國社會中“私人信仰”為何成為一種陷阱,旨在揭示當代中國人走出“私人信仰”陷阱的諸多可能性。
“私人信仰”問題的提出
中國人的“私人信仰”,主要是通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信仰方式形成了,既能從私我的修身、齊家形式延伸、拓展到治國、平天下的公眾領域,把個體私人納入到天下大同、敬天順人等普遍性信仰方式之中;同時又能夠建構成為以公控私、以家天下、公為正祀、私為淫祀的信仰控制方式。其既具有宗教特征、卻又不局限于宗教,十分獨特而又難以把握。
一方面,個體私人的信仰能夠通過公眾權力而得以建構成為公眾信奉的對象;另一方面,私人的信仰卻又無法超越公眾權力的控制。這里,關鍵在于這個所謂的私人是家國社會之象征、眾所崇拜的圣人,還是庶民百姓。某一私人一旦順天應人而成為家國象征或者圣人,就會被建構成為天下的、普遍的信仰對象,原來局限于私人的思想、觀念等等也會通過家國權力的建構而成為公開的信仰內(nèi)容。于是,就國家正祀對于淫祀的控制而言,那些原先不在國家祀典、不具公眾意義的私人信仰也就具有了特別的權力意義,成為防止私人信仰侵蝕公眾信仰,危害家國信仰結構的力量。
中國信仰傳統(tǒng)中公私關系的界限模糊,導致了國家權力秩序與宗教信仰之間的復雜關系,它們始終糾纏在一起。那些能夠被權力所界定的宗教信仰類型,能夠獲得一種“正祀”之名號,獲得國家、地方權力的認同,建構其在地方社會中的影響力,進而成為權力建構秩序的有效資源。而那些無法被國家、地方權力所認同的信仰類型,則只好成為一種“正祀”之外的“淫祀”,僅限于一地一隅、一人一家。可見,國家權力與宗教信仰雖屬于兩大領域,但其實是一種分隔而又意義交叉、資源各異卻又秩序共享的關系,由此構成了信仰等級關系、信仰方式中的公私矛盾。
這一矛盾的本質(zhì),并不在于是有神信仰、還是無神規(guī)定,關鍵在于中國人按照什么方式在建構神人關系、組織信仰方式、安排自己的精神與靈魂,關鍵在于國家權力采用什么方式來獲取自己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在任何地方,宗教利益都不過是社會利益和道德利益的象征形式”, 在中國,公私之間的矛盾及其整合,恰好是這一關系的呈現(xiàn)。所以,中國社會中的宗教信仰,并非簡單對宗教的選擇與信仰,而是宗教信仰在實踐過程中如何嵌入現(xiàn)實權力關系并發(fā)揮總體倫理的治理機制,如何處理公眾信仰與私人信仰之間相互整合、彼此沖突而又意義交叉的公私關系。正是因為公私界限的模糊或混淆,中國人在信仰層面的表達總是將其看作是一種精神生活中的私人象征或私人欲望的補償。在很大程度上,神靈的崇拜與信奉對于許多中國人來說,其實是權力、財源和人際關系的象征性處理方法及在社會競爭中的象征性補償。通過宗教信仰中人與神、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與互動,作為宗教信仰者的個人,希望在其信仰實踐中找到歸屬與認同,基于人與神而來的人人關系希望得到一定的資源累計與價值關聯(lián)。希望獲取家國資源者,大多會追求私人信仰方式的公共權力形式;相反,庶民百姓就只好局限于“神事”,不管正祀與淫祀,在神圣的崇拜之中求得私己欲望的具體實現(xiàn)。
這就是信仰方式層面中國社會公私矛盾最基本的體現(xiàn)。這一矛盾致使中國社會中宗教信仰層面的神人關系及其內(nèi)在表達,始終存在家國權力與私人信仰之間的內(nèi)在隔離。這其實是一種社會學意義上的“兩向性”,其在最廣泛的意義上是指對于指定給社會中的一個身份,或一組身份的態(tài)度、信念和行為之相互沖突的規(guī)范期望; 它在最狹窄的意義上,則是指某單一身份之單一角色所必須同時滿足的相互沖突的規(guī)范期望。它們具有內(nèi)在的價值同一性,卻又在具體實踐形式層面充滿著矛盾,總是存在著彼此替代的沖突。
在此,我們將社會角色視為一個由規(guī)范和反規(guī)范構成的動態(tài)組織,而不是將它視為一個由各種居于主導地位特征構成的復合體。主要的規(guī)范和次要的反規(guī)范輪流制約著角色行為,從而造成了兩向性格。這種兩向性格,其實就是一組相互聯(lián)系且存在對立關系的存在特征。如傳統(tǒng)中國信仰中有關受命與革命、合法與非法、公己與私己、正統(tǒng)與邪惡……神人互惠關系、天命人道關系、人際倫理關系、和諧與沖突、分裂與統(tǒng)一等等,均在不同程度上源自于這種規(guī)范與反規(guī)范的矛盾、沖突,因而具有了雙重性質(zhì)。此兩向性沖突反反復復地、自始至終地制約著中國歷史上神或人的角色行為,制約著在此兩向性關系之中的具體呈現(xiàn),亦公亦私、公私混淆、以公控私、假公濟私、大公無私、以私害公……于是,在國家、社會、個人、自我等層面都模糊了當代中國社會的公私界限。
即特殊、即普遍的私人信仰
中國民眾提及宗教信仰之時,常常會說的一句話就是“宗教信仰就是教人勸善的、做好事的”;即便是基于中國人最持守、最習慣的祖宗崇拜,亦會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句話中喪失了最普遍的信仰認同。表面上很簡單的一句話,實際上道出了中國人看待宗教信仰問題及宗教的道德化與私人化特征。盡管這種宗教信仰的話語表達并無問題,卻深刻地呈現(xiàn)了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局限于私人及其精神領域的實踐特征,即將宗教信仰視為個人道德及其行動實踐的某種標準,構成了一種特殊主義的私人信仰類型。在此影響下的中國人常常要以個人的道德信仰去處理整個政治與社會問題。然而,普遍通用的道德與信仰卻缺乏一個共識與共享的標準。
中國傳統(tǒng)之中存在著特殊主義與普遍主義的內(nèi)在矛盾,主要表現(xiàn)為天下主義(公己)與以修身齊家為倫理本位(私己)之間的關系,即是雙重建構,也是兩向沖突。這就是中國式信仰及其理論特征很不同于西方之處。普遍與特殊的兩種取向,在公己與私己的雙重關系之中都能夠兼顧,都能夠偏向。能否實現(xiàn)呈現(xiàn)這個特征,關鍵在于處于這一公己與私己矛盾關系的個我,是圣化的個人,還是普通的庶民百姓。能夠實現(xiàn)這個轉換、交換的,唯有圣化的強人。
盡管天命信仰有其固有的私人特征,但其信仰的社會本質(zhì)是一種特殊主義的價值,這種天命信仰能夠經(jīng)由湯武革命中或受命、或革命的權力運作機制,轉變?yōu)樯鐣傮w整合的媒介。個人的天命信仰一旦經(jīng)由湯武式革命的成功而成為國家主人,其所具有的公共主義特征,便會使整個社會成員在天命眷顧的價值關懷基礎上,不分界限被權力整合起來,形成了共同的普遍主義信仰連帶,此時此刻,個人的天命信仰便會擴大到私人道德、情感的界限之外,呈現(xiàn)了天命信仰私人性與國家權力公共性的相互整合。所謂“天下即國家”的概念,以及“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其深層意義即是把一種“祭祀”為特征的信仰方式、依靠權力、暴力或武力(戎)建構為天下國民的信仰。天命信仰本位私人信仰方式的這種特殊主義,由此而具有了普遍主義的權力整合功能。但與此同時,在天下或者宗族關系之外的場合,中國人常常要采取特殊主義的方法,使用特殊主義的方法來獲得普遍主義的權力整合及其道德要求。
在中國語境中,特殊主義與普遍主義之間不存在明顯的界限。天下的天命觀念和天命信仰,是普遍主義;而依據(jù)關系本位而來的資源占有與利用,神人交往中的交換互惠關系,則是特殊主義。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之間的整合,關鍵就在于這一重要的關系機制。關系能夠將普遍主義轉換為特殊主義,亦能夠從特殊主義中體現(xiàn)出普遍的意義。依著中國社會中這種獨特的關系主義機制,中國社會構成了一種普遍的特殊主義,它既是特殊的,亦是普遍的。它們更是特殊的普遍主義,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權力更替中、在以公控私或假公濟私的倫理策略中得以不斷地復制。
這就是中國社會、中國宗教信仰方式的特殊之處,而非一般的特殊主義,即具有普遍主義特征的特殊主義。私我能夠通向天下,大同歸于一家正統(tǒng)。就此來理解中國宗教、信仰,確實是難以定義、難以理解的。
中國信仰的私人傳統(tǒng)
就儒家信仰來說,儒教之論“公”與“私”,雖與西方近代所謂的“公領域”和“私領域”不盡符合,但它們之間還是具有相通之處。可以把“修身、齊家”劃歸為私領域,而把“治國、平天下”劃歸為公領域。這兩個領域之間雖然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但同時也存在著一道明確的界線。公領域不再是私領域的直接延伸,但兩個領域還是互有影響的。
這兩個領域實際上是可以彼此轉換、相互整合的兩個領域,其間存在著一層信仰關系,比如,“得一人即可得天下”的信仰傳統(tǒng),即是對私己信仰的強調(diào),同時也是公己領域源自私己信仰的互動規(guī)則。它們之間的關系卻非如余英時所言,與西方政教分離相類似。其特點與霍布斯在《利維坦》一書中所說的極其類似:專制政體中的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基本一致,本無所謂的分合關系。專制政體的利益整合了所有公私利益。
為此,“私人信仰”方式似乎就是一種權力技術,處于修齊治平模式中的這個以“私人”為中心的中國信仰,包括后來的佛道教信仰,究其正統(tǒng)的形式而言,的確是圣人君子各個按照其角色關系的期待和要求而體現(xiàn)出來的所謂宗教信仰,而非一般凡夫俗子的信仰方式,所以是一種服從于個人角色關系的信仰方式。它的非制度化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即是一種權力類型,一種行使公己權力的軌道。私己的信仰方式既是公己權力得以實現(xiàn)的基礎,也是私己化信仰方式走向公己、國家、天下生產(chǎn)的精神動力,進而導致了信仰者個人不可能接受天命信仰的約束,把天命信仰轉換成為一種至上的約束規(guī)則,其角色關系也無法定義清楚,最終就以其私人德性來詮釋天命、天性,無法呈現(xiàn)出應有的結構性意義。
“私人信仰”在這樣一種社會結構之中,真正擔心的倒不是“私人信仰”的非正當性或非公共性。它總是在期待著自己的信仰方式和內(nèi)容層面能夠合法化或公共化。這些“私人信仰”或私人型象征資本的擁有者總是在希望以自己“受命”的“越位”形式,以促使自己的身份改變,導致信仰的方式能夠合法公共化。這就構成了“私己信仰”方式所內(nèi)涵的天生的可能性,公私雙向式的實踐方式。所以,信仰方式的公私之間盡管存在差異,但是其信仰規(guī)范及其形成的權力秩序則是一以貫之,不用改變;信仰對象始終一致,沒有意外。
“信私不信公”的私人陷阱
時下,人們極為關注的信仰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宗教管理的法治化要求,宗教-信仰價值的公共性、社會認同等問題,應當就出現(xiàn)在固有的公共宗教與私人信仰張力之間所變異出來的宗教-社會領域,尤其是表現(xiàn)在1980年代后在國家與個人間的新生地帶所呈現(xiàn)出來的信仰方式變遷領域中。
這是中國當代社會所獨有的信仰社會學現(xiàn)象。它導致了中國宗教的發(fā)展,在如何進入法治化建設領域的問題上,不得不制約于國家、政統(tǒng)的神圣化要求以及“私人信仰”的群體性、或組織性的表達路徑。為此,公共宗教、“私人信仰”以及信仰群體——即宗教組織的制度化,由此表現(xiàn)為政統(tǒng)信仰、“私人信仰”、社會信仰之間的三角變量關系。它們之間的大小、強弱、寬窄關系的任何變動,都會影響或制約了信仰方式與中國信仰、中國社會宗教發(fā)展的內(nèi)在關系,特別是制約了中國信仰方式、宗教工作的社會化、中國宗教的公共性表達及其表達方法。
因此,我們把宗教需求視為“私人信仰”之表達所必需的組織資源、信仰群體組織化必須具備的合法性條件、中國人的信仰如何神圣化等的基本要件。這些與中國宗教-信仰緊密相關的神圣需求內(nèi)涵,實際上就構成了當代中國社會緊缺的神圣資源。而這些神圣資源在國家、私人和社會三大層面之間的分配和使用狀況,客觀上就決定了國家、社會、個人對于神圣資源的不同需求及其層次結構,從而打造了當代中國“私人信仰陷阱”、“宗教社會化”、“宗教法治化”的特殊語境,最后也構成了當代中國宗教的公共性表達困境。
走出“私人信仰陷阱”的可能性
從信仰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出發(fā),一個抽象的信仰概念可被分離出若干層次,政治信仰、傳統(tǒng)信仰、宗教信仰、文化信仰、民間信仰、民族信仰……。當然,任何信仰首先便應該個人的信仰,基于臣民、國民、公民自己的精神選擇,至于本文所論的“私人信仰”方式則是那種無法進入公共領域或者是被限制在公共權力之外的信仰方式。
其實,任何一種宗教強調(diào)中國人全都信仰該宗教的說法,總是難免“私人信仰”的局限,最終陷入總體崇拜的權力陷阱,無法拓展出信仰者個體理性的建構路徑。這種從私人到個體理性的最后改變路徑,主要的并不是在于精神信仰的改變,而是在于“私人信仰”、權力表達方式的雙向改變,在于權力崇拜的制度設置必須取得以法人團體的形式、專業(yè)化、制度化的形式,進而真正實現(xiàn)宗教生活、信仰方式的現(xiàn)代團體組織形式。當宗教、信仰成為個人、公民之精神權利的時候,國家權力理性化以及中國社會真實祛魅的過程,就可以基本告一段落了。
盡管,具有民法意義特征的私人領域及其建構在當代中國變遷中尚需一個過程,但那些以“私人信仰”為紐帶的團體、組織,則能促使社團行動及“私人信仰”轉變成為是一種現(xiàn)代社會認可的交往結構及其行動邏輯,兼顧信任信徒和公民交往的雙重身份,進而支撐“私人信仰”及其實踐的權利,構成一種“制度化的個人主義”、或者實“團體化的私人信仰”,從而把“私人信仰”真正變成私人的精神權利,即不再局限于神秘的身體治理、心性凈化及其神秘認同方式。
因此,中國信仰中公私關系的調(diào)整,將涉及中國信仰與社會結構在未來的進一步變遷與改革。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摘自《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7年第1期;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民間信仰研究”(10&ZD113)的階段性成果,研究工作獲“汕頭大學文學院基督教研究中心 ”資助,編號為:STUCCS201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