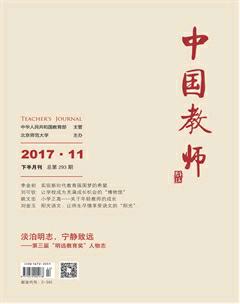永無止境的“問題化學習”研究之路
王天蓉
記得是2002年的秋天,我去祝智庭教授那兒匯報幾個信息化教育基地的研究進展。在他的辦公室里,他給我看了他在寶山實驗小學聽課的記錄,是一位數學老師(周吉)設計的“有趣的余數”,教學過程的設計是一個從解決老問題到解決新問題,再到解決疑難題的闖關游戲。他跟我解釋,這是他看到的關于自己“問題化學習”猜想的實踐例證。接著他補充,如果最后讓學生自己編題目則更好,也許還會發現新的問題。祝教授說,創新教育需要大量實踐來驗證,目前他的想法只能算是一個猜想。他邀請我參加該課題,利用我具有一線教研實踐的優勢,在中小學各個學科開展問題化教學實驗。
當時我的腦子里沒有多少關于問題解決學習的認知背景。唯一的印象,就是關于加涅的累積學習理論中關于智慧技能的類型:辨別、概念、規則、問題解決(高級規則)的學習。于是,我回去進一步查閱了學習理論中關于問題解決的定義,發現與祝老師所談的“解決老問題、解決新問題、解決疑難題、發現新問題”里的問題解決在內涵上有很大的差異。再說,諸如“是什么”“為什么”這類的問題也許還沒有涉及學習論中的問題解決。“是什么”的問題也許只涉及事實性的知識,還不涉及思維的高級層次,即問題解決。
由于受到這個問題的困擾,我并沒有馬上開展實踐。
祝教授后來解釋說:可以說是解答問題,是一種廣義的問題解決。
于是我開始尋求研究的伙伴,我問他們在教學中是否思考過這些問題,他們說沒有刻意的想過,但可能碰到過,我建議他們做教學設計。
我先做了一份問題類型的基本說明。包括是什么、為什么、怎么樣、假如、由何的說明,還賦予了案例。如何區別老問題、新問題與疑難題呢,我遇到了困難。2002年的冬天,我們在月浦新村小學一個溫暖的會議室中進行了問題化學習的第一次研討,基本確立了以“解決老問題—解決新問題—解決疑難題—發現新問題”為學習鏈的設計模式。同年12月,在祝教授的指導下,我們申報了課題“基于網絡的問題化學習”,結果被立項為全國教育科學“十五”規劃國家重點課題。這是一個非常意外的事件。但是,既然被學界認可了它的價值,就得更好地去做,而且,我們在研究中越來越意識到問題化學習在教學中的意義。
在問題化學習研究的道路上,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我們不停地遇到問題,我們也不斷地探索和解決。
比如,在課堂中,我們發現教學路徑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問題鏈的設計也不是一成不變的:1.可以將任何一鏈作為學習切入口,可以從解決老問題開始,也可以從解決新問題或者解決疑難題開始,甚至從發現新問題開始。有的時候學習需要更加穩健,而有時則需要一些懸念,激發學生的探究欲望。這完全要根據學生的情況、教學內容的特點等決定。2.學習中,不一定按照“解決老問題—解決新問題—解決疑難題—發現新問題”的順序進行,鏈中的每一環不是固定不變的,可以隨意組合。3.問題化學習鏈不一定是完整的,一堂課或一個教學單元,不一定包含解決老問題、解決新問題、解決疑難題、發現新問題這些所有的學習類型,要根據具體教學而定。
由此,在數學課堂的實踐中發現了單式完全循環、單式不完全循環和、復式循環幾種變式。而在OM綜合領域:我們按照開放性程度把問題化的框架梳理成預設型、生成型與折中型三種變式。
而且我們還發現另一個問題:有些問題對于這個學生來說是老問題,而對于另一個學生卻是新問題。所有的這些實際情況都需要教師在教學中靈活處理,需要用更彈性的藝術去應用基本模式,用變通的方式創造教學中的變式。
……
在做了很多的課堂探索之后,我們的研究卻碰到了困難。困難不在于如何去做,因為按照教師的實踐智慧,他們通常都知道如何去做,也感覺得到效果,但卻很難將他們的做法與效果之間建立清晰的因果關系,因為具體做法的內在機理并不像提出假設那樣簡單,它還有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比如教師用了“解決老問題—解決新問題—解決疑難題—發現新問題”的問題鏈學習模式開展教學,也明顯地感受到學生對解決同類問題(即便是變化問題情境)的進步,但是否就是因為這種模式在起作用,還是因為教師本身對教材的鉆研更深入了?而且,通常教師都不樂意做實驗研究,因為他們覺得自己一共帶兩個班級的課,明明預計到新方法對學生更有利,為什么還要放棄另一個班,如果老方法不好,難道自己再花時間去補嗎。而讓不同的老師做比較,是否做實驗的那個老師以及他班的學生就有一種心理暗示呢?
為了追求研究的科學性,我們在數學學科就實施問題鏈學習模式對學生解決新問題的能力做過一些實驗研究。在做的過程中,對樣本的科學性、命題的準確性、統計方法的取舍,都對自己提出過質疑。也有做出顯著差異的,也有無差異的。但問題是,即便是同樣的實驗方案,不同的老師對于同等的學生,做出來的效果也不盡相同,況且,是否選擇的就是同等的學生,也是要打問號的。
我想,我們不拒絕量的研究,但它必須恰當的用,當那些學習行為可以明確測量并可控時,科學的求證也許是有效的。但我們的課題大多涉及高級思維,其內在的條件本身就夠復雜,做量的求證就一定要非常小心。顧泠沅老師的建議是雙管齊下,可以適當地做一些實證報告,但在無法求證的情況下,可以用大量的事實進行描述性說明,因為那更符合基層教師的特點……
走到今天,圍繞“問題化學習”的研究,我們團隊持續了14年,經歷了7個研究階段:教學設計起步、深入學科的實踐、探索課堂形態、研究學生學習、基于學校的實踐、區域整體架構與推進、創建母體學校全面改革實驗。我想與大家一起分享的體會是:研究仿佛無法結束,因為每一位老師都在他的課堂中發現了新的研究點,他們(她們)在不斷探索的過程中倍感欣慰,像語文組的蔡玉銳老師與唐秋明老師,當她們看到課堂里學生積極提問時,它所激活的生命的涌動與智慧的生長,讓人覺得是那樣的生生不息。她們表示希望帶領自己的徒弟或同伴能夠一起進行新一輪的實踐。而數學組的顧峻崎老師,他會在電話那頭帶著一份沖動,告訴我們,他希望有一種新的嘗試,希望課題組的老師一起過去聽他的課,和他一起“爭論”,然后大家就四面八方地過去支援他……我想,也許大家喜歡的是這樣一種智慧的碰撞,這樣一種實實在在的課堂實踐,這樣一個民主的活力團隊……當所有的這些都變成是一種自發行為的時候,也許超越了教育研究本身。
在那個難以忘卻的激情燃燒的歲月,為了共同的旨趣與理想,我們相聚在共同求索的道路上。交流與碰撞催生了更多的智慧;協作拓展了我們專業的視野,互助則讓自己擁有更多的歸屬感,而做中學,則是最好的行動方式與學習法則。
回味求索之路,我們感慨地發現:如果我們只看重研究的結果,那么這種結果很難催生出新的探索;如果我們更關注探索的歷程,那么這種歷程會讓我們在啟示與頓悟中找到新的實踐之路。
在探索中獲得啟迪是人生的體驗,也因此豐富了自己對人生的感受。
研究永無止境,就好比我們的問題化學習,永遠在發現問題中解決問題,又在解決問題中發現問題。沿用英國哲學家波普爾的話,我們的探索永遠始于問題,終于問題,越來越深入的問題,越來越能啟發新問題的問題。
責任編輯:肖佳曉
xiaojx@zgjszz.cn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