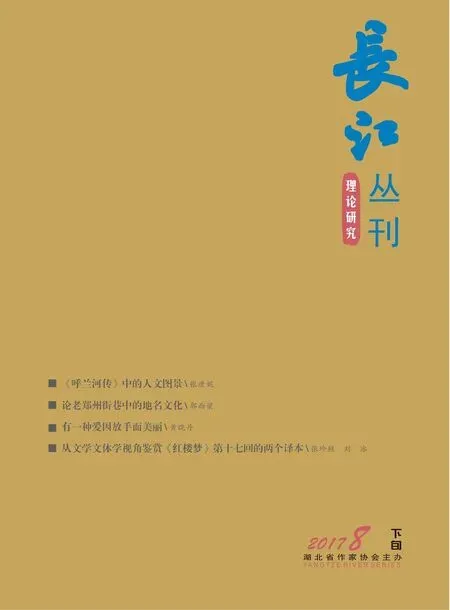簡析網絡環境下的網民群體
吳 敏
簡析網絡環境下的網民群體
吳 敏
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截止2016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已達7.10億,互聯網普及率為51.7%,且網民數持不斷上升趨勢。網民群體在社會中的影響越來越大,發揮著愈發強大的集體力量。他們在種種網絡群體事件中推濤作浪,其影響不容忽視。本文試圖從微博事件中分析網民群體的特征,并探討其形成原因。
網民群體 微博事件
勒龐認為所謂群體并不是普通意義上的大眾或群眾,許多人偶然集合在一起,即使人數再多也不構成群體。群體指的是受某一激情事件、刺激性意見而聚集在一起,為某個目標或某些精神需求而有所行動的人。[1]在網絡世界中,充斥著因為各種事件而聚集在一起的網民,網民雖然不能聚集在一起,但他們因為共同關注某一話題,具有共性,稱為群體。網民群體是由兩個或者更多的網民為了滿足某種目的、實現某一目標而聚集在一起,彼此互動的整體。網絡群體也有“烏合之眾”的某些特征。
一、“網民群體”的一般特征
(一)個性與理性消失,沖動與從眾滋長
勒龐認為,個性的消失是群體形成的最初特征。有意識的個性消失,無意識的個性得勢。群體行為因不受大腦控制而在行動中做出非理性行為,呈現出沖動、易變、急躁和偏執的特征。[1]在網絡生活空間中,信息傳播的低門檻使得傳播者魚龍混雜,信息混淆雜亂,網絡群體因群體智力低于個人智力而失去正常判斷力易受其影響,執拗偏信某一觀點,行為多為不理性。在藝人王寶強離婚事件這一網絡群體事件中有明顯表現。2016年8月14日王寶強在微博上發布了離婚聲明。聲明稱妻子馬蓉出軌經紀人宋喆。接著在短時間內各媒體、網絡大V從各種角度報道離婚事件。網友評論一邊倒,都在痛斥出軌方。當事人馬蓉和宋喆在事件爆出后一直隱身,網友瞬間化身王寶強最堅實的后盾,滿世界尋找馬蓉宋喆。出了不少鬧劇,因為和宋喆同名,微博名叫宋喆同學的成了網友炮轟的對象,網絡暴力不絕于耳。更有甚者一位聲稱王寶強粉絲組團從北京到大連抓宋喆,在大連找了一天未果遂返回。王寶強離婚事件本是明星的私事,但在媒體的渲染和網民的過分關注下成為全民茶余飯后的熱點。部分網友對于此次事件的主角更是群情激憤,恨不得親手抓住并對其施加暴力才能發泄內心的憤怒,但整件事情無論當事人誰對誰錯,都是他們的私事,在媒體的不斷報道渲染中,缺乏理性的網友瞬間被“正義”支配,一個個口誅筆伐。因為在聲討中找到共鳴,失去對于事件的獨立思考,理性消失,沖動助長了非理性行為。由此彰顯出網民群體易變且沒有理性支配行為的特征。
(二)易受暗示,輕信謠言
網民群體相對于現實群體而言,更易受暗示,輕信謠言。新媒體的發展,使得信息傳播從傳統媒體時代的單向獲取到新媒體時代的雙向信息互動,在網絡世界,網友不僅可以輕易獲取信息,也可以通過簡單的編輯成為信息的生成者和傳播者。這種信息互動使得受眾對其傳播的信息深信不疑,在此過程中缺乏理性思考進而采取不理智行為。周子瑜事件始于黃安微博舉報在韓國活動的臺灣藝人周子瑜是臺獨。此事件不斷發酵,一石激起千層浪,激起網友強烈的“愛國情懷”。臺灣媒體三立新聞趁機造謠聲稱挪威和瑞典支持臺獨,不少網民在此暗示下,未經考究信息的真實性與正確性就攻占了挪威和瑞典駐華官方微博,最終致使挪威和瑞典官方正式發聲,堅持一個中國立場。[2]在此事件中網民群體表現出極度的熱忱,打著愛國的旗號討伐“臺獨”,但實質上其行為娛樂性意味更濃,行動本身沒有起到任何實質性作用,且在行動過程中暴露出網民群體立場不堅定,輕信謠言的特征尤為明顯。
(三)感情的夸大化和極端化
群體雖然有著沖動和多變的特質,但是群體并不能稱為不道德,甚至可以說他們的行為都是以道德、正義的名義進行的。網絡群體以公平正義為道德信仰,為網絡事件的受害者伸張正義是他們的使命。如眾所周知的藥家鑫事件。網絡上對藥家鑫口誅筆伐,認為其是道德的敗壞,高呼懲罰藥家鑫。一旦有人站出來說出與公眾所持相悖的言論,便會破壞網民群體心中對公平正義的信仰,成為眾矢之的,激起網民群體的圍攻。西安五位教授聯名呼吁免除藥家鑫死刑,認為此案的審理是在一個很不公平的輿論環境中進行的,但卻被網友認為是想借此炒作,輿論喊殺聲一片。網民認為藥家鑫把普通的交通事故變成故意殺人案是缺乏人性的舉動,如果不判處最重的刑罰就是意味著縱容犯罪,這種極端的道德信仰是靠“暴力”維持的,各種情愫被放大,相互傳染,進而極端化。
二、網民群體出現的原因
個體在網絡群體事件中表現出與現實生活不同的特質,會對某一特定事件高度關注、激烈討論并付諸行動,在這一過程中形成強大的網絡輿論力量。他們的“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傳染作用而轉向一個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觀念轉化為行動的傾向”。[1]這時,個體便具有群體特征,現代媒介環境下的網民群體就誕生了。
(一)“無名氏”的獨特身份
根據2016年7月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38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6年6月,中國網民規模達7.10億,互聯網普及率為51.7%。僅從新浪微博運行機制上看,新浪微博注冊用戶中除去一部分名人、政要是實名制注冊的,大多數用戶是匿名注冊的,這就形成了“無名氏”群體。束縛個人行為的責任感在虛擬世界不復存在,人便會肆意妄為而不受約束。龐大的數量以及匿名性,使得隱藏在群體中有意識的個性消失,無意識的個性得勢,感情和思想通過暗示和傳染被引到某個方向,可能會把暗示的思想變成行動。“抹去個性的無名氏意識到法不責眾使他不必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網民“不過是眾多沙粒中的一顆,可以被風吹到無論什么地方”。個人很清楚孤身一人勢單力薄,即使面對誘惑理智能戰勝它,不為所動。但成為群體中的一員,多數使得誘惑成為正確,群體在面對誘惑總會被賦予“正義”的力量,這些足以讓他屈從誘惑。
(二)群體領袖“功不可沒”
領袖在群體意見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對于現代媒介環境下的網民群體來說,名人、網絡大V等實質上就是起到“領袖的作用”,他們往往能夠一呼百應。在網絡群體事件中,如果沒有網絡推手的存在和媒體的渲染推動,很多時候事件也無法受大眾的高度關注。為了博取眼球,新聞記者在捕捉新聞時,忽略了還原事件本身才是新聞的價值,以夸張甚至是虛構來吸引大眾,網民在接受新聞時往往習慣性忽略判斷事情的真偽,給網民群體以錯誤引導。
(三)群體盲思和群體極化
在現實社會中遭遇不公平待遇或者本身境況不好的公眾,成為現實生活中的弱勢群體。他們或許抑郁不得志,或許憤世嫉俗。虛擬的網絡世界正好為現實生活中的弱勢群體提供了宣泄空間。在虛擬世界中無人知曉他的境遇,不會因為身份的不同而遭受不公平待遇,可以自由言論而不受限制,甚至可以在網絡上發表個人述求而得到社會的幫助。所以他們在網絡中異常活躍。弱勢群體通過依據他人的結論而粘合起來,并非對事件的完整性與真實性有過了解才發表意見,最終出現群體盲思。網絡環境為群體極化創造了條件,它把持不同意見、觀點的人吸引到一起,關注同一件事,并逐漸通話他們的觀點,使得偏見加深,尤其是一切 對現實不滿的個人,在網絡中找到共鳴,出現群體極化。
三、結語
在現代媒介環境中每個人都是發言人,我們確實進人了勒龐所說的群體時代。為了營造良好的網絡輿論環境,首先完善網法網規與健全網絡監督責任制度。填補網絡監管漏洞,實行網絡實名制。讓網絡不再是“無名氏”的溫床,通過加強監管,增強網民群體責任意識。其次利用好新媒體,設立輿情監測機制。對網絡輿論尤其是具有煽動性、脫離事實根據的不當言論進行過濾篩選和監管。正確處理好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關系,以正確態度審視新媒體,利用新媒體自身信息傳播便捷、覆蓋面廣等優勢與傳統媒體相互合作,共同推動網絡輿論環境的治理。最后,作為網民群體的個人要抵制盲從,約束自我行為。網民的固有特性即知識水平是關鍵因素,具有更高知識水平的網民能更深入的發表有影響力的言論。此外,網民的認知模式和情緒表達方式具有重要影響,即使滿腹經綸如果不能理性表達自己的觀點,也不能促成高質量的網民群體。網民個人在遵守網絡規則的同時要努力提升自身價值,讓網民群體在網絡時代共同傳播理性聲音,塑造和諧網絡環境。
[1](法)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M].胡小躍,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5:3,13~18.
[2]王瑩瑩.新媒體時代下的“烏合之眾”——以FB表情包大戰為例探究網絡群體事件[J].新媒體研究,2016,2(5):91~92.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
吳敏(1992-),女,漢族,安徽無為人,研究生在讀,南京師范大學,研究方向:中外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