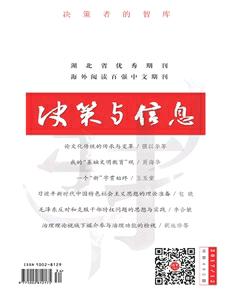我的“基礎文明教育”觀
肖海華
[摘 要] 基礎文明教育是相對于僅僅給予受教育者單純文化知識傳受的教育,是“立人”“樹人”必備基本道德素養的教育,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素質教育。在世界不斷趨新的文明時代,對小學生進行必要的基礎文明教育,不但有利于他們做未來合格公民,同時有利于他們成才,有利于他們終身幸福。基礎文明教育首先必須繼承中華傳統文化注重“修身”“養性”啟蒙,其次應與家庭教育緊密結合,促使小學生走出“嬌慣”陰影,再次是與社會教育掛鉤,教育小學生養成良好習慣,養成既能有對不良社會影響之“抗力”,又能具備堅持走正路的“耐力”,成為一個正派的人。
[關鍵詞] 小學生;道德;基礎文明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成人”教育
[中圖分類號] D64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8129(2017)12-0029-08
《決策與信息》2017年第8期刊發了明芬老師的《關注德育啟蒙》一文,讀后受益匪淺,說明小學生德育是人生道德教育的基礎,是所有教育的目標。因為“人不可以盲目做人”,所以應該有正確的人生目的[1] 32。借此,筆者不揣淺陋,也談點想法,以就教方家。
關于學校德育,在新中國建立以來的60多年間,有許多提法,諸如“學生思想教育”“政治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品德教育”等等,時下又稱作“道德與法治教育”。竊以為,這些提法,并未超出中國傳統文化中流傳下來的“立人”“樹人”“成人”教育,如果說一定有區別的話,只是強調了“道德”的份量而已。
應當承認,以上關于德育的種種提法,體現的是德育的人生意義,目的在于督促我們的學校教育應重在育人。然而從教育社會學意義看,德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是有區別的,這種區別就新中國或者新中國的當時代而言,我們的德育強調的是為社會主義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應該肯定,這一點永遠沒有錯。然而在實踐中,因為不能簡單地重復過去成功做法以達到今天的目的,所以在學校德育中,往往又出現了“與歷史對著干”的認知混亂。譬如新中國建立之初,為顯示新中國的教育宗旨,我們的教育方針明文規定在培養學生“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前提下,強調無產階級革命性,明眼人一看,這是對著漫長封建社會和舊中國的,因而在堅持了17年之后,又延續了多年,直到結束“十年動亂”,實行改革開放之后,因為立足“初級階段”理論,國家教育方針由“德智體”擴展為“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明顯表現為與此前不同,但在事實上,德育領先,地位雖然未變,然而隨著恢復高考后“應試教育”潮的愈演愈烈,“智育凸顯”,現實迫使我們的學校德育在實際上退居其次,于是,學校德育“需要的是創新、借鑒以至慎重的取舍和整全”的呼聲見諸于各界尤其是教育理論界[2] 60。當下,學校德育首先是小學生德育又進了一步——與法治教育結合,應該說,這確實是創新了——小學教育不僅是為上一級學校輸送學生,也是為未來社會培養“公民”。然而在實際上,這只是形式的改變(不否定內容充實),因為學校教育手段和這種手段下的德育目的,并未有實質性變化。鑒于這種歷史和現實,筆者認為,小學生(不排斥大中學生)在德育課程名稱和時代主體目標甚至基礎內容不變前提下,與時俱進,應著力突出“基礎文明教育”。這就是本文應時而作的原因。
眾所周知,自學校(中國最早為私塾)產生起,學校教育就是一個給予學習者知識的場合,理所當然就是“育人”的地方。與此相關聯的學校制度(近代后的小學-中學-大學;家庭-學校-社會)教育教程就是一個系統教育和多維發展的漸進過程,是學生由啟蒙到自主發展和不斷提高的自我教育訓練并與行為協調發展的過程。在這樣一個十多年的教育和自我教育過程中,從啟蒙教育(幼兒園和小學初年級教育)到基礎知識灌輸(小學高年級含低年級和中學各課程學習),再到自主的專業學習和訓練(大學分科學習),均離不開“自覺”做人,故此,“基礎文明教育”生。
所謂“基礎文明教育”,是在給予受教育者基礎文化知識學習的同時,向受教育者傳授人之所以為人及其必備基礎文明的教育,是一種健康生活方式的教育。因為文明是人類跨越野蠻的“入口”(人類文明誕生),步入未來“大同”的階梯。回顧漫漫歷史長河,雖然人類經歷了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即經過“農業文明”(人類文明的第一次飛躍)和“工業文明”(人類文明的第二次飛躍),剝削與反剝削、壓迫與反壓迫、強制與反強制,在社會主義時代都將變為過去,特別是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進步,人類文化尤其是科學的不斷發展,人類正經歷新的文明飛躍,伴隨這一文明飛躍,人類一定走向“大同”,盡管這是一個理想,但向一代又一代后繼者進行文明教育,是時代的重任,也是未來世界的需求。當然這是從廣義而言。從狹義而論,改革開放,與世界各國交往將越來越頻繁,外國友人走進來,國人走出去,相互交往也將會越來越密切,作為“禮儀之邦”的中華人,不但應從自身行為展現東方文明,亦必然通過大中華的每一個國民的文化素養包括禮儀風貌,讓世界認識中國,認識中國人民。就是說,不管歷史的過去如何,從野蠻到文明,多少年演義和定型后的文明社會所需求的人文基本要素(所謂世界觀)必須是包容的、大度的。這是首先一點。
其次,世界是發展的,是日趨新的文明時代的。但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人們因為所選擇的制度不同,且不同國家的價值觀各異,但作為人類發展大方向的要求,后續個體人必須具備文明基礎是相同的,這種文明基礎教育水平(文盲占據率低、普及教育率高、接受高等教育比率不斷上升)除信念教育(哲學世界觀、科學人生觀、職業選擇、自我實現等),政治定向教育(四項基本原則、“24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合格公民教育(憲法教育、法律知識等)外,就是“基礎文明教育”,相對于以上教育,“基礎文明教育”內容涵括習俗道德教育,良好生活習慣教育和生活中的倫理價值觀念教育等等[2] 61。
必須說明的是,基礎文明教育在任何時代、任何國情、任何民情下是必須的,但在同樣情況下又不是孤立的。譬如“文明行為”下的“文明禮貌”,在當今世界,不受地域和國家限制,幾乎是同一的,這一點,雖然在我們國家不同時代曾有過不同理解,譬如人們熟知的“行動從思想來”理論(這一理論本身并不錯),將“禮貌用語”和人與人交往行為都認定為階級性,應該說是不妥的。正因為如此,改革開放近40年后,已回歸正常。正所謂我們曾經的學生“政治思想教育”出發點雖然不容否定,但因其內涵失真而使這一教育效果有失偏頗。這一點是需要我們重新認識的。endprint
中國是禮儀之邦,僅就“基礎文明教育”內容而論,在中國傳統文化典籍中可以說是無處不存、無處不在,隨手拈來的首先如《三字經》中的“孝于親,所當執”(孝);“弟于長,宜先知”(悌);“父子親,夫婦順”(順);“曰仁義[3] 18-19,禮智信”(禮);“長幼序,友與朋”(悌,義);“講道德,說仁義”(仁)。其次如《千字文》的“知過必改,得能莫忘”(“受施慎莫亡”,感恩);“德建名立,行端表正”(儀);“孝當竭力,忠則盡命”(忠,孝);“上和下睦,夫唱婦隨”(睦)[3] 36-37。再次如《名賢集》的“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善);“柬之雙美,毀之兩傷”(義);“禮下于人”(禮);“老實常在”(睦)[3] 51-53。還有如《弟子規》的“泛愛眾”(睦);“兄弟睦,孝在中”(睦、孝);“路遇長,疾趨揖”(尊);“步從容,立端正”(禮);“凡出言,信為先”(信);“凡是人,皆須愛”(愛)[3] 71-76。另還有《小兒語》的“一切言動,都要安祥”(儀);“不要輕薄,惹人笑罵”(儀);“須好認錯,休要說謊”(誠);“世間第一好事,莫如救難憐貧”(誠)……等等。如斯俯拾皆備的還有《增廣賢文》的“錢財如糞土,仁義值千金”(仁、義)[3]109;“從儉入奢易,從奢入儉難”(勤儉)[3] 127;“欺老莫欺少,欺人心不明”(善)[3] 129;“千經萬典,孝義為先”(孝義)[3] 133。還有《閨訓千字文》(女子教育)的“孝順父母,惟令是行”(孝、順)[3] 142;“捐軀殉歿,雖死猶存”(忠、義)[3] 145。還有《改良女兒經》的“撫百姓,勸寬仁”(仁)[3] 157;“尊長至,要親敬”(尊、親)[3] 157;“舉止時,切莫輕”(儀)[3] 158。至于《治家格言》《二十四孝》《女兒經》《百家姓》等等,都包含了德育內容。可貴的是,中國古代洋洋若數萬言的這些文化大典,還有了縮寫本即著名的《幼學瓊林》,從天文地理、山川河澤、農林醫患、道德規范描述至清,將中華文明發展尤其是文明經典中的忠、孝、廉、恥、禮、義、信、悌等等一一呈明。從總體看,這些實際上的啟蒙教本雖然充斥著封建糟粕,但選章摘句無不具針對性、系統性和實踐性,“簡明扼要,通俗易懂,便于記誦,切于實行”,易于幼兒并全社會認同,因為將家庭教育、學塾教育和社會道德教育有機結合,從而凸顯了長期以來我國“立人”“樹人”“成人”教育思想精華,成為我們今天家庭和學校道德文明教育的參照系。
這里值得一提的是,封建中國的這些經典集編是為《小學》,即古時15歲前少童之教材,亦即人們常說的15歲前盡讀《小學》——以學會做人;15歲后當熟讀《大學》——以學會做事(做學問),因而被中國當代教育大師王炳照先生認定為“中國古代蒙學教材”[3] 13,恰如周谷城先生所認為,這些蒙學書“在傳授基本知識、進行道德教育……這一點上,即自有其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價值”理所當然,亦應為當代小學生道德文明教育的參照系。
那么,21世紀面對“獨二代”(獨子之獨子)小學生“基礎文明教育”當如何進行呢?筆者想法很簡單(狂放了),但卻難行,然必行之。
首先,基礎文明教育必從小抓起。古代中國,當小孩牙牙學語起,便誦讀《三字經》《百家姓》以開蒙。可以想象,以上諸經對一個三四歲、五六歲的孩童而言,難言理解,但讀得多了,背得熟了,也就被強制地鐫刻在腦子里,盡管開始他們并不識字,伴隨誦讀,字也就認識了,因為讀得多了,隨著年齡的增長,隨著父者、長者、師者的講解,也就慢慢理解了。“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大概就是這樣得來的。舉例說,杜甫的才華世人皆知,其才華如何得來?用他自己的話說:“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何能如此早惠?他說皆因“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用今天的話說,在年少時就可充當參觀王都的來賓,是因為少時就讀破了無數卷書,下筆做文章才如有神助。再如李賀,盛唐時號稱“詩鬼”,其耳熟能詳的“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鉤”,人人知曉。歷史記載,李賀7歲做文章就驚動了當時的名人韓愈和皇甫湜,引起二名人“是真是假”的疑問,于是登門查觀,時札著兩羊角辮的李賀迎門納客,當著名人面作詩,韓愈大為驚訝,乃親自為他重新扎了頭發。如此“神童”在中國古代典籍中,可以說比比皆是。
破萬卷書誠若孔丘“韋編三絕”,是苦差事,皆因“苦”,方換得才識,方換得“一舉成名天下揚”。而這種苦,大概就是古人所言,“吃得苦中苦”的必然經歷。相比之下,當今所謂“快樂”學習的論調是該休息了。從中我們可以悟出這樣的道理,基礎文明教育必須從早抓起,且必須是強力推行的教育。這種早教,是為基礎,基礎打牢實了,自然會分清是非,自然會識得做人的道理,用今天的話說,因為基礎好且優,待長成后就是一個“根正苗壯”者。相反,基礎不牢,“根淺”“干斜”,待等長成后,歪根歪長,想要扶直,只能“矯枉過正”,而矯枉過正卻已失卻教育的“最佳期”“關鍵期”(井深大語),用同行明芬的話說,“早期家庭教育及初年級小學啟蒙教育決定人生”“這種灌輸教育可能對大學生無多大吸引力,但對初入校的小學生而言,卻是活力無窮”[4]。
其次,基礎文明教育必須與家庭教育結合。家庭“是兒童這棵幼苗得以成材的苗床”[5]。再說,“母愛是幼兒的至寶,沒有任何保姆的愛可以代替”[1] 113。在教育理論界看來,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是人生必須經歷的教育形態,不論你認識深淺如何,都不可能擺脫。無論家庭教育是否自覺,是否科學,父母及家人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實際上都在對幼兒(從嬰兒開始)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待到幼兒適齡后,必須到學校接受教育(九年義務教育),至于農村特別是偏遠山區孩子無幼兒園可上,但上小學念初中卻是必然的。遺憾的是,時下,很多的家庭教育并不理想,而且是極不理想,諸如年輕家長責任心不強,以及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對孩子過分嬌縱,因而形成了“學校不敢管,家庭不愿管”的普遍現象。
說“家庭不愿管”其實并不準確,只是家庭不需要學校管小學生的做人是否到位,說白了,就是驕縱行為,自己不管也不讓學校管,當然不少家長也已發現自己孩子的品行不規范,不盡人意,但這種“不讓”背后卻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希望且極希望學校管好管到位,那就是“考分”如何上去,如何使自己的孩子考上重點中學,以實現上重點大學之目的。這就必然發生小學(當然中學也不例外)教師不好做的問題。其中折射的當然是家庭道德教育即基礎文明教育不到位的問題。endprint
對于小學生基礎文明教育涉及方方面面,諸如怎樣進行熱愛中國共產黨的教育?怎樣培養孩子熱愛祖國的感情?如何教育孩子熱愛社會主義制度?怎樣培養孩子團結友愛的品性?怎樣培養孩子具有誠實的品質?怎樣培養孩子尊敬師長和父母?怎樣培養孩子的勞動習慣?怎樣培養孩子學習禮貌語言等等。這在前述古人“忠孝廉恥,禮義信悌”典籍中已有綜述。問題是家庭和小學(不排斥中學甚至大學)如何有效聯合并適時有效進行,必須引起重視。
遵嚴元章先生的倡議,重要的是“從教育方法入手,改革家庭教育”[1] 113。即推動家庭的全面更新,往實處說,不僅是培養好兒童,同時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質,具體說,就是要通過家庭教育的改革,通過有關方面、有關部門輔導家長,科學地培養孩子。這一點,說起容易,做起來卻是一個系統工程。但是否因為難就不做呢?回答是必須做!“為母是人生的光榮:孟母岳母以及許多無名的賢母,都是崇高的”,因而,作為“賢母”“居家教子也是服務社會”,唯有如此,“子女入學后,小學教育順利……中學教育順利”“跟學校教育積極配合,分擔培養子女成人成材重任”[1] 113-114。可見,“家庭是人生最重要的教育機會”“家庭教育才是真正的,基本教育,”[1] 114。
問題在于,我們的學校教育尤其是小學教育又尤其是小學初年級教育如何做到與家庭教育攜手合作呢?
實事求是地講,家長將孩子考分當作“生命”并不能全怪家長,學校在其中起了關鍵作用。譬如當下小學教育,孩子一入學便進入“應試”狀況,才離開幼兒園的天真浪漫的幼小心靈便受到摧殘,于是,幼童們上學的新鮮感沒了,好奇心也沒了。接下來,個性沒了,業余愛好沒了,理所當然,李白、杜甫、李賀等古圣賢的“狂放”更不可能有了。現在小學表面上無家庭作業,無分數記于冊,只記等級;實際上,按分排名仍在大行其道,各種考卷對于一個小學一年級學生已司空見慣,如此之下,《弟子規》只是早讀時播播,午休時讀讀,《道德與法制》讀本只是加重孩子書包重量而已,如此何能實現古時小兒熟讀天下書的景象?!
學校教育同家庭教育的有效結合,質言之就是讓千千萬萬一代又一代小孩子從“應試教育”中解放出來,同時,讓我們的廣大教師能像孔子那樣“并不是為教書而教書,卻是為教人而教書”,真正實現教師對學生“在真知、實學、健身、立品”上下功夫[1] 119,而不是將“育人”責任連同“應試教育”一起轉嫁給家庭。恰若孔丘所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學校教育尤其是小學“立人”“立德”“立志”的關鍵時期,教育應加重文化份額,加強文明分量,必要時當回歸傳統。雖然并不一定在實際上要求我們的兒童放棄數理化生而搖頭晃腦背誦經典,也大可不必在形式上讓小兒著漢裝而朝拜圣賢,但做人習慣,尊民習俗,做“公民”準備必是教育正道。當知小學教師的職責是“教”,是“教學”是“教人學”是“教學做人”,教人“成人又成才”“是教人學做人的人”[1] 138。一句話,教師是傳授文明的使者。
其三,基礎文明教育必須與社會教育結合起來。教育,是人與人之間互為影響的活動。當代文明教育恰如梅克所言;“社會教育已不僅僅是學校教育的延伸和補充。”[1] 111社會教育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社會教育即蔡元培先生于1912年鄭重提出的也是中華民族第一次與世界教育接軌,與“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對應而起的正規或非正規的教育活動,具體所指是家庭和學校以外所有主辦或兼辦的教育機構,就是近些年來所熱辦和正在廣泛推行的職業技術教育(培訓),成人教育,這類教育即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指終身教育。無疑,現在的在校小學生不少將是這類教育對象。這不是本文所論內容。
廣義的社會教育指的是“無院墻”學校即人們通常所說的“社會大學”。在這樣的大學里,其教育過程是自我領悟的教育,完全在于受教育者的自我觀察、自我領悟、自我歸納和自我提高,真正的“無師自通”,實際上,除去“匠技”的學習外,“匠心”自修全靠學習者——無論其過去是否接受過系統的學校教育——小學、中學、大學乃至研究生教育,作為“社會人”都必須適應社會。即便是僅僅接受過“九年義務教育”的學生,進入社會也得經過這一關。這就要求我們的受教育者在“安身立命”這一點上過好關——真正學會以優良人品而“處世”——完成中國道家所創導的“入世”和“出世”過程。
那么,我們的小學能教會和應教會他們什么呢?那就是他們的“基礎文明”觀。
——試想,一個被嬌慣寵大的孩子,如果我們的小學教師不對他的自私霸道予以校正,那么,他能被未來社會接納嗎?他能無私無畏面對社會的不良行為而走正道嗎?
——試想,一個不愛父母(更多的單親家庭出身或失孤孩子)的孩子,一個不尊重師長的孩子,他在未來的職業和人生中能愛單位、能愛崗敬業甚至能愛國家、愛這個社會嗎?
——試想,一個從小連基本的禮貌語言都不眷顧、不在乎的孩子,成人后,他能是一個遵紀守法的模范公民嗎?
——試想,一個從小邋遢,不整潔,作業不認真、拖拉,就業后能敬業從而認真工作嗎?
……
興許可能,因為還有未來的教育等待他們。但是,教育并不是萬能的,尤其是面對一個缺乏基礎文明教育的“先天不足”者,所有教育都可能顯得蒼白無力。這就是中國古人所言“三歲看大、七歲看老”和外國人“八歲看人生”的真諦所在。因此,在早期學校教育尤其是在小學初年級學生的基礎文明教育過程中,我們的學校我們的教師在教育“小公民”時,應從基本的文明禮貌語言和行為入手,教他們友愛的知識,教他們正確的金錢觀念,教會他們能有“抗力”抵制社會不良影響,能有“耐力”堅持正確的社會方向,善于分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壞的;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什么是應該放棄的,什么是應該堅持的,等等。如古人所言,真正使他們打好良好文明教育基礎,成為一個正正當當的人,堂堂正正的人;正直的人,正氣的人,正義的人,正經的人;講正話的人,行正路的人,且成為一個不走極端的人,不偏于極端主義的人,更是有勇氣與邪惡對著干的人[1] 46。人做好了,事倍功半;人做不好,一切為零。
補充一點,在小學生基礎文明教育全過程中,師德是關鍵。作為教師,不但應在語言表達、行為舉止方面做出表率,而且在一些看似細微末節的問題上,如自身的穿著打扮,對待學生平等,對待家長和藹——謙恭有禮,落落大方,皆為學生的楷模。
最后以著名評論家余心言的話作為結束語:人類在走上文明時代的時候……從個人來說,就是要認清歷史發展的規律,適應歷史發展的規律。越是看得清楚,人們就越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6] 135。
[參者文獻]
[1]嚴元章.中國教育思想源流[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
[2]劉 萍,王慧敏,黃新憲,等,當代中國教育的熱門話題綜論[M].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
[3]夏 初,惠 玲.蒙學十篇[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壯,1990.
[4]明 芬.關注德育啟蒙[J].決策與信息,20017,(8).
[5]劉榮才,玲 儀.家庭教育問答[M].武漢:湖北少年兒童出版社,1983.
[6]余心言.道德鼓吹錄[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責任編輯:曾 菡]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