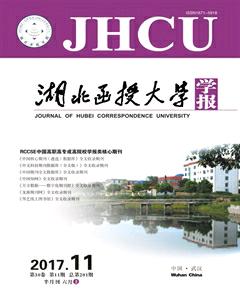日語專業教學中全面導入日本“隱性文化”的必要性及途徑
賈璇+邢文柱
[摘要]教育部高校日語專業教學指導分委員會研究制定了日語專業國家質量標準,將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作為人才培養的重要基準。基于該標準,要求教師必須將學生的學習視角引向更為本質、更為核心的不可見的隱性文化。通過在基礎課程教學中有意識地啟發學生思考語言現象及文學作品背后蘊藏著的“隱性文化”,在高年級階段增設《跨文化交際》、《日本研究》等系統講授日本“隱性文化”的課程,定期開設專題講座等途徑,將對日本“隱性文化”的學習全面導入日語專業教學中。
[關鍵詞]日語專業教學;新國標;隱性文化;必要性;途徑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教育部關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若干意見》以及《教育部、財政部關于實施高等學校創新能力提升計劃的意見》,教育部高校外國語言文學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日語專業教學指導分委員會研究制定了日語專業國家質量標準,通常被稱為“新國標”。“新國標”旨在提高日語本科教學工作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將日語本科教育定位為“人文教育中的日語教育”,將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作為人才培養的重要基準,前所未有地凸顯了文化教育在日語專業教學改革中的核心地位。突破了我國大多數高校日語語言文學專業普遍存在的語言知識為主、文學知識為輔的教學模式的局限,在學習領域上,將課程擴展為語言學課程、文學課程、文化課程。明確要求學生跨越、克服文化上的障礙,用對方可以接受的語言方式和行為習慣,達到自如交際的學習效果。“新國標”在日語本科專業方向課程的設置上,除了此前常規的語言學、文學、翻譯學、外語教育和專門用途日語外,著重強調了跨文化交流、日本研究等類別。
一、日本的“隱形文化”
文化,是一個極為廣泛、又極難定義的概念,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纂的《現代漢語詞典》(第五版)中將“文化”定義為“①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特指精神財富,如文學、藝術、教育、科學等。②考古學用語,指同一個歷史時期的不依分布地點為轉移的遺跡、遺物的綜合體。同樣的工具、用具,同樣的制造技術等,是同一種文化的特征,如仰韶文化、龍山文化。③指運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識”。有學者針對文化的內涵,將文化劃分為顯性文化和隱性文化。認為文化“包括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個方面。物質文化是指人類創造的物質文明,包括交通工具、服飾、日常用品等,它是一種可見的顯性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分別指生活制度、家庭制度、社會制度以及思維方式、宗教信仰、審美情趣,而這些屬于不可見的隱形文化”。在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比起可見的顯性文化,那些不可見的隱形文化似乎發揮著更為重要的作用。
日本作為一個獨立的民族共同體,無疑有著屬于自己的獨有的文化特征。對這些文化特征的學習便是開啟跨文化交流之門的鑰匙。日本是一種“縱向”的社會結構,類似于一種親子關系。這種親子關系始于日本早前的職業訓練之初,其后才逐漸發展為日本基本的社會結構和人際關系,如具體化為師生關系、公司里的上下級關系等。日本著名的社會人類學家中根千枝在其英文原著《Japanese Society》(《日本社會》)中指出:“日本的集團是由兩個人之間縱向聯系的總和構成的,因此個人地位永遠游移在這樣一個關系網中”。這種社會結構必然要求生活于其中的每個獨立的個人具有強烈而明確的等級序列意識。同一集團內部資格不同者自不必說,即便是同一集團內部資格相同者也有著更為驚人的細致的排序方式,對這種等級序列意識的敏感似乎是每個日本人與生俱來的,也是根深蒂固的。離開了等級序列意識,在日本便難以正常生活和交際。日本也是一種單一社會,日本人往往只從屬于一個集團,或者說主要從屬于一個集團,即便是同時從屬于其他集團,其他集團的地位也在其主要從屬的集團之下。這種對唯一集團的忠貞性,是完全日本式的社會特征,是不同于歐美各國以及亞洲其他國家的。日本在制度文化上的這些異質性,是日語學習者在跨文化交流中必須儲備的知識。
關于日本人的心理文化,日本學者土居健郎通過其著作《依賴心理的構造》,深入分析了日本人的依賴心理。土居認為,在研究日本人思維方式時通常被關注的“內與外”、“罪與恥”、“義理與人情”皆是源于依賴心理,日本人在彼此依賴的關系中獲得安全感,沉浸于那種平和、安穩的氛圍。“依賴”不僅僅是理解日本人思維方式的關鍵詞,更是了解日本獨有文化的關鍵詞,是日本人際關系的核心。其次,對一個國家宗教信仰的理解,也是異文化交流中不可或缺的行之有效的認知手段之一。日本人的生活與宗教有著密切的關系,往往是“出生時神道,結婚時基督教,送終時佛教”。如此復雜的宗教信仰,其本質源于日本人的“現世(現實)利益中心主義”。“神與人的關系,實際上是自然與人的關系和社會關系的反映,其中包含著人們對人生的理解和解釋,因而決定著特定民族的基本生活態度。”此外,日本人的審美情趣敏銳而豐富,這個民族的好美精神幾乎滲透到生活的各個角落。日本獨特的風土造就了日本人細膩的審美情趣——物哀、空寂、閑寂、風雅、幽玄。唯有讀懂了日本人的美意識,才能觸及到日本文學作品的靈魂,才能捕捉到日本文化的神髓。
“新國標”以跨文化交際能力作為日語專業人才培養的目標,這就要求教師針對日本文化的教授,必須透過可見的顯性文化,將學生的視角引向更為本質、更為核心的不可見的隱性文化。
二、日語專業教學中全面導入日本“隱性文化”的必要性
首先,日語專業教學中全面導入日本“隱性文化”,有利于學生對日語語言知識的學習,掌握正確的語言表達。眾所周知,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沒有對他國文化的理解,對他國語言的學習無疑是淺層次的,在語言的實際運用中也勢必會常常碰壁。尤其是日本的隱性文化,對日語語言的影響力更應引起學習者的足夠重視。例如,日語中作為學習難點之一的敬語,蘊含于其中的隱性文化背景即是日本縱向的社會結構和等級序列意識。對長輩或上級使用敬語,是與日本人交流時最基本的常識。為了表達對話題人物或聽者一方的敬意,說話人靈活運用著尊敬語、自謙語和鄭重語。同樣,由于日本人的依賴心理,說話人往往會顧忌聽者的感受,擔心自己不為對方接受,無法構成依賴關系,因此不能直率地闡明觀點和意見,除了在語言中減少直接使用明確的第一人稱“我”作為主語外,也常常在表達中,特別是否定意見的表達中“欲言又止”,即所謂的“以心傳心”。這些隱形文化的特質決定了日語語言的最大特征——“曖昧性”(意為模糊、不清楚)。唯有在專業教學中全面導入日本的“隱性文化”,學生對日語語言知識的學習才能達到“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才能在異文化交流中自如地使用語言和準確理解對方的表達意圖。endprint
其次,日語專業教學中全面導入日本“隱性文化”,有利于學生對日本文學知識的理解,培養學生的文學鑒賞能力,透視不同時代日本人的價值觀。以日本美學理論中的“物哀”為例。不理解“物哀”中的美,就無法觸及日本古典文學的精髓,無法剖析日本傳統文學的民族特色,更無法將日本文學與他國文學進行比較研究。日本國學家本居宣長在其著作《石上私淑言》中指出,和歌的宗旨即是表現“物哀”。本居亦在其專著《紫文要領》中,以“物哀”的全新視角解讀了《源氏物語》這部日本文學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巔峰之作。本居稱“看到對方的美而心動,即是感知‘物之心,而女子能體會到男子的心情,即是感知‘物之哀”,“《源氏物語》中有很多處這樣的情節,為了愛情不惜獻出自己的生命,是‘物哀中最為銘心刻骨的”,“《源氏物語》舍棄對善惡的判斷,只為追求‘物哀”。可見,對日本的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的知識儲備,是學生閱讀日本文學作品,分析作品人物形象的必要前提。
再次,日語專業教學中全面導入日本“隱性文化”,有利于加深學生對日本“顯性文化”的認識,避免因文化差異而造成的交際障礙。例如,和服是日本頗具代表性的“顯性文化”之一。與同是代表傳統民族文化的中國旗袍相比,日本和服體現了日本人對于同一性或者說集團性的追求。和服的剪裁基本由直線構成,穿著在身上呈直筒型,巧妙地隱藏了身材曲線的不同,使得每個個人都安穩而寧靜地處于整齊劃一的集團當中。在服裝色彩的選擇上亦是如此,不同于強調個人主義的韓國在傳統服裝上對明亮艷色的喜好,日本的服裝多數為中間色系。這其中無不體現了日本的國民性。日語專業學生在與日本人的交際中,必然會接觸到衣食住行等諸多日常文化,理解這些表層文化背后的深層文化,才能真正做到求同存異,友好交流。
三、日語專業教學中全面導入日本“隱性文化”的途徑
首先,在《基礎日語》、《高級日語》、《日本文學概論》等課程的講授中,授課教師有意識地啟發學生思考和探究語言現象及文學作品背后蘊藏著的“隱性文化”。例如,《基礎日語》講授人稱代詞時,在基本詞義及用法的講解后,應著重強調日語中人稱代詞的使用頻率遠遠低于漢語,避免學生出現日漢互譯上的失誤。日語人稱代詞使用頻率較低,除了語法因素外,還源于文化因素。其一,日本人具有濃厚的集團性意識和等級序列意識,避免突出自我,在非正式場合中較少使用第一人稱“我”,且往往用職務名或其他敬語性結尾詞等尊稱替代第二人稱“你”和第三人稱“他(她)”。其二,日本文化的曖昧性,反映在語言交流上,便是最大程度的“以心傳心”,即使省略了人稱代詞,在同質性較強的日本,也不會產生理解上的偏差。《高級日語》教材的內容通常以一定篇幅的文章為主,或為議論文,或為文學作品節選,無論是何種題材的文章,其中必定包含著日本的制度文化和日本人的心理文化的縮影,而對這些“隱形文化”的認識和理解,是授課教師有必要引導學生深入思考和討論的。同樣,在諸如《日本文學概論》等文學類課程的授課中,無論是對作家本人還是對其作品主題的分析,離開對日本“隱性文化”背景的探討,都是淺嘗輒止、缺乏深度的。因此,在語言學課程及文學課程中,授課教師應適時地結合學習內容,由表及里、由淺入深地逐步導人日本的“隱性文化”,并培養學生的研究興趣。
其次,在高年級階段增設《跨文化交際》等必修課和《日本研究》等選修課,系統講授日本的“隱性文化”。將學生在低年級階段以及在語言學課程、文學課程中接觸到的較為零散的“隱性文化”的知識點系統性地整理、歸納和總結。從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心理文化三方面學習如何真正做到“跨文化交際”。在物質文化的章節中,學習日本人的衣食住行。在制度文化的章節中,通過對敬語的使用和日語曖昧性等的理解,學習日本社會的縱向結構以及對單一集團的從屬性。在心理文化的章節中,結合“授受關系”等語言現象以及夏目漱石的《哥兒》等文學作品中主人公形象,學習日本人的依賴心理、“內外之別”、“義理與人情”、“恩與報恩”等心理文化。唯有系統地學習日本獨有的文化,從文化的角度理解日語語言和日本文學,才能在與日本人的實際交流中,真正跨越異文化這一障礙,有效溝通。
再次,向學生推薦相關書目,定期開設專題講座,配以主題“文化沙龍”,激發學生對日本“隱性文化”的求知欲,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部分研究日本“隱性文化”的經典著作,如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小泉八云的《日本與日本人》、戴季陶的《日本論》、本居宣長的《日本物哀》、和辻哲郎的《風土》、土居健郎的《日本人的心理結構》、中根千枝的《Japanese society》(《日本社會》)、津田左右吉的《日本的神道》、丸山真男的《日本的思想》等,應作為課外必讀書目有計劃地推薦給學生。定期邀請國內外的相關專家學者為師生開設專題講座,并繼而針對性地舉辦主題沙龍活動。將學習模式由學生被動地接受知識轉變為主動地汲取知識。
“新國標”中多處強調了對日語專業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這里所需跨越的實則是隱藏在語言、文學、顯性文化背后的“隱形文化”,即作為一個國家的制度文化和作為一個民族共同體的心理文化。因此,在日語教學中應從專業課程設置、教學大綱修改等方面著手,全面導入日本“隱性文化”,綜合培養專業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