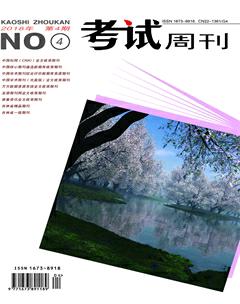高中語文教學(xué)呼喚歷史知識(shí)的運(yùn)用
摘 要:自古以來一直強(qiáng)調(diào)“文史不分家”,任何文學(xué)經(jīng)典的誕生有其必定的歷史背景,并體現(xiàn)這一特定的社會(huì)歷史,同樣,許多歷史內(nèi)容都是依靠文字形式記錄下來的,本身就包含了文學(xué)的性質(zhì),許多歷史現(xiàn)象的追述、許多歷史人物的傳記本身就是一部非常優(yōu)秀的文學(xué)作品。因此,歷史和語文無論在以前還是當(dāng)下,都有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語文教學(xué)需要運(yùn)用歷史知識(shí)豐富和完善自己。
關(guān)鍵詞:語文教學(xué);歷史知識(shí);運(yùn)用
一、 歷史知識(shí)與語文教學(xué)不可分割
從文學(xué)批評(píng)的角度來講,中國古代長(zhǎng)期存在著“依史論文”之說,余虹在《中國文論與西方詩學(xué)》一書中寫到:“‘歷史作為文性敘事評(píng)價(jià)自身的唯一尺度長(zhǎng)期支配著中國文性敘事理論的發(fā)展,文性敘事只有不斷證明自己的‘歷史性才有存在的理由。”這種“依史論文”的看法在很長(zhǎng)的歷史時(shí)期主宰著人們的傳統(tǒng)文學(xué)觀念。
從語文的學(xué)科性質(zhì)上來講,王富仁曾經(jīng)提到:“在現(xiàn)代教育中的歷史、地理、政治乃至經(jīng)濟(jì)、軍事、植物、動(dòng)物在中國古代教育中都內(nèi)含于中國語文教學(xué)之中。”由此可見,語文作為一門綜合性相當(dāng)強(qiáng)的學(xué)科應(yīng)該加強(qiáng)與歷史知識(shí)的聯(lián)系,朱紹禹也曾有過類似的論述:“在現(xiàn)代的語文教材中,文章的寫作時(shí)代、作家的生活道路、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乃至建筑、器物等等,幾乎無不涉及歷史內(nèi)容,因而也就經(jīng)常需要借助歷史課程的知識(shí)配合。”
二、 歷史知識(shí)對(duì)于語文教學(xué)的意義
(一) 適應(yīng)當(dāng)前的教學(xué)改革需要
北京大學(xué)教授季羨林曾經(jīng)說道:“今天學(xué)術(shù)發(fā)展的總趨勢(shì)是,學(xué)科界線越來越混同起來,邊緣學(xué)科和交叉學(xué)科越來越多,像過去那樣,死守學(xué)科陣地,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已經(jīng)完全不合時(shí)宜了。”隨著對(duì)語文基礎(chǔ)教育質(zhì)量與目標(biāo)要求的明晰以及語文課程、教材改革的不斷深化,關(guān)于語文教學(xué)與其他各科的關(guān)系特別是文史關(guān)系,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guān)注。
(二) 傳承我國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
中華文明源遠(yuǎn)流長(zhǎng),是在5000多年的歷史積淀中孕育而來的。歷史延續(xù)到今天,我們面臨這樣一種選擇,也就是中華文明是否能夠繼往開來。在這樣的時(shí)代背景下,語文教學(xué)理當(dāng)起到承先啟后的作用。文學(xué)是文化的載體,語文教學(xué)是文明傳承的重要路徑,而文化和歷史之間又有著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錢穆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提到:“文化即是歷史,惟范圍當(dāng)更擴(kuò)大,內(nèi)容當(dāng)更深厚……文化乃是歷史之真實(shí)表現(xiàn),亦是歷史之真實(shí)成果。舍卻歷史,即無文化。”王富仁也在《語文教學(xué)與文學(xué)》一書中寫到:“對(duì)于我們,學(xué)習(xí)文言文是為了了解和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的,是為了掌握我們古代文化的。”因此,在語文的教學(xué)中加以歷史知識(shí)的滲透,對(duì)傳承和發(fā)展自強(qiáng)不息、敬業(yè)樂群、扶危濟(jì)困、臨危不懼、尊老愛幼等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精華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三、 歷史知識(shí)在語文教學(xué)的運(yùn)用策略
(一) 知人論世 走進(jìn)文本
了解文本的創(chuàng)作背景對(duì)我們解讀文本會(huì)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閱讀教學(xué)中,如果能讓學(xué)生致力于閱讀作家創(chuàng)作的歷史背景,就可以讓學(xué)生感觸作家創(chuàng)作時(shí)的真情流露,從而走近作者,感受文本。
例如,在學(xué)習(xí)蘇軾的《定風(fēng)波》時(shí),雖然我們領(lǐng)悟到了蘇軾在逆境中的從容不迫、恬然自適,但是作者筆下的“風(fēng)雨”不是單純地指自然界中的“風(fēng)雨”,而理解文中“風(fēng)雨”的具體指向是解讀這首詞的關(guān)鍵。究其根源,還是與當(dāng)時(shí)的人生遭遇有所關(guān)聯(lián)。1079年,蘇軾因一篇《湖州謝上表》被卷入了“烏臺(tái)詩案”,在經(jīng)過103天的牢獄之災(zāi)后被貶黃州,烏臺(tái)詩案讓蘇軾險(xiǎn)些喪命,來到黃州之后,因?yàn)榻?jīng)濟(jì)問題不得不自己開荒種田,脫下文人的長(zhǎng)衫,穿上農(nóng)夫的短丁,在物質(zhì)和精神上的雙重壓力之下作此詩歌。蘇軾創(chuàng)作的《定風(fēng)波》就是那時(shí)面對(duì)困境時(shí)心里最真實(shí)的想法,這些歷史背景是我們?cè)陂喿x過程中必須留心的。只有著實(shí)領(lǐng)會(huì)了《定風(fēng)波》寫作的歷史背景,才有可能更加深刻地去理解詩歌中透露出來的蘇軾的蕭然豁達(dá),隨緣自適的人生態(tài)度。
(二) 歷史圖表 直觀生動(dòng)
歷史圖表法一般是用于歷史知識(shí)的講習(xí)中,但在語文教學(xué)中也是不能缺少的一方面,尤其是在文言文教學(xué)中最為明顯。在文言文的學(xué)習(xí)中會(huì)涉及大量地域、地名,的當(dāng)教師在為學(xué)生講解古代區(qū)域分界及具體的地名時(shí),最為直觀的一種教學(xué)方式無疑是運(yùn)用歷史圖表法進(jìn)行教學(xué)。
在高中文言文學(xué)習(xí)中,大量文本會(huì)或多或少關(guān)涉一些古代地名及地理區(qū)域劃分,雖然有的地理名稱會(huì)有注解,但有的學(xué)生不太重視,一直到這一課學(xué)完都搞不清楚文中的地理名稱的含義,比如在學(xué)《過秦論》這篇文章時(shí),文中會(huì)出現(xiàn)許多地名:“秦孝公據(jù)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大多數(shù)學(xué)生不太了解崤函、雍州、漢中等古代地理坐標(biāo),這樣會(huì)對(duì)文本的理解產(chǎn)生阻礙,即使教師給予一定的口頭解釋,也顯得很抽象。因此,老師可運(yùn)用歷史圖表這一重要的教輔工具來解決該難題,學(xué)生直觀地看到六國形勢(shì)分析圖,對(duì)那個(gè)風(fēng)起云涌的戰(zhàn)國時(shí)代會(huì)有形象的了解,可以讓學(xué)生更加深刻的體會(huì)文章中汪洋恣意的氣勢(shì)。另外,在高中語文的學(xué)習(xí)中還會(huì)遇到《燭之武退秦師》、《廉頗藺相如列傳》等文章,這一類文章有一個(gè)共同點(diǎn),就是發(fā)生的時(shí)代背景都在春秋戰(zhàn)國時(shí)期,如果教師可以制作一張《春秋列國形勢(shì)圖》,那么各個(gè)諸侯國之間的關(guān)系就能得到形象化的體現(xiàn),學(xué)生對(duì)諸侯國的區(qū)域關(guān)系也更容易理解。
四、 結(jié)語
總而言之,語文和歷史知識(shí)之間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歷史的記錄、傳承缺少不了筆墨的記敘,語文中又囊括了大量的史學(xué)資料、歷史人文、歷史事件等方面。語文教學(xué)需要運(yùn)用歷史知識(shí)完善自己,歷史知識(shí)在語文課程中的地位是舉足輕重的。筆者在此僅僅是拋磚引玉,以期待歷史知識(shí)在語文的教學(xué)實(shí)踐中會(huì)起到更好的效果。
參考文獻(xiàn):
[1]余虹.中國文論與西方詩學(xué)[M].北京:生活·讀書·三聯(lián)書店,1999.
[2]王富仁.語文教學(xué)與文學(xué)[M].廣東:廣東教育出版社,2006.
[3]朱紹禹.中學(xué)語文課程與教學(xué)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作者簡(jiǎn)介:
李正,寧夏回族自治區(qū)固原市,寧夏師范學(xué)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