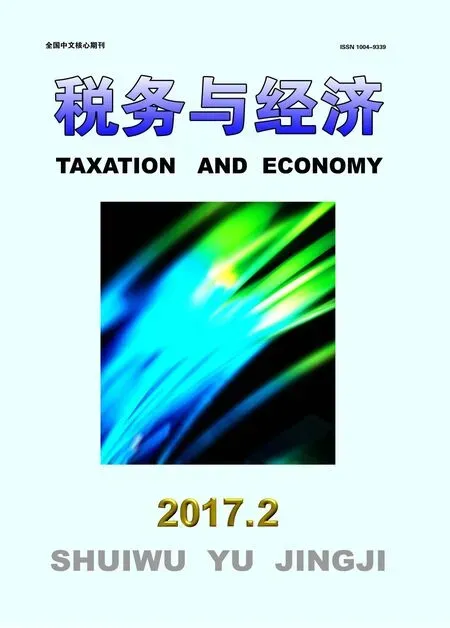城鄉(xiāng)金融非均衡與城鄉(xiāng)收入差距
——以吉林省為例
賈 非
(吉林財經(jīng)大學(xué) 統(tǒng)計學(xué)院,吉林 長春 130117)
一、引 言
金融發(fā)展對經(jīng)濟(jì)增長具有重要意義是理論界的共識。基于這一認(rèn)識,20世紀(jì)90年代Greenwood和Jovanovic運(yùn)用一個動態(tài)模型證明了金融發(fā)展產(chǎn)生的“門檻”可以引致收入分配的“庫茲涅茨效應(yīng)①庫茲涅茨認(rèn)為收入分配的長期變動軌跡呈現(xiàn)先擴(kuò)大后縮小的“倒U”形狀,即為收入分配的“庫茲涅茨效應(yīng)”[2]。”[1],從而引發(fā)了關(guān)于金融發(fā)展與收入分配關(guān)系的討論。張立軍等將金融發(fā)展影響收入差距的方式總結(jié)為“門檻效應(yīng)”、“非均衡效應(yīng)”和“降低貧困效應(yīng)”。[3]在我國城鄉(xiāng)經(jīng)濟(jì)二元結(jié)構(gòu)的背景下,“非均衡效應(yīng)”成為金融發(fā)展影響城鄉(xiāng)收入差距最為顯著的渠道。
各地區(qū)金融發(fā)展非均衡對地區(qū)間收入差距有顯著影響,金融發(fā)展在地域上的非均衡延緩了地區(qū)經(jīng)濟(jì)增長的收斂速度。[4]長期以來,我國金融資源配置表現(xiàn)出明顯的城市化傾向,從而形成了金融發(fā)展的城鄉(xiāng)非均衡。金融資源配置的不均衡使城市居民受益,而農(nóng)村居民和中小企業(yè)則獲益較少,從而擴(kuò)大了城鄉(xiāng)收入差距。[5]姚耀軍等從實證分析的角度證實了我國城鄉(xiāng)金融非均衡是城鄉(xiāng)收入差距的Granger原因,且二者具有顯著的長期均衡關(guān)系,進(jìn)一步驗證了城鄉(xiāng)金融非均衡擴(kuò)大了城鄉(xiāng)收入差距。[6]值得關(guān)注的是,我國經(jīng)濟(jì)、金融發(fā)展具有顯著的地域差異性,不同地域城鄉(xiāng)關(guān)系的表現(xiàn)也明顯不同。因此,各地區(qū)城鄉(xiāng)金融非均衡影響城鄉(xiāng)收入差距的機(jī)制也可能存在差異。為體現(xiàn)地域性,魏麗莉等曾對城鄉(xiāng)發(fā)展雙滯后的甘肅省進(jìn)行了分析,實證結(jié)果表明,甘肅省金融發(fā)展規(guī)模的城鄉(xiāng)差異明顯拉大了城鄉(xiāng)收入差距,而金融發(fā)展效率的城鄉(xiāng)差異對城鄉(xiāng)收入差距影響較弱。[7]但目前類似的相關(guān)研究仍較為匱乏。
吉林省城鄉(xiāng)經(jīng)濟(jì)發(fā)展具有特殊性,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城鎮(zhèn)經(jīng)濟(jì)相對滯后而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相對發(fā)達(dá)。2013年吉林省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異系數(shù)*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異系數(shù)=1-農(nóng)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通常認(rèn)為S≥0.5為城鄉(xiāng)二元結(jié)構(gòu)狀態(tài),0.2≤S≤0.5為由二元結(jié)構(gòu)向城鄉(xiāng)一體化的過渡狀態(tài),S<0.2基本上完成了城鄉(xiāng)一體化。為0.568,大于臨界值0.5,但低于全國的0.670,說明吉林省該年度處于城鄉(xiāng)收入二元結(jié)構(gòu)狀態(tài),但城鄉(xiāng)收入差距程度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從金融發(fā)展角度看,吉林省城鄉(xiāng)金融不均衡程度較高,金融發(fā)展總體相對滯后。橫亙在城鄉(xiāng)間的金融二元結(jié)構(gòu)直接阻礙了城鄉(xiāng)二元結(jié)構(gòu)的改變。目前學(xué)術(shù)界尚缺乏關(guān)于吉林省金融發(fā)展對城鄉(xiāng)收入差距影響機(jī)制的經(jīng)驗分析,吉林省金融發(fā)展是否對收入增長具有顯著影響以及城鄉(xiāng)金融非均衡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引起城鄉(xiāng)收入差距擴(kuò)大等問題尚未解決。為此,本文運(yùn)用實證分析方法,研究吉林省金融發(fā)展對城鄉(xiāng)收入差距的影響機(jī)制,并試圖從金融發(fā)展非均衡角度對吉林省城鄉(xiāng)收入差距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這一基本事實進(jìn)行解釋。
二、吉林省城鄉(xiāng)收入差距與金融非均衡的經(jīng)驗事實
(一) 吉林省城鄉(xiāng)收入差距的經(jīng)驗事實
吉林省與全國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異系數(shù)曲線如圖1所示。直觀上,兩條曲線均呈現(xiàn)波動上升的走勢,吉林省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異系數(shù)始終低于全國同期水平。根據(jù)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異系數(shù)臨界值可以判斷,2000年以來吉林省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異系數(shù)超過臨界值0.5,而全國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異系數(shù)大多數(shù)年份超過0.5(除1982~1985年),城鄉(xiāng)收入二元結(jié)構(gòu)明顯。
從圖1可看出兩條曲線具有相似的波動特征,統(tǒng)計分析表明,兩個序列的相關(guān)系數(shù)高達(dá)0.91。具體而言,改革開放初期,無論是吉林省還是全國城鄉(xiāng)收入差距均呈現(xiàn)下降趨勢,這是因為改革開放初期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在農(nóng)村的推行促進(jìn)了農(nóng)村居民收入大幅增長,從而縮小了城鄉(xiāng)收入差距。1983年中央下發(fā)1號文件,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迅速在全國范圍推行開來,這一年無論是吉林省還是全國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異系數(shù)均降至最低。1986年隨著市場化步伐的推進(jìn),城鎮(zhèn)居民收入大幅增長,城鄉(xiāng)收入差距開始逐漸擴(kuò)大。“十一五”期間惠農(nóng)政策落實到位,2010年吉林省和全國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異系數(shù)又開始緩慢下降。

圖1 全國與吉林省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異系數(shù)數(shù)據(jù)來源:歷年《吉林省統(tǒng)計年鑒》和《中國統(tǒng)計年鑒》。
分別從城鎮(zhèn)和農(nóng)村兩個角度來看,改革開放以來,吉林省城鎮(zhèn)經(jīng)濟(jì)發(fā)展相對滯后。由圖2可知,吉林省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國的百分比始終圍繞在-0.2附近,說明吉林省城鎮(zhèn)居民人均收入長期低于全國水平20%左右。然而,吉林省農(nóng)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在大多數(shù)年份高于全國水平,1985年以前吉林省農(nóng)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超過全國水平20%以上,這說明1985年以前吉林省農(nóng)業(yè)優(yōu)勢較為明顯。1985年起這一比率大幅下降,個別年份(2000~2003年)小于0。依據(jù)公式[∑(吉林省農(nóng)村人均純收入-全國農(nóng)村人均純收入)/∑全國農(nóng)村人均純收入]計算動態(tài)平均數(shù),吉林省農(nóng)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在平均水平上仍高于全國水平4.41%。綜上,吉林省城鄉(xiāng)收入差距低于全國水平的主要原因是農(nóng)村人均收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而城鎮(zhèn)人均收入低于全國水平。

圖2 吉林省農(nóng)村、城鎮(zhèn)居民收入與全國水平對比注:吉林省農(nóng)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高于全國百分比=(吉林省農(nóng)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全國農(nóng)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全國農(nóng)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吉林省城鎮(zhèn)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國百分比同理計算得出。數(shù)據(jù)來源:歷年《吉林省統(tǒng)計年鑒》和《中國統(tǒng)計年鑒》。
(二) 吉林省城鄉(xiāng)金融非均衡的經(jīng)驗事實
一般認(rèn)為,金融發(fā)展主要表現(xiàn)為金融總量的提升,用于衡量金融發(fā)展的指標(biāo)通常表示為金融總量與產(chǎn)出之比,如FIR和M2/GDP等。Pagano認(rèn)為金融轉(zhuǎn)化效率具有增長效應(yīng)*Pagano(1993)通過模型推導(dǎo)得出公式:g=Aφs-δ ,其中g(shù)為經(jīng)濟(jì)增長率,A為技術(shù)水平、φ為金融轉(zhuǎn)化效率、s為儲蓄率、δ為資本折舊率。[8]。金融轉(zhuǎn)化效率應(yīng)定義為銀行中介的投資量與銀行吸收儲蓄的比例,因此,金融轉(zhuǎn)化效率高低是衡量金融發(fā)展水平的重要方面。故本文從金融規(guī)模和金融轉(zhuǎn)化效率兩個角度衡量金融發(fā)展水平。金融規(guī)模可由金融總量與GDP之比計算得出,計算城鄉(xiāng)金融規(guī)模時,由于股票、債券和保險等金融資產(chǎn)缺乏城鄉(xiāng)的分類數(shù)據(jù),因此分別用城鄉(xiāng)存貸款總額代替金融總量;農(nóng)村GDP由第一產(chǎn)業(yè)增加值與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總產(chǎn)值之和計算得來,城鎮(zhèn)GDP由全國GDP與農(nóng)村GDP做差得到;金融轉(zhuǎn)化效率為貸款與存款之比,表示存款轉(zhuǎn)化為貸款的能力和效率。
通過計算動態(tài)平均數(shù)對吉林省與全國金融發(fā)展非均衡程度進(jìn)行比較分析。根據(jù)相對數(shù)平均發(fā)展水平計算的基本思想,金融規(guī)模平均發(fā)展水平運(yùn)用所有樣本點(diǎn)(Σ(存款+貸款)/ΣGDP)計算得到。通過計算可知,1978~2013年吉林省城鎮(zhèn)金融規(guī)模平均水平為1.81,農(nóng)村金融規(guī)模平均水平為1.05,全國城鎮(zhèn)金融規(guī)模平均水平為1.93,農(nóng)村金融規(guī)模平均水平為0.96。可見,吉林省城鎮(zhèn)金融規(guī)模高于農(nóng)村,差值為0.66,比值為1.72;全國城鎮(zhèn)金融規(guī)模也高于農(nóng)村水平,差值為0.97,比值為2.01。這意味著,無論是吉林省還是全國都存在城鄉(xiāng)金融發(fā)展總量非均衡現(xiàn)象,但吉林省非均衡程度低于全國水平。同理,金融轉(zhuǎn)化效率平均水平運(yùn)用所有樣本點(diǎn)(Σ貸款/Σ存款)計算得到。得出吉林省城鎮(zhèn)金融轉(zhuǎn)化效率平均水平為1.56,農(nóng)村金融轉(zhuǎn)化效率平均水平為0.54,全國金融轉(zhuǎn)化效率平均水平為1.02,農(nóng)村金融轉(zhuǎn)化效率平均水平為0.84。可見,吉林省城鎮(zhèn)金融轉(zhuǎn)化效率高于農(nóng)村,差值為1.02,比值為2.89;全國城鎮(zhèn)金融轉(zhuǎn)化效率也高于農(nóng)村水平,差值為0.18,比值為1.21。這說明,吉林省和全國均存在城鄉(xiāng)金融轉(zhuǎn)化效率非均衡現(xiàn)象,但吉林省非均衡的程度高于全國水平。
(三) 對比分析
表1總結(jié)了吉林省城鄉(xiāng)收入差距和金融發(fā)展非均衡程度以及與全國的對比情況。吉林省城鄉(xiāng)收入差距低于全國水平,金融規(guī)模差異程度低于全國水平而金融效率差異程度高于全國水平。基于金融發(fā)展對經(jīng)濟(jì)增長的促進(jìn)作用,可以判斷吉林省較高的城鄉(xiāng)金融轉(zhuǎn)化效率差異并沒有導(dǎo)致城鄉(xiāng)收入差距快速擴(kuò)大,城鄉(xiāng)收入差距仍低于全國水平,而較小的城鄉(xiāng)金融規(guī)模差異可能對城鄉(xiāng)收入差距存在顯著影響。由此推測,吉林省金融效率差異對收入差異的影響機(jī)制可能存在阻滯。為此,本文將通過協(xié)整分析來判斷吉林省城鄉(xiāng)收入差距、金融規(guī)模和轉(zhuǎn)化效率差異的長期穩(wěn)定關(guān)系,并進(jìn)一步專門針對金融轉(zhuǎn)化效率對收入差距的影響機(jī)制進(jìn)行實證分析。

表1 吉林省城鄉(xiāng)收入差距、金融發(fā)展非均衡及其與全國對比情況
三、吉林省城鄉(xiāng)金融非均衡影響城鄉(xiāng)收入差距的實證檢驗
(一) 指標(biāo)選擇與數(shù)據(jù)處理
實證部分將涉及到城鄉(xiāng)金融非均衡指標(biāo)與城鄉(xiāng)收入差距指標(biāo),為統(tǒng)一量綱,所有變量均以比值來表示。具體而言,城鄉(xiāng)收入差距由吉林省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nóng)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做商計算得出,記為Yt;城鄉(xiāng)金融非均衡從金融規(guī)模差距和金融轉(zhuǎn)化效率差距兩個角度來衡量,金融規(guī)模差距由城鎮(zhèn)金融規(guī)模與農(nóng)村金融規(guī)模做商計算得出,記為X1t;金融轉(zhuǎn)化效率差距由城鎮(zhèn)金融轉(zhuǎn)化效率與農(nóng)村金融轉(zhuǎn)化效率做商計算得出,記為X2t;另外,城鎮(zhèn)化水平是城鄉(xiāng)收入差距的重要影響因素[9],因此,選取人口城鎮(zhèn)化指標(biāo)作為模型的控制變量,該指標(biāo)由非農(nóng)業(yè)人口與全部人口做商計算得出,記為X3t。數(shù)據(jù)樣本區(qū)間為1978~2012年,所有數(shù)據(jù)均來自各期《吉林省統(tǒng)計年鑒》、《中國統(tǒng)計年鑒》、《中國農(nóng)村統(tǒng)計年鑒》和《中國金融年鑒》。
(二) 金融發(fā)展非均衡與城鄉(xiāng)收入差距的協(xié)整分析
本部分使用JJ(Johansen-Juselius)協(xié)整檢驗考察吉林省城鄉(xiāng)金融非均衡與城鄉(xiāng)收入差距之間的長期關(guān)系。ADF單位根檢驗顯示在10%的顯著水平下所有變量均為一階單整序列(如表2),選擇滯后期為4,協(xié)整檢驗結(jié)果顯示,4個變量中至少存在2個協(xié)整關(guān)系(如表3),正規(guī)化的協(xié)整方程如式(1)所示,括號內(nèi)則為標(biāo)準(zhǔn)差。

表2 單位根檢驗結(jié)果
注:***、*分別表示在99%和90%的置信水平下拒絕原假設(shè)。

表3 協(xié)整檢驗結(jié)果
注:*表示拒絕原假設(shè)。
式(1)表明,吉林省城鄉(xiāng)收入差距與金融非均衡存在長期均衡關(guān)系,協(xié)整系數(shù)均為正數(shù),說明吉林省城鄉(xiāng)收入差距隨著金融非均衡程度的增強(qiáng)和城鎮(zhèn)化水平的擴(kuò)大而逐漸擴(kuò)大。從協(xié)整向量估計值可以看出,金融規(guī)模差距(X1t)的系數(shù)較大,標(biāo)準(zhǔn)差較小,這意味著城鄉(xiāng)金融規(guī)模差距與城鄉(xiāng)收入差距的長期關(guān)系較為穩(wěn)定,如果城鎮(zhèn)金融規(guī)模超過農(nóng)村1倍,城鎮(zhèn)人均收入將超過農(nóng)村2.228倍。協(xié)整向量估計值還顯示,金融轉(zhuǎn)化效率差距(X2t)系數(shù)較小,標(biāo)準(zhǔn)差較大,如果城鎮(zhèn)金融轉(zhuǎn)化效率超過農(nóng)村1倍,城鎮(zhèn)人均收入將超過農(nóng)村0.326倍,但這種長期關(guān)系并不穩(wěn)定。這一結(jié)果與本文第二部分的推測是一致的,即吉林省較大的城鄉(xiāng)金融轉(zhuǎn)化效率差異對城鄉(xiāng)收入差距影響不大,金融規(guī)模差距對城鄉(xiāng)收入差距更具解釋力。另外,城鎮(zhèn)化水平(X3t)的協(xié)整系數(shù)較大,說明城鎮(zhèn)化水平提升對城鄉(xiāng)收入差距(Yt)具有較大影響,但這種關(guān)系的穩(wěn)定性稍差。
由于城鄉(xiāng)金融轉(zhuǎn)化效率差異與城鄉(xiāng)收入差距長期關(guān)系不穩(wěn)定,下文將專門針對吉林省城鄉(xiāng)金融轉(zhuǎn)化效率差異對城鄉(xiāng)收入差距的影響機(jī)制進(jìn)行分析。
(三) 金融轉(zhuǎn)化效率差距影響城鄉(xiāng)收入差距的具體機(jī)制
為考察吉林省金融轉(zhuǎn)化效率差距影響城鄉(xiāng)收入差距的具體機(jī)制,本文對1978~2012年吉林省城鎮(zhèn)和農(nóng)村的金融轉(zhuǎn)化效率與收入關(guān)系分別進(jìn)行回歸分析,結(jié)果如表4所示。UYt和RYt分別表示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nóng)村居民人均純收入,UXt和RXt分別表示城鎮(zhèn)和農(nóng)村金融的轉(zhuǎn)化效率。為避免自相關(guān),故加入了AR(1)項。

表4 OLS分析結(jié)果
注:*表示在5%的顯著水平下拒絕原假設(shè)。
根據(jù)表4可知,城鎮(zhèn)金融轉(zhuǎn)化效率對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影響并不顯著,這是較高的城鄉(xiāng)金融轉(zhuǎn)化效率差異沒有引起城鄉(xiāng)收入差距有效擴(kuò)大的原因;農(nóng)村金融轉(zhuǎn)化效率提高顯著提升了農(nóng)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金融轉(zhuǎn)化效率提升1單位則農(nóng)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提升472.326單位,這意味著推動農(nóng)村金融轉(zhuǎn)化效率提升是進(jìn)一步縮小吉林省城鄉(xiāng)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
四、結(jié) 論
本文選取城鄉(xiāng)收入差距低于全國水平的吉林省為研究對象,對吉林省城鄉(xiāng)金融非均衡影響城鄉(xiāng)收入差距的機(jī)制進(jìn)行了多角度實證分析。發(fā)現(xiàn)吉林省城鎮(zhèn)經(jīng)濟(jì)相對滯后而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相對發(fā)達(dá),城鄉(xiāng)收入差距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吉林省城鄉(xiāng)金融非均衡表現(xiàn)為金融規(guī)模非均衡程度低于全國水平,金融轉(zhuǎn)化效率非均衡程度高于全國水平。實證結(jié)果表明:(1) 吉林省城鄉(xiāng)金融規(guī)模非均衡、金融轉(zhuǎn)化效率非均衡以及人口城鎮(zhèn)化進(jìn)程均與城鄉(xiāng)收入差距具有長期正向關(guān)系,這意味著金融規(guī)模和轉(zhuǎn)化效率非均衡擴(kuò)大以及人口城鎮(zhèn)化進(jìn)程均能引起城鄉(xiāng)收入差距擴(kuò)大。(2) 吉林省金融規(guī)模非均衡與城鄉(xiāng)收入差距之間的長期均衡關(guān)系最為穩(wěn)定,協(xié)整系數(shù)較高,這意味著吉林省較低的金融規(guī)模差距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吉林省城鄉(xiāng)收入差距低于全國水平這一事實。(3) 吉林省金融轉(zhuǎn)化效率非均衡與城鄉(xiāng)收入差距之間的關(guān)系穩(wěn)定性稍差,協(xié)整系數(shù)較小。進(jìn)一步的實證分析表明,吉林省城鎮(zhèn)金融轉(zhuǎn)化效率提高對收入沒有顯著影響,因此,較高的城鄉(xiāng)金融轉(zhuǎn)化效率差異沒有顯著引起城鄉(xiāng)收入差距擴(kuò)大;農(nóng)村金融轉(zhuǎn)化效率提高對收入影響顯著,這意味著提高農(nóng)村金融轉(zhuǎn)化效率是提高農(nóng)村收入的關(guān)鍵。
綜上,吉林省城鄉(xiāng)金融差異對城鄉(xiāng)收入差異低于全國水平這一事實具有解釋力,縮小吉林省城鄉(xiāng)收入差距應(yīng)從發(fā)展農(nóng)村金融、縮小城鄉(xiāng)金融非均衡程度入手。提升農(nóng)村金融轉(zhuǎn)化效率尤為重要,一方面應(yīng)通過提升資金利用效率直接提高農(nóng)村收入水平,另一方面應(yīng)降低農(nóng)村資金外溢,這不僅能夠直接提升農(nóng)村金融轉(zhuǎn)化效率,還有利于間接提高農(nóng)村金融規(guī)模從而提高農(nóng)村收入水平。
[1]Greenwood, J., Javanovic, B..Financial Development, Growth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98(5):1076-1107.
[2]Kuzents, S..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6,(45):1-28.
[3]張立軍,湛泳.金融發(fā)展影響城鄉(xiāng)收入差距的三大效應(yīng)分析及其檢驗[J].數(shù)量經(jīng)濟(jì)技術(shù)經(jīng)濟(jì)研究,2006,(12):73-81.
[4]Dayal-Gulati A, Husain A M. Centripetal Forces in China′s Economic Take-off[R].IMF Working Paper, 2000:1-86.
[5]孫永強(qiáng).金融發(fā)展、城市化與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距研究[J].金融研究,2012,(4):98-109.
[6]姚耀軍,劉華華.金融非均衡發(fā)展及其經(jīng)濟(jì)后果的經(jīng)驗分析[J].華中科技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05,(4):75-78.
[7]魏麗莉,馬晶.雙重滯后型區(qū)域城鄉(xiāng)金融非均衡發(fā)展對城鄉(xiāng)收入差距影響的實證分析[J].蘭州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14,(1):118-126.
[8] Pagano,M..Financial markets and growth: an overview[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3,(37):613-622.
[9]吳先華.城鎮(zhèn)化、市民化與城鄉(xiāng)收入差距關(guān)系的實證研究——基于山東省時間序列數(shù)據(jù)及面板數(shù)據(jù)的實證分析[J].地理科學(xué),2011,(1):68-73.
- 稅務(wù)與經(jīng)濟(jì)的其它文章
- 所得稅優(yōu)惠、R&D投入對企業(yè)業(yè)績的影響
——來自醫(yī)藥生物上市公司的經(jīng)驗證據(jù) - 我國互聯(lián)網(wǎng)金融發(fā)展的問題與對策
- 基于價格重構(gòu)視角的中國稀土資源稅改革
——廣晟有色和北方稀土案例 - 中美大豆價格的投機(jī)性泡沫檢驗
- 區(qū)域創(chuàng)新環(huán)境影響創(chuàng)新能力的理論與實證探究
- 經(jīng)濟(jì)快速下滑與基于貸款損失準(zhǔn)備的商業(yè)銀行風(fēng)險應(yīng)對
——來自中國上市、非上市商業(yè)銀行的經(jīng)驗證據(j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