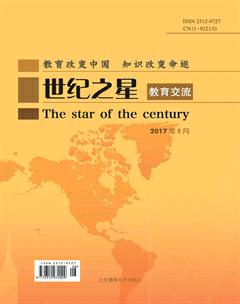風雨泗州城
李宏玉
[摘 要]泗州城遺址位于江蘇省盱眙縣淮河鎮城根村和沿河村一帶,始設于南北朝時期的北周大象二年(580年),隋朝毀于戰亂,唐代修建,宋代擴建,明代最為鼎盛,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黃河奪汴入淮,泗州城遭沒頂之災,康熙三十五年,泗州城徹底被泥沙淹沒,城址面積約2.4平方公里。泗州城作為州治城市共興盛了945年,它見證了一座因古汴河、淮河而興的漕運城市,訴說了一部與水相關的城市興亡史。經過三年多的考古發掘,目前泗州城遺址的輪廓、布局已經基本清晰,部分重要遺存已經揭露出來,其歷史、文化價值極高。
[關鍵詞]泗州城遺址;漕運中心;興盛;淹沒
泗州城遺址它是中國惟一一個災難性古城遺址,也是我國唯一遺址尚在但完全廢棄的古代州城遺址,被稱為“東方的龐貝古城”。泗州城位于盱眙縣城西,淮河鎮城根村、沿河村及大橋漁場三個自然村,北有扁擔河,南為淮河。面積約2.4平方公里,城址平面形狀略呈長圓形,其中有約六分之一面積處在淮河及其支河河道里。因淤墊很深,遺址整體保持狀況較好。
一、歷史沿革
泗州始設于南北朝時期的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州治初在宿預(今宿遷),歷160余年。隨著汴河的開通,汴河入淮口的地理位置變得極為重要,開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泗州移臨淮(即今盱眙縣淮河鎮境內),這里成為泗州州治。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州治沉沒,共945年。從清康熙十九年至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裁虹并泗,泗州在盱眙,歷97年。從乾隆四十二年到民國建元(公元1912年),廢府州制后,改泗州為泗縣,在原虹縣 (今安徽省泗縣),歷135年。
現今盱眙泗州城遺址即為公元735年—公元1680年的泗州州治所在,該城址為唐代始建,宋代擴建,明代最為鼎盛。關于泗州城在宋初《太平寰宇記》、清代《泗州志》等文獻中均有記載。
唐宋時期的泗州城有 “北枕清口,南帶濠梁,東達維揚,西通宿壽,江淮險扼,徐邳要沖,東南之戶樞,中原之要會”的特殊地理地位。泗州地處淮河下游,汴河之口,為中原之襟喉,南北交通之要沖,是古代典型的河口城鎮。 “天下無事,則為南北行商之所必歷,天下有事,則為南北兵家之所力爭”。是黃河、淮河、長江水道的中轉點,唐宋時的漕運中心,有“水陸都會”之稱。
二、州城淹沒
泗州城唐代初建時本身就位于淮水和泗水的交匯處,地勢較低。據水文地質資料和多次對泗州城遺址進行的勘探,唐代地面高程海拔為6.7米,明代地面經勘探在現地面以下6米(現泗州城遺址海拔高程為13米)。在南宋黃河奪淮前,泗州城就有七次被洪水浸害的記錄。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宋將杜充決開黃河,由泗達淮,使黃淮合流。元代以后,為了保證北方的供給,京杭運河成為治水重點。明萬歷六年(公元1578年)總理河漕的潘季馴推行 “蓄清刷黃濟運”的治漕、治河方針,即“筑堤障河,束水歸槽;筑堰障淮,逼淮注黃;以清刷濁,沙隨水去”。在泗州淮口下游筑高家埝(即今洪澤湖大堤),人為地把淮水蓄高,致使泗州地區受害慘重。清代和元、明一樣盡力保護漕運,使蓄淮濟運方針得到進一步貫徹實施,泗州城則長期處于洪澤湖正常水位之下。黃河奪淮以后,被稱為“水漫泗州”的大水,年有十多次。清康熙元年、四年、五年、九年、十一年、十五年,泗州都遭大水為害,受災非常頻繁。“康熙十八年冬十月大水,水勢洶涌,州城東北面石堤潰,決口七十余丈,城外居民抱木而浮,城內堙門筑塞,至日暮,城西北隅忽崩數十丈,外水灌注如建瓴,人民多溺死,內外一片汪洋,無復畛域,自是城中為具區矣”。自康熙十九年連續大水以后,泗州城再也沒有恢復的希望,因此歷史上把泗州沉沒的時間定為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
究其泗州城最后沉沒的原因,除了清康熙19年大雨是無可阻擋之天災之外,其最大的根源是洪水到了泗州一帶沒有了泄洪的出路。泗州歷史上,因為地勢比較低洼,飽受洪水之害,唐貞觀3年(629年)至南宋紹熙五年(1194年)的500多年間,受大水災患就達29年;宋代黃河南徙后,攔入清口,遏淮不得直下。元朝建都于北京,為了更便于江南的物資能直接運抵北京,下大力氣取直修通了北京直通杭州的京杭大運河,泗州城開始逐漸失去了漕運帶來的繁榮城市的機遇。大明王朝的后期,雖然泗州城的漕運之盛逐漸歸于平淡,但屢屢發生的黃河奪淮,洪澤湖、大運河水位抬高,直接侵害泗州城池和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然而,對于當時的大明王朝來說,京杭大運河是大明朝廷和大明天下最最重要的命脈之河,京杭大運河不能通航,直接影響是江南的鹽糧、貢品等不能及時抵達北京。所以,明代萬歷年間,國家“河漕總理”的潘季馴治理黃河奪淮之水患方法是,在與淮河相接的洪澤湖東岸,加筑起防洪大堤高家堰,來提高淮河水位,從而使淮河之清水從淮安清江浦的黃河奪淮主道口的清口處,倒灌黃河,以此清水來沖刷黃河帶給大運河的泥沙,以此來達到“濟運”安全,保證朝廷的經濟大動脈京杭大運河暢通無阻。應該說,潘當時實施這一治水方略,根本無法保證洪澤湖西岸的泗州城及周邊區域不被淹沒。但是,兩害相權取其輕,保證江南的糧、鹽和稅賦進京,維護皇權利益,這是壓倒一切的重中之重不可替代的大事。在明萬歷統治時期的23年(1596—1619年)中,黃河決口18次。泗州古城沉沒的第二個原因便是明清兩代所推行的“蓄清刷黃”、“濟運保漕”的錯誤治水政策。明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劉大夏主持治河時,堵塞黃陵岡,修筑太行堤,截斷黃水北流各泛道,逼黃水南泛,主要走汴泗、睢泗、渦河入淮,使黃河泥沙在淮河下游淤積日益加重。
明萬歷32年(1604年),還開辟了微山湖以下至駱馬湖之間的運河,以避免黃河航運的危險,這就是現在的韓莊運河的一部分。朝廷特派巡按御史邵陛前往泗州治水,邵陛所筑的邵公堤和保護明祖陵的磚石堤,換來了暫時的太平與安寧 ,明代之所以能夠把泗州城給保持住,其中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明朝皇家的龍脈在這個地方。在整個“水漫泗州”的歷史過程中,封建統治者為了他們各自的利益,對泗州河防工事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一些治理水患的官員怕危害明祖陵的顧忌,多次修筑防洪堤,在治水策略上也采取過“分黃導淮”和在洪澤湖大堤增設減水壩等措施,到了滿清王朝,康熙皇帝與大臣們只知筑壩攔水,不思疏導根治水患,其結局已注定了泗州城難逃淹沒的厄運,最終導演了這座千古名城沉沒的悲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