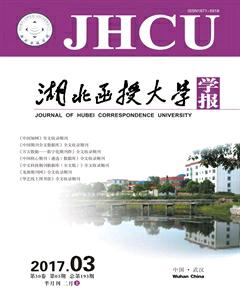淺析知識分子對北上參加新政協的響應
閻舒
[摘要]“五一口號”的提出是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長期合作的結果,這種對話,協商,并取得斗爭共識的民主形式,鼓舞了長期堅持斗爭的各民主黨派。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對于“五一口號”的熱烈響應,具有非同尋常的、而且是標志性的重要意義。而他們對邀請的接受與拒絕也表現出其內心情感的變化。
[關鍵詞]知識分子;北上響應
抗日戰爭的勝利使百姓看到光明,可是國民黨獨裁統治的野心使百姓再一次陷入深淵。長期被國民黨蒙蔽的知識分子終于看清楚他們的真實面目,他們對國民黨失去了信心。此時,中國共產黨發布的“五一口號”“全國勞動人民團結起來,聯合全國知識分子、自由資產階級、各民主黨派、社會賢達和其他愛國分子,鞏固與擴大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為著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而共同奮斗。”它提出各民主黨派聚在一起,以對話,協商的模式共同為中國的未來尋找一條合適的道路。口號的發出,讓這些知識分子激動不已。“五一口號”的內容發布到香港之后,得到了香港各界人士的熱烈響應。他們聯合發出《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聲明》,聲明中他們寫道,中國共產黨號召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是一個合時,并且讓大家感到十分激動,興奮與快慰的事情,他們愿意響應這個提議,愿意以這種協商的方式為中國的未來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一、對“五一口號”的響應
一些知識分子清楚地知道,即將到來的這個新中國,他們對其雖然是陌生的,但是值得期待。對于知識分子來說,不論他們曾經的想法是什么樣的,當下的局面與轉折,除舊布新,無可避免。國共兩黨協商簽署的“雙十協定”,舊政協的舉行,重慶會談的召開,這些都使知識分子對當時結束一黨專政、和平建國的政治決策抱有希望,他們相信國家將會和平發展,但事實卻讓他們非常失望。政治局勢的混亂,物質的極度匱乏,物價的不斷上漲,經濟的滑坡,國民黨內部的腐敗,都讓他們灰心;人民群眾的生活再一次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他們更是心如刀絞。這種現實與理想的矛盾沖突,一點點地毀滅了知識分子對國民黨曾抱存的希望與信任。由此,于無形當中把知識分子推向倡導并致力于聯合政府的新政權一中國共產黨。同時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迅猛推進,使大批知識分子選擇“北上”。
新舊政權的交替,格局不斷地變化,許多未知無法預測,前進的道路雖難以接受,但他們不愿流亡他鄉;面對民族的未來,各民主黨派及無黨派人士躍躍欲試,期待能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毛澤東主席在“五一口號”發布之后,給李濟深、沈鈞儒寫了一封信,信中他這樣寫道:“在目前形勢下,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加強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相互合作”,李濟深、沈鈞儒收到信函之后,激動不已,即刻召集了當時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的領導人聯名致電毛澤東,表明他們積極響應中共號召的決心,同意并期待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同時發表通電,號召國內外各界人士“共同策進,完成大業。”孤立蔣介石的偽裝民主思想,掀去南京獨裁政府的面具,共同為建立新中國而奮斗。旅港各界人士的聲明,在香港掀起了一個“迎接新政協”的熱潮,各界人士的響應、擁護都幻化成文字,在1948年中旬的《華商報》上一篇接一篇的刊登。民主黨派對“五一”口號的回應,標志著一個新的政黨制度的誕生,標志著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團結與合作。
二、對北上邀請的回應
社會各界對于“五一口號”的積極響應,使中共對未來更加充滿信心。在這種形式之下,中共開始籌備新政治協商會議,而會議中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敲定與會人員。戰后的中國百廢待興,在這樣的時刻更加需要知識分子聚在一起,共商國是。雖有少數知識分子會猶豫在中共的帶領下,他們會失去“自由”的學術之風,但是面對從中共發出的北上參加新政協會議的邀請,許多知識分子還是懷揣著夢想,決定北上。對北上邀請的回應,是知識分子心態變化最開始的一個寫照。
許多知識分子在面對中共中央的邀請的時候也是懷有遲疑的,比如張元濟先生。在中共的邀請函還未送到這位老先生手里的時候,在他與老友陳叔通的通信中,便得知自己被列為新政協代表的消息,可他馬上就回信拒絕了這個“身份”。而且當他正式收到中共邀請的時候,數次回信婉拒,左思右想,難以決定北上。且日記中寫到“故一時行止尚難決定”。中共再次誠意相邀,使其從原來的辭謝婉拒,到之后的觀望猶豫發生了些許的轉變。面對北上的誠意邀請,張元濟開始松動,一直到最后,當其逐漸了解了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之后,才決定接受邀請,北上赴會。這位經歷過中國動蕩的知識分子,他的心中對祖國抱有與其他人不一樣的深情與期待,他的北上行程承載了中國幾代知識分子對于未來的希望與夢想。
身為浙大校長的竺可楨,他的學術造詣與社會地位使他的選擇在當時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而瀕臨崩潰的國民政府也意識到人才的重要性,他們想要將這些知識分子帶去臺灣,為他們還未湮滅的野心儲備力量,可是一切并不如其所愿。面對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杭立武的邀請,竺可楨果斷拒絕,并提出要辭去浙大校長一職。竺可楨毫不猶豫的留在大陸并最終選擇北上,是因為他對國民黨貪腐、暴戾的不滿,宋子文、孔祥熙明目張膽的貪污使百姓的生活水深火熱;而蔣介石為了自身欲望,一次又一次的壓迫學生,更是讓他深惡痛絕。當然,中共地下黨不斷的爭取與團結也一直在轉變他的心態。收到中共的新年信函,雖沒有表露其內心的變動,但是竺可楨開始通過多種渠道,去了解中國共產黨。竺可楨在日記中寫道“法界與河南之英界公共汽車已照常行使。解放軍在路邊站崗,秩序極佳,絕不見欺侮老百姓之事。在研究院門前亦有崗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之站崗者倦側臥地,亦絕不擾人,紀律之佳誠難得也。”這種感性認識,使他最終答應了中共北上的邀請。
當然,也有少數知識分子最終拒絕北上。雖然對國民黨執政深感失望,但是面對陌生的中國共產黨,他們也不敢輕易北上。比如陳光甫,在國民政府搖搖欲墜的時候,他的社會聲望讓蔣介石十分想招致麾下。不過,由于他對國民黨的失望與不滿,加之信息的匱乏,使他對中國共產黨知之甚少。對于中共的邀請,他思慮再三,他曾寫道:“思想復雜,頗思至美一行,即可解決上海之一切煩惱。”但想法歸根結底只能是想法,現實的形勢還是要面對,經濟會議的邀請使他去往了香港,香港的整齊與繁榮又使這位知識分子感嘆不已。由于不了解所導致的對中國共產黨存在的偏見,讓他對于這個政權還處于觀望的態度。就是這樣的一位知識分子,中共的爭取與勸說從未停止過。
許多知識分子看到了中共對新政協充分的準備,再加上他們的親身經歷,使他們愿意相信共產黨。所以,當中共“五一口號”發布,當中共中央的邀請到達的時候,他們選擇了北上。有果斷、有猶豫、也有拒絕,每個人看待事情的角度不同,導致知識分子在面對北上邀請時,表現出了不同的態度。
當然在“五一口號”發布之后,國民黨特務與英國方面加強了對知識分子的監視,致使大部分在香港避難的知識分子十分厭煩,這種惡化的局面,也成為知識分子考慮北上的因素。這大范圍的監視,也為后來中共安排知識分子安全北上增加了難度。與此同時,共產黨的真誠相邀,時時從解放區傳來的百姓安定祥和的生活環境,更加加速了知識分子北上的進程。無論國家的局勢如何動蕩不安,人們內心所堅守的信念是不會更改的,對于生于斯長于斯的這方土地,知識分子對其傾注的感情是難以用語言形容的。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