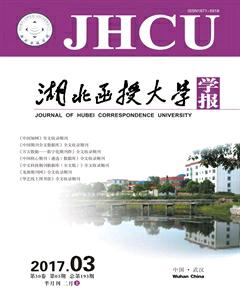關于錯誤出生損害賠償請求權相關問題的實證分析
尹進輝
[摘要]因醫療機構及醫務人員的過錯使畸形胎兒的出生成為可能和必然時,這不可避免地會產生胎兒父母與醫方的損害賠償問題。錯誤出生損害賠償范圍及請求權的行使主體,一直是國內外人格權理論研究的難題,而相關理論研究和立法對此定性莫衷一是。以期對錯誤出生損害賠償請求權相關問題的理論梳理與實證研究,對我國司法實踐解決此類糾紛與訴訟有所裨益。
[關鍵詞]畸形胎兒;過錯;損害賠償;請求權
一般而言,懷孕婦女大都會在醫療機構接受產前檢查及產前診斷等項目,以確保胎兒的健康出生。然而,在現實社會中,依然存在著大量畸形胎兒出生的狀況。這種現象不但與國家提高生育質量和人口素質的政策相違背,也給殘疾孩子的父母帶來嚴重的精神傷害和財產損失。在司法實務中,存在三方民事主體以醫療機構及醫務人員的過錯為由訴諸法院的情況,即殘疾孩子及其父母親。殘疾孩子父母親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的基礎及范圍,在司法實踐及理論研究中爭議不大。但殘疾孩子是否具有原告主體資格,一直是國外及國內理論研究的難題,即殘疾孩子因醫療機構及醫務人員的過錯來到人世,是否可對其的不出生主張損害賠償?在下面敘述的寧波魯天成案件,我國法院對殘疾孩子的原告主體資格是否認的。此外,錯誤出生案件涉及的損害賠償請求權范圍問題,有待理論研究及司法實踐綜合法律、政策、倫理等因素,作出較為可行且合法、合理的選擇。
一、錯誤出生損害賠償的請求權基礎
(一)父母的損害賠償請求權
1.以違約之訴提起損害賠償
患者在醫療機構接受醫務人員的檢查、診斷和治療時,這無形之中已在患者與醫方之間成立一個醫療服務合同,但在我國《合同法》中,并未對此作出具體規定。根據司法實踐的通常做法,對此可參照服務合同、委托合同以及其他相關合同的規定。具體言之,胎兒的父母因胎兒的健康狀況到醫院進行產前檢查和產前診斷,并支付相關費用,醫方有義務根據現有的醫療技術水平對胎兒做出準確的診斷,并應對胎兒父母履行告知義務。但因醫方的過錯,應能及時發現胎兒的缺陷而未發現,或者已發現胎兒的畸形而未告知,這不可否認地剝奪了胎兒父母對胎兒是否出生做出最優選擇的權利,使胎兒父母不得不面臨殘疾孩子已出生的事實。由此可見,醫方違反合同的規定,使得胎兒的父母造成巨大的精神損害及撫養殘疾孩子的損失,殘疾孩子的父母是有權要求醫療機構作出適當的財產賠償。
2.以侵權之訴提起損害賠償
我國傳統民法理論認為,在違約之訴中,不能提起精神損害賠償請求。在錯誤出生案件中,基于合同相對性原則,胎兒的父親作為原告主體資格存在諸多限制。申言之,以侵權為由提起損害賠償訴訟,胎兒的父母不僅可獲得財產上的賠償,精神損害也可獲得賠償,既包括直接損失,也包括間接損失。這也是司法實踐中,大多數殘疾孩子父母以侵權作為案由的重要原因。此外,在錯誤出生侵權責任理論研究中,多數學者堅持認為醫方違反注意義務侵犯了母親的健康權、知情權、優生優育權等,相比而言,父親的健康權卻未被侵犯。我國侵權責任構成要件理論有三要件說,四要件說等,但無論采取何種學說,殘疾父母須在承擔一般舉證責任的基礎上,還須滿足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
(二)錯誤生命的損害賠償請求權
1.主體是否適格的爭議
理論通說認為,殘疾新生兒以自己的名義起訴醫療機構或醫務人員請求損害賠償的錯誤出生案件中,稱為“錯誤生命”案件。殘疾孩子是醫療機構或醫務人員過錯產生的直接受害者,依據《我國侵權責任》第16條、第22條等規定,其有權獲得精神損害和財產損失的賠償。但錯誤生命作為原告主體資格引起最大的爭議是其因醫療機構或醫務人員的過錯獲得生命的利益,若無侵權行為或違約行為,其生命將不復存在。這種悖論不但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及理論研究中定性不一,也是國外相關理論探討的較大難題。國外司法實踐中,有些國家是支持錯誤生命之訴的,例如美國某些州法院判例,但也有些國家是明確排斥錯誤生命之訴的,例如德國法院判例。
2.錯誤生命損害賠償請求權的價值取舍
依據合同相對性原理,錯誤生命顯然不具備提起違約之訴的主體條件。那么錯誤生命是否具備提起侵權之訴的主體條件呢?其提起侵權之訴的價值基礎是什么?國外相關理論及司法實踐很少認可殘疾孩子的損害賠償請求權。究其原因,有以下幾方面:一是醫療機構或醫務人員對殘疾胎兒不負有注意義務。新生兒的殘疾是因遺傳或先天性因素而非醫療過失所造成,這涉及到“死亡要好過殘疾的生命”的悖論,這也有違我國社會公共利益的基本價值取向。二是法律并未規定任何主體可以主張其的不出生可獲得利益,出生并不是對權利主體的一種損害。進一步來講,若認為殘疾生命有權獲得賠償,那么法院在其賠償范圍及賠償數額尚無法律法規依據,且容易導致醫療機構及醫務人員的防御性治療行為。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也有很多學者認可錯誤生命的損害賠償請求權,一方面可不探討“死亡要好過殘疾的生命”命題,主張醫療機構及醫務人員對殘疾孩子的事實上的損害;另一方面可基于公共政策的原因,以殘疾孩子與同齡孩子在財產上多支出的費用,由醫療機構進行適當賠償,但應嚴格限制醫療機構的賠償責任。
二、寧波魯天成案件及引起的反思
(一)案情簡介
魯天成的母親張小榮懷孕后到被告某衛生院做保健檢查,在該院做了四次B超檢查,但原告魯天成出生后左手腕關節以下缺失。原告魯天成認為,因被告B超診斷過錯使其殘疾出生,對其未來人生帶來很多不利影響,故以醫療事故人身損害賠償為由訴至法院,要求被告賠償精神損害以及多項醫療財產損失。法院認為,本案為優生優育選擇權賠償糾紛,依我國《民法通則》相關規定,在被告對原告母親張小榮進行產前檢查時,原告并未出生,故為無民事權利能力,其優生優育選擇權只能由其父母行使。在殘疾胎兒出生后,原告父母若以殘疾新生兒名義起訴,要求原告對自己生存權利做出選擇,明顯不符合常理,原告家長作為法定代理人超越代理權限,本案原告主體不適格,故魯天成不具備成為本案原告的主體資格。endprint
(二)案件引起的反思
根據我國《民法通則》、《繼承法》等法律的相關規定,公民的民事權利能力始于出生,終于死亡,但涉及胎兒繼承問題,又肯定了胎兒活體出生時的遺產分割特留分。目前,胎兒民事權利能力范圍尚未在學界取得共識,但值得稱贊的是《民法典·總則(草案)》對胎兒利益的保護,視為已出生的規定,這將從法律層面肯定胎兒的利益保護范圍。因此,本案法官在審理錯誤出生案件,全盤否定胎兒的民事權利能力欠缺合理性。此外,錯誤生命之訴案件,不僅涉及胎兒的民事權利能力的規定,還與醫療機構及醫務人員的具體侵害行為有關。大陸法系及英美法系理論研究及司法判例也未在公共政策保護領域方面達成共識。
三、錯誤出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范圍的限制
(一)父母的過錯
在侵權責任法上,受害方在受到侵害時也獲得相應利益時,侵害人可主張在損害賠償中抵消受害人所獲得利益的部分,此種理論稱為“損益相抵理論”。具體言之,在錯誤出生案件中,父母因胎兒出生獲得情感利益,可在損害賠償方面適當減輕醫療機構及醫務人員的賠償責任。然而,此理論適用于錯誤出生案件中獲得較大詬病,損害賠償與父母享受的情感利益性質不同,即前者屬于財產利益后者是精神利益。此外,在享受為人父母喜悅上強行加上價格標簽,有違反社會公共利益傾向。在錯誤出生案件中,因醫療行為的特殊性,父母的不配合、未如實告知醫務人員其身體的特質、未遵照醫囑進行相應的治療,以及有不良嗜好等,都可對殘疾胎兒的出生造成不可估量的影響。因此,在權利人行使錯誤出生損害賠償請求權時,醫療機構及醫務人員可主張相應的抗辯。
(二)醫療水平的限制
根據我國《侵權責任法》第60條第1款第3項的規定,在錯誤出生案件中,限于當時醫療水平未準確顯示出殘疾胎兒的狀況,從而未履行告知義務,醫療機構及醫務人員可主張醫療損害責任的免責。醫生的防御性治療,即是醫生在具體的治療行為中為使自己不承擔醫療損害責任而采取的消極性行為。在錯誤出生案件中,若不加限制地賦予殘疾孩子父母的損害賠償請求權,以及錯誤生命的損害賠償請求權,這無疑會導致醫療機構及醫務人員的防御性治療,進而使得我國醫療行業陷入被動的局面。此外,殘疾孩子的損害賠償范圍以及父母的精神損害賠償范圍的限制,這對于平衡權利人及醫療機構的責任分配,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總之,在處理錯誤出生案件中,不但要合理滿足權利人的訴求,也要避免醫療機構及醫務人員的防御性治療。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