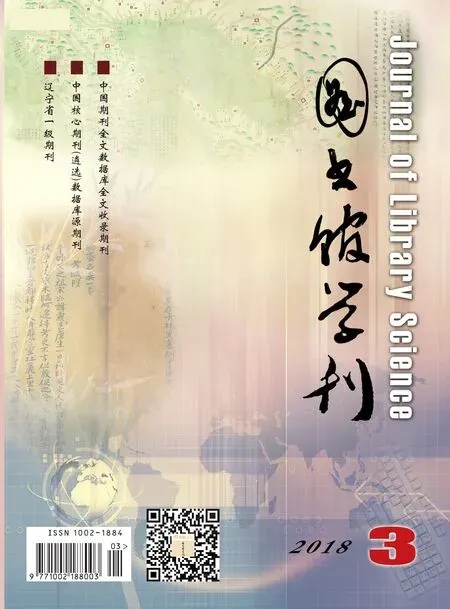我國圖書館復制權例外制度的適用與完善
劉 俏
(深圳市鹽田區圖書館,廣東 深圳 518000)
復制權是版權財產權中的一項最基本而核心的權利,在版權制度誕生之初,權利人就享有了復制權。按照1709年英國頒布的世界上第一部版權法──《安娜女王法》的規定,作者對已印制的圖書在重印時享有專有權,對創作完成但尚未印刷的作品也有同意或者禁止他人“印刷出版”的專有權[1]126。在《伯爾尼公約》聯盟成立時,所有簽字國的法律都對復制權作了規定,但是直到1967年《伯爾尼公約》斯德哥爾摩文本才將復制權作為一項最低標準納入其中,原因是在此之前各成員國沒有就復制權的內容與范圍達成一致意見[2]。復制權限制是《伯爾尼公約》提出的明確要求,也是各國版權法用來平衡版權利益關系的重要制度,而圖書館是這項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針對圖書館的需求逐漸建立起了適用于模擬技術和數字技術的復制權例外制度,對圖書館收藏、保存與開展信息服務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我國圖書館復制權例外制度在實踐中還存在不適應的問題,需要得到不斷改進和創新。
1 我國對圖書館復制權例外制度的立法
1.1 模擬復制權例外制度的立法
關于圖書館復制權例外,在國際公約中沒有直接的或者明確的依據,一般認為《伯爾尼公約》第9條第2款對復制權例外的“三步檢驗法”是圖書館復制權例外制度的法律基礎[3]。《伯爾尼公約》第9條第2款規定:“本同盟成員國法律得允許在某些情況下復制作品,只要這種復制不損害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致無故侵害作者的合法利益。”以此為依據,許多國家都建立了圖書館復制權例外制度。比如英國《版權法》規定,政府指定的圖書館,可以為研究和個人學習之目的,復制作品的一部分,可以為保存和替代之需要,復制圖書館的永久收藏物。澳大利亞《版權法》規定,在無償的前提下,圖書館可以為學習研究、館際互借以及保存、替換之目的復制館藏作品[1]。1984年6月,我國文化部頒布的《圖書、期刊版權保護試行條例》第15條規定,在尊重作者權利,說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稱、出處的前提下,“圖書館、檔案館、資料或文獻中心,為了借閱、存檔或為專業人員提供專業資料,復制本館或本中心收藏的作品,而不在市場上出售或借此營利”。這是我國制度體系中最早的關于圖書館復制權例外的規定。1990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頒布,其第22條第8款規定,在注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稱和出處,并且不侵害著作權人依法享有的其他權利的前提下,“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紀念館、美術館等為陳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復制本館收藏的作品。”這項規定在2001年、2010年《著作權法》的修訂中都未改變。
1.2 數字復制權例外制度的立法
復制權例外是否適用于數字技術曾在國際上引起較大爭論。《伯爾尼公約》第9條第2款用了“以任何方式和采取任何形式”的表達。1971年《伯爾尼公約導讀》認為,“以任何方式和采取任何形式”達到了足夠寬泛的程度,能夠覆蓋所有的復制方式,包括:設計、平面印刷、打字、照相復制、靜電復印、錄音……等已經和其他未知的復制方法[2]。1996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WCT)關于第1條第1款的議定聲明規定:《伯爾尼公約》第9條所規定的復制權及其所允許的例外,完全適用于數字環境,尤其是以數字形式使用作品的情況。不言而喻,在電子媒體中以數字形式存儲受保護的作品,構成《伯爾尼公約》第9條意義下的復制。WCT第10條的議定聲明還指出,締約各方可以將《伯爾尼公約》允許的限制與例外繼續適用并適當地延伸到數字環境[4]。至此,各國有了建立數字復制權例外制度的國際法根據。比如,1998年美國《跨世紀數字版權法》(DMCA)第404條規定,圖書館可以出于保存、替換之目的,對館藏制作三份數字化復制件,但不能向館舍外傳播。2006年7月我國《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第7條規定:“圖書館、檔案館、紀念館、博物館、美術館等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通過信息網絡向本館館舍內的服務對象提供本館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數字作品和依法為陳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數字化形式復制的作品,不向其支付報酬,但不得直接或者間接獲得經濟利益。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還規定:“前款為陳列或者保存版本需要以數字化形式復制的作品,應當是已經損毀或者瀕臨損毀、丟失或者失竊,或者其存儲格式已經過時,并且在市場上無法購買或者只能以明顯高于標定的價格購買的作品。”這是目前我國圖書館適用例外制度以數字化方式復制作品的最主要法律依據。
2 我國圖書館復制權例外制度的適用
2.1 適用主體要件
許多國家的版權法對適用復制權例外制度的圖書館類型作了明確限定。比如在英國必須是“政府指定的圖書館”,在美國則應是“向公眾開放,或者至少是開放給附屬于本圖書館或圖書館所屬機構研究者之外的研究者的圖書館”。[5]無論是我國《著作權法》第22條第8款,還是《條例》第7條都使用了“圖書館”這種最寬泛的概念,意味著在我國法律框架中任何類型的圖書館都是復制權例外制度的適用主體,而無論其主體性質,也不論其是否開放,或者開放的范圍與程度,既包括公辦的公共圖書館、高等學校圖書館、科研圖書館,還包括私立圖書館(比如私營醫院圖書館、私營企業圖書館、私營科研圖書館、民辦高校圖書館等)。
2.2 適用性質要件
“例外”是一種版權限制政策,用戶可以非經授權地使用作品,而且不必向權利人支付報酬。所以,出于公平和保護權利人利益的考量,版權法對“例外”設置了“反限制”條款,其中最重要的規定就是要求用戶復制作品“不得有經濟利益”。比如,美國《版權法》第108條規定,圖書館的復制行為不得有直接或商接的商業目的。按照我國《著作權法》第22條的規定,圖書館復制作品“不得侵犯著作權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權利”,“其他權利”就包括“經濟權利”。《條例》第7條也規定,圖書館復制作品“不得直接或間接獲得經濟利益。”因此,我國無論何種類型的圖書館,適用復制權例外制度均不能獲取任何商業利潤,即便是營利主體性質的圖書館亦是如此。
2.3 適用目的要件
按照《著作權法》第22條第8款的規定,我國圖書館享有的復制權例外權利只能在“陳列”或者“保存”版本的情況下行使,不得將復制件外借(包括外借給用戶個人或者外借給其他圖書館,或者其他組織),這與許多國家的法律規定相比,局限性明顯。比如按照美國《版權法》第108條第d款、第e款的規定,圖書館可以應用戶請求開展復制,也可以為館際互借目的開展復制,只要復制的“累計數量”未“替代作品的訂數或者購買”。我國《條例》第7條從“明顯復制例外”和“隱性復制權例外”的不同角度分別對圖書館的數字復制例外權利作了規定。“明示復制例外”指“為陳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數字化形式復制作品”,“隱性復制權例外”是將“復制”作為圖書館在館舍局域網中傳播作品所“必須”的一個前置程序。因為,《條例》第7條既然允許圖書館通過館舍內的局域網傳播作品,就首先要允許圖書館對作品進行數字化復制。
2.4 適用作品要件
圖書館復制權例外制度對適用作品類型有嚴格的規定。按照我國《著作權法》第22條第8款的規定,圖書館只能復制“本館收藏的作品”,而不能復制其他圖書館收藏的作品。在這里,“本館收藏的作品”應理解為本館享有所有權的作品,對于本館收藏的不享有所有權的作品(比如權利人寄存的作品、權利人交給圖書館臨時展覽的作品)不得復制。按照《條例》第7條的規定,圖書館復制的作品同樣應是“本館合法收藏”,并且出于陳列、保存版本需要以數字化方式復制的作品還必須是“已經損毀或者瀕臨損毀、丟失或者失竊,或者其存儲格式已經過時,并且在市場上無法購買或者只能以明顯高于標定的價格購買的作品。”另外,在我國版權制度框架內,圖書館適用復制權例外制度復制的作品還應是已經出版或者發表的作品,未出版和未發表的作品不得復制。
2.5 適用范圍要件
按照我國《著作權法》第22條第8款的規定,圖書館出于陳列、保存復制的作品復制件只能是“圖書館自己使用”,不得用于其他用途,包括不得外借給其他圖書館和個人。按照《條例》第7條的規定,如果圖書館通過信息網絡向用戶傳播作品,那么其受益用戶只能是“本館館舍內的服務對象”,“本館館舍”指的是“物理館舍”而非“虛擬館舍”,也就是說數字作品的傳播范圍必須控制在圖書館“物理館舍”之中,而不能向用戶遠程提供。另外,按照《條例》第10條的規定,用戶不能采取任何手段復制圖書館傳播的作品,只能閱讀和瀏覽。學術界對于“本館館舍內服務對象”內涵的理解尚存在分析,從利益平衡角度認識,應只限于“正式注冊”的圖書館館舍內的用戶,在圖書館內的臨時訪問、參觀人員等不在其列。
2.6 適用形式要件
按照我國《著作權法》第22條第8款的要求,圖書館復制作品應當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稱。美國、英國、加拿大等許多國家的版權法都有同樣要求。這是因為,“例外”限制的通常是權利人的財產權利,而不限制署名權等精神權利,這既是出于對權利人作出的智力創造貢獻的尊重,也是出于利益平衡的需要,同時也防止了作品在不斷傳播利用中可能出現的權利主體混亂現象。
3 完善我國圖書館復制權例外制度的建議
3.1 引入開放性立法模式
我國對版權例外制度的立法采取了“封閉立法模式”,即事先由法律擬定合理使用清單,再將使用作品的行為與其相對照,從而判斷該行為的合法性。但是由于技術的發展具有動態性和持久性特征,因而既定的合理使用清單不可能將新的使用作品的行為納入其中,造成法律的僵化與滯后。比如,在大數據時代,文本與挖掘技術將在圖書館領域得到越來越廣泛的應用,那么“挖掘”行為是否能夠被復制權例外制度涵蓋就是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目前,在國際范圍內,圖書館在對文本和數據挖掘技術的應用中遇到的諸多版權爭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對版權例外制度采取“封閉立法模式”導致的弊端。從全球觀察,對版權例外制度采取”開放立法模式“,以使法律具有更大的彈性和包容性是一個重要發展趨勢。比如,韓國、菲律賓、新加坡、以色列等國家都在版權例外制度的變革中吸納了開放立法的合理因素。建議在對我國圖書館復制權例外制度的創新中引入開放式立法,并與封閉式立法有機結合,更好地應對新技術的的挑戰。
3.2 細化相關的法律規定
“量化”是最明晰的標準,但是我國《著作權法》第22條第8款和《條例》第7條都沒有圖書館復制作品的“量”的規定,這使圖書館難以把握法律的界限,可能面臨不可預知的法律風險[6]。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的版權法對圖書館復制作品都有“量”的限制性規定。比如,按照美國《版權法》第108條第c款的規定,圖書館出于替換、丟失、被盜之目的,可以制作最多3件復制品。澳大利亞《數字時代版權法修正案》第51條規定,為學習和研究之目的,圖書館可以復制和傳輸一部作品或者期刊文章的10%[7]。除了“量化”不明晰之外,我國《條例》第7條的規定還有其他模糊之處。比如,何為直接經濟利益和間接經濟利益?如何判斷作品的存儲格式已經過時?什么是衡量作品在市場上無法購買,或者只能以高于標定的價值購買的標準?以及如何界定“本館館舍內的服務對象”?等等。要減小圖書館適用復制權例外制度的責任風險,就應該盡可能使相關規定得到“量化”,對于確實無法量化的條款或者術語,也要通過司法解釋厘清其內涵。
3.3 限制合同的法律效力
《條例》第7條在規定圖書館享有復制權例外權利的同時,又規定“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這種規定表面上是為了更好地協調權利人與圖書館之間的利益關系,但是在實踐中會更傾向于對權利人利益的保護,甚至可能使圖書館享有的法定權利化為烏有,變成紙上兵,造成法律規定的形同虛設。因為,按照“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的規定,權利人就可以利用其掌控版權的強勢地位,在與圖書館的談判中提出種種苛刻條件要求圖書館接受,否則就會以拒絕許可相威脅,或者通過對協議施加單邊意志極力擠壓圖書館的權利。特別是在數字技術條件和網絡環境中,“點擊合同”、“拆封合同”等特有的協議模式,更是使圖書館喪失了話語權,處于被動和無奈的境地。目前,我國《著作權法》及其配套法規并沒有就權利限制與合同的關系作出規定,而《合同法》對以格式條款排除和削弱版權例外的情形也無能為力[8]。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賦予圖書館復制權例外制度具有強行法的屬性,排除與例外制度相悖的版權合同的法律效力,使這種合同失去法律基礎。
[1]吳漢東,等.西方諸國著作權制度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126.
[2]保羅·戈爾斯坦著,王文娟譯.國際版權原則、法律與慣例[M].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3:252.
[3]吳偉光.著作權法研究──國際條約、中國立法與司法實踐[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418.
[4]國家版權局辦公室.國際版權條約和鄰接權條約[M].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0:388-391.
[5]秦珂.中美圖書館合理使用著作權的立法比較[J].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9(5):55-58.
[6]秦珂.2006年以來我國圖書館合理使用數字版權立法研究綜述[J].圖書館論壇,2016(8):55-60.
[7]露西·吉博著,劉躍偉譯.在為公共利益傳播知識任務方面版權和鄰接權限制與例外的性質與范圍:對其適應數字環境的展望[J].版權公報,2013(4):1-45.
[8]朱理.信息社會著作權的邊界[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