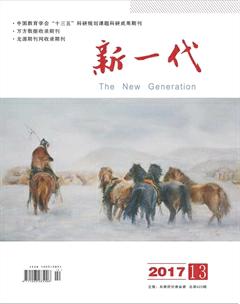語文期待文學
宣會霞
不覺中年齡早已邁過三十這個坎,從事語文教學也有十幾個年頭。從業生活中的點點滴滴,足令我嗟嘆!嘆息生活的匆忙,嘆息素養的缺失,嘆息氛圍的不協調等等。教學過程中困惑和茫然很多,當自己苦思無果后,我貪婪拜讀名師著作,以求解惑。名家的風格各自迥異,見解也是各有千秋,甚有矛盾抵觸的。其中王崧舟老師的詩意教學和王文麗老師的清新而又輕松的教學風格讓我耳目一新。王崧周老師的講納蘭性德的《長相思》讓大家真正體會到了那蕩氣回腸的情感。
我試圖反思自己,模擬他們,我發現他們都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有捕捉語言的敏感性,評價語言的準確性,從而引導語言的文學意味。“人文”即“人紋”,就是“人的印跡”、“人的特性“人的屬性”、“自身特點”。
語文是最重要的交際工具,是人類文化的組成部分。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是語文課程的基本特點(《語文課程標準》)。人文精神不應該是以追求崇高神圣為目的的,呼應思想政治教育,而應是張揚人的生命精神的自由,生命精神的真實,生命精神的獨立,生命精神的尊嚴。人文性特點的體現主要通過文學,因為文學的內涵即為“真、善、美”。我們理應讓語文課堂洋溢著文學氣息。
但是目前的教育現狀并不容我們樂觀。
目前在語文第一線執教的80%以上都是青年教師(也包括我),他們的大部分深層文化素質,文化底蘊很是不足。
為什么?
因為不讀書,有文化底蘊的書讀的尤其少。曾經有報道:在一中文系畢業生的寢室里轉一圈,發現的文學名著極少,畢業生們自我解嘲:要畢業了,要讀點實用點的;在中文系低年級寢室里轉一圈,發現的名著真多,《紅樓夢》、《茶花女》、《基督山伯爵》、《戰爭與和平》等等。拿起書一翻嶄新嶄新,似乎還沒動過。書的主人略帶羞澀的回答:大部分都是同學朋友送的生日禮物,還有一部分是自己買的,也一直沒抽出時間讀。這些將來要做中學教師的中文系學生,讀不懂先秦諸子的原著就看白話譯文,有的只看蔡志忠的漫畫,沒有讀過原著《紅樓夢》,看的是電視劇《紅樓夢》。
走上語文教學崗位后,在教學之余,閱讀最多的是晚報、電視報和各類流行雜志。一度使快餐文化盛行。在商業文化大潮使中國人的文化世風日下的境況下,“士”風與師風也有日下之趨勢。
這種風氣造成的不僅是教師語言文學功底差,更嚴重的是造成思想蒼白,情感貧乏,精神萎頓。很多人至今對《紅樓夢》中林黛玉的性格持簡單粗暴的否定、批判的態度,對其不理解,更不同情了;也有一些老師不理解《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保爾所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不理解不認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不理解不認同《最后一次演講》中聞一多的聲色俱厲,大義凜然。他們不相信“革命”、“斗爭”,又跟中國古代的傳統,跟人文關懷接不上頭。
上課怎么辦?只要依綱循本,死搬教參。這樣就使我們的語文教育抽取了人文底蘊,人文血脈,這也是當今語文教育缺乏感人魅力、枯燥乏味的主要原因。語文教育在“貧血”。博凡先生說:當今社會,人們越來越覺得荷馬、莎士比亞、托爾斯泰于我如浮云,他們想象不出除了上網聽流行歌曲看電視看晚報之外,還有什么更好的享受。(博凡《現代人的貧困》)。
突出人文就應該讓我們的課堂洋溢著文學氣息,這就要求我們語文教師走進文學,提高文學素養,增強文學底蘊。“自在飛花輕似夢,無邊絲雨細如愁”,其中的意境需要我們涵游品析,沉浸玩味。讀書者,自美麗,那是源于文學帶來的美麗。只有自己美麗,才能游刃有余地帶領學生實現美麗。
那么讀什么書?
個人認為,教師首當讀古詩。我們現代人從小接受的是白話教育,如今作為教育者對教育者實施的也是白話教育。我們對諸子百家,先秦文學,經但試問知之甚少,不爭的事實——我們與文言文有了隔閡。文言與白話是母子關系、根葉關系。白話絕大部分源于文言,大部分雙音節詞是文言的附綴演繹而來。絕大部分鮮活的成語源自文言典故。據有人研究,大陸傳媒,知識分子乃至文化人的語言表達失去了典雅精美,失去了古風,變得日益“淺白化”,“粗俗化”。我們拜讀一下汪曾祺先生的文章,雖是白話,卻詮釋了語言典雅凝練、回味無窮的感覺。不難發現汪老的文言功力十分深厚,他的語言特點應該源于此吧。
魯迅、郭沫若一代反對文言,自有他們那一代的歷史文化背景。他們之所以成為一個“鑒古知今”、“中西兼通”的文化人,成為一代知識分子的“圣賢”,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相當程度上與少年時期文言教育和傳統文化熏陶有直接關系。古文中有精華,但也有封建的糟粕。古人寫詩一般更能體現人的真性情,古文寫作中文人容易做偽。寫詩作詞,似乎屬于消遣娛樂。文似乎關于國運,寫文一般正經嚴肅。可以說文是古人的正面、外面,詩詞是古人的背面、里面。詩詞是心靈情感的外觀,文是先祖先宗的教喻。所以我們應讀詩詞。再者,生活在這個匆忙的時代,如果經典大餐不容有機會嚼的話,古詩詞就是最好的彌補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