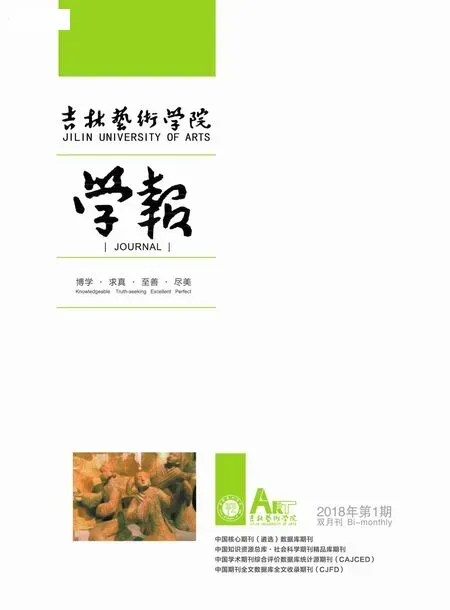變與思辨
——評劉曉真《走向劇場的鄉(xiāng)土身影》的舞蹈史敘事
屠志芬
(吉林藝術(shù)學(xué)院,吉林 長春,130021)
與其說這是一部舞蹈人類學(xué)著作,勿寧說是一部投注了人類學(xué)眼光的、別致的當(dāng)代舞蹈史學(xué)著作。它之所以打動我,除了青年學(xué)者劉曉真之年輕——完稿時僅32歲芳華,更因為32歲的她在行文間透露出的膽識、氣度和出色的治史能力。作者將鼓子秧歌置于60多年來中國社會變遷的大語境中,以時間為縱脈,貫通微觀(山東商河鼓子秧歌)、中觀(中國民間舞蹈)、宏觀(中國當(dāng)代社會)三個層面;關(guān)涉鄉(xiāng)野、課堂、劇場三度空間;輻射政治、文化、社會、歷史諸領(lǐng)域,于種種縱橫交織的繁雜關(guān)系中梳理鼓子秧歌自身的傳衍流變,同時深究這一典型民間舞蹈事象在文化風(fēng)貌、功能價值等方面發(fā)生變遷的外因與內(nèi)因。圍繞一個“變”字,于變中思辨,以思辨窮其變,令這部著作充滿開拓的睿智和理性的力量。
與以往同類著作相比,《走向劇場的鄉(xiāng)土身影——從一個秧歌看當(dāng)代中國民間舞蹈》(下文簡稱《走》)的突出特色是采取了一套獨特的網(wǎng)狀敘事策略。
一、網(wǎng)狀結(jié)構(gòu)
歷史是動態(tài)的。治史的難點之一就在于,能在動態(tài)結(jié)構(gòu)和關(guān)系中對歷史人物及事件之變進(jìn)行清晰描述和準(zhǔn)確客觀的判斷。傳統(tǒng)的歷史敘事常常采取“析出”的辦法,即把人或事件從復(fù)雜的社會關(guān)系中抽離出來,就其發(fā)生發(fā)展、傳承變異作線性描述,其間雖有前因后果的分析、對時代背景的關(guān)注,但為了集中呈現(xiàn)核心歷史事件,還是要建立相對獨立閉合的時空系統(tǒng)。同樣是為了求得歷史之“真”,《走》著則采取了一種“投入”式敘事,即把事件投入、或還原到復(fù)雜的社會歷史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中,予以開放性闡釋。
作者認(rèn)為,“在一個流動開闊的時空里,民間舞蹈的方位會更加明晰和真實”[1]2。在這個“流動開闊”的時空里,鼓子秧歌只是作者注目的核心對象。除此之外,作者還希望通過鼓子秧歌自身的發(fā)展演變,洞察當(dāng)代中國民間舞蹈的發(fā)展演變歷程,進(jìn)而透視1949年以來中國社會變遷的一個側(cè)面,同時闡明這三個層面的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正如緒言所論,《走》著“不再受限于狹義的本體形態(tài)研究和西學(xué)思維中的文化論述,而是……從一個更加寬闊的視野里重新審視作為社會文化因子的舞蹈究竟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并且聯(lián)結(jié)出其中的文化結(jié)構(gòu)”[1]9。如果說“析出”法能夠更加凸顯歷史事件自身的發(fā)展演變過程,那么這種盡最大努力還原文化語境的方式則體現(xiàn)了對整體真實、結(jié)構(gòu)真實、關(guān)系真實的追求。于是,傳統(tǒng)線性敘事在《走》著中變成了更為復(fù)雜的“網(wǎng)狀”敘事:以鼓子秧歌為綱,同時并置交叉民間舞蹈、中國社會兩條脈絡(luò),于鄉(xiāng)野、課堂、劇場三類空間場所轉(zhuǎn)換穿插,令政治、民俗、藝術(shù)、教育、學(xué)術(shù)研究諸側(cè)面互相關(guān)照。猶如影像拍攝時,虛化的中景、遠(yuǎn)景在鏡頭中被拉實,原本有虛實關(guān)系的長鏡頭,變成了以鼓子秧歌為主角的,民間舞蹈、國家行為交叉敘事的蒙太奇。這種處理方式,與傳統(tǒng)方法相比,無疑是一種更為繁難的歷史敘事方式。
二、核心事件
當(dāng)然,網(wǎng)狀敘事得以實現(xiàn)的前提是鼓子秧歌這一核心事件具備足夠強(qiáng)大的關(guān)聯(lián)功能,能夠以小見大,有效地集結(jié)起豐富的社會文化要素。如作者所言:“山東鼓子秧歌作為主角在國家發(fā)展的歷史中,不僅是一種民俗,還在不同時期穿梭在鄉(xiāng)村、首都舞臺、外省賽場各種空間和事件中……通過其表現(xiàn)形態(tài)、社會構(gòu)成的傳承和轉(zhuǎn)變,使人看到的不僅僅是傳統(tǒng)文化的沉淀、當(dāng)代人所賦予的審美,更有中國社會自身發(fā)展的各種問題……這種情形之下,對于山東鼓子秧歌研究的獨特性也隨之顯露,它引領(lǐng)人們進(jìn)入劇場演藝、國家意志、社會進(jìn)程所構(gòu)筑的當(dāng)代舞蹈史中”[1]4。作者敏銳意識到鼓子秧歌這個生長于魯西北的,從鄉(xiāng)野走向劇場、進(jìn)而進(jìn)入國家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鄉(xiāng)土“玩意兒”身上交織了太多中國歷史的、社會的、政治的、文化的、藝術(shù)的、教育的問題,對這一典型個案的研究,頗有牽一發(fā)而動千鈞的效應(yīng),因此才將其置于核心位置,沿橫向和縱深兩個方向延展敘事網(wǎng)絡(luò),建構(gòu)起小宇宙中的大世界。
三、關(guān)系之結(jié)
“網(wǎng)狀”敘事結(jié)構(gòu)的確立,使作者在核心事件之外,尤其注重對“關(guān)系”的研究和闡釋。如前所述,三條脈絡(luò)、三度空間以及社會歷史諸要素之間交互作用,形成錯綜復(fù)雜的關(guān)系,而鼓子秧歌的傳衍就是在這些繁雜關(guān)系中進(jìn)行的。如何實現(xiàn)對鼓子秧歌與當(dāng)代民間舞蹈及時代社會之間關(guān)系的準(zhǔn)確判斷和描述,找到“關(guān)系之結(jié)”成為十分關(guān)鍵的問題。“關(guān)系之結(jié)”就是敘事網(wǎng)絡(luò)上的交叉點,是指圍繞事物發(fā)展,由其自身和周邊時空要素交疊而形成的具有關(guān)鍵作用的人物、事件或物象等。《走》著中頗多對于此類關(guān)結(jié)點的準(zhǔn)確把握和巧妙處理。
如1989年商河鼓子秧歌參加“蓉城之秋”全國民間舞大賽并獲得金獎即是一例。該事件既是鼓子秧歌自身從復(fù)蘇走向轉(zhuǎn)型期的關(guān)鍵性事件,由它引發(fā)了鼓子秧歌自身的一系列變化——建立了比賽評獎機(jī)制,專業(yè)眼光開始影響鼓子秧歌的創(chuàng)作和表演,商河鼓子秧歌的社會影響力增強(qiáng),開始到全國各地參加演出、“全國首屆商河鼓子秧歌研討會”召開、獲得“中國民間藝術(shù)之鄉(xiāng)”稱號,民間藝人身份意識發(fā)生轉(zhuǎn)變等等,同時又從另一個側(cè)面勾聯(lián)起民間舞蹈在時代背景下的復(fù)蘇與發(fā)展?fàn)蠲病黝悤菡寡萑粘梢?guī)模,比賽制度影響力越來越大,全國范圍內(nèi)民族民間舞蹈挖掘整理工作成果日豐,民間舞蹈與專業(yè)創(chuàng)作、專業(yè)教育之間相互影響日深……對于繁雜現(xiàn)象背后的關(guān)鍵觸發(fā)點,作者對“蓉城之秋”不惜一再提及。
以人物作為關(guān)系之結(jié),典型例子是將“文化館員”這一社會角色置于鼓子秧歌傳衍過程的關(guān)結(jié)點上。按照常理,民間藝術(shù)有其自然的傳承體系,民間藝人理應(yīng)擔(dān)當(dāng)主要角色,然而由于作為“社會文化因子”的鼓子秧歌在當(dāng)代中國的特殊意義,致使文化館員反客為主,成為鼓子秧歌從鄉(xiāng)土走向劇場過程中承載多重功能、銜接多種關(guān)系的主導(dǎo)性人物。如作者所言,“地方文化館員是打通政府與民間上下兩方的重要渠道,他一方面身為政府文化政策的代言人和執(zhí)行者,另一方面是深入民間的文藝工作者。……因而在鼓子秧歌當(dāng)下的生存機(jī)制中,地方文化館員成為連接民間活動與地方政府、文化政策的不可缺少的環(huán)節(jié)”[1]144,“地方文化館員是繼‘二老藝人’也就是文藝工作者之后,在重構(gòu)層面上對鼓子秧歌影響最大的社會角色,他們都使鼓子秧歌在舞臺上實現(xiàn)了藝術(shù)價值,并且以此實現(xiàn)了國家的文化建設(shè)事業(yè)”[1]145。
以意象為關(guān)系之結(jié),可見于鼓子秧歌當(dāng)代變遷的相關(guān)闡釋中。作者抓住“土地”這一意象,通過土地與農(nóng)民關(guān)系的變化,透視農(nóng)民與民間舞蹈的關(guān)系,進(jìn)而反思以鼓子秧歌為代表的民間舞蹈的當(dāng)代命運。“土地”就是一個凝結(jié)了中國革命和社會轉(zhuǎn)型期所有問題的焦點意象,對于生于斯、長于斯的諸多民間藝術(shù)而言,更與其有著生死相依的聯(lián)系。圍繞這一焦點意象,《走》著于末章專辟“土地與舞”一節(jié),從更深刻的社會層面闡釋了鼓子秧歌這個生于斯長于斯、卻最終遠(yuǎn)去的“鄉(xiāng)土身影”的經(jīng)行脈絡(luò)。打開歷史之結(jié),疏通變異之途,也因此成為《走》著的重要敘事特色之一。
四、“望遠(yuǎn)鏡”+“放大鏡”
如何織就敘事網(wǎng)絡(luò)?如何使關(guān)于民間舞蹈的歷史敘事既有清晰流暢的整體感,又具備觸手可及的細(xì)膩質(zhì)感?《走》著采用了一種“望遠(yuǎn)鏡”+“放大鏡”的方法,即“以個案為線索,進(jìn)行貫穿歷史的梳理,結(jié)合了歷史學(xué)的大視野和當(dāng)代文化人類學(xué)的微觀描述,讓舞蹈的歷史事件和區(qū)域生活相互穿引”[1]10。“望遠(yuǎn)鏡”,即如前文所述,是將鼓子秧歌置于民間舞蹈以及中國社會發(fā)展變遷的大語境中進(jìn)行整體觀照的方式,有關(guān)其發(fā)展史的梳理作為縱脈貫穿于敘事網(wǎng)絡(luò),茲不贅述。
“放大鏡”則是對歷史場景、事件乃至人物心理的精微描述和深入挖掘,此類“放大”化處理隨見于各個時期,尤其以“新千年之景”部分就三帽、商家、魏集、楊廟、白集五個村莊對鼓子秧歌的不同傳衍情況所做的描述最為典型——各村方位面積人口等自然狀況、與鼓子秧歌的淵源及傳承特點、代表性傳承人或組織者介紹、人物口述、參加會演比賽等相關(guān)事件等,皆作詳盡敘述。“放大鏡”下,鼓子秧歌在最基層的傳承單位——村莊的生存狀態(tài)真實而清晰地呈現(xiàn)出來。不同時期的精微描述,有的得自于作者深入細(xì)致的田野考察,有的源自當(dāng)事人的回憶或自述,對于史料的選擇和運用,既見出作者的硬功夫,也見出作者的巧功夫。
除了精微描述,“放大鏡”的妙用還在于對歷史細(xì)節(jié)的深入挖掘,能夠透過細(xì)節(jié)辨析事理,洞察本質(zhì)。通過現(xiàn)今民間鼓子秧歌演出活動中“棒”和“花”二個角色的缺失,看到“學(xué)院派”審美教化對民間舞臺創(chuàng)作的影響;通過民間舞蹈的空間形式由繁到簡的變化,發(fā)現(xiàn)原生民間舞蹈在現(xiàn)代社會的生存環(huán)境之變;通過2007年第四屆CCTV電視舞蹈大賽中14支參賽秧歌隊無一例外地都將參賽經(jīng)歷和獲獎情況作為簡介的核心內(nèi)容,透視出比賽機(jī)制下秧歌人的主體意識的變化:“他們更在意自己外出的經(jīng)歷,用這種出外的經(jīng)驗來證明雖是鄉(xiāng)土‘玩意兒’,但一樣具有世界的經(jīng)驗,在開放的社會里,一點也不落伍”[1]147。這種對于細(xì)節(jié)的把握和處理,無不體現(xiàn)出年輕學(xué)者相當(dāng)?shù)拿翡J度和洞察力。
五、人類學(xué)視角
就研究方法而言,人類學(xué)方法固然不是作者運用的唯一方法,但確是使她對歷史材料進(jìn)行重新判斷的最重要視角。
如楊廟村李傳禎因為二進(jìn)中南海而充滿榮耀和自豪,不斷地、甚至有所夸張地向人敘述其經(jīng)歷。“在老人的生命里,鼓子秧歌所給他的情感內(nèi)容已完全不是通常人們印象中的農(nóng)民在民間舞蹈中抒發(fā)對土地的熱愛和期望——那完全是‘文藝情懷’式的想象,更不是年節(jié)進(jìn)奉祖先祈求平安儀式中的虔誠,而是真實發(fā)生的鼓子秧歌作為‘社會資歷’的‘老生常談’”[1]150。人類學(xué)的視角使鼓子秧歌傳承人作為社會角色的真實心理得以還原。
對于“文革”時期文藝創(chuàng)作中的情感表達(dá)問題,作者寫道:“我們不能以后來者的眼光簡單地判定其中的情感就是虛假的,在全民狂熱、不能對政治決策說‘不’的年代,疊加重復(fù)的藝術(shù)內(nèi)容所產(chǎn)生的社會心理暗示使大部分沒有受過啟蒙感召的來自底層勞動階層的工農(nóng)兵們來說,確是能夠制造、營造出真實的情感”,作者進(jìn)而認(rèn)為,“可以通過身體的行為感受從眾心理、權(quán)威意識和集體主義這些人性在特定社會環(huán)境中如何被放大、加強(qiáng),它為審視人與社會、歷史的關(guān)系提供了獨特經(jīng)驗”[1]67。
可以說,正是人類學(xué)的思維方式?jīng)Q定了作者的敘事姿態(tài)——不在鄉(xiāng)土與劇場之間進(jìn)行高下評判,不對城市化進(jìn)程中的日益遠(yuǎn)去的民間鼓子秧歌背影盲目感喟,“盡量少地用經(jīng)典理論闡釋中國經(jīng)驗”,而“更愿意在材料與材料的聯(lián)系中建構(gòu)文化的認(rèn)識”[1]10,甚至不去理會所謂的學(xué)科邊界,也使《走》著獲得了諸多富有新意的價值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