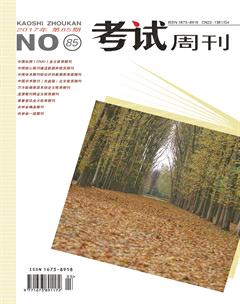語言與性別差異研究述評
摘 要:性別是影響語言運用的重要因素之一。語言與性別之間的差異研究正成為語言學領域中一個越來越熱門的話題。除了西方語言學家對此有過深入研究外,一些中國學者也在漢語語境下對語言與性別進行了一些研究。本文擬綜述國內外的相關研究,以期有助于相關社會語言學研究。
關鍵詞:性別差異;語言;研究綜述
一、 “sex”和“gender”的概念
要研究男女之間的語言差異,必須明確區分sex和gender的不同概念。sex和gender經常被誤用和濫用。長期以來,關于這兩個詞的意義的研究也存在著很大的爭議。雖然sex和gender在中文對應的翻譯都是“性別”,但它們在英文意義上卻有很大的不同。
在18世紀之前,這兩個詞是表達相同的意義,很少有學者關注兩個概念的具體差異。直到六十年代,女性主義蓬勃發展,與女權主義運動有關的女權主義者試圖區分相關用法概念,這其中就包括“sex”和“gender”。
Bonnie Mcelhinny(2003)在其“Theorizing Gender in Sociolinguistics and Linguistic Anthropology”一文中介紹了sex 和gender的一些概念和論點:
在將一系列生物事實與一系列文化事實相比較時使用sex 和gender非常有用。我在使用術語時很謹慎,只有當我談到男性和女性之間的生物差異時,才會使用“sex”這個術語,而當我將社會、文化、心理結構強加于這些生物差異時才會使用“gender”這個術語。
sex和gender試圖反對將男女之間的差異和不平等歸因于性別或生物學的觀點:
在所有靈長類動物社會中,按性別分工創造了一個高度穩定的社會制度,主導的男性通過控制領土,控制和防止其他侵略者,撫養年輕女性并與其他女性形成聯盟來維護少數男性之間的秩序。在這種社會生物學觀點中,沒有性別,因為沒有人類生活的文化決定因素。區分sex 和gender的女性主義者并不一定放棄男女生物差異的觀念,但大多數人試圖明確地界定這種分歧。在這種區別中通常隱含的是社會建構(gender)可以比生物差異(sex)更容易轉變。
二、 語言與性別差異研究發展歷史
(一) 零星研究時期(1960年以前)
最早的關于語言和性別的研究始于古羅馬和古希臘時期。在那個時候,一些人認為“屬”(一個語法術語)象征著“sextus”(一個生物學術語)。盡管這一點沒有證明人類的性別可能會決定一些語法術語,但它仍被廣泛接受,甚至影響了一些后來的語言學家。除此之外,一些學者根據他們的非語言經驗,認為陽性名詞象征著語言意義的正能量,而女性名詞則象征著否定和從屬意義。
17世紀,歐洲人開始在亞洲和美洲大陸上進行開發探索。讓他們大為吃驚的是,當地原始居民的男性和女性的語言是如此不同,他們甚至認為是兩種語言。自1664年開始出現相關的描述性報告。盡管缺乏系統的研究,但有人指出,男性的語言被認為是正常的表達,而女性的則是非正常表達。
秦秀白(1996)指出,在遙遠的18世紀,一個名叫羅蘭·瓊斯的威爾士語言學家,他專門研究了男性和女性的語言并得出一個結論,女性不如男性,這種不平等現象在所有語言中都存在,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
1922年,Jesperson在其頗具影響力的語言學著作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的一章中描述了女性語言的特點。他指出,女性和男性使用的詞匯有很大的不同,女性通常比男性使用更委婉、更少的咒罵語。因此,他得出結論,女性在語言使用方面仍然比男性更傳統。這位語言學家對使用母語和第二語言的移民進行了一項調查,發現女性移民經常會說母語,而男性則更快掌握新語言。Jesperson還指出,男性在句子結構上使用了更多的階段性句子和從句,因為他們更聰明,在智力上更有優勢。
總的來說,這一時期關于語言和性別的研究是零散的。人們普遍認為男人的語言是正常的,而女人的語言是非常規的且表現出明顯的貶斥色彩。
(二) 系統研究時期(1960年代以來)
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作為語言學和社會學之間的邊界學科,社會語言學首先在美國興起和發展。社會語言學從社會學的角度,借鑒語言學的研究方法,對人們的語言特征進行研究和分析。性別、年齡、職業和居住環境對語言上的影響和作用都逐漸被報道。這種定量分析表明,性別確實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人們的言語行為。
從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女權運動(婦女解放運動)在美國民權運動的推動下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女性要求男性在各個方面都有更多的平等。這種女性主義浪潮也促進了語言學的發展,極大地促進了語言和性別的研究。甚至一些學者也提出了“女性語言學”和“女性語言批評”兩個新術語。1978年,美國科學院在其新出版的著作《Gender and Sex: Is difference meaningful?》中提出建立“性語言學”。
英國語言學家拉波夫在他的著作《Language and Womens Place》中指出,在語言世界里,男人占據了中心位置,女人的形象被打破了。他的這項研究頗具挑戰性和試探性,運用了人類所有的科學來描述語言,包括心理學、社會學、民族學、人類學和歷史學等學科,研究結果甚至成功地影響了一些語言政策的制定。
這個領域的其他代表包括P Trudgill, Zimmerman, L. Pusch 和 S. Tromel一Plotz。(楊信彰,2010)
三、 語言性別差異的研究視角
本文試從詞匯研究,語篇研究,社會研究視角來述評相關研究。
(一) 基于詞匯的研究endprint
作為語法范疇的性別在一些語言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且主要表現在名詞上。例如在法語中表示女性的單詞往往屬于陰性,而表示男性的單詞往往屬于陽性。古英語中就有陰性,陽性和中性三個語法性別。隨著曲折詞尾的消失,性別逐漸失去了其語法范疇。在現代英語中,性別主要是語義范疇。
早在1922年Jespersen就提出女性語言模式的存在。他在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一書中討論了語言中的性別差異,尤其是詞匯上的差異,并列出許多男女使用的詞匯變體。
語言學界對于語言與性別研究的重大突破始于Robin Lakoff。1972 年,Robin Lakoff發表了Language in context一文,引發人們對語言與性別的研究。Layoff 曾經選取了強調詞“so”作為研究,她發現“so”出現在女性的語言中比男性更頻繁。
(二) 基于語篇的研究
早期的研究比較了同一階層的男女語言差別,發現女子多使用標準的語言,而男子更多使用非標準語言(如Labov, The Social, Trudgill, “Sex, Covert Prestige”)。后來,Sunderland(Gendered Discourse; “Girls Being”)考察了男女孩話輪的分布。Holmes調查了交際過程,發現男女的交際目標不同。男子更關注語言的概念功能,女子則更關注語言的人際功能。她還發現男女使用贊揚的方式不同,贊揚者、被贊揚者和贊揚的功能也不同。她分析了新西蘭的贊揚以及人們對贊揚的反應,發現男女采用的社會語用規則不一樣,女子把贊揚看作是親和信號,男子經常把贊揚看作保護或損面子的言語行為。她的另一發現是女子的道歉行為多出現在熟人和一般朋友的談話中。Tannen(1990)的研究表明,話語層的特征主要體現了男女社會化中的變異。例如,男子似乎把交談的目的看作是收集信息,而女子把交談看作是支持機制。這些特征會轉化到不同的語言行為上:在男女混合組中,男子往往會統治時間和話輪,女子往往會支持和回答。男子主要向女子解釋問題,而女子則提出更多的問題,使用更多的“私下渠道雜音(backchannel noise)”(如:uhhuh, yeah, yes, hmm),邀請他人參與。
(三) 基于社會角度的研究
根據“SapirWhorf假說”,語言不僅是社會的產物,而且會反過來影響人的思想。因此,一些語言學家認為,由父系制度和社會階層制度所限制的語言反映了男性主導世界的性質可以通過語言的細節來證明。
具有女性特征的詞匯總是含有貶義。許多致力于改變此現象的語言學家試圖通過實現語言平衡來達到性別平等。Pauwels(2003)寫道,大多數人試圖通過對現有的形式、規則和語言的使用(有時被標記為替代策略)提出修正來實現性別平等。性別中和和性別規范是實現這一目標的主要機制。性別中立化的目的是“中和”,或將與性別和性別標記相關的語言表達方式和其所指代的隱含意義盡可能地減少。然而性別規范(也稱女性化)策略則相反:在其所指中明確地標記了性別。性別中和的一個例證是用后綴如ess, ette, trix(如actress, usherette, aviatrix)來消除女性職業名詞。英語中性別規范的一個例子是使用他或她來代替“他”的通用用法。這兩種機制的應用主要局限于詞匯層面,我們相信詞語水平的變化可以對消除話語層面上的性別歧視產生積極的影響。
四、 結語
從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我們需要從多個視角探索語言與性別的關系。我們對語言與性別的研究不應只局限于語言的表面句法形式和語法結構差異,還應該從與哲學、社會學、社會語言學、心理語言學、語用學、語義學等理論結合,從交際策略、話語風格等方面入手進行分析,從而豐富研究的理論基礎,使研究視野拓寬。
參考文獻:
[1]Holmes, J.&Maria, M. Relational practice in the workplace: Womens talk or gendered discourse?[J]. Language in Society,2004,33(3).
[2]McElhinny B. Theorizing gender in sociolinguistics and linguistic anthropology[J].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gender,2003:20-42.
[3]Jesperson, O.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New York: Allen&Unwin,1922.
[4]Labov, W.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1966.
[5]Lakoff, R. “Language in Context”. Language 48(1972):907-924.
[6]Romaine, S. A corpusbased view of gender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English[J]. Gender across languages,2001,(1)pp:153-175.
[7]Sunderland, J. “Girls Being Quiet: A Problem for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2,1(1998):48-82.
[8]Tannen, D. You Just Dont Understand: Women and Men in Conversation. New York: William Morrow,1990.
[9]秦秀白.英語中性別歧視現象的歷時文化透視—評介Grammar and Gender[J].現代外語,1996,(2):18-25.
[10]楊信彰.語言與性別的多視角研究[J].當代外語研究,2010,(1).
作者簡介:
楊弦,湖北省荊州市,長江大學外國語學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