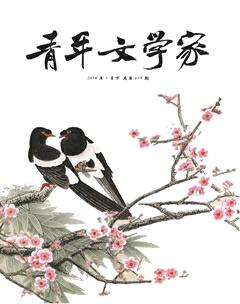孤獨的絕唱
摘 要:詩人小引作為網絡詩歌寫作的代表,作品并未受到文壇太多的重視,但在網絡上他的詩歌卻得到了一定的關注,其中首推被改編成民謠歌曲的《西北偏北》,然而迄今為止,并沒有相關的文章對該詩歌進行過深入細致的解讀。通過運用文本細讀的方法,對詩中特定地域意象進行深入挖掘,探索詩人在詩歌中內心歷程的變化,從而揭示出詩人對“孤獨”這一人類生存狀態的獨特領悟。
關鍵詞:西北偏北;孤獨;宗教;救贖
作者簡介:邱良云(1994-),女,江西人,云南師范大學文學院研究生,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小說方向研究。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03-0-02
《西北偏北》
西北偏北 羊馬很黑
你飲酒落淚 西北偏北 把蘭州喝醉
把蘭州喝醉 你居無定所
姓馬的母親在喊你 我的回回 我的心肺
什么麥加 什么姐妹
什么讓你難以入睡
河水的羊 燈火的嘴
夜里唱過古蘭經 做過懺悔
誰的孤獨 像一把刀 殺了黃河的水
殺了黃河的水 你五體投地 這孤獨是誰
海德格爾說“作品要通過藝術家而釋放出來,達到它純粹的自立”[1],意思是說,藝術家在創作中自我消亡,作品一旦完成,作品就處于完全獨立的狀態,只等待藝術的欣賞者去進行解讀。很多研究者海德格爾的這一說法深以為然,雖然并非所有的文學作品都適合“內部研究”,但詩歌卻可以作為文本“內部研究”的最佳范本。本文便是通過對小引的《西北偏北》進行文本細讀研究,試圖對詩中所表達的宗教觀念和孤獨意識加以闡釋。
在古代中國,“西北”是“乾卦”之方位,一直是帝王的象征,《古詩十九首》中也有“西北有高樓,上與浮云齊”之句,此處的西北就是指代。但就自然條件而言,“西北”歷來就屬于荒涼之地,中國的地域差異極大,西北越往北地理環境也越惡劣。詩人用“西北偏北”作為題目,不僅僅是表明詩歌創作的地理位置,更是詩人心境的寫照。“西北”的荒涼還不足以匹配詩人內心的荒涼和孤獨,詩人的荒涼比西北大地的荒涼更荒涼,詩人的孤獨比西北大地的孤獨更孤獨。
“西北偏北/羊馬很黑”,“羊”上出人人之氣,指代平均、美好,易卦中“乾為馬”。《康熙字典》釋“黑”:“《說文》:火所熏之色也。韓康伯曰:北方陰色。”《易·說卦》有言“坤,其於地也為黑”。中國西北地區的居民多信奉伊斯蘭教,多為回民,再加上自然條件不甚優渥,能夠飼養的主要動物就是羊和牛,交通則多依賴于馬。這一句詩不僅僅蘊含中國人常說的陰陽相調合,也進一步暗示了西北偏北的荒涼。“黑”不僅僅是一種色彩,也是詩人心靈的在現實當中的投射。荒涼的西北大地,詩人放眼望去,目之所及皆為黃土的延伸,沒有其他的色彩。暮色里,牧民趕著羊踏塵土而來,夜色漸濃,羊和馬也籠罩在暮色里,大地越顯凄涼。
“你飲酒落淚/西北偏北/把蘭州喝醉”,“蘭州”位于中國西北部,地處黃河上游,是唯一有黃河穿越市區中心而過的省會城市。在中國的地理版圖中,蘭州的地理位置并非真正處于西北偏北地區,但因為蘭州在中國歷史上一直是一處邊關要塞,險要的邊關形象是古詩詞中關于蘭州書寫的主要內涵。唐詩宋詞中的“邊城觀念”對后人影響深遠,也成了大眾想象蘭州的“集體記憶”[2]。而詩人常常會將城市命運想象成個人命運,蘭州在此處的出現更多的是屬于文化心理因素上詩人個人命運的表征。
“把蘭州喝醉/你居無定所”,在這荒涼寂寞之地,能想到的只有飲酒,只有酒才能讓人忘記這荒涼和寂寞,古人不是說過酒可以消愁嗎?可為何這酒一飲下,淚便落了下來,原來喝酒并不能讓你遺忘西北偏北的荒涼,你又一次意識到你仍孑然一身,亦不知今晚棲身于何處,這西北之大,竟找不到一處地方可以容下你這幾尺身軀,圍繞著你的荒涼和寂寞并未消失。
“姓馬的母親在喊你/我的回回/我的心肺”,“姓馬的母親”,西北多為回民,而“馬”是伊斯蘭教最普遍的姓氏。“回回”是元代至民國時期對回族的泛稱,有時也引申稱呼穆斯林地區。現今為回族的特定別稱。“心肺”此處指代重要的事物。恍惚中,仿佛有人在喚我,那是母親嗎?我已經不記得有多久沒有人這樣喊我了,在我居無定所之時,回民如母親一般呼喚我,在這一刻我似乎得到了救贖,我的內心不再是一片荒蕪,詩人開始在親情和宗教中尋找擺脫孤獨的救贖。
“什么麥加/什么姐妹/什么讓你難以入睡”,“麥加”是伊斯蘭教的圣地,“麥加朝覲”是每年伊斯蘭教最盛大的宗教活動。“朝覲”是伊斯蘭教為信徒所規定的必須遵守的基本制度之一,每一位有經濟和有體力的成年穆斯林都負有朝拜麥加的宗教義務。所有穆斯林,無論男女,都會盡最大努力爭取一生至少要前往麥加朝覲一次。“姐妹”信奉某一宗教的人,習慣于把擁有同樣信仰的人稱為“兄弟姐妹”。“姐妹”一詞在此也指出伊斯蘭教的包容。自己雖然居無定所,卻能夠得到回民親人一般的關愛,詩人似乎此刻再無孤獨的理由了。可是“我”依然難以入睡,“麥加”和“姐妹”并未給我真正的救贖。
“河水的羊/燈火的嘴/夜里唱過古蘭經/做過懺悔”,《古蘭經》是伊斯蘭教的經典著作,在穆斯林當中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同時規范著穆斯林的行為準則,《古蘭經》告誡信仰者應堅忍、順從、行善、施舍,穆斯林在生活中需要經常頌讀《古蘭經》。“懺悔”本為為佛教語,佛教規定出家人每半月集合舉行誦戒,給犯戒者以說過悔改的機會,后遂成為自陳己過,悔罪祈福的一種宗教儀式。引申為認識了錯誤或罪過而感到痛心并決心改正。伊斯蘭教的“懺悔”經常說作“討白”,指穆斯林向真主真心誠意地悔罪。這個詞及其派生詞在《古蘭經》中出現過多次,并且有“討白”章,由此可見“討白”的重要性。在夜里唱《古蘭經》,向真主安拉做懺悔,這是詩人在宗教和親情中得不到救贖之后,內心向宗教本源更深入的一次追溯,但是這種追問,也沒有讓詩人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解脫。endprint
“誰的孤獨/像一把刀/殺了黃河的水”,詩人第一次點明讓自己難以入睡的是——孤獨,這里詩人一改陳述的方式,開始了對孤獨的質疑,此刻孤獨不僅僅是一種狀態,孤獨變得有了力量,孤獨擬物化,成為一種具體的存在之物,詩人把孤獨想象成一把刀,想用如刀一般鋒利的孤獨,去殺了黃河的水。千年前的詩仙李白到達黃河之時就發出過“黃河之水天上來”的感慨,黃河是中國的母親河,是中華民族文明的起源地,“殺了黃河的水”是孤獨患者以孤獨為刃對孤獨的反抗,是一種發泄、復仇的方式。詩人決意改變孤獨這種無力的狀態,通過殺了黃河的水,讓自己得到“復活”。
“殺了黃河的水/你五體投地/這孤獨是誰”,黃河水一路東去奔流不息,這一江之水也正似西北的荒涼和詩人的孤獨,在以孤獨為刃阻斷了黃河之水之后,詩人對孤獨產生了由衷的欽佩,全身心的折服在孤獨的腳下。就在詩人以為在孤獨中得到救贖之時,忽然產生了不知“這孤獨是誰”的疑問。如果真孤獨真的是詩人的,在殺了黃河之水,作者拜服在孤獨之下,為孤獨唱起了贊歌之時,這孤獨是否能稱其為孤獨,如果不能稱其為孤獨,那阻斷黃河之水的又是什么?詩人卻至此又陷入虛無之境。
《西北偏北》整首詩都是關于孤獨的吶喊,“西北偏北/羊馬很黑/你飲酒落淚/西北偏北/把蘭州喝醉/把蘭州喝醉/你居無定所”是詩人對孤獨的直觀感受,通過“黑”“飲酒”“落淚”等一系列意象營造一種孤獨的氛圍。“姓馬的母親在喊你/我的回回/我的心肺/什么麥加 /什么姐妹/什么讓你難以入睡/河水的羊/燈火的嘴/夜里唱過古蘭經/做過懺悔”,詩人感受到孤獨無邊的侵襲之后,希求能在宗教和愛中尋找到擺脫孤獨的路徑。但在夜里唱過古蘭經、做過懺悔這一系列的救贖活動之后,詩人依然難以入睡,在宗教中尋求解脫也以失敗告終。“誰的孤獨/像一把刀/殺了黃河的水”,最后詩人屈服于孤獨,在孤獨的淫威之下,詩人變得決絕,以為孤獨的力量可以顛覆一切,甚至可以斬斷自己的根,獲取全新的生命形式。“殺了黃河的水/你五體投地/這孤獨是誰”,但在以孤獨之刃割斷與生命之源的聯系以后,詩人卻發現自己并不認識這已化為利刃的孤獨,至此又陷入疑惑之中。
詩人最后認識到孤獨是人類永恒的宿命,西北偏北也好,蘭州也罷,宗教也好,親情也罷,所有的一切都不能實現人類對自我孤獨的救贖。整個人類在冥冥之中注定永遠與孤獨為伴,人類充其量只能停留在對孤獨狀態的感知上,并不能獲悉孤獨的真正面目。而以孤獨為刃進行的反抗也是無意義的,人類如果妄圖對孤獨進行救贖和反抗,最后只能陷入虛無之境。
參考文獻:
[1]馬丁·海德格爾(德).海德格爾文集,林中路[M].孫周興 譯.商務印書館.2015.
[2]郭茂全.古體詩詞中的蘭州城市文化記憶.[J].蘭州交通大學學報,2014,33.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