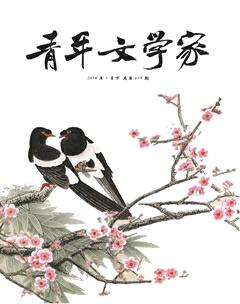在人性與瘋癲間掙扎的赫索格
摘 要:小說呈現了赫索格深刻的創傷意識,這不僅是對婚姻失敗的創痛感受,也是苦難的猶太歷史及現代社會價值觀的劇烈沖擊所引發的充滿痛感的創傷體驗。這種意識遠遠超越了機械所導致的物理性受創,具有文化、種族和現代性暴力方面的深刻意義。
關鍵詞:赫索格;創傷體驗;猶太民族;現代性
作者簡介:陳沖(1993-),女,漢族,山東菏澤人,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碩士在讀,研究方向:英美文學。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03--02
《赫索格》是美國當代著名的猶太作家索爾·貝婁的代表作品,曾獲得美國全國圖書獎。在小說中,主人公赫索格出生于一個猶太家庭,是一位大學的哲學系教授。這個“天真漢”經歷了兩次失敗的婚姻,感情受創后變得沮喪抑郁、暴躁沖動,不斷給四面八方的人們寫信。他還周旋于各地,在為時五天的“奧德賽之行”中不斷地思考各種形而上問題。
在小說中,赫索格在得知馬德琳和格斯貝奇的背叛后,健康狀況日漸惡劣,性格愈加沖動,受迫害意識頻頻出現,常出現歇斯底里的癥狀,呈現了意識的交錯和非理性特征,儼然一個經受了強烈精神創傷的受害者形象。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論》中認為,“一種經驗如果在一個很短暫的時期內,使心靈受一種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謀求適應,從而使心靈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擾亂,我們便稱這種經驗為創傷的”。[1]
創傷(Trauma)源自希臘語τρυμα,本意指外力給人的身體造成的物理性損傷。后來意義擴大化,更多指向了精神層面。1980 年美國精神病學協會頒布的《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首次正式收入“創傷后應激障礙”(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詞條,此后對心理、文化、歷史、種族等創傷的文化書寫、社會關注和學術研究蔚然成風,創傷一躍成為左右西方公共政治話語、人文批判關懷乃至歷史文化認知的流行范式。[2]
小說呈現了主人公深刻的創傷意識,不僅是對婚姻失敗的創痛感受,也是苦難的猶太歷史及現代社會價值觀的劇烈沖擊所引發的充滿痛感的創傷體驗。這種意識遠遠超越了機械所導致的物理性受創,具有文化、種族和現代性暴力方面的深刻意義。
一、赫索格的“瘋癲王國”
在小說中,妻子馬德琳不僅耗盡了赫索格的財產和才智,更是把赫索格重視的一切——職業、精神狀態、男子氣概、自尊心——都榨干了。馬德琳的情夫格斯貝奇威脅并最后占有了赫索格的世界,完全滲透其中并成為另一個摩西·赫索格,而赫索格的精神世界也相應地賦予了馬德琳和格斯貝奇的形象以“妖魔化”的特質。赫索格腦中充滿了幻覺、狂想和怪念,并伴隨著譫妄,他向精神病醫生要了一份精神失常的臨床癥狀列表(“驕傲,憤怒,過分的‘理性,同性戀的傾向,好勝,對感情不信任,不能受批評,敵意的心理投射,妄念”。)當他看到這些癥狀后激動得叫道:“全在這兒了——全在這兒!”。福柯說“瘋癲的根本語言是理性語言,但是這種理性語言被顯赫的心象籠罩著”。[3]能夠憑借清晰的邏輯和理性的話語明確表達自身的瘋癲性質的赫索格,正是福柯在《瘋癲與文明》中定義的譫妄的瘋癲者。
瘋癲的赫索格以及譫妄的話語是由創傷意識觸發的。當赫索格得知女兒瓊妮被格斯貝奇關在車里時,他極端暴怒的宣布“我就要宰了他!我非宰了他不可!”但事實上,殺死格斯貝奇的沖動一直潛藏于他的潛意識之中。而當他回到父親的老房子時,童年時父親拿槍意圖殺死自己的記憶閃現,與現實中婚姻與情感創傷相互交織,使赫索格完全進入了非理性的境地。E·A·卡普蘭認為弗洛伊德創傷理論的核心是一種無意識動機(a motivated unconscious),“在這種情況下,創傷性事件可能會觸發早期的創傷經歷,而這種經歷也許已經和幻想混合起來,塑造了當前所經歷的事情。”[4]由此,小說情節沖突達到了極點,赫索格人物的瘋癲特質誘使創傷意識出現,展現了人物性格的復雜性和瘋癲者眼中的世界。
在創傷意識的激發下,赫索格憑借譫妄的話語作為把握世界的方式,也是借以維持他的瘋癲王國平衡的工具。赫索格意圖“把信件灑滿整個世界,為的是阻止它,不讓它逃跑。我要不安保留在人的形體之中,所以我就幻想出一個完整的環境,把它網羅其中。”[5]這種良心的“織網工作”維系著赫索格思想中隱喻的世界,而一旦這個道德堡壘崩塌,瘋癲就將赫索格從道德王國中拖了出來,進入了混亂、幻想的瘋癲王國。
二、我的“應許之地”?
赫索格來自于一個俄國猶太移民家庭,他從小接受正統的猶太教育,有個極具猶太特質的名字——“摩西”,是個“正宗的、愛講感情的舊派猶太人”,民族和種族的文化印記將始終是赫索格自我意識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猶太歷史也實為一部創傷史,赫索格個人的精神創傷事實上也是猶太民族集體記憶中的一部分,并通過這一民族的苦難歷史折射出來。
赫索格有如現代的奧德修斯,他為期五天的奧德賽之行正是猶太民族幾千年離散生活的縮影,是古老民族創傷體驗的歷史性回射。對于這個流散了兩千多年的民族來說,“今天的庇護所可能會變成明天的地牢”。[6]赫索格從紐約出發到馬薩葡萄園,又回到紐約,之后來到芝加哥,最后回到路德村,苦苦尋找著古老記憶中上帝的“應許之地”,找尋著心靈的解放和真正的獨立、自由。赫索格一家渴望重回想象中的家族顯赫的時光,赫索格也相信“世界全賴他的新著問世,因為他的新著將改變歷史,影響人類文明的發展。”[7]他相信自己不僅是猶太民族的領袖摩西,更是帶給全世界光明的摩西,在他的領導下,奴役將轉化為自由,黑暗將變為光明,帶領人類走出創傷的歷史,找到“流奶與蜜之地”。
事實上,赫索格的理想破滅了,他成了一個渺小的、被欺騙的“反英雄”人物。赫索格認為作為正統猶太人中的一員,作為“上帝的選民”,苦難是必須要承受的。這種苦難意識貫穿著猶太民族的整個經驗世界并轉化成為他們在無數次困境中堅強活下去的信念,并最終找到生活的意義和生命的價值。[8]這種價值觀以及貫穿全文的形而上思想來自于猶太傳統。貝婁在早期的采訪中也承認猶太思想和自身的生活經歷對他早年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endprint
三、現代社會的創傷體驗
猶太人對自我身份的困惑是猶太傳統和現代性撞擊的產物,是兩者互相排斥的結合。赫索格事實上是按照猶太民族的“史前天性”和原始的智慧維持自我生存,“在古代,人類的天才主要用于創作隱喻。而現在人們的天才主要用于創造事實。”[9]通過創造隱喻來完成對世界和周圍事物的認知。赫索格向四面八方的人寫信,“希望把一切都變成語言”,用語言追求現實,作為理想建構的武器。
現代社會卻憑借工業技術瓦解了價值標準,資本主義社會“更相信看得見的好處”,數字力量的增長代替了個人價值,用直觀和經驗的方式創造事實。于是,在“西方橘黃色的塵霧”之中,世界成了一個戲劇舞臺,人們在自我表演的悲喜幻覺中忘掉現實世界而沉溺于虛構世界。赫索格的哥哥威利正是猶太價值觀屈從于現實的代表,他為了適應以事實價值為標準的社會,削平了赫索格家的人天生暴躁的脾性,變得不露感情、克制、禮貌,這正是猶太價值觀面對西方社會時的創傷式反應。
在小說中,現代社會呈現了一種施虐-受虐狀態,人類意識呈現出焦灼與危機,小說對資產階級社會的批判揭示了猶太民族在面對文明衰退和黑暗社會浮現時的創傷感受,正是文明固有的死亡本能和深度創傷的產物。
在小說中,主人公赫索格經歷了三重創傷體驗。他承受了現實中經驗社會的層層盤剝,承受了精神世界的辛苦勞役,在他瘋癲的背后是創傷意識的涌現。這種創傷也是猶太民族幾千年來的離散生活、受迫害意識與驅逐感的歷史的復現,更是現代文明中的主人公古老的猶太價值觀與資本主義價值觀矛盾沖突的產物。“長時期來,猶太人見外于全世界,而現在反過來,全世界也被見外于猶太人。”[10]但赫索格始終相信憑借尊嚴、愛和責任能夠重拾人性的光輝、獲得拯救,他選擇“重新回到人群中去尋找原始性的治療”,以期實現“真正的內心的一變”。
注釋:
[1][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高覺敷譯,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217頁。
[2]陶家俊:《創傷》,外國文學,2011年,第四期,第117頁。
[3][法]福柯:《瘋癲與文明》,劉北城、楊遠櫻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93頁。
[4]E.Ann Kaplan.Trauma Culture:The Politics of Terror and Loss in Media and Literature[M].London: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5:32.
[5][美]索爾·貝婁:《赫索格》,宋兆霖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27頁。
[6][美]索爾·貝婁:《赫索格》,宋兆霖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21頁。
[7]同上,第125頁。
[8]同上,第113頁。
[9]同上,第310頁。
[10][美]索爾·貝婁:《赫索格》,宋兆霖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05頁。
參考文獻:
[1][美]索爾·貝婁. 赫索格[M]. 宋兆霖譯. 上海: 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2][法]福柯.瘋癲與文明[M].劉北城、楊遠櫻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
[3][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M].高覺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4]陶家俊.創傷[J].外國文學,2011(04).
[5]E.Ann Kaplan.Trauma Culture:The Politics of Terror and Loss in Media and Literature[M].London: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5:32.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