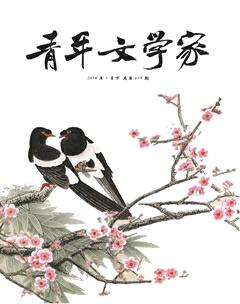從《呼嘯山莊》兩個中譯本看英語文學文本漢譯的結構轉換
摘 要:在英語文學的翻譯工作中,譯者會對英語句子結構進行一定的“本土化改造”,以滿足中國讀者的閱讀體驗和理解便捷度。基于此,本文從“被動句-被動句”、“被動句-主動句”兩種結構轉換角度入手,圍繞其中的有施動者被動句、無施動者被動句、主謂結構主動句、泛指人稱主動句、“是……的”結構主動句進行了分析,意在通過《呼嘯山莊》兩個中譯本研究出英語文學文本漢譯的結構轉換方法。
關鍵詞:施動者;主動句;閱讀體驗
作者簡介:杜先一,海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13級英語涉外翻譯專業(yè)。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03--01
引言:
在日常的漢語交流和寫作中,我們更傾向于用主動結構敘述事件;而在英語文學中,被動結構句的應用遠比主動結構句要多得多。所以,大多數(shù)中國翻譯者在英譯漢的過程中,會將英語的敘述結構進行改變,以符合漢語的語用情境,同時也為有助于漢語譯本表述得更加準確。所以,我們有必要對英語文學文本漢譯的結構轉換進行分析研究。
一、英語被動句與漢語被動句的結構轉換
首先,在英語被動句含有“不幸”這一含義的時候,可以通過“被”、“給”等銜接介詞將施動者引入到譯本中,翻譯成漢語的被動句形式。例如原文中“My companion,sitting on the ground, was prevented by the back of the settle from remarking his presence or departure”一段,被楊苡(簡稱楊)譯為“我的同伴,坐在地上,正被高倍長靠椅的椅背擋住,看不見他在這兒,也沒看見他離開”,被方平(簡稱方)譯為“我的伴侶坐在地上,給高高的椅背攔住了,不曾看到他在那兒,也沒看到他往外走”。結合這段話的語境(卡瑟琳在與“我”談論求婚一事使,被深愛她的希克厲聽到了,而“My companion”卡瑟琳卻被椅背擋住,并沒看到希克厲在那兒)可以看出,原文這段話帶有較強的“不幸感”,使得“椅背”這一施動者意向得以通過“被”或“給”兩個介詞保留到翻譯文本中,構成了帶有委婉、抱歉語氣的漢語結構被動句[1]。
其次,在英語被動句含有“不愉快”這一含義的時候,也可直接通過“給”、“被”等銜接介詞翻譯成漢語,不必將施動者照搬到譯本中。例如原文中“If I had been,I would have set my signet on the biter.”一句,楊翻譯為“我要是給咬著了,我可要在這咬人的東西上打上我的印記呢”,方譯為“要是我給咬著了,我可要給那咬人的東西留下個磨滅不了的印記呢”。在這個句子中,雖然“If I been”之后的“bitten by one of the dogs”被省略了,在翻譯中仍然要把“我被狗咬到”這件不愉快的事呈現(xiàn)出來。但此時由于施動者較為明確,所以可以將“狗”這一意向省略,直接使用“被”或“給”字將原文譯成漢語結構被動句。
二、英語被動句與漢語主動句的結構轉換
由于被動結構在漢語中應用較少,故翻譯者在進行英譯漢的過程中,時常會將原句中的被動結構通過語言改動變?yōu)橹鲃咏Y構。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
第一種,英語被動句向主謂結構漢語主動句的轉換。以原文中“His hair and clothes were whitened with snow”一句為例,楊譯本中為“他的頭發(fā)和衣服都被雪下白了”,方譯本中為“他的頭發(fā)和一幅,積了雪,變成白白的一片”。在楊的譯文中,“衣服被雪下白”這一被動陳述方式被保留了下來,但不免給中國讀者以別扭之感。而與之相比,方的譯文將其改為“雪使衣服變白”這一主動結構,更加符合中國人的語用習慣。
第二種,英語被動句向泛指人稱主動句的轉換。以原文中“Hell love and hate equally under cover,and esteem it a species of impertinence to be loved or hated again”一句為例,楊譯本為“他把愛和恨都掩蓋起來,至于被人愛或恨,他又認為是一種魯莽的事”,方譯本為“他愛,他恨,全都擱在他的心里;而且認為假使再要人家愛他恨他,那就分明是一件不很體面的事兒”。在原文當中并未給出“愛”和“恨”的具體實施者,此時方譯本中的“要人家愛他恨他”與楊譯本中的“被人愛或恨”相比,更加偏向于指向性,也更符合中國讀者的閱讀方式和思維方式[2]。
第三種,英語被動句向“是……的”結構主動句的轉換。以原文中“The letter was finished and forwarded to its destination by a milk fetcher who came from the village”一句為例,楊譯本為“信還是寫了,而且是由村里來的送牛奶的人送到目的地去”,方譯本為“信還是寫了,是由村里來的一個送牛奶的給送過去的”。在這一句中,“信被送去”這一行為在兩種譯本中的表達方式大致相同。但來回閱讀幾次便可發(fā)現(xiàn),楊的翻譯文本過于尊重原句結果,繼而變得有些“語無倫次”,對中國讀者的閱讀體驗造成了一定障礙,而相比之下方的翻譯文本則要通順得多。
總結:
綜上所述,譯者將英語文學進行適當?shù)臐h語結構轉換,對中國讀者閱讀體驗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分析可知,通過分析《呼嘯山莊》的楊、方兩版譯本,我們可以了解到英漢兩種語言之間的結構差異。據(jù)此,翻譯者在進行漢譯時,要遵循漢語的語用習慣,重視到語句的連貫性和通順性,以便實現(xiàn)英語文學的本土化傳播。
參考文獻:
[1]陳婷婷,李紅梅. 文本分析模式視角下《呼嘯山莊》兩個中譯本的比較研究[J]. 語文學刊(外語教育教學),2013,(04):50-51+61.
[2]仲亞娟. 從《呼嘯山莊》的兩個中譯本看語篇翻譯中的銜接意識[J]. 南京工業(yè)職業(yè)技術學院學報,2007,(03):34-36.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