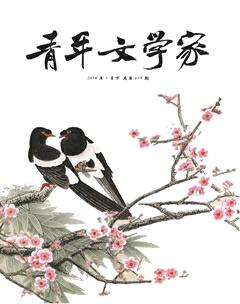王鐸隸書簡析
摘 要:王鐸一生為官,卻因書而留名,并把晚明大膽獨造的浪漫書風推向了極境。啟功先生用七言絕句盛贊王鐸:“破陣聲威四海聞,敢移舊句策殊勛。王侯筆力能扛鼎,五百年來無此君。” [1]王鐸在草書上的成就人盡皆知,篆隸似乎都在其巨幅行草下所淹沒,本文主要以其隸書為研究脈絡,探尋這位千古一人的隸書書寫面貌及價值。
關鍵詞:崇古觀;俗字;遵漢;隸本與篆;學術空氣
作者簡介:韓煥霞(1991.2-),女,安徽人,泉州師范學院書法碩士。
[中圖分類號]:J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03--03
1.王鐸的崇古觀
王鐸(1592-1652),字覺斯,號嵩櫵,今河南孟津人。他與倪元璐和黃道周三人在明代為官時皆以清流著稱,時常抗疏直諫,人稱“三珠樹”。“三珠樹”皆好古,但同樣沒有什么實際的政治才能。三人在后來亡國時雖有不同的政治取舍,但他們為官時的無所作為卻可以等而視之,有論者甚至將之與他們在文藝上的崇古聯系在一起。清人陸隴其對他們的崇古作風更是語詞激烈,甚至將亡國歸咎于他們的文風:
倪鴻寶《代序詩》云:“俗格與陳調,掃除以寸鐵。”覺斯之文病正在此,而鴻寶、石齋亦所不免。即就石齋所作《覺斯集序》觀之,以駁雜為富,以佶屈為奇,文怪僻而意膚淺。……文運至此,國安得不亡。”[2]在陸隴其看來,王鐸等人想要以“古”來振興文運只會落得膚淺滑稽的結局,并無經世致用之學。可見王鐸等人的崇古用心與后世評價實為不和,當然也有人為王鐸辯護,他避難蘇州時,常為人作書,寫小楷必遵奇古,有人譏笑他“借篆隸法破體杜撰,欺人自欺”,清代詩畫書法大家顧復卻尊其為 “奪造化入神奇者”,因為他十分理解王鐸參通古碑而擯棄俗字的良苦用心。
宋元以來,隸書的書寫者不絕如縷,但我們通常把明末清初這段時間視為隸書的復興時期,原因便在于當時的書家都無一例外地取法漢碑,并以此作為習隸的標準,王鐸也不例外。與郭宗昌等人對于漢法的崇重有所不同的是,王鐸更加關心那些保留較多篆書字形的漢碑,在為葉羽遐題《明拓尹宙碑》時,他說:“淳樸道逸,篆法黎然”,即便是在評價一塊隸書碑刻時吸引王鐸的也正是其情有獨鐘的篆法,顯然,這個“法”并不是書寫之法,而是字形之法。贈葉羽遐《長歌》有“籀法至漢能無慝”之句,亦是說漢碑之中饒有篆籀之形,因此我們大體可以這樣推測—王鐸關注漢隸,與其中蘊含的篆籀字形有很大的關系,和郭宗昌等人追求漢法之“不衫不履”還不盡相同。王鐸一直提倡學習漢晉以來的名家書法,認為那是“古”的象征,但又說“羲、獻不過姿之秀婉耳,畫不知古”,所謂畫不知古,是說他們的書作中充斥著俗字,于是王鐸搬出了更古的篆隸傳統,借以修正晉唐名家書法中的訛字、俗字。
有清以來,斯文掃地,這個由滿族建立起來的專制帝國已經沒有了大漢帝國的胸襟和包容性,雖然在乾嘉時期出現過短暫的輝煌,但它的體制弊端,狹隘保守已登峰造極,清代漢族文人終其一生的努力也不可能進入清朝的主流社會,少數的漢族官僚飛黃騰達也總是帶有犧牲人格的味道,倘若我們把王鐸等人的崇古觀及其在書寫上的表現放到當時的社會情境下去分析的話也不難發現,王鐸等人以“古”為依歸的歷史想象不僅是他們對藝術的追求,也是這些朝廷重臣平息當下焦慮感的良藥,同時亦是他們營構新的文化樣式即政治秩序的利器,其終極目的乃是民族國家的振興。王鐸尋古訪碑,大量使用隸書篆寫,正是其崇古觀念在文字書法中的體現。包括行楷,不管是豐碑大碣還是單行的題跋,也都充斥著大量的篆書字形楷寫。他的隸書也很少直接挪用漢碑的字形,除了一些有遺存篆書字形的。但奇怪的是,篆書并不是其學書生涯中臨摹與創作的主要書體,他也并無意于成為篆書名家,即便是隸書在他的傳世作品中所占的比重亦微乎其微。由此可以窺見,王鐸對于篆隸并非真正有熱愛之情,王鐸的隸書運用“古”的寫法,通過對“篆籀”這一特殊的為時人所淡忘的文化符號的追溯,來謀求對歷史的重構,而并非真正意義上的仿古,他與后代碑學書家的區別不僅在于篆隸書并非他最傾心的書體,而且對于篆隸書的“古拙”趣味,王鐸也并不在意。雖然此舉并無鍛造個人藝術趣味的意思,但是它也深深地影響了王鐸篆隸的書寫形式。
2.王鐸學隸歷程與作品分析
在王鐸時代,篆籀文字的出土較少,出版物也并不常見,起初他專注于漢代的八分碑版。至晚明,由于學者親歷訪碑,漢碑陸續出土并得到追捧,王鐸也曾在山野間尋訪金石遺跡,《漢八分隸書歌柬漱六、羽遐》有云:
“蒼頡作字苞善矩,道大體變無不該。秦人易之用八分,拓本尚不失根菱。我生好古遐為搜,深崖窮壑擷其該。籀法至漢能無慝,殘章斷碣出云雷。因是輦載數千里.披闋照耀拂麈。蔡邕墨碑不驟多,寶重何異躪與瑰”。[3]
這首詩告訴了我們幾個信息點:一是王鐸曾在深崖窮壑間搜尋漢碑;二是漢碑中猶有篆籀遺味;三是當時漢碑出土并不多,很寶貴。由此可知,王鐸確實曾經親歷訪求漢碑,并有幸收藏漢人篆隸二十余種,自題云:“學書不參通古碑書,法終不古,為俗筆多也。”很顯然,這些古碑都是他矯正名家書法俗字的重要依據。
王鐸大致是在崇禎末年(1643)避難于河南輝縣時才開始學習漢隸,此時他已53歲高齡,現今為人所熟知的《隸書三潭詩卷》便作于次年,后有隸書跋語29字:“予素未書隸,寓蘇門始學漢體,恨年異壯,學之晚。雖然,羲之、高適五十可也。”可見他雖悔學隸甚晚,但覺五十學隸也未有不可,王鐸接觸漢隸的時間應該較早,1638年他就在郭宗昌所藏《華岳碑勢拓本》之后題詩,同年在為《淳化閣帖肅府本》所作題跋中,亦提及肅府“秉有西京以來碑版”但他一直不寫隸書,或因為“恐應者不暇”。但也因為他書隸時間較晚,現今流傳隸書作品甚為罕見。他臨習漢隸的作品未留書史,但從數件隸書作品中不難看出其對《曹全碑》、《禮器碑》、《史晨碑》皆有臨習,并受北碑影響。今所見其隸書有詩卷(如崇禎十七年1644年二月舟中為翼隆所書詩卷)、簽題(如1647年為孫北海舊藏《初榻淳化貼》所題)、引首(如順治三年草書《杜甫詩卷》引首“杜陵秋興)、石刻(河南浚縣大丕山題字)、個人叢貼《擬山園帖》,他在題跋時偶爾也使用隸書(如弘光元年為孫承澤家藏《蘭亭刻本》題跋)。endprint
王鐸的隸書在當時亦受到人們的關注。在隸書大行于世的乾嘉時代,錢謙益、彭而述、曹寅、翁方綱、錢坫等都給予其很高的評價,認為王鐸取徑甚高,無唐以后習氣。由此可見,在王鐸的時代其隸書作品還是受到普遍認可的。王鐸的隸書與其草書一樣風格獨特,趣味十足,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面目,這也與晚明革新派追求個性解放的理念相契合。“求新尚奇”在其隸書作品中的體現遠超于他屢屢強調的尋古追漢之情。王鐸隸書娟秀如曹全,略有禮器、史晨之意,但已偏離其甚遠,章法用筆都不見漢隸的古樸渾穆,反而呈現出一種拙作氣,字法上更是突破前人加入眾多的篆籀字形。《白苧村桑者》云:“覺斯為袁石寓寫大楷一卷,法兼篆隸,筆筆可喜……”[4]也指出其楷書中有篆隸法。然而其純粹的篆、隸體作品卻甚為罕見。河南浚縣大丕山還留有王鐸的隸書“鷺濤虎岫”、“仙烤”,題字,字徑均70厘米,前者高170厘米,寬180厘米;后者高90厘米,寬250厘米。二者都鑿刻于大丕山龍洞南崖壁,為崇禎十七年春回鄉省親后返京途經大丕山所作。筆法遒勁,字勢開張,寓奇險于端莊之中,并加入有篆和楷的結字特點。其中 “鷺”字“鳥”的四點,“仙”字右邊上半部分,“虎”字的下面皆用篆書寫法,“岫”字右邊的由字又有魏碑內圓外方的特點,“崿”字也接近于楷書筆法,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
《隸書三潭詩卷》 (遼寧省博物館藏)是目前罕見的隸書墨跡,作于崇禎十七年甲申(1644年)53歲,通篇多處以篆正隸,字態憨厚,保持著隸書的扁形,字形上有曹全的痕跡在,但已明顯加入楷意,結構亦時見大小、正欹變化,其書風已是隸、楷結合,同年春在豐沛舟中書《五律詩卷九首》,收錄在《擬山園帖》第四卷末,清人翁方綱評其“作隸書卻不工,然自有拔俗之氣,知其平日未嘗染指開元以后八分也”,《擬山園帖》中很大一部分作品都盡顯曹全風韻,如第五卷中《立馬高原七律詩》,瀟散逸韻中見靈動之勢,用筆多藏鋒,奇險端莊、縱橫有度,在當時此種別有異樣的筆韻應頗具新鮮感,清人錢坫認為:“此種筆格,蓋有漢人之骨而間以北魏之趣者”。第五卷中《夔府孤城七律詩》書寫更加大膽,率性十足,起落有致,痛快淋漓,改變漢隸平穩之體勢,自化成體,與其楷書作品有異曲同工之妙,大概皆是受其行草書奔突取勢的影響所致。現藏于廣州美術館的王鐸《杜陵秋興》隸書引首,從中不難看出受《華山碑》的影響。其結體端正,用筆沖和遒美,有廟堂氣象,當是王鐸學習漢隸的最佳例證。《洪洞十櫵》為王鐸丙戌(1646年)55歲所作,此時隸書的蠶頭燕尾在整幅作品中已很少見,點畫之間略有行意。與三潭詩卷的去方變圓相比有了更多楷體的方折,更多自由靈動之勢。如站在當代的角度再去回看王鐸的藝術作品實際已與漢隸相去甚遠,少了許多的端莊規整,再加上其書寫的篆字字形,甚至古文文字的隸寫,假借字通用字的使用使其作品有種怪異感,由于沒有像乾嘉時代那樣對于文字學研究成果的支撐,不免出現一些錯字。清順治四年(56歲)以后便沒再見其隸書作品,最終他的隸書也沒能像行草書那樣達到新的高度,其隸書作品流動有余而古樸不足,與其書學觀點并不一致,心手不應。除此之外,王鐸對于漢隸本身的書寫旨趣并未有更進一步的發掘與闡釋。
《三潭詩卷》紙本,261.2*27.3厘米,自作詩七律一首,凡32行,共103字,自署書于崇禎十七年(1644),遼寧省博物館藏。
王鐸丙戌(1646年)55歲所作《洪洞十櫵》局部。
3.小結
綜上所述,王鐸雖在隸書的認知與實踐上下過一番功夫,但其作品仍離古意尚遠,并有訛字與結構乖誤之處,略顯怪誕。這與當時訓詁考據學的不盡成熟有莫大的關系,隸書的尚奇與自造在乾、嘉以前清初諸人的作品中都有體現,如王時敏、戴易、萬經等人寫隸師法唐人,時時有乖誤之處,鄭簠雖肆力于漢碑用筆也未能盡脫習氣,與王鐸交好的傅山也是過于刻意,朱彝尊倒是以其學者的身份對漢碑的特點有更嚴謹的把握,至清代中期丁敬、鄧石如等人在隸書創作上已經煥然一新,道光以后金農、伊秉綬等人更是借助于這股風氣競相出新。而王鐸等人的隸書作品在清代隸書的中興上雖然不盡成熟但其對篆隸書體的復興及由此而引發的碑學運動有著先驅作用。王鐸的崇古觀及對漢隸的追捧、篆意的尋求也對后學者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清代隸書集大成者無一例外的取法漢碑,清代中期篆隸書體的繁榮、書家對漢碑版的臨習研究,皆得益于這種學術空氣的熏陶,而王鐸等人在此次浪潮中也起到了先導作用。
注釋:
[1]王幅明著,天堂書屋隨筆,大象出版社,2014.07,第194頁。
[2]南京藝術學院藝術研究所主編,藝術學研究 第一卷,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第207頁。
[3]南京藝術學院藝術研究所主編,藝術學研究 第一卷,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第198頁。
[4]單國強著,古書畫史論集續編,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05,第194頁。
參考文獻:
[1]《九都洛陽歷史文化叢書》韓忠厚等編著,中國科學文化出版社,2001.10月第1版。
[2]《王鐸傅山劉墉書法鑒賞》紫都,耿靜編著,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3]《藝術學研究》南京藝術學院藝術研究所主編,第一卷,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
[4]《清代隸書要論》王冬玲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
[5]《天堂書屋隨筆》王幅明著,大象出版社,2014年7月第1版,2014年07月第1次印刷。
[6]《王鐸史料存真》韓仲民,海天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
[7]《一筆一畫-關于隸書的書寫狀態》鄭培亮,榮寶齋出版社,2011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8]《王鐸年譜》張升編著,上海書畫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