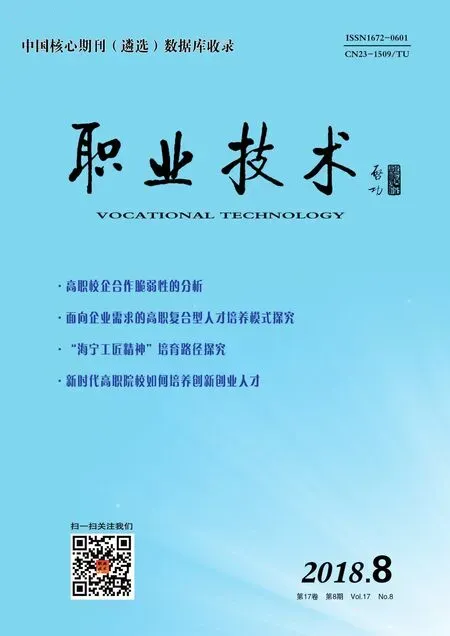新生代農民工城市適應問題研究
——以農民工培訓為研究起點
張建萍
(廣東科學技術職業學院,廣東 珠海 519090)
0 引言
現在我們經常提到的新生代農民工特指那些年齡16周歲到30周歲的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這一群體目前在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的總人數1.5億人里面大約可以占到60%[1]。他們出生以后就走入校門接受基礎教育,很多人完成九年制義務教育以后就進入城市打工。相對來講,這一群體對于農業、農村、土地、農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同時,他們渴望進入城市、期盼能夠徹底地融入城市生活,而目前絕大多數城市在很多方面還沒有完全做好接納新生代農民工群體融入城市的準備。新生代農民工這一群體相較于以“三高一低”為主要特征:接受義務教育普遍程度較高,對未來職業生涯發展規劃期望較高,追求物質、精神享受的期望值較高,工作過程中抗壓能力值低。朱力將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城市適應概括為三個依次遞進的層次:經濟層面、社會層面、心理層面。“這是進城務工農民工群體適應的三個不同的方面,又是依次遞進的層次:進城務工農民工群體從農村來到城市,首先必須找到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獲得一份相對穩定的收入和住所,才能在城市中生存下去,經濟層面的適應是立足城市的基礎;在完成了初步的生存適應之后,新的生活方式和社會交往是進城務工農民工群體城市生活的進一步要求,它反映了進城務工農民工群體融入城市生活的根源廣度;文化層面上的適應是屬于精神上的,它反映出進城務工農民工群體對城市化生活方式等的認同程度”[2]。新生代農民工這一群體城市適應、城市融入問題的產生的根源在于缺乏足夠的基本技能,在城市中很難站穩第一步,在勉強站穩腳跟之后又缺乏改變自身境遇的手段。一般的觀念可能都認為,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城市適應問題應該屬于城市問題范疇,但值此力爭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實現的歷史階段,任何問題的解決都必須跳出固有的窠臼,新生代農民工這一特殊群體的徹底城市融入問題自然也不可能例外。目前,我們應該需要認識到新生代農民工這一特殊群體城市適應問題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這一群體還普遍不具備在城市生存競爭中需要的勞動技能,往往只能從事最臟、最累、最苦、勞動報酬最低的勞動,且這一群體目前還普遍缺乏吃苦耐勞的精神,導致用工單位容易對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形成片面的認識,可能會導致新生代農民工這一群體的城市融入問題的大量涌現。
1 珠海市農民工基本狀況
新生代農民工的根在農村,他們接受了基本的義務教育,在知識水平有所提高的基礎上,假如能有某些組織為他們提供在城市打工必備的基本技能培訓,使即將外出務工的新生代農民工有機會接觸到實用基本技能;在初步掌握這些基本技能之后利用一定時間來逐步熟悉所需技能,并最終參加全國某一單項技能資格考試,獲得技能等級證書,這樣的新生代農民工外出務工的薪金起點無疑會提升到一個令人滿意的程度。農民專業合作社作為被各級政府寄予厚望的組織形式,有責任為順利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城市適應問題提供前期的基本性輔助功能,而發展良好、經濟實力較強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恰恰具備這種能力。
2 農民專業合作社參與培訓的客觀基礎
2.1 在農村社區群眾基礎好、可信度高
農民專業合作社的領辦人一般是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奮力搏殺,真正證明了自己的農村致富帶頭人,其對市場經濟競爭基本規律的把握頗有心得體會,在農村中其影響力、號召力、說服力較強,由其領辦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往往比政府建立的培訓機構更容易得到農民的認可。
2.2 新生代農民工組織性更強
根據李偉東(2009)的調查結果顯示,明確表示需要新生代農民工自己組織起來的比例達到40.5%[3],這在一定程度說明新生代農民工這一群體較之第一代農民工有著更為強烈的歸屬性需求,更希望通過自己組織起來維護自身權利,而不是像以往只是單單的通過訴求,寄希望通過引起其他社會群體的重視來提高自身的社會、經濟地位。新生代農民工更應該建立屬于自己的組織,過去的想法往往是通過在務工地建立相應的組織來實現新生代農民工所預期的功能,但由于不同來源地、不同文化觀念、不同生活習慣等容易造成彼此融合的困難,那不妨換一種思路,建立同屬地務工人員組織。這種組織有些類似于過去所說的“老鄉會”,無疑一起參加過職業技能培訓的外出務工人員更容易形成緊密型的群體組織,彼此間的互信、融合問題必將輕易化解。經濟實力較強、運作規范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參與到外出務工人員基本技能培訓工作中來,不僅可以有效地解決農村職業教育培訓機構缺乏的問題,還可以通過參與外出務工人員的培訓解決合作社成員家庭內部、周圍利益相關農戶的家庭富余勞動力問題,變被動為主動,通過培訓鍛煉隊伍,使受過培訓的外出務工人員形成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良好印象,使其中部分人今后回鄉創業成為可能。新生代農民工與第一代農民工的本質區別還在于遷移的方式是“融入型遷移”而不是“候鳥式遷移”,如果不及時采取預防性措施,很難避免我國農村出現類似于日本農村的那種90%的人口都轉移到城市當中的情況。在外出務工人口增多的前提下如何為農業生產留足、留好充足的勞動力這一問題還只能寄希望于與農民群眾聯系緊密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只有通過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有效組織,才能使留在農村居住的人口其生活水平、子女受教育程度、精神文化需求的滿足與城鎮居民不存在比較大的差距,才能真正留住一部分農民群眾的心。現在的情況是絕大多數農民群眾不具備轉移的條件,未來條件成熟不排除轉移的可能。農民專業合作社參與到農民培訓中來能夠做到未雨綢繆,為解決問題提供了可能。
2.3 農民專業合作社更加了解農民的需求
“訂單制”培養這種在產業工人塑造過程中非常有效地方式目前還沒有應用到外出務工人員培訓中來,過去的做法無論是采取“培訓券”還是“涉農專業人才培養”,其操作的主體都是大學等培訓機構,其理論知識體系遠離生產實踐,無法滿足實際工作的需求。而真正深入生產實踐,了解掌握外出務工群體基本能力,采取有效方式盡可能地與勞務輸入地用人單位進行對接,將第一手的勞動用工信息盡快地反饋到外出務工群體中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必將更好的服務外出務工群體,減少其在不同城市間由于勞動用工信息不透明造成的時間、金錢成本。
2.4 參與新生代農民工培訓有利于壯大合作社
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水平相對滯后,多數農民專業合作社還不具備培訓新生代農民工的能力。啟動依托于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新生代農民工培訓有利于搶抓機遇,做大、做強一部分專業合作社,使合作社的發展由注重數量的增長轉變為注重經濟實力、服務能力的提升方面。目前國家、省級政府對于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扶持主要還是采取“廣撒網”的方式,并沒有建立并完善根據專業合作社規范化、標準化發展水平來予以資金、物資等扶持的制度。開展農民專業合作社牽頭的新生代農民工培訓不僅可以實現彌補、替代農村中職的目的,還可以使農民專業合作社獲得資金支持,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形式的資金支持并不受世界關貿總協定“黃箱政策”的限制,有利于扶持一定數量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壯大實力,主動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實現維護我國農業領域利益的目的。
3 農民專業合作社培訓新生代農民工的具體做法
3.1 提供必備的勞動技能培訓
為了快速適應新生代農民工這一群體的典型特征,在選擇人員開展基本職業技能培訓之初,首先就要開展最基本的篩選,確定某一種技能所對應的就業崗位是否能夠真正給參與培訓者帶來充分的勞動滿足;其次需要針對參與培訓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實際掌握狀況,組織接受培訓的新生代農民工參加國家承認的各級基本職業技能等級考試;最后還需要積極聯系用工城市具體企業,與企業形成合力,最終做好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城市融入工作。
3.2 促進新生代農民工群體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新生代農民工這一群體,如果想改變上一代農民工無法徹底融入城市,最終無奈返鄉的狀況,就需要他們從自身著手做出徹底的改變,從行為方式、生活習慣等方面改變無法徹底融入用工城市的痼疾所在。要認識到很多習慣的改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特別是由于意識形態的不一致所造成的生活習慣的不協調,但我們應該堅信發展才是硬道理,所有的問題都可以通過后續的持續改進得以最終的解決。組織培訓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等組織機構需要積極聯系輸入地用工企業,由具體的用工企業責成專人為參與培訓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講授輸入地城市的風土人情等狀況,將促進新生代農民工群體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作為培訓是否合格的重要參考指標。
3.3 促進正確心理調節能力的養成
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城市融入問題,是未來能否實現“三化同步”所需要面臨的最嚴峻考驗,“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最終徹底解決才能尋找到真正的突破口,而新生代農民工這一群體在面臨融入城市過程中所展現出來的心理調節能力缺乏,需要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組織開展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基本勞動技能培訓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應該積極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榮辱觀,敢于面對用工城市務工過程中所面臨的各種艱難困苦考驗,要認識到遭遇挫折是融入城市生活所必需的,即使來自不同的城市都可能面臨不同文化、不同觀念的強烈碰撞,由農村向城市轉移同樣不能避免,甚至將更加強烈。
3.4 提供相對完備的城市適應保障支持
新生代農民工這一群體的城市適應,乃至最終的城市融入必然是一個長期發展、動態存在的過程,在這一問題得到最終解決之前可能會面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我們相信只要堅持“中國的城鎮化是所有人民共同的城鎮化”這一基本原則,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在融入城市生活中面臨的所有問題必將得到很好地解決。農民專業合作社等組織機構應該在培訓全程灌輸用工城市的基本勞動技能信息,并提供一定時期內的勞動技能更新服務,保證新生代農民工群體能夠徹底地融入用工城市,實現農村富余勞動力的有序轉移。
4 必要的保障措施
4.1 必要的經費保障
“涉農”專業逐步免費應該是必然的趨勢,畢竟我國目前農業人才儲備還不足以支撐我國農業現代化的順利實現。而農民專業合作社參與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培訓,這不僅僅是一個教育的問題,也是影響到今后一個較長時間段內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能否保持穩定、快速增長的一個關鍵問題,解決的好,長期制約我國發展的“三農”問題的解決將拉開帷幕,解決不好,我國政府所提出的“三化同步實現”將會成為一紙空談。因此,有必要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培訓提供必要的經費保障,將符合條件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建成農村職業教育的“橋頭堡”,可以考慮由政府提前支付一部分費用,待對新生代農民工綜合素質的考評結果出來后,再以獎勵的形式支付后續費用,調動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積極性,保證這種新生代農民工培訓不像其他類型培訓一樣流于形式。
4.2 強化基礎教育
農民專業合作社對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提供的以城市適應為導向的培訓,注定只能是一種“短、平、快”的過程,對于新生代農民工基本素質的提高不可能產生非常大的影響。這在一定程度就要求有關部門逐步強化農村基礎教育,使外出務工者在義務教育階段能夠掌握與未來接受培訓相適應的基本文化知識。
4.3 合作社與企業、大學的對接
新生代農民工的培訓光靠農民專業合作社是無力完成的,只有積極地與用工企業、大學進行有效對接才有可能完成。合作社與企業、大學進行對接有助于結成勞動培訓用工聯盟,改變產業工人無人培訓的現狀,為新生代農民工逐步適應城市、融入城市更好的服務。
5 結語
以農民工培訓為研究切入點,以農民專業合作社為組織形式,從深層去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勞動技能不足、勞動報酬偏低、生活習慣不良、社會適應性較差、心理調節能力匱乏的狀況,從經濟層面、社會層面、心理層面去關注新生代農民工城市適應問題,讓他們由內而外的蛻變,從根本上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城市適應問題,從而解決我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