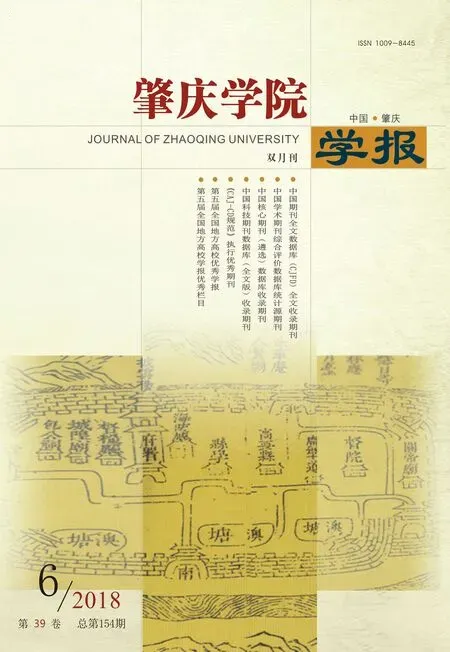偏正復合詞論元角色的構成關系分析
徐天云
(肇慶學院 文學院,廣東 肇慶 526061)
一、看待論元結構的2個角度
關于論元結構,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理解。Williams在不考慮謂詞的情況下把它理解為“一個詞項的論元結構就是該詞項所能擁有的一組已經標有名稱的論元”[1];顧陽、沈陽則在考慮謂詞的情況下把它理解為“論元結構就是指動詞和論元的構成形式”,[2]123即由名詞性成分與謂詞一起構成的語義結構。
有關論元結構,我們可以從謂詞角度看待,也可以從名詞性成分角度看待。從謂詞角度看待論元結構,一般強調謂詞的決定作用,強調謂詞對論元角色的指派;對于一個論元結構來說,確定了謂詞,就確定了名詞性成分充當的論元角色,所以可以說論元結構是用謂詞給名詞性成分定位。利奇就說到:“謂詞決定變元的數量和性質,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謂詞是主要的成分。”[3]袁毓林從詞項價的觀念出發,把句法結構中的主要成分區分為支配成分和從屬成分。根據支配成分與從屬成分之間的語義關系,把一定的格賦予給從屬成分。他認為是由支配成分給從屬成分指派語義角色,強調動詞的特征對名詞成分角色類型的規定作用[4]。
然而,實際上論述謂詞具體怎樣決定、指派名詞性成分論元角色的并不多,更多的反而是從名詞性成分角度觀察論元角色,討論名詞性成分相對于謂詞所起到的作用,認為名詞性成分的論元角色不過就是成分表達的功能,是用來說明動詞某一方面語義特征的。袁毓林就直接認為:“動詞的論旨角色是根據不同的論元跟動詞的語義關系而劃分出來的,或者說是根據論元在由動詞及其論元構成的述謂結構中的語義作用而確立的。”[5]例如述謂結構“媽媽愛孩子。”中的名詞性成分“媽媽”具有施動性,其論元角色就是施事;“孩子”具有受動性,其論元角色就是受事。
二、論元角色理論在偏正復合詞上的推廣
(一)包含動詞性成分的論元結構
論元角色理論是從討論句法層次的動詞跟名詞性成分之間的語義關系開始的。尹世超根據與作定語的動詞的關系,將名詞中心語分為施事中心語等14個類別。尹世超給出的分類理由是“動詞直接作定語時,盡管在功能上有體詞化傾向,在語義上有屬性化傾向,但功能語義并無根本性的改變,仍然是表示某種動作行為的動詞。這就決定了在定語位置上的動詞和在中心語位置上的名詞的語義關系,同非動詞定語和名詞中心語的語義關系有所不同,也決定了同在謂語或述語位置上的動詞和在主語或賓語位置上的名詞之間的語義關系大同小異。”[6]例如對于以動詞“閱讀”為定語的偏正結構“閱讀對象”來說,中心語“對象”與修飾成分“閱讀”之間在語義上仍然保持著施事與其所發出的動作的關系,這種關系并不因為“閱讀”降級為從屬成分有所改變。
后來這種理論在詞法層次的復合詞結構分析中也得到應用。如果復合詞包含動詞性成分,研究者就依照以動詞為主導的論元結構進行處理。顧陽、沈陽集中論證了動詞作修飾語的復合詞中動詞與論元的關系,其中的動詞性成分被看作謂詞,名詞性成分被看作論元,把句法中的論元結構直接類推到復合詞中。他們認為“地板、三角鐵、百貨商店、圖書資料室”等修飾成分為體詞性的復合詞“NP-N偏正式”在意義上只有修飾限定和被修飾限定的關系,在結構位置上沒有變化。而“伴郎、放牛娃、話劇演員、節目主持人”等修飾成分為謂詞性的復合詞“VP-N偏正式”在意義上不單有修飾限定和被修飾限定的關系,其動詞性成分和名詞性成分之間還具有動作和論元角色的關系。如“放牛娃”,除了“放牛的孩子”的意思以外,因修飾成分中有一個動詞“放”,這個動詞與名詞性成分“娃”就又有施事者和動作的關系;這個動詞與另一個名詞性成分“牛”還具有動作和客體的關系。該復合詞的結構可以看作是通過“娃放牛”這樣的結構變化來的[2]122-123。
(二)不包含動詞性成分的論元結構
處理動詞跟名詞性成分之間語義關系的論元角色理論也被用來處理名詞性成分之間的語義關系。袁毓林指出,配價本來指動詞和名詞性成分之間的共現關系,但這種動詞配價的觀念也可以推廣到名詞上去,說明有些名詞在語句中也有配價的要求,表現為支配性名詞在語義上要求與其所支配的從屬名詞共現。如在“這個活動老王有建議”的例子中,“有”是二價動詞,帶了“老王”和“建議”2個配項;剩下的“這個活動”不是動詞“有”的配項,而是名詞“建議”的配項,同時“老王”也是“建議”的配項。從語義上看,“建議”關涉到某人及其所針對的某人或某事2方面,可見“建議”要求兩個配項,如果其中的1個配項不出現,那么這種詞語組合的語義就不完足,比如“這個活動老張有”“老張有建議”都因為少了1個配項,所以讀起來顯得語義有欠缺[4]205-206。
論元角色理論在句法層次處理名詞性成分與名詞性成分之間語義關系的理論認識在詞法層次的偏正復合詞結構分析中同樣得到應用。朱彥認為還原出成分之間的述謂關系,是對帶有隱含成分的結構進行語義理解的前提。她說道:“格關系或說論元結構關系不僅存在于包含動作語素的復合詞內,而且存在于所有的復合詞結構中,像‘毛筆、布鞋、百貨商店、節目時間表’這類復合詞。”[7]邵敬敏在處理不包括謂詞的名詞性結構時也持類似看法,他認為“不同的詞語在句法結構中所擔當的語義角色,不僅指動詞跟名詞之間的語義角色,也包括名詞之間以及形容詞跟名詞之間的語義角色。”[8]據此他把修飾成分與中心成分的語義關系處理成語義格同現結構,并認為名詞與名詞組合成一個句法結構時,可能會形成若干種語義格類型。比如同樣是“翡翠”,在“翡翠鐲子”的結構里語義格體現為“質料”,在“翡翠工人”里體現為“職業”,在“翡翠店鋪”里體現為“行業”,等等[9]。
三、傳統論元角色理論的分析角度
(一)線性組合關系分析
在傳統的論元角色理論分析中,有一種意見堅持對結構的線性成分做組合關系分析,重視分析結構成分的組配關系。如顧陽、沈陽劃分中心語論旨角色類別的時候把“存錢罐”的“罐”確定成“處所”的論旨角色,把“紅燒肉”的“肉”確定成“受事/客體”的論旨角色,就是根據中心成分“罐”“肉”與修飾成分“存錢”“紅燒”之間的組合性語義關系來處理的[2]124-125。
(二)隱性語義關系分析
1.謂詞隱含的語義結構
在論元角色理論分析中,另一種意見試圖擺脫組合關系分析的思路,從超形態和隱性語義關系角度考慮問題。施春宏曾提出:“在研究句法關系中設立論旨角色這類概念,就是要將句法結構中的各個成分在現實世界中的地位描寫出來,其根本目的就是為了使句子的表層結構有一個統一的語義解釋,擺脫形態標記和線性句法序列的束縛。”[10]
用論元角色理論來說明名詞性成分之間的語義關系時會出現一個困難,就是找不到一個指派名詞性成分論元角色的動詞性成分。解決矛盾的辦法是在名詞成分之間添加上表層結構原本沒有(1977)所說的名詞復合詞(例如“snake poison”)多義性的原因[11],Levi從生成語言學的角度出發,認為是在定語從句進行句法轉換時,在表層結構中刪除了表示語義關系的謂詞。但在語義理解時,這個謂詞需要得到恢復。所以名詞復合詞只不過是屬于謂詞隱含的情況[12]。
朱彥也認為:“述謂關系是語言結構中成分之間的必有語義關系,沒有述謂關系,一定的語義成分無法組成結構,無法對客觀世界做出指稱和陳述;不求助于述謂關系,人們無法對語義作出相應的理解。”[7]34所以要說明帶有隱含成分的語義結構,需要還原成分之間的述謂關系。在她看來,不包含動作語素的復合詞結構中,同樣存在論元關系,只不過其語義層面的謂詞沒有顯現,而是處于隱含狀態罷了。例如,如果把“兒歌”理解成“適合兒童的歌”成立的話,那就意味著在語義上存在一個“歌適合兒童”的述謂結構。這個述謂結構轉換成表層結構時,只有施事“歌”、受事“兒童”得到表達,謂詞“適合”則處于隱含狀態。
2.謂詞隱含理論的幾個難題
對于存在多種語義關系的偏正結構,如果能夠復原其中隱含的具體謂詞,其結構語義關系似乎還可以獲得解釋。然而這個隱含謂詞不是語義結構固有的,而是外加的,故此在尋找隱含謂詞時會碰到2個困難。
其一,被激活的隱含謂詞可能不止一個。袁毓林認為在通過NP1和NP2之間的語義關聯激活被隱含的謂詞時,如果被激活的謂詞出現2個以上,就可能形成歧解。如把“拉斐爾的畫像”還原成“拉斐爾(畫)的畫像”和“(畫)拉斐爾的畫像”,把“魯迅的小說”還原成“魯迅(寫作/收藏)的小說”都會造成歧義[13]242。
譚景春也有同樣的困惑:雖然在2個名詞之間加上表示語義關系的詞語后,語義關系會從隱性變成顯性,但這并不能消解偏正結構的多義性,而只能使多義性顯露出來。比如名名偏正結構“紙杯”和“紙簍”都可以構成2種語義搭配格式:“被容物+容器”和“原料+制品”。“紙簍”可以理解為“裝紙用的簍”,也可以理解為“用紙做的簍”。同樣,“紙杯”可以理解為“裝紙用的杯子”,也可以理解為“用紙做的杯子”[14]347。所以有些時候即便找到隱含謂詞,偏正結構語義關系的多義性并不能消除。
其二,有些偏正結構不能找回并復原其中隱含的具體謂詞。袁毓林(1995)指出:“‘VP+的+N<X>’中所隱含的謂詞在表層結構中大都不出現或不能出現。并且,許多VP跟N<X>之間的述謂關系不一定能用現成的動詞來表達。”例如在把“說英語的機會”改寫成“機會[V?]說英語”后,隱含的謂詞就得不到還原[13]242。
正因為尋找隱含謂詞的困難,所以傳統的論元結構理論在確定復合詞的語義角色時不能貫徹始終。譚景春在把名名偏正結構語義關系分成12種類型時明確說明,自己的分類角度并不完全相同。“比如領屬、屬領關系和施受、受施關系是從隱含謂詞的角度劃分出來的,材料、工具、時間、處所主要是從名詞(作者按:準確講只是名詞1)角度劃分出來的,而用途是從用品(名2)的角度劃分出來的。”[14]344
四、詞法論元角色的構成關系分析
研究者普遍認為,確定名詞性成分的論元角色需要有一個謂詞性成分。結構中有謂詞性成分的就把它作為確定名詞性成分論元角色的依據,沒有的就需要添加出某個隱含謂詞。袁毓林有所不同,他并不認為結構中的謂詞性成分能同體詞性成分直接連接成一個述謂結構,而是把一個隱含的謂詞插入到謂詞性成分同體詞性成分之間。在他看來,謂詞性成分和體詞性成分的語法屬性相同,都是與隱含謂詞相連的論元,謂詞性成分的詞性特征不能成為其充當述謂結構謂詞的理由[13]241-243。在結構中,體詞性成分和謂詞性成分,都是結構的論元,這一點我們同袁毓林的認識是一致的。然而袁毓林認為結構的論元與隱含謂詞形成一個述謂結構,論元角色是由隱含謂詞指派的;而我們認為,這個“謂詞”不能外求,不能強加,而要從結構內部尋找。
如果我們把由謂詞和名詞性成分組成的述謂結構本身看作一個事件,那么句法的論元角色就是用名詞性成分凸顯出來的說話者的某種語法意圖。比如“用勺吃飯”凸顯了吃飯事件的使用工具的意圖;“在食堂吃飯”凸顯了吃飯事件發生場所的意圖;“在食堂用勺吃飯”則既凸顯了吃飯事件使用工具的意圖,又凸顯了吃飯事件發生場所的意圖。
偏正復合詞沒有圍繞謂詞展開,結構成分之間不能形成一種述謂關系,由結構成分組成的結構不能被看作一個事件,而是要被看作事物。但是,其構成成分在組成結構時同樣凸顯出事物的某種結構意圖,同樣可以用來表明其相對于偏正復合詞所起到的語義作用。比如對于“存錢罐”來說,根據“存錢-”“-罐”與“存錢罐”之間的語義關系,可以認為“存錢-”凸顯了“目的”的結構意圖,因為“存錢罐”是用來存錢的;而“-罐”凸顯了“范疇”的結構意圖,因為“罐”主要是為了說明“存錢罐”在范疇上的歸屬是“罐”,而不是“盒”“筒”和“箱”。
既然謂詞性詞組中的句法成分凸顯事件某種語法作用可以看作論元角色,那么我們也有理由把偏正復合詞中凸顯事物某種結構意圖的結構成分所擔當的功能也看作是論元角色。名詞性成分既然可以擔當相關述謂結構的論元角色,當然也可以擔當相關復合詞的論元角色,結構成分與其所說明的偏正復合詞結構之間也形成一定的論元結構。論元角色不一定是只能說明述謂結構的,也可以是用來說明偏正復合詞的。相對于句法論元結構,我們把結構成分與其所構成的結構之間構成的論元結構稱之為詞法論元結構。
詞法論元結構中結構成分與結構之間形成構成關系。根據構成關系可以分析結構成分對結構所起的作用,即論元擔當的論元角色。我們認為,偏正復合詞修飾成分、中心成分的論元角色都是由與偏正復合詞的關系,即由構成關系確定的,所以確定修飾成分、中心成分的論元角色,應該從結構成分與結構之間的構成關系出發,看其在構成復合詞時所起到的作用。可以說,當復合詞的所指對象確定時,結構成分的論元角色就確定了,所以偏正復合詞是用復合詞來指派復合詞成分的語義角色的。按照傳統的論元角色理論分析“瘀斑”,要把“瘀”同“斑”按照組合關系進行理解分析,“瘀斑”是“瘀成斑痕”,其中“淤”揭示了動作過程,是述謂結構的謂詞;“斑”揭示了形成的結果,是述謂結構的結果論元。按照詞法論元結構理論進行分析,我們認為,“淤”和“斑”都是用來說明“瘀斑”的,“瘀斑”可以理解成“因為淤血而形成的斑痕”,所以“淤”表示“瘀斑”形成的原因是淤積成的,屬于“原因”論元角色;因為“斑”主要是指出了“瘀斑”在范疇上的歸屬,所以屬于“范疇”論元角色。
(本文在新加坡“第七屆現代漢語語法國際研討會”上宣讀,有關專家提供了寶貴的意見,謹表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