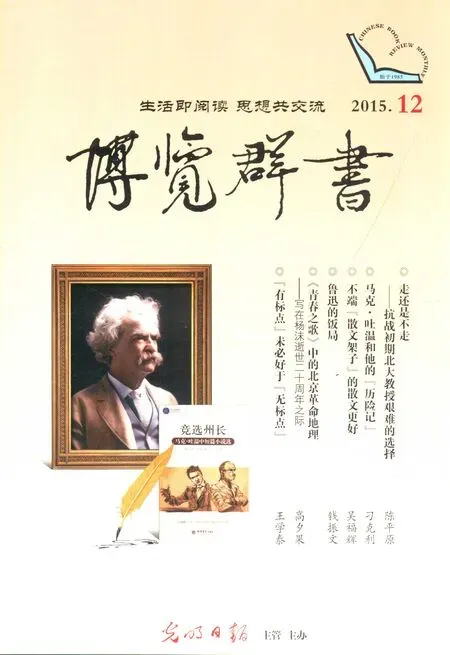笨功夫的樂趣
孫洪偉
我是2004年進入孫玉文老師門下攻讀博士學位,2008年畢業,畢業論文的題目是《上古至中古主之謂結構研究》。
對這個題目的興趣可追溯到本科時。當時受陸儉明老師的影響,我很崇拜朱德熙先生,讀了很多他的論著,尤其喜歡他討論名物化和關于自指與轉指的文章,他對各種不同意義上的“名物化”概念的離析,邏輯清晰,立論明快;他用自指、轉指、句法提取等理論對漢語相關現象的梳理,貫穿今古,嚴謹周密,令我大開眼界。這建立起我對指稱化問題的初步印象。
讀碩士時,確定將漢語語法史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系里很多老師對指稱化問題都有進一步的探討,很多在這一時期發表出來。郭銳老師的博士論文《現代漢語詞類研究》2002年出版,里面為指稱化現象構建了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后出轉精,勝義紛呈;宋紹年老師對古漢語的指稱化現象用力甚深,有很精辟的意見,在“《馬氏文通》研讀”課上曾充分地討論,這都加深了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碩導邵永海師當時剛完成博士論文,文中對《韓非子》主之謂結構的描寫細膩周到,個別例句的推敲細致入微,并往往由此引出新穎的見解,讓我見識到細節的力量;文章對主之謂結構的話題功能的討論,也讓我認識到需要從語用語篇的角度來考察這一現象。
進入博士階段,孫老師并未急著讓我確定論文選題。他要求我全面地打好基本功,音韻方面要自己動手制作《廣韻》韻圖,系聯《詩經》韻腳字;訓詁方面要標點《十三經注疏》,要讀《說文解字注》《廣雅疏證》。這些是大家常說的“笨功夫”,相對于學一點時髦的理論而言,既枯燥,又見效慢。我有時向孫老師抱怨,他并不多做解釋,回應就是簡單的兩個字:“要看。”且常常叫我去聊天,耳提面命,令我不敢懈怠。不過時間一長,也漸漸體會到了其中的樂趣,知道了笨功夫得來的東西更切實。這對后來博士論文寫作時的例句推敲工作大有裨益。
在博士一年級的“漢語語法史專題”課上,我做了一次關于主之謂結構的課堂報告,第一次比較全面地梳理了前人的意見,發現爭議很大;且初步地接觸了一下語言事實,有了一些模糊的想法,覺得這個題目似乎可以做出些東西來,也許可以作為博士論文的選題。但也有些擔心,因為這是一個老題目了,很多前輩學者都曾花費心力,自己能有多少創新,不太有把握。二年級下學期要確定論文題目了,我去跟孫老師商量,他意外地非常支持。他說,做的人多,爭議大,說明值得做;當然也說明這是塊硬骨頭,但是做研究就是要敢扎硬寨打硬仗,這才鍛煉人;不要迷信前輩學者,只要更全面更細致地分析材料,提煉出規律,文章必有價值。有了他的鼓勵我就下定了決心,并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寫出了開題報告。
開題報告通過后,開始搜集分析語料的工作。我本著“更全面更細致”的原則,選取了二十幾部上古中古文獻,將其中疑似主之謂結構的例句全部提取出來,逐個分析其功能、語義,確定其性質;對于比較特殊的例句,將其全部排列出來,核對版本,查閱注釋,從句法、語義和語用諸角度反復推敲其特點,歸納類別,說明性質;按時間先后將所考察的文獻排隊,觀察不同時期的變化,細大不捐,梳理變化脈絡;對分析有爭議的例句,更強調放到上古漢語語法系統中觀察,強調分析的可驗證性。由此果然發現了很多前人忽略或言之不詳的現象,漸漸地將一些看似一團亂麻的現象理出了頭緒,在主之謂結構的界定、性質和歷時演變等方面都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材料的初步分析大概做了大半年的時間,2007年6月開始了論文的正式撰寫。到10月,開始每周修改出一章請孫老師審閱。孫老師幾乎都是第二天就給出意見,從文章的結構到具體例句的分析、個別字句的表達都有確切的指導。還著重指出兩個問題:一是看前人的著作不夠仔細,有忽略誤解處;二是闡述自己觀點不夠耐心,常常行文過簡,讓人不易看懂。有些觀點他不完全同意,但若我堅持己見,且言之成理,他也就尊重我的意見。這樣到11月底完成了初稿。12月預答辯順利通過,之后又稍作修改,2008年6月通過了博士論文答辯。
現在看來,這篇文章并沒有多少奪人眼球的地方,若說有點可取之處,主要得益于長期以來老師們的熏陶,得益于孫老師下笨功夫細功夫的教誨。
寫作過程中還有幾件事至今印象深刻,值得說說。
論文開題后,我曾隨孫老師、邵老師到何樂士先生家拜訪,并留下開題報告請她指教。何先生當時大病初愈,身體很虛弱,但很快看完打電話給我,詳細地談了她的看法,對文中的一些新的角度非常贊賞,也直言指出了文中的幾處疏漏。之后又兩次打電話關心我的寫作狀況,給我熱情的鼓勵,歡迎我有問題時與她討論。但論文初稿完成時,何先生已不幸病逝,再欲請益已無門,思之不禁泫然。
論文對我的很多老師的觀點都有所質疑,包括宋紹年老師、劉子瑜老師和邵永海師,他們前后參加了我的論文開題、預答辯、答辯,對此完全不以為忤,對有創見的地方真誠地稱贊,對不能同意的地方也只是平和的討論,展現了真正的學者風度。
那段時間我常去孫老師家跟他交流,孫老師當時已經完成了他的《變調構詞考辨》初稿,正在錄入電腦,案頭擺著《考辨》的手稿,近200萬字,寫在八開的稿紙上,字體工工整整,一筆不茍。論文寫作時語料的搜集、分析和統計大多是很枯燥的工作,常常讓人有偷點懶糊弄一下的想法,這時想到孫老師的手稿,頓覺慚愧,就咬咬牙繼續做下去。
(作者系中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