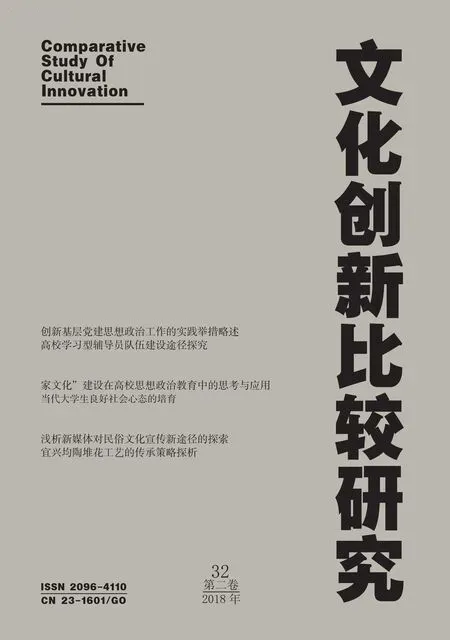老子“行不言之教”教育哲學思想探析
趙陽
(山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山東濟南 250300)
隨著社會高速發展,在我國傳統教育思想和現代功利主義教育共同推動下,教育一方面高速發展,創造著非凡的業績;另一方面教育又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一些社會不和諧因素的助推器。教育需要變革,教育喚醒轉型。老子的“行不言之教”教育原則,文在說古,意在論今,具有豐富的教育內涵。
1 “不言”及“不言之教”
“言”作為名詞,即“語言”之意,包括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作為動詞,即“言說”之意,人們運用“言”這一方式和手段實現與“人”之外的萬物相聯系和溝通。可見,“言”是一種人們認識自我和對事物進行描述的重要途徑之一。在此之外,有另外一種方式與“言”相對,此即“不言”。此處的“不”字并非表示現代漢語中的“否定”之意,其意表示的是一種“相反”的狀態,蘊含著隱性世界與顯性世界之間“相反”的含義。可見,“不言”是和顯性世界中“言”的相反的,二者在本質上并非相互沖突,甚至在一些層面上互相補充,共同助力于人們的認知和實踐活動。
“是以圣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此處的“行不言之教”主張運用自然的、非強制的教育方法,包含著豐富的教育哲學內涵。
首先,“不言之教”是以“道法自然”為本原的無為之教。此處“行不言之教”并非真的“不言”,而是不要妄言、多言,要“少言”且合乎自然之道。在老子看來,“行不言之教”與“處無為之事”二者是相互聯系的。“不言”即“無為”,“不言之教”即“無為之教”,正如王弼在《老子道德經注》中所注:“自然已足,為則敗也;智慧自備,為則偽也。”可見,在教育教學實踐中,教育者須以“無為”的方式對受教育者實施教化,當然,教育者的“無為”并不是對受教育者無所作為,任其發展,而是要在秉承“無為之教”的原則下,充分尊重受教育者的自然本性,發揮受教育者的主觀能動性,讓受教育者自身有所作為。正所謂:“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以“無為”的教學方式和手段才能達到“無不為”的教育目的和境界。
其次,“不言之教”是以“自化自仆”為根基的自我教化。“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在沒有外界妄為的條件下,人們便可以遵循自然之道展現自然本性,實現自我發展。此處,老子強調以“自化”和“自仆”的方式來實現自我價值,通過自我觀察和體驗感悟知識,達到“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的境界,正如葉圣陶先生所言:“教就是為了不教”。而“自化”“自仆”的教育境界要求教育者不是機械而單一地施教于受教育者,而是強調受教育者的主體地位,通過自己學習、親身實踐和躬行來學習知識。
2 老子“行不言之教”的原因及理論依據
“行不言之教”作為老子的教育哲學思想,在“反智”等某些方面與當下的教育主流意識形態相背離,但是,所謂“儒道互補”方為“道”,它穿梭千年流傳至今,為很多學者所研究、探索,有其自身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也有成其價值的內在理論。
首先,“有言之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正如《周易》所說“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言說的往往只是事物的表面,對于“意”的領會依靠的絕不是“言”,而恰恰就是“不言”給人以更大的余地和空間來領悟“意”。教育者依靠過多的“言說”傳授知識,往往重灌輸,輕引導;重書本,輕實踐;無法真正調動受教育者的學習積極性,正如雅思貝爾斯所言:“教育者以種種人為的方法來保持受教育者對他的敬畏”,此種“有言之教”往往容易顛倒師生在課堂中的地位,忽略受教育者的主體性地位,從而使教育充斥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的色彩。而老子提倡的“不言之教”更加注重受教育者的主體地位,尊重受教育者的多元發展和多樣個性,以學促教,只有摒棄固定的教育程序和教育模式,才能真正實現受教育者自然、自由地發展。
其次,教育之“道”具有一定的玄妙性。“道可道,非常道(第一章),”表明了能用言辭表述的大道,就不是永恒的大道;“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可見“道”具有模糊性、不確定性和復雜性。老子的思想是圍繞“道”展開的,在老子看來,真正的“道”是不可言說的深層奧妙,而“有言之教”恰恰背離了“道”自然無為的特征,只有“不言”才是最為符合“道”之自然、無為、混沌的特征。正因為不確定之“道”的不可言說,所以教育之“道”亦應該遵循“無教則無不教”的原則,正如老子所說“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尊重受教育者自然本性,順應其個性,實現受教育者的自由發展。
3 “行不言之教”對當今教育的建設性意義
老子的思想中直接涉及教育的言論并不多,較典型的觀點便是“行不言之教”。此處“不言”的意義便是和儒家“有言”相互對立并互為補充的,而“不言之教”本身便包含著重塑儒家教育價值的傾向,它與儒家功利主義的教育出發點相互補,對當今的教育發展有其建設性意義,細細探討,有理可尋。
首先,關注學習本質,提高自身精神境界。學習之“道”,便是向自然學習,以萬物為師。對于知識的學習,不應僅僅局限于課本的內容和脈絡,教科書知識學習中的一個要素,學習的本質在于,與自然萬物、與自我本性地交流中,獲得生成的、整合的知識,從而不斷促進自我個性地發展,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而精神境界的提升是以不斷減損人的感性欲求為前提的,所謂“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學習知識以不斷增加和積累為特征,提高精神境界則以不斷減損為特征,減損的正是人內心的欲望。無欲而學,靜心而學,自然而學,乃是老子所提倡的學習之“道”。
其次,重建師生關系,突出受教育者主體地位。教與學,師與生,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辯證統一的兩個方面。在傳統的教育模式中,教育者的角色是“傳道、授業、解惑”,是教學活動的中心和權威。但是,在“行不言之教”原則指導下,教育者的角色便是遵循教育規律說必要的話,做必要的事情,即受教育者是課堂的主導者,居于主體地位;教育者是課堂的指導者,提點、助力受教育者學習。教育者應“不言、希言”,尊重受教育者在教學活動中的主體地位,從受教育者個體出發,重在發展受教育者自身的自然本性,促進受教育者的自由發展,進而達到教與學的和諧與平衡。
最后,重構教學方法,注重實踐反思。如今以應試教育為出發點的“填鴨式教學”使教育者成為機械化傳遞知識的“工具人”,受教育者成了被動接受知識的“符號人”,課堂上的知識傳遞承擔不了教育目的的實現,對于解放自身和促進社會進步作用甚微。可見,“有言之教”在教育目的應然與實然之間存在著根深蒂固的矛盾,只有通過“身教”,通過實踐與反省的教育路徑才能達到受教育者個體進步的目的。實踐反思的教育正是老子所言的“自化、自正、自富、自樸”,是摒棄了“言”之規范性、強制性的教育。
4 “行不言之教”思想本身的局限性
老子“行不言之教”思想,作為一種教育手段和教育原則,在功利主義教育盛行、唯分數論英雄的當下,有其積極意義。但就教育本身的廣度、深度和教育目的而言,是有其較大局限性的。
首先,就教育廣度而言,“不言之教”很難突破時空限制,實現知識和文明的傳遞。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乃是將人類的精神文明成果代代傳承,而名家著作、理論書本在文明傳播、交流與傳承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這,恰恰是“有言之教”,也正是“有言”使得知識成文化、確定化,提高了教育的便捷性,超越了知識傳遞的時間和空間,大大擴大了人類文明和理論知識傳播的廣度,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不言之教”無可企及的。
其次,就教育深度而言,一方面,教育者很難僅僅依靠“不言”實現“傳道、授業、解惑”。學習和實踐過程中往往有很多較為晦澀的隱性知識和緘默經驗,以及晦澀難懂、理論性較強的知識,再加上受教育者本身心智的不成熟、生活經驗的極度缺乏,“不言之教”這種手段是無法準確地將知識傳達到受教育者心中,使其真正理解并且接受的。另一方面,受教育者很難自覺、自律地內化于心。“不言之教”可以達到較好教育效果的前提,那便是受教育者具有刻進骨子里的自律,可以在“不言之教”的隱性提點下就可以順利實現自我內化,有效發揮主體自身的自覺性。但現實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受教育者都具有較強的自覺性,受教育者對于教育者的“不言之教”,領悟到何種程度,能否真正內化于心是不確定的,那便無法保證“不言之教”的效果究竟如何。
最后,就教育目的而言,所謂教育,就是不斷提高人的綜合素質的實踐活動,綜合素質的兩大主要要素便是“德”和“才”,無“仁義”不成德,無“禮智”不成才,無德無才便無法立足于當今社會去做一個 “完整”的人。“不言之教”帶有較為強烈的“反智愚民、反文明、絕仁棄義、絕圣棄智”的傾向,希望摒除仁義禮智的規范,以“不言”達到對人教化,使社會穩定和諧的目的。此種教育目的與儒家“有教無類、教學相長”的教育主張有很大不同。“不言之教”的“反智”傾向,很大程度上是同當下教育價值取向相悖的,究其根本,是一種超脫世俗的自由和清凈,然而這種“自然之教、自我教化”能為個人個性的自由發展提供多大的指導價值,是不得而知的。
雖然以“不言之教”來解讀當下教育在某些方面會略顯蒼白和牽強,但是其內涵卻能引起人們的思考,不講空話,不說教,化用禪宗一句妙語:“菩提無樹鏡無臺,靈山何處惹塵埃”。安住在無為不執的境界中,希冀于少一些教的執念,實現真正的自我內化和自我修行,或許會開拓教育的另一番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