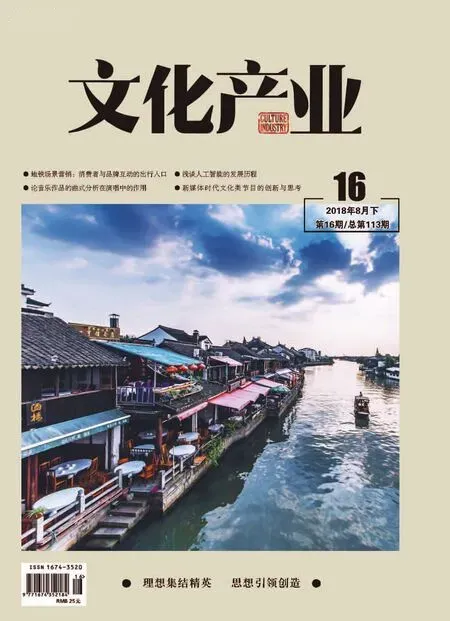宋明理學婦女婚姻觀下的“反常”
——以客家地區的“二婚親”問題為例
◎葉海強
(溫州大學人文學院 浙江 溫州 325035)
一、程朱理學婦女婚姻觀的背景
客家民系的歷史過程大體經過孕育、成熟、發展三個階段,分別為六朝至北宋,北宋至宋元之交,以及元末至明清。特別在南宋時期,客家民系發展最為成熟,而這一時期也正是宋明理學在思想界取得統治地位的時期。宋明理學對倫理道德的改造和強調,特別是婦女婚姻觀,對客家人的社會心理、客家婦女的婚姻都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據史料記載,宋明理學在客家地區的傳播是相對薄弱的,但事實并非如此。理學的開拓者周敦頤,他一生為官30年,其中有20年是在客家地區生活,還有閩學在客家地區的傳播,以及王陽明任南贛巡撫一職,節制廣東、江西、湖廣、福建四省,這些事實都反映出理學在客家地區的廣泛傳播。
程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餓死事小,失節是大”的言論要求客家婦女必須遵從“三綱五常”“三從四德”,而這也是當時社會每個女子必須遵守的準則,理學背景下婦女婚姻觀的集中體現。
(一)理學“三綱五常”“三從四德”觀
“三綱五常”“三從四德”之說極大地表現出程朱理學對婦女的壓迫。“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是三綱,“在家從父,已嫁從夫,夫死從子”這是“三從”,社會上還把婦女的“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的嚴格要求稱為“四德”。宋代的理學家們花費了很大的力氣,為封建“三綱五常”作論證。把“三綱五常”“三從四德”這一套理論強調到天理的高度,使婦女失去了獨立的人格和地位,嚴重者甚至被壓迫到社會的最下層,徹底淪為父、夫、子的附庸。
(二)婦女婚姻的具體表現
一般來說,宋代以前,社會對婦女的壓迫和束縛還不至于太嚴格,所以那時候的男女之事也不像后世那么僵硬,婦女的風雅韻事也很多。如晉代公卿王渾的妻子鐘琰,一次與王渾在廳堂共坐,王渾的侄兒從庭前經過,王渾很高興地對妻子說“生子如此,足慰人心”。意思是說侄兒一表人才,感到欣慰和自豪但卻沒想到鐘氏卻說:“若新婦得配參軍,生子故不啻如此”。參軍指王渾的弟弟,即那位侄兒的父親。鐘氏的意思是,如果我和你弟弟結婚,生出來的兒子還要更出眾。一個婦道人家,敢于這樣開玩笑,這在封建衛道士看來,那真是無恥之尤了。再如隋唐時期婦女改嫁問題也十分常見。唐代公主再嫁人數眾多,據文獻記載,在唐肅宗以前的公主共有九十八人,其中有二十七位公主嫁過兩次,有三位公主嫁過三次。唐代文學家韓愈之女也嫁過兩次,社會對再嫁的女子也沒有太大的歧視,因此改嫁之風在隋唐是合乎禮儀并為社會所接受的。再有更過分的,南朝宋國的山陰公主,曾公然對前廢帝說:“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托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前廢帝沒辦法,只得給她置面首(即男寵)三十人。但是這個山陰公主還不滿足,大臣褚淵俊美,又要求前廢帝讓褚淵伺候她十日。山陰公主的行為雖然“淫恣過度”,但也是時代的風氣使然。若是像宋代以后那般對婦女的道德要求那么嚴苛,即使貴為公主,即使再“淫恣過度”,也不敢公然有這樣的言行。
在宋初,社會上關于貞節的觀念,也尚與唐代相去不遠(隋唐時代,受北方胡族風氣的影響,婦女生活也是多姿多彩),如王安石在婦女貞節問題上的態度:王安石之子王雱,因患有精神病,日日與妻子打鬧,王安石考慮到媳婦是無辜的,主張讓他們離婚,又考慮到怕媳婦蒙受惡名,便替她找了位夫婿嫁出去了。這樣的事,也是后來的道學家們絕對做不到的。
然而,隨著周敦頤、程顥、程頤等理學家的思想廣泛傳播以后,當時社會婦女的婚姻觀念便為之一變。
《近思錄》記載了程頤與人關于貞節問題的一段問答:問“或有孤孀貧窮無托者,可再嫁否?”答曰:“只是后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但對男子,他卻主張可以出妻,休妻再娶。見《性理大全》的一段問答:“問,妻可出(休)乎?”程子曰:“妻不賢出之何害?”[1]
這兩段對話,反映了北宋理學典型的男子中心主義,男尊女卑,要求女人為男人無條件地犧牲青春、犧牲幸福,乃至犧牲性命。很顯然“北宋”在理學的婦女觀影響下,跟以前的男女風氣相比大為不同。
二、程朱理學對客家婦女婚姻觀的影響
宋朝之前,閩粵地區(包括客家地區在內)男女婚姻相對來說是比較自由的,但隨著宋明理學在客家地區傳播,這一現象逐漸有了微妙的變化。如根據程朱理學制定族規和鄉約、限制客家婦女的婚姻自由等。這種變化在相關方之中有所體現,如《康熙寧化縣志》卷五(禮儀志):“明初……臣庶以下,冠、婚、喪、祭,一遵朱子之書”[2]。
在程朱理學影響下的客家地區主流婚姻形式大都遵循朱熹的《家禮》。即按照儒家禮教的“六禮”,不過這一般只在書香人家或大戶比較通行。
三、程朱理學下客家地區的“二婚親”
朱熹的《家禮》雖有勸喻按照禮教行事,嚴懲“傷風敗俗”的條文,但其執行情況和實際效果卻因時、因地、因不同階層而大有差異。如在程朱理學婚姻觀影響下的客家地區寡婦再嫁問題上,當時的社會意志、士紳愿望與市井細民、村夫農婦的實際行徑存在著極大的反差。
寡婦再嫁稱為“再醮之婦”,在客家地區被稱為“二婚親”,在粵東北地區則被稱為“馬頭婚”。這是理學封建綱常與客家落后現實,以及歷史蠻風夷俗相結合的產物。宋明理學的理念透過宗法族規的推行,使寡婦在社會上備受歧視,結婚儀式也不能與普通婚姻等同。如在《大埔縣志》中所記載的:“再醮之婦,由媒引至男家,謂之查家門,若二人合意,則相授默定之物……成議后……夜間偕媒至新夫家,略擇時日,辦牲敬祖,是夜亦或有拜花燭者,但不如初婚時之鬧洞房耳。其余歸寧時期及送年、轉門與初婚者略同。”[3]
在這段話中,并沒有真正寫出寡婦被歧視的狀況,只是當時的方志作者雖然受到了封建禮教思想的影響,認為這樣的婚姻其實并不光彩,故其記載多流于表面。例如這段話中沒有涉及寡婦再嫁不得穿紅衣、不得在廳堂正門出入、再嫁時要提前一兩天離開原來的家、有的地方還要在半路上轎、接親時間不能在晚上而在白天等方面的內容[4]。這些規定都是當時社會在程朱理學婚姻觀影響下客家地區寡婦遭受歧視的具體表現。因此,對寡婦再嫁,朱熹的《家禮》和各宗族的族規一般是嚴格限制的,但實際情況復雜多樣,不能一概而論。
自宋明理學占統治地位后,客家地區貞節觀念更體現得淋漓盡致,正如魯迅先生指出的:“節是丈夫死了,絕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的越早,家里愈窮,她便節的愈好。烈是有兩種:一種是無論已嫁未嫁,只有丈夫死了,她便也跟著自盡;一種是有強暴來侮辱她的時候,設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殺,都無不可。這也是死得愈慘愈苦,她便節得愈烈,倘若不及抵御,竟受了侮辱,然后自戕,便免不了議論。”[5]在宋明理學影響下,客家婦女節孝貞烈的觀念大大加深,而且各地節烈婦女的數量驚人。然而,據閩西、粵東北和廣西部分客家地區的調查(其調查范圍包括廣東梅縣、大埔、興寧、和平、花縣、廣西桂平、福建寧化等地)顯示,客家地區寡婦改嫁并不是“極少數”三字所能說明的(理學下的反常)。例如,在廣東和平縣,一位81歲的老大娘陳斌說:“婦女死了丈夫可改嫁,大多改嫁。”福建上杭才溪鄉老大娘闕招金說:“婦女死了丈夫可改嫁。”她的祖母改嫁過兩次,她自己也改嫁過兩次。
四、客家地區出現“二婚親”的原因
究其根源與客家這一地區古代男女關系比較開放自由相關,換言之,源于客家先民的“蠻夷”之風。此外,客家的宗族、家族準不準許寡婦再嫁,歸根結底是以利益為準則的[6]。理由如下:
第一,客家地區人多地少,土地資源異常缺乏,因此宗族成員并不希望寡婦特別是沒有兒子的寡婦留在本宗族內。即使有了兒子的寡婦,其兒子“隨母嫁爺”,既不改變身份,又可減少本家族的負擔,族人因此樂觀其成。所以有時會產生這樣一種奇怪的現象——寡婦不愿再嫁要受到很大的阻力,會被丈夫的兄弟被迫改嫁,以免分取家產。丈夫的兄弟強迫寡婦再嫁有兩個好處,一是少一人分取家產,二是可以得到出嫁聘金。
第二,客家婦女特別能干,“婦女……耕田、采樵、織麻、縫紉……無不為之”。婦女“立產業、營新居、謀婚嫁、延師課子,莫不井井有條”。甚至于有“男子不務正業而賴妻養者”。在這樣的情況下,那些因貧困而娶不上妻子的大齡光棍和喪妻的人,對寡婦也就“忌諱不多”[7]。
第三,客家地區的婚姻關系和繼承關系靈活多變。“隨母嫁爺”的兒子,雖然隨前夫姓,但經過兩個宗族的協商,也可由前夫、后夫共同擁有。將來如果有兩個以上的孫子,可以按照協議分別隨前夫、后夫姓。有兒子的寡婦可以嫁到新夫家,也可以招一個男人進門。
五、結語
程朱理學影響下的客家地區之所以會出現“不在少數”的客家婦女改嫁問題(理學下的反常),并不是理學對客家婦女的貞節觀念影響不強,而是理學下的封建禮教對客家地區寡婦的控制,并不能完全消泯在客家地區的實際婚姻生活和客家的“蠻夷”文化傳統影響,這是理學封建綱常與客家落后的現實以及歷史遺留蠻風夷俗相結合的產物,并且宗族、家族準不準許寡婦再嫁,歸根結底還是以利益為準則[8]。一方面,客家婦女特別能干,寡婦作為宗族的勞動力,常結合貞節觀念,將寡婦留置宗族,以免勞動力和財產流失;另一方面,當寡婦影響家庭財產的分割時,宗族又會置貞節觀念于不顧,強迫寡婦再嫁。這也是為什么受理學影響下的封建禮教迫害嚴重的客家地區會出現“不少數”寡婦再嫁的主要原因。
客家地區除了與宋明理學相違背“二婚親”,還存在許多落后、畸形甚至野蠻的婚姻形態,它們也是理學封建綱常與客家地區貧窮落后的現實以及歷史遺留的蠻風夷俗相結合的產物。例如“童養媳”“隔山嫁”“入贅婚”“沖喜婚”等。毫無疑問,這些舊時代婚俗的出現存在歷史的必然性,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當時社會的發展。隨著時代的進步,這些歷史遺留下來的蠻風夷俗也相繼被淘汰,成為了一個時代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