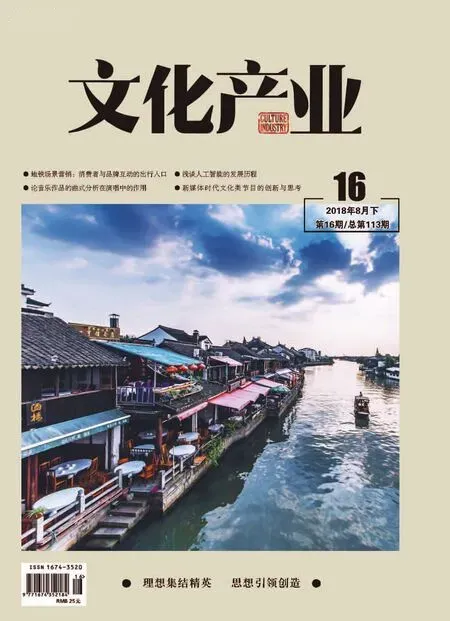當代大學生反網絡社交行為的個案研究
——以微信社交軟件的應用為例
◎劉翠林
(上海師范大學哲學與法政學院 上海 200234)
一、網絡社交問題的提出
隨著網絡時代的到來及快速發展,電腦和手機的普及使得網絡社交已成為人們社會交往的重要方式之一。網絡社交這種涉及我們生活方方面面的新型社交已經改變了人們的傳統思維。以微信這一網絡社交軟件為例,微信社交軟件從一開始為了社交的需要、滿足對軟件的新奇開始安裝使用,到后來在使用中產生了一些煩惱與困惑,從而降低了對該社交軟件的使用。人們對微信社交軟件的使用心理與態度的變化,反映了他們對網絡社交軟件的看法,由此而產生了一系列行為,比如減少使用頻率、不再發布朋友圈、更改朋友圈的權限,甚至干脆卸載,拒絕使用微信。可以將以上幾種行為稱為“反網絡社交行為”。
大學生群體是網絡社交的主體之一,也是活躍在網絡社交的群體之一,該群體的反網絡社交行為又是如何呢?以微信社交應用軟件為例,來了解分析大學生的網絡社交現狀,調查的內容主要包括:大學生對微信使用的廣度和深度、微信網絡社交中存在的問題、對微信網絡社交的看法、是否有反社交行為及其為什么產生這種行為等。從反社交應用軟件的興起開始,研究大學生反社交行為的表現,從而找出更好地應對方式,對大學生的微信社交中的行為進行引導與梳理。
二、微信與反網絡社交行為
何為微信?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微信(WeChat)是騰訊公司于2011年1月21日推出的一款為智能終端提供即時通訊服務的免費應用程序。“微信,是基于手機通訊錄直接建立與聯系人鏈接的一款即時通訊軟件,它的推廣是彌合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對立的一次試水,更是互聯網發展的必然趨勢”[1]。根據微信官方網站公布的數據得知,2018年2月,微信全球用戶月活人數首次突破10億大關;另外,根據凱度集團在2017年的《中國社交媒體影響報告》數據顯示微信的使用用戶數量和影響在所有的社交軟件中都已排名前列。
(一)微信構筑起來的社交圈子
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就已經描繪出了生活在現代大都會下人們的精神生活,陌生疏離感是大城市人們主要的一種狀態,即使住在對門,也大有可能互相不認識。這也許是人們從鄉村這個“熟人社會”走入“陌生人社會”不可避免會產生的一種狀態。但是,隨著互聯網的出現,特別是網絡社交媒介,比如微信的出現,使人們之間的勾連不再僅僅局限于地理位置上的“熟人社會”,在微信里人們加入很多微信群,使之構成自己的社會圈子。現在很多人初次見面大多數先掃一掃,加個微信與之建立一種聯結。微信重新建立了多樣化的“熟人社會”,讓每個人都可以在微信中找到“知心朋友”,建立自己的“文化圈”[2]。微信將現實社會的人際關系“無縫鏈接”到虛擬世界的移動終端,實現了社交網絡節點的延伸與信息交換空間的拓展[3]。有研究者將微信這種“線上線下共勾連、線上維系”的新型人際交往模式,引發為人際關系的新類型—“輕熟人社交關系”[4]。
(二)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矛盾交織
微信的出現,在人際互動與信息傳播過程中生成了多級化、多元化、個性化等“微時代”特征,實現了社會大眾的自我賦權與技術增權,激活了普通個體的自我意識、表達意識與行動意識,微信成為各個階層標榜“我在”參與議題、分享觀點、構建社群的“新公共領域”[5]。由此,原本屬于比較私密的朋友圈由一個私人領域變成了新的公共領域。
互加微信已成為時下最為主流的社交方式,朋友圈里除了朋友,還有各種復雜微妙的社會關系:職場上的客戶、同事和領導;家族里的親戚和長輩;某次飯局上結識的僅有一面之緣的人……面對社會關系如此凌亂的朋友圈,用戶在想要發布信息或狀態時,便會產生各種顧慮[6]。原本屬于個人私密圈子領域變成一個不再那么私密的領域了。
通過微信朋友圈展示、分享個人信息已成為人們普遍的社會交往方式。然而,隨著朋友圈好友不斷增長、點贊與評論的糾結、微信社交泛化所引起的交往疲勞、朋友圈私人領域的公共化,“停用朋友圈”“不發朋友圈”等社交媒體倦怠行為逐漸顯露并引起關注[7]。以微信社交軟件為例,如“屏蔽別人的朋友圈”“自己的朋友圈對他們屏蔽”“更改隱私權限為3天可見”“停用朋友圈”“不發朋友圈”“不刷朋友圈”甚至“停用微信”等一系列社交倦怠行為,可以將其統稱為反網絡社交行為。
朋友圈發布的內容會影響到人們的心態,并且朋友圈占用了大量的時間且多為無效社交,讓用戶產生倦怠感[8]。學者蔣建國認為:“微信的低門檻與泛朋友使得情感溝通的邊界模糊,加上朋友圈的批量轉發與商業營銷,人們之間的信任降低,消解了情感互動的意義,使用戶降低使用熱情,導致主體缺失和交往疲勞。”因此,人們在使用微信的過程中,出現了從“互動”“運動”到“反動”的一個現象。
三、網絡社交研究對象
2017年,凱度集團發布《中國社交媒體影響報告》。該報告指出,微信在九類社交媒體的滿意度最高,用戶評分高達83.5分,并且在不同的年齡群體中都得到了較高的分數。該報告總體來說,年輕人群對于社交媒體的負面影響更為警覺。例如,“90后”對“社交媒體讓我空虛浮躁”(31%),“不能集中注意力”(34%)和“受到負面價值觀的影響”(29%)的提及比例都是各人群中最高的。他們也更愿意采取果斷措施抑制社交媒體的負面影響:有39%的“90后”說已經關閉了社交媒體的推送提醒。由此可見,“90后”是最容易做出反社交行為的年輕群體。
接下來主要的分析對象為大學生群體,抽取上海某高效大學生,發放問卷并與之深度訪談,進而分析大學生群體對微信等社交媒體的態度。
四、調查個案分析
(一)微信的使用:時間、頻率與功能
在個案訪談中,在問到對于微信使用時間的問題后,根據他們的回答,得出調查對象對微信的使用時間、頻率不同,但是每個人每天都會使用的結果。在調查者回答“平常使用微信的哪些功能”這一問題的回答時可以看出,大學生群體對微信的使用較多,聊天和朋友圈功能幾乎是每天必須使用的,使用較多的功能還有微信支付、公眾號和一些小程序。可見,微信對于我們的日常生活已經是一個不可缺少的具有多功能的生活平臺。
(二)對朋友圈的認識和看法
大多是調查對象對微信朋友圈的看法都是積極的,雖然有一些廣告等消息的存在,但是并沒有影響他們的使用,但是有一個對象對朋友圈的看法是負面的。有些學生稱:“自己經常使用微信訂外賣與同學聊天。微信雖然方便了生活但是浪費學習時間”,也有學生認為朋友圈作是一種低成本的社交方式,可以有效的維持人們的關系,通過一個贊或者一個評論就可以避免甚至增強人們之間的聯系。(“我覺得朋友圈我是一種比較低成本的社交方式,就是一種低成本維持社交的一種方式。就比如說點贊和評論,這就可以維持這種關系”)。既然通過微信構建了與他人的一種社交關系,那么這種線上的社交關系不轉為線下的話,那么靠什么來維持這種輕熟人的社交關系呢?很多人通過點贊與評論來維持微信中的好友社交關系。而評論朋友圈中好友發布的動態可與之發生互動,這種互動也使朋友圈中的好友增加了聯系。
(三)朋友圈隱私權限
大部分訪談對象對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隱私權限都是有一定設置的,發布的內容也會進行分組可見,其中訪談對象D1和E5認為剛剛加的陌生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分析出自己的習慣和隱私。設置權限就可以避免了陌生人對自己性格和生活習慣的猜測。C3認為朋友圈信息中包含了大量的個人信息。所以會對自己的朋友圈的隱私進行權限設置。訪談對象對個人的真實信息填寫都是比較謹慎的,很多對象不會填寫或者只填寫一兩類,大家都比較擔心個人信息泄露會對自己造成威脅。有些人還認為在微信朋友圈中配上自己的位置,那么這就可能暴露自己經常出行的地點,給一些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機。
(四)微信上收到的騷擾情況
訪談中還是有多數人受到過騷擾的,比如編號為C1、D1、E1、E4、F1的幾位訪談對象。這些騷擾造成的結果便是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降低,特別與是陌生人之間。還有遭受過騙局的。他們表示:“我遭到陌生人騷擾很多次,大多數都是以女性的身份來添加我,微信頭像還往往全是漂亮女性,然后以有急事找你為由申請加好友。我當時也不知道是誰,也沒多想,然后就接受了,之后這些人有可能會發一些這個理財或者其他推銷之類的,反正全是各種亂七八糟的東西,讓人很反感,然后我就通通刪掉了,可是刪掉之后,居然還會再換另外一個號來加我,但是我能看出來這種微信號風格是一樣的”。
遭到微信騷擾的大多為陌生人添加的好友,這種微信上存在的騙局,使社會的信任減少,也使人們在添加沒有說明身份的好友時更為警惕。
(五)微信的影響
積極影響方面,方便了人與人的交流,生活變得簡單快捷。微信的負面影響也存在很多,如垃圾廣告、隱私暴露等。微信會增加人們的虛榮心,把微信朋友圈當成一個展示的平臺,在朋友圈中發布一些炫耀的信息,而且降低學習效率,對健康影響也很大,還會刺激自己增加支出。比如“我覺得對視力不太好,然后那個關注的公眾號推送,看不完心里就會很焦慮,然后還有微信未讀消息就會有一個小紅點,這個小紅點看見就想點,有點強迫癥。同時,微信支付還會刺激你的消費欲望,你每次購買東西都會給你發紅包嘛,這些紅包不用你就會覺得很虧”“我覺得微信有一個很大的負功能就是分割自己的時間,導致自己做事比較慢,效率降低。”
(六)微信與現實的溝通對比
回答訪談對象中,選擇更喜歡微信溝通的有3人、選擇喜歡現實溝通的有9人,而難以作出選擇,覺得兩者都好的有6人。選擇微信的人認為微信溝通更加方便而且還可以說一些現實中說不出來的話。“更喜歡微信溝通,因為你有一些說不出口的話可以通過這個說出去”。選擇現實中的溝通是因為面對面交流顯得更加的真誠、尊重對方而且可以注意到一些對方的語言和態度以及做出一些肢體動作。雖然微信很方便但面對面交流作為一種最基本的溝通方式是無法被替代的。
對于是否有過減少或不使用微信的想法這個問題的回答來看,在調研對象中是有一部分人產生過這樣的想法的,但是這種想法,大多數人是很難堅持的,最后使用頻率并沒有減少。“與社交工具抗爭了很久,我好像并沒有取得什么實質性的成果。我依舊害怕自己錯過朋友圈的信息,我依舊想要不斷地獲取外界的信息。更重要的是,我發現自己也有強烈的表達意愿,在有各種奇怪的想法時,總是希望發到社交工具中,夠得到別人的認同。所以,從個人角度來說,想要杜絕使用社交工具是十分困難的……”[9]。
五、反網絡社交與反微信
目前,微信社交媒介中的“反網絡社交”的方式主要有三種,一種是完全退出,既不和微信中的朋友交流,也不和現實好友進行微信上的互動,而是完全回歸現實生活,即退出對微信的使用;另一種則是借助一定技術支撐加以限制,如設置好友上限,圈定好友親疏程度等手段,對一些好友設置權限,從而屏蔽微信平臺上的無序社交和陌生人社交,但依舊保持特定圈子內與熟人之間的微信社交關系。還有一種是有過以上兩種行為,但是后來又按照原來的習慣繼續使用微信的。在矛盾心理之后又認為微信已經成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這一種方式也屬于反網絡社交。
調查結果分析,很多學生隨著上網時間的增長、上網頻率的增高,越容易出現反網絡社交思想,越想逃離網絡社交給人帶來的一些束縛,越容易出現一些反網絡社交行為。有些訪談對象因為周圍有同學漸漸消失在朋友圈,然后自己也厭倦了,也感覺應該回歸到現實生活中去,受其影響也出現了反網絡社交的行為。
六、深探反網絡社交行為
反網絡社交行為產生的原因主要有:一,個人隱私存在泄露風險。在國內有些用戶會頻頻受到垃圾短信的騷擾,很大原因就是互聯網公司對用戶個人信息保護不周造成用戶數據的泄露。微信上的個人信息、照片、視頻如果被不法分子利用也存在泄露隱私的風險,此外微信上也有很多存在危險的鏈接。二,網絡社交媒體中存在的暴力。社交媒體中的網絡暴力行為也是阻止青年遠離社交媒體的重要原因。例如微信群中對于一個社會熱點的評價,人們往往會有不同的觀點,同時如果一條評論的內容過于極端那么很可能引發一場對罵使沖突升級。三,社交關系的表面化與形式化。無論是“熟關系人群”,還是“生關系人群”,一旦通過微信平臺的好友認證,其交往行為便趨于一致,即通過私信、群聊、點贊、評論和瀏覽朋友圈來維系人際關系。交往流于表面,交往手段也逐漸淪為一種范式[10]。正是因為這種社交關系的表面性與形式性導致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難以深入,這種關系的維護也很難持久。四,沉迷虛擬,導致現實社交的弱化。有些人每天使用微信時間長達6小時,占據全天時間的四分之一,對微信的過度使用與依賴會讓人慢慢變得孤立,逐漸失去社交的動力,甚至恐懼社交,在現實世界中變得沉默與孤獨[11]。虛擬交往與現實交往的沖突性。比如點贊行為的虛擬意義與現實意義相悖,漸漸失去了原有的贊許認可的意義,而變成一種習慣或是為幫助朋友積贊的溝通意識的行為,這是與現實交往中的點贊的意義是相悖的[12]。五,時間碎片化,個人浮躁與焦慮的產生。由于網絡互聯,使得網絡社交可以隨時隨地不受時空距離限制地發生,消息的接收與發送也無須很長時間,人們可以一直“在線”等待網絡另一端的消息互動。看似方便溝通實則分散個人的時間,使得個人的時間變得碎片化。網絡信息五花八門,通過網絡社交中朋友圈傳達的各種信息更是對個人的體驗與生活產生一定的影響,比如看著朋友圈中的各種微商廣告,心生厭煩。同時,網絡社交中的信息也容易讓人活在“朋友圈”中,把朋友圈當成一個表演的舞臺,花費大量時間來進行表演。隨著不斷的時間消耗與個人現實生活投入降低,人們會變得浮躁與焦慮。于是,在盲目追逐粉絲量的腳步停下后,“反社交”成為引發共鳴的一種需求。但隨之而來的就是對現實社交的重視與回歸。
七、結語
以往的研究顯示,社交媒體使用與社會資本有一定的關系。但是這個社會資本的形成也只有從現實社交轉移到線下社交才會形成真實有效的社會資本,畢竟真實社交的含金量是遠遠高于線上微信社交。之所以如此強調社交要走出去是因為當下線上社交大都是蜻蜓點水、點贊之交,彼此之間很難深入交流,即便加入一個龐大的交友微信群也是如此。微信提供的只是一個平臺與媒介,微信等社交軟件是網絡發展的必不可少的結果,只有正視它的作用,才能合理利用線上社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