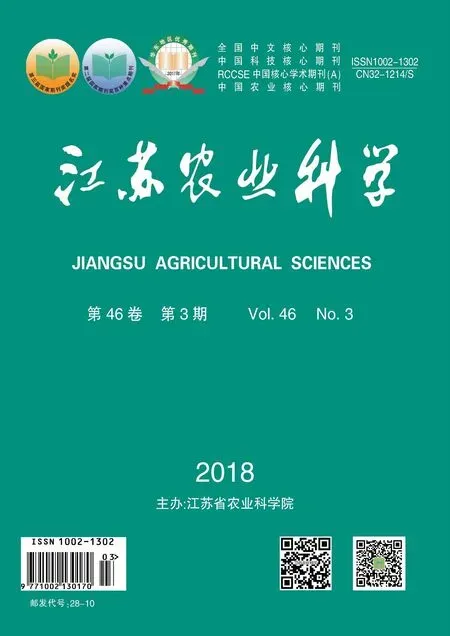欠發(fā)達(dá)地區(qū)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市場(chǎng)化服務(wù)體系構(gòu)建
劉 松, 李超穎
(長(zhǎng)江大學(xué)管理學(xué)院,湖北荊州 434023)
2013年,中央一號(hào)文件提出鼓勵(lì)和支持承包土地向?qū)I(yè)大戶、家庭農(nóng)場(chǎng)、農(nóng)民合作社流轉(zhuǎn)的精神,進(jìn)一步凸顯出新型農(nóng)業(yè)主體在我國(guó)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的關(guān)鍵地位。現(xiàn)階段,我國(guó)農(nóng)業(yè)主體已發(fā)生結(jié)構(gòu)性變化,以專業(yè)大戶、家庭農(nóng)場(chǎng)、專業(yè)合作組織、產(chǎn)業(yè)化龍頭企業(yè)為代表的各類新型農(nóng)業(yè)主體不斷地發(fā)展,已成為促進(jìn)區(qū)域農(nóng)業(yè)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提升的主要?jiǎng)恿ΑH欢芏嗲闆r下新型農(nóng)業(yè)主體雖然引起了生產(chǎn)組織形式和生產(chǎn)方式上的轉(zhuǎn)變,但并沒(méi)有從根本上改變“小生產(chǎn)與大市場(chǎng)”間的矛盾格局。特別是對(duì)于中西部欠發(fā)達(dá)地區(qū)而言,新型農(nóng)業(yè)主體總體上仍處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流通、消費(fèi)全過(guò)程缺乏組織化的大環(huán)境,它們對(duì)完成生產(chǎn)與市場(chǎng)的對(duì)接,保證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穩(wěn)定、質(zhì)量安全以及低成本流通的作用有限,甚至在局部區(qū)域內(nèi)造成更嚴(yán)重的農(nóng)業(yè)主體增產(chǎn)不增收的尷尬局面。因而,欠發(fā)達(dá)地區(qū)的家庭農(nóng)場(chǎng)、專業(yè)大戶、農(nóng)業(yè)合作社等新型農(nóng)業(yè)主體以及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下的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者更可能成為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是指在農(nóng)業(yè)資源和農(nóng)產(chǎn)品上具有潛在市場(chǎng)化優(yōu)勢(shì),但受區(qū)域政策、產(chǎn)業(yè)基礎(chǔ)、運(yùn)營(yíng)模式等方面的限制,經(jīng)營(yíng)積極性和經(jīng)營(yíng)績(jī)效受制于外部農(nóng)產(chǎn)品供給量和價(jià)格波動(dòng),致使其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中處于弱勢(shì)地位的農(nóng)業(yè)主體[1]。欠發(fā)達(dá)地區(qū)如何在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基礎(chǔ)薄弱、支持政策滯后、市場(chǎng)化能力有限的條件下,促進(jìn)新型農(nóng)業(yè)主體充分市場(chǎng)化,并帶動(dòng)比重更大的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群體共同發(fā)展是全面實(shí)現(xiàn)我國(guó)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急需解決的關(guān)鍵問(wèn)題。本研究以欠發(fā)達(dá)地區(qū)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的培植為導(dǎo)向,研究欠發(fā)達(dá)地區(qū)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市場(chǎng)化的突破口,并圍繞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市場(chǎng)化的多階段路徑建立起系統(tǒng)的市場(chǎng)化服務(wù)體系,以期使欠發(fā)達(dá)地區(qū)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能逐漸實(shí)現(xiàn)從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弱勢(shì)地位到優(yōu)勢(shì)地位的轉(zhuǎn)變。
1 研究現(xiàn)狀
我國(guó)正在加快構(gòu)建公益性服務(wù)與經(jīng)營(yíng)性服務(wù)相結(jié)合、專項(xiàng)服務(wù)與綜合服務(wù)相協(xié)調(diào)、多元化市場(chǎng)主體廣泛參與的農(nóng)業(yè)社會(huì)化服務(wù)體系[2-3]。以誘致性制度變遷為基礎(chǔ),政府強(qiáng)制性變遷為主導(dǎo),以名優(yōu)新品種引進(jìn)為突破口,以產(chǎn)業(yè)集群建設(shè)為重點(diǎn),培育農(nóng)業(yè)龍頭企業(yè),發(fā)揮其輻射帶動(dòng)作用;以包裝傳統(tǒng)特色農(nóng)產(chǎn)品為依托,發(fā)展特色農(nóng)業(yè),并以工業(yè)化思維推動(dòng)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化是我國(guó)長(zhǎng)期以來(lái)開(kāi)展市場(chǎng)化服務(wù)的主要思路[4]。近年來(lái),“公司+基地(農(nóng)戶)”及其衍生的市場(chǎng)化服務(wù)模式在我國(guó)農(nóng)業(yè)主體市場(chǎng)化實(shí)踐占有主導(dǎo)地位,它是一種以龍頭企業(yè)帶動(dòng)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化,為基地(農(nóng)戶)提供生產(chǎn)、流通和銷售保障的市場(chǎng)化服務(wù)模式。如湖北省福娃集團(tuán)在糧食深加工方面就廣泛采用“公司+基地+農(nóng)戶+科技”的發(fā)展模式,實(shí)現(xiàn)了政府、企業(yè)和農(nóng)戶“三贏”的目標(biāo)。新型農(nóng)業(yè)主體產(chǎn)生后,我國(guó)逐步形成了以農(nóng)民合作社、龍頭企業(yè)和各類經(jīng)營(yíng)性服務(wù)組織為支撐,多種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組織共同協(xié)作的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yíng)體系,出現(xiàn)了以“公司+農(nóng)民合作社+家庭農(nóng)場(chǎng)(農(nóng)戶)”為主導(dǎo)的市場(chǎng)化模式[5]。該模式通常以形成一定規(guī)模的種植戶或養(yǎng)殖戶作為基層生產(chǎn)單位,專業(yè)合作社以法人身份按產(chǎn)業(yè)鏈、產(chǎn)品、品牌等組建聯(lián)合社,而聯(lián)合社是把更多的家庭農(nóng)場(chǎng)聯(lián)合起來(lái),為家庭農(nóng)場(chǎng)或?qū)I(yè)大戶進(jìn)一步提供生產(chǎn)技術(shù)、農(nóng)產(chǎn)品銷售、生產(chǎn)設(shè)施等多方面的服務(wù)。建設(shè)區(qū)域性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集群也是我國(guó)農(nóng)業(yè)主體市場(chǎng)化服務(wù)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6],它有利于降低農(nóng)產(chǎn)品交易費(fèi)用,形成區(qū)域農(nóng)業(yè)品牌優(yōu)勢(shì),并將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鏈向下延伸到農(nóng)產(chǎn)品的銷售渠道和客戶,側(cè)面擴(kuò)展至輔助性產(chǎn)品的制造商以及與技能、技術(shù)或投資相關(guān)的公司。總體上,依托于“公司+基地(農(nóng)戶)”“公司+農(nóng)民合作社+家庭農(nóng)場(chǎng)(農(nóng)戶)”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集群等基本形式,我國(guó)多元化市場(chǎng)主體廣泛參與的農(nóng)業(yè)社會(huì)化服務(wù)體系日漸完善,但仍然存在金融支持力度不夠、合作組織規(guī)范性欠缺、龍頭企業(yè)規(guī)模偏小、公益性組織服務(wù)能力不足等問(wèn)題[2-5]。
歐美國(guó)家的市場(chǎng)服務(wù)體系特別強(qiáng)調(diào)產(chǎn)業(yè)升級(jí)、農(nóng)業(yè)扶持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以引導(dǎo)農(nóng)產(chǎn)品的安全生產(chǎn)和流通,確保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穩(wěn)定與農(nóng)民收入的增長(zhǎng)[7-8];同時(shí),通過(guò)政府機(jī)構(gòu)主導(dǎo)的生產(chǎn)技術(shù)創(chuàng)新和契約化社會(huì)服務(wù)來(lái)提高農(nóng)產(chǎn)品生產(chǎn)的效率和質(zhì)量,解決農(nóng)戶在貸款、技術(shù)應(yīng)用等方面的困難[9]。農(nóng)協(xié)是日本農(nóng)業(yè)社會(huì)化服務(wù)體系的主體,遵循尊重農(nóng)民主體地位、民主監(jiān)管、現(xiàn)代企業(yè)模式運(yùn)行、政府扶持等普遍性原則,同時(shí)承擔(dān)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發(fā)展的經(jīng)濟(jì)功能、社會(huì)管理服務(wù)、保護(hù)農(nóng)民權(quán)益等重要作用[10-11]。美國(guó)構(gòu)成了公共農(nóng)業(yè)服務(wù)系統(tǒng)、合作社農(nóng)業(yè)服務(wù)系統(tǒng)、私人農(nóng)業(yè)服務(wù)系統(tǒng)協(xié)調(diào)互補(bǔ)的三個(gè)層次[12]。公共機(jī)構(gòu)主要側(cè)重于長(zhǎng)期性、基礎(chǔ)性的科研工作,合作社在提供覆蓋全程的農(nóng)業(yè)服務(wù)方面發(fā)揮著積極作用,私人機(jī)構(gòu)主要側(cè)重于應(yīng)用性領(lǐng)域[13]。德國(guó)的服務(wù)體系形成了初級(jí)合作社、地區(qū)級(jí)合作社聯(lián)社和國(guó)家級(jí)合作社聯(lián)盟[14]。值得一提的是,國(guó)家農(nóng)業(yè)市場(chǎng)化服務(wù)體系的構(gòu)建特別注重農(nóng)產(chǎn)品電子商務(wù)平臺(tái)的開(kāi)發(fā)與應(yīng)用,并伴隨著農(nóng)業(yè)信息服務(wù)體系的建設(shè),能為農(nóng)業(yè)主體市場(chǎng)化提供信息采集、加工處理及信息發(fā)布等全過(guò)程服務(wù)[15]。
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和農(nóng)業(yè)主體的市場(chǎng)化具有很強(qiáng)的地域根植性,經(jīng)濟(jì)較發(fā)達(dá)地區(qū)、欠發(fā)達(dá)地區(qū)、貧困落后地區(qū)的市場(chǎng)化模式應(yīng)該有不同的選擇[6,16]。國(guó)內(nèi)農(nóng)業(yè)主體市場(chǎng)化服務(wù)體系的研究以總結(jié)農(nóng)業(yè)資源優(yōu)勢(shì)突出、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區(qū)域的建設(shè)經(jīng)驗(yàn)和啟示為主,對(duì)欠發(fā)達(dá)地區(qū)農(nóng)業(yè)主體的市場(chǎng)化模式研究較為少見(jiàn)。欠發(fā)達(dá)地區(qū)如果直接移植發(fā)達(dá)地區(qū)或國(guó)外成熟市場(chǎng)化服務(wù)模式,容易造成片面地追求服務(wù)平臺(tái)硬件建設(shè)、產(chǎn)業(yè)集群規(guī)模擴(kuò)大,而忽略支持農(nóng)業(yè)主體市場(chǎng)化和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持續(xù)發(fā)展的政策環(huán)境、輔助機(jī)構(gòu)以及商業(yè)模式等方面的創(chuàng)新,產(chǎn)生嚴(yán)重的移植失效問(wèn)題。“公司+基地(農(nóng)戶)”或“公司+農(nóng)民合作社+家庭農(nóng)場(chǎng)(農(nóng)戶)”等服務(wù)模式本質(zhì)上仍是農(nóng)業(yè)企業(yè)主導(dǎo)的供應(yīng)鏈,農(nóng)業(yè)主體始終處于失去經(jīng)營(yíng)自主權(quán)的弱勢(shì)地位[14]。一方面,由于欠發(fā)達(dá)地區(qū)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生產(chǎn)規(guī)模或產(chǎn)品質(zhì)量沒(méi)有達(dá)到較高的水平,加入或不加入合作社的利益并沒(méi)太大差異;另一方面,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沒(méi)有擴(kuò)展農(nóng)產(chǎn)品供應(yīng)鏈的能力,仍然改變不了類似于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模式下的被動(dòng)地位。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集群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并不是隨著產(chǎn)業(yè)的集中而自然出現(xiàn),產(chǎn)業(yè)集群的外部經(jīng)濟(jì)、合作效率以及技術(shù)創(chuàng)新潛力需要生產(chǎn)機(jī)械化、經(jīng)營(yíng)信息化和勞動(dòng)力高素質(zhì)化等優(yōu)勢(shì)資源和組織化的環(huán)境將其激發(fā)、轉(zhuǎn)化。而這些是欠發(fā)達(dá)地區(qū)在短期內(nèi)很難具備的。總體而言,適應(yīng)于欠發(fā)達(dá)地區(qū)生產(chǎn)資源現(xiàn)狀、農(nóng)業(yè)主體結(jié)構(gòu)、生產(chǎn)流通特征、區(qū)域市場(chǎng)、政策環(huán)境條件,能促進(jìn)欠發(fā)達(dá)地區(qū)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向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地位轉(zhuǎn)變的市場(chǎng)化服務(wù)體系還沒(méi)得到應(yīng)有的關(guān)注和系統(tǒng)地建立。
2 欠發(fā)達(dá)地區(qū)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市場(chǎng)化的突破口
從世界各國(guó)農(nóng)業(yè)發(fā)展的路徑看,農(nóng)業(yè)主體市場(chǎng)化的初始階段不可避免地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17]。我國(guó)農(nóng)業(yè)管理部門同樣也制定了專門的財(cái)稅、用地、經(jīng)營(yíng)、保險(xiǎn)等方面的扶持政策;很多發(fā)達(dá)地區(qū)還通過(guò)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yíng)主體發(fā)展專項(xiàng)基金,通過(guò)貼息、補(bǔ)助、獎(jiǎng)勵(lì)等措施,支持新型農(nóng)業(yè)主體興建生產(chǎn)服務(wù)設(shè)施、建設(shè)原料生產(chǎn)基地、擴(kuò)大生產(chǎn)規(guī)模、推進(jìn)技術(shù)改造升級(jí)等。受財(cái)政能力的限制,欠發(fā)達(dá)地區(qū)往往將有限的資金直接用于農(nóng)業(yè)主體的多元化和規(guī)模化,而忽略在農(nóng)業(yè)主體的定位、商業(yè)運(yùn)作模式創(chuàng)新、市場(chǎng)化服務(wù)組織化、戰(zhàn)略性政策等方面的支撐,使建立在單一優(yōu)勢(shì)資源上的比較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因同質(zhì)性競(jìng)爭(zhēng)而逐漸喪失,導(dǎo)致欠發(fā)達(dá)地區(qū)農(nóng)業(yè)發(fā)展越來(lái)越困難。農(nóng)業(yè)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直接來(lái)源于農(nóng)業(yè)的集中度、效率優(yōu)勢(shì)以及規(guī)模優(yōu)勢(shì)等方面,體現(xiàn)在農(nóng)產(chǎn)品價(jià)格、農(nóng)產(chǎn)品質(zhì)量、農(nóng)產(chǎn)品結(jié)構(gòu)以及農(nóng)產(chǎn)品的差異性與趣味性等方面,同時(shí)受技術(shù)創(chuàng)新、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政府支持、勞動(dòng)者素質(zhì)、自然資源以及農(nóng)業(yè)標(biāo)準(zhǔn)等因素的影響。盡管欠發(fā)達(dá)地區(qū)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在競(jìng)爭(zhēng)力直接來(lái)源及影響因素方面均難具有突出優(yōu)勢(shì),但根據(jù)波特的價(jià)值鏈理論,欠發(fā)達(dá)地區(qū)的農(nóng)業(yè)價(jià)值鏈仍然存在具有潛力的增值環(huán)節(jié)。問(wèn)題關(guān)鍵在于,如何圍繞欠發(fā)達(dá)地區(qū)農(nóng)業(yè)價(jià)值鏈的特征,找到激發(fā)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潛在外部經(jīng)濟(jì)性、合作效率以及創(chuàng)新能力的突破口,使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能獲得較為穩(wěn)定的經(jīng)濟(jì)收益,從而培養(yǎng)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主動(dòng)參與市場(chǎng)化的積極性。
在我國(guó)加速推進(jìn)城鎮(zhèn)化的背景下,區(qū)域城鎮(zhèn)居民規(guī)模會(huì)越來(lái)越大,農(nóng)產(chǎn)品消費(fèi)必然具有很強(qiáng)的增長(zhǎng)潛力。欠發(fā)達(dá)地區(qū)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在暫時(shí)缺乏跨區(qū)域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的情況下,其農(nóng)產(chǎn)品市場(chǎng)化服務(wù)定位應(yīng)該是充分利用近地優(yōu)勢(shì),使農(nóng)產(chǎn)品的供給能適應(yīng)區(qū)域城鎮(zhèn)居民的消費(fèi)水平、消費(fèi)習(xí)慣以及消費(fèi)品質(zhì)等方面的需求。基于這種考慮,欠發(fā)達(dá)地區(qū)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市場(chǎng)化的突破口在于建立面向區(qū)域城鎮(zhèn)居民農(nóng)產(chǎn)品消費(fèi)需求的適應(yīng)性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即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在短期內(nèi)不追求在農(nóng)產(chǎn)品質(zhì)量、供給速度和價(jià)格上的絕對(duì)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而將其產(chǎn)品生產(chǎn)目標(biāo)客戶直接定位于區(qū)域城鎮(zhèn)居民,利用接近消費(fèi)市場(chǎng)的優(yōu)勢(shì),提供適應(yīng)區(qū)域城鎮(zhèn)居民固有消費(fèi)偏好和消費(fèi)趨勢(shì)的農(nóng)產(chǎn)品。聶華林等認(rèn)為,特色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是我國(guó)西部等農(nóng)業(yè)欠發(fā)達(dá)地區(qū)實(shí)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基本取向[18]。適應(yīng)性優(yōu)勢(shì)挖掘并不排斥欠發(fā)達(dá)地區(qū)特色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和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的培植,只是主張欠發(fā)達(dá)地區(qū)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在宏微觀條件欠佳的情況下,通過(guò)服務(wù)區(qū)域內(nèi)特定的目標(biāo)消費(fèi)群來(lái)突破市場(chǎng)化瓶頸,在積累市場(chǎng)化信心的基礎(chǔ)上再將區(qū)域內(nèi)定向的適應(yīng)性優(yōu)勢(shì)升華為內(nèi)生發(fā)展動(dòng)力,逐步促進(jìn)具有規(guī)模經(jīng)濟(jì)性的特色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
欠發(fā)達(dá)地區(qū)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適應(yīng)性優(yōu)勢(shì)分析模型見(jiàn)圖1。欠發(fā)達(dá)地區(qū)農(nóng)業(yè)主體需要選擇一個(gè)農(nóng)業(yè)資源特征和發(fā)展環(huán)境相近但相對(duì)發(fā)達(dá)的地區(qū)作為參考標(biāo)桿,對(duì)比農(nóng)產(chǎn)品在價(jià)格、質(zhì)量、結(jié)構(gòu)、差異性、趣味性等方面的差異,以及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影響因素方面的差異,對(duì)競(jìng)爭(zhēng)弱勢(shì)地位起重要作用的關(guān)鍵差異就是欠發(fā)達(dá)地區(qū)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市場(chǎng)化服務(wù)體系需重點(diǎn)解決的問(wèn)題。適應(yīng)性優(yōu)勢(shì)分析模型認(rèn)為,欠發(fā)達(dá)地區(qū)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的優(yōu)勢(shì)在于能準(zhǔn)確地把握區(qū)域城鎮(zhèn)居民的農(nóng)產(chǎn)品消費(fèi)習(xí)慣及消費(fèi)趨勢(shì),從而能以創(chuàng)造“滿意的消費(fèi)偏好”和“滿意的消費(fèi)方式”為主要目標(biāo),兼顧“價(jià)格控制”目標(biāo),并針對(duì)區(qū)域城鎮(zhèn)居民在農(nóng)產(chǎn)品品質(zhì)、消費(fèi)提前期、價(jià)格敏感性、休閑體驗(yàn)、風(fēng)俗習(xí)慣等維度的特殊要求,在農(nóng)業(yè)價(jià)值鏈中的生產(chǎn)、流通、加工、銷售和服務(wù)等環(huán)節(jié)挖掘出響應(yīng)這些特殊要求的“適應(yīng)性優(yōu)勢(shì)”。“適應(yīng)性優(yōu)勢(shì)”通常可以體現(xiàn)在農(nóng)產(chǎn)品即時(shí)供應(yīng)、產(chǎn)品質(zhì)量可回溯性、農(nóng)產(chǎn)品生產(chǎn)互動(dòng)性、消費(fèi)習(xí)慣匹配性等方面。

3 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市場(chǎng)化服務(wù)體系建設(shè)內(nèi)容
3.1 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市場(chǎng)化服務(wù)體系的框架
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的市場(chǎng)化能力應(yīng)該以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的提升為依托,因而市場(chǎng)化服務(wù)體系的建設(shè)需圍繞農(nóng)業(yè)主體競(jìng)爭(zhēng)力的培植過(guò)程逐步開(kāi)展。在以適應(yīng)性優(yōu)勢(shì)作為市場(chǎng)化突破口的條件下,欠發(fā)達(dá)地區(qū)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的市場(chǎng)化服務(wù)體系在短期內(nèi)應(yīng)服務(wù)于適應(yīng)性優(yōu)勢(shì)的挖掘和強(qiáng)化,長(zhǎng)期內(nèi)需要服務(wù)于欠發(fā)達(dá)地區(qū)農(nóng)業(yè)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因素及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影響因素的優(yōu)化,從而為適應(yīng)性優(yōu)勢(shì)向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的轉(zhuǎn)化提供持續(xù)動(dòng)力。按照這種思路,可將欠發(fā)達(dá)地區(qū)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的市場(chǎng)化進(jìn)程分為市場(chǎng)化奠基、市場(chǎng)化提升、市場(chǎng)化溢出3個(gè)階段,欠發(fā)達(dá)地區(qū)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的市場(chǎng)化服務(wù)體系在每個(gè)階段都應(yīng)有明確的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培植目標(biāo),并通過(guò)匹配的服務(wù)平臺(tái)建設(shè)和服務(wù)模式創(chuàng)新來(lái)支撐各個(gè)階段性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培植目標(biāo)的實(shí)現(xiàn)(圖2)。

3.2 市場(chǎng)化奠基階段的服務(wù)體系
在市場(chǎng)化奠基階段,欠發(fā)達(dá)地區(qū)市場(chǎng)化服務(wù)體系的階段性任務(wù)是挖掘和強(qiáng)化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的適應(yīng)性優(yōu)勢(shì),實(shí)現(xiàn)激活欠發(fā)達(dá)地區(qū)可利用的市場(chǎng)化資源,提高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參與市場(chǎng)化積極性的目標(biāo)。歐美農(nóng)業(yè)主體市場(chǎng)化服務(wù)體系的實(shí)踐表明,農(nóng)業(yè)電子商務(wù)平臺(tái)性組織有助于產(chǎn)生規(guī)模化的市場(chǎng)渠道、緊密的合作組織結(jié)構(gòu)、信息共享和信任機(jī)制以及公共的支持環(huán)境等,并且由平臺(tái)性組織而引起的交易模式變革會(huì)促進(jìn)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內(nèi)部結(jié)構(gòu)的調(diào)整[15]。欠發(fā)達(dá)地區(qū)在市場(chǎng)化奠基階段可借鑒有關(guān)經(jīng)驗(yàn),由電子商務(wù)實(shí)體企業(yè)或農(nóng)村各種合作組織創(chuàng)建“適應(yīng)性優(yōu)勢(shì)集成服務(wù)平臺(tái)”。該服務(wù)平臺(tái)以“資源共享、交易便捷、消費(fèi)娛樂(lè)性、服務(wù)公益性”為特色,通過(guò)集成區(qū)域農(nóng)業(yè)資源、簡(jiǎn)化農(nóng)產(chǎn)品流通渠道、壓縮交易時(shí)間、信息共享等途徑,使欠發(fā)達(dá)地區(qū)各類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在邏輯上形成一個(gè)整體,實(shí)現(xiàn)小規(guī)模適應(yīng)性優(yōu)勢(shì)資源的集成,打破小規(guī)模分散供給受制于大市場(chǎng)的農(nóng)產(chǎn)品價(jià)值鏈結(jié)構(gòu);同時(shí),還要具有將各種適應(yīng)性優(yōu)勢(shì)資源轉(zhuǎn)化為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經(jīng)濟(jì)利益的功能。
長(zhǎng)江大學(xué)科研團(tuán)隊(duì)與荊州地區(qū)多個(gè)特色農(nóng)產(chǎn)品合作社進(jìn)行合作,開(kāi)發(fā)了區(qū)域農(nóng)業(yè)適應(yīng)性優(yōu)勢(shì)集成服務(wù)平臺(tái),該平臺(tái)主推農(nóng)業(yè)供需信息咨詢、虛擬家庭農(nóng)場(chǎng)、農(nóng)廚對(duì)接、生態(tài)農(nóng)場(chǎng)管理以及特價(jià)農(nóng)產(chǎn)品拍賣5項(xiàng)功能。區(qū)域城鎮(zhèn)消費(fèi)群可以通過(guò)該平臺(tái)了解生態(tài)農(nóng)產(chǎn)品生產(chǎn)和經(jīng)營(yíng)的相關(guān)政策、科技、市場(chǎng)動(dòng)態(tài)以及服務(wù)流程,并利用“農(nóng)廚對(duì)接”“虛擬家庭農(nóng)場(chǎng)”功能進(jìn)行農(nóng)產(chǎn)品的在線采購(gòu)、在線預(yù)訂、在線領(lǐng)養(yǎng)、在線農(nóng)產(chǎn)品拍賣等交易。注冊(cè)供應(yīng)商可自動(dòng)查詢?cè)诰€的農(nóng)產(chǎn)品訂單需求,及時(shí)響應(yīng)城鎮(zhèn)居民的消費(fèi)需求。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可以通過(guò)“農(nóng)業(yè)供需信息咨詢”功能尋找交易機(jī)會(huì),“生態(tài)農(nóng)場(chǎng)管理”功能使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的生產(chǎn)行為可被統(tǒng)一納入平臺(tái)所屬的生態(tài)農(nóng)場(chǎng)基地進(jìn)行管理,使其種植、養(yǎng)殖活動(dòng)規(guī)范化,以共同面對(duì)區(qū)域城鎮(zhèn)消費(fèi)市場(chǎng)。最重要的是,區(qū)域農(nóng)業(yè)適應(yīng)性優(yōu)勢(shì)集成服務(wù)平臺(tái)可以讓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提前得到具體價(jià)格保障的預(yù)售訂單,實(shí)現(xiàn)各種農(nóng)業(yè)資源的定向供給和價(jià)格鎖定,確保農(nóng)業(yè)主體的經(jīng)營(yíng)收益處于較穩(wěn)定的水平。目前,荊州地區(qū)的葡萄、綠色蔬菜、淡水養(yǎng)殖、生態(tài)豬肉等特色產(chǎn)品,已通過(guò)適應(yīng)性優(yōu)勢(shì)集成服務(wù)平臺(tái)實(shí)現(xiàn)了初步市場(chǎng)化,其產(chǎn)品質(zhì)量已獲得區(qū)域城鎮(zhèn)消費(fèi)者廣泛認(rèn)可。同時(shí),各領(lǐng)域的地方專業(yè)合作社依托適應(yīng)性優(yōu)勢(shì)集成服務(wù)平臺(tái),已經(jīng)建立起組織化的農(nóng)產(chǎn)品市場(chǎng)化服務(wù)機(jī)構(gòu)和經(jīng)營(yíng)服務(wù)模式,使荊州市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逐漸擺脫了市場(chǎng)化經(jīng)營(yíng)的弱勢(shì)困境,提高其參與農(nóng)產(chǎn)品生產(chǎn)和市場(chǎng)化的積極性。
3.3 市場(chǎng)化提升階段的服務(wù)體系
市場(chǎng)化提升階段的主要任務(wù)促進(jìn)適應(yīng)性優(yōu)勢(shì)向比較優(yōu)勢(shì)轉(zhuǎn)化,實(shí)現(xiàn)降低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市場(chǎng)化的成本、增加農(nóng)產(chǎn)品規(guī)模和市場(chǎng)化收益、打造區(qū)域性農(nóng)業(yè)品牌的目標(biāo)。為此,欠發(fā)達(dá)地區(qū)市場(chǎng)化服務(wù)體系要著力建立起能促進(jìn)農(nóng)資、農(nóng)產(chǎn)品、農(nóng)業(yè)信息、農(nóng)業(yè)科技等關(guān)鍵要素低成本流通的生產(chǎn)服務(wù)網(wǎng)絡(luò)。由于欠發(fā)達(dá)地區(qū)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基礎(chǔ)薄弱,加之區(qū)域財(cái)政困難,要建立起類似發(fā)達(dá)地區(qū)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服務(wù)網(wǎng)絡(luò)存在較大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欠發(fā)達(dá)地區(qū)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服務(wù)網(wǎng)絡(luò)的建設(shè)要解決好幾個(gè)關(guān)鍵問(wèn)題:(1)如何有效控制生產(chǎn)服務(wù)網(wǎng)絡(luò)建設(shè)的成本;(2)如何使素質(zhì)相對(duì)較低的農(nóng)業(yè)主體便捷地接受服務(wù);(3)如何降低向農(nóng)業(yè)主體提供服務(wù)的成本。湖北壟上新公社有限責(zé)任公司的運(yùn)作模式為解決這些問(wèn)題提供了參考。
2009年,湖北長(zhǎng)江壟上傳媒集團(tuán)依托其品牌節(jié)目“壟上行”的影響力,與內(nèi)蒙古永業(yè)集團(tuán)共同投資建立了湖北壟上新公社有限責(zé)任公司(簡(jiǎn)稱壟上新公社),將區(qū)域電視媒體的品牌節(jié)目與市場(chǎng)渠道網(wǎng)絡(luò)、政府資源、社會(huì)資本整合起來(lái),建立了一種以電視受眾為基礎(chǔ),集農(nóng)產(chǎn)品推廣、農(nóng)資銷售、技術(shù)服務(wù)及生活?yuàn)蕵?lè)于一體的農(nóng)資流通網(wǎng)絡(luò),并逐漸將流通網(wǎng)絡(luò)向全面服務(wù)于“三農(nóng)”的功能擴(kuò)展[19]。本研究將壟上新公社的運(yùn)作模式稱為“區(qū)域媒體驅(qū)動(dòng)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服務(wù)平臺(tái)”,可視為一種面向欠發(fā)達(dá)地區(qū)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yíng)性服務(wù)組織。在欠發(fā)達(dá)地區(qū)建設(shè)“區(qū)域媒體驅(qū)動(dòng)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服務(wù)網(wǎng)絡(luò)”至少具有下列優(yōu)勢(shì):(1)利用區(qū)域媒體開(kāi)展生產(chǎn)服務(wù)網(wǎng)絡(luò)品牌宣傳和渠道建設(shè),可以以低成本將穩(wěn)定的電視節(jié)目受眾群轉(zhuǎn)化為目標(biāo)服務(wù)群,增加區(qū)域農(nóng)業(yè)主體對(duì)生產(chǎn)服務(wù)網(wǎng)絡(luò)的信任度。(2)媒體驅(qū)動(dòng)的生產(chǎn)服務(wù)網(wǎng)絡(luò)可降低欠發(fā)達(dá)地區(qū)完善區(qū)域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基礎(chǔ)設(shè)施的投資。(3)媒體線上服務(wù)與線下服務(wù)網(wǎng)絡(luò)互補(bǔ),使欠發(fā)達(dá)地區(qū)素質(zhì)較低的農(nóng)業(yè)主體能在不同的場(chǎng)合潛移默化地接受配套的技術(shù)推廣服務(wù);同時(shí),可為加盟商提供廣告促銷、產(chǎn)品銷售、質(zhì)量管理、農(nóng)技推廣和售后服務(wù)支持。(4)媒體驅(qū)動(dòng)的生產(chǎn)服務(wù)網(wǎng)絡(luò)能夠發(fā)揮規(guī)模化、標(biāo)準(zhǔn)化和品牌化的優(yōu)勢(shì),為欠發(fā)達(dá)區(qū)域涉農(nóng)產(chǎn)品、農(nóng)資的采購(gòu)、流通和消費(fèi)提供量、質(zhì)、價(jià)三方面的服務(wù)保障,有效地促進(jìn)適應(yīng)性優(yōu)勢(shì)向比較優(yōu)勢(shì)轉(zhuǎn)化。
然而在壟上新公社現(xiàn)有的運(yùn)營(yíng)模式下,傳媒集團(tuán)、壟上新公社及代理商間存在潛在的利益沖突,特別是其生產(chǎn)服務(wù)網(wǎng)絡(luò)有推高區(qū)域農(nóng)資市場(chǎng)價(jià)格的傾向,尤其在不斷獲得某些新產(chǎn)品壟斷經(jīng)營(yíng)權(quán)的情況下,區(qū)域農(nóng)資價(jià)格上漲的傾向更為明顯。壟上新公社在生產(chǎn)服務(wù)網(wǎng)絡(luò)中的作用實(shí)質(zhì)是延長(zhǎng)了區(qū)域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服務(wù)鏈,它與代理商之間只是簡(jiǎn)單的“委托/代理”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中的伙伴在利益訴求上存在競(jìng)爭(zhēng)性。為此,建議壟上新公社對(duì)現(xiàn)有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服務(wù)網(wǎng)絡(luò)進(jìn)行優(yōu)化,加強(qiáng)對(duì)渠道變動(dòng)成本的控制和市場(chǎng)定價(jià)權(quán)的管理,以便更有效地落實(shí)“統(tǒng)一定價(jià)”政策。從發(fā)展戰(zhàn)略層面看,壟上新公社要盡早地實(shí)現(xiàn)從生產(chǎn)服務(wù)網(wǎng)絡(luò)中的代理商角色到區(qū)域品牌化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服務(wù)平臺(tái)角色的轉(zhuǎn)換,承擔(dān)更多的促進(jìn)荊州地區(qū)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資源整合的社會(huì)化服務(wù)。這種改變將使壟上新公社不再是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服務(wù)網(wǎng)絡(luò)中的直接盈利環(huán)節(jié),而成為生產(chǎn)服務(wù)網(wǎng)絡(luò)參與許可權(quán)的審批者和經(jīng)營(yíng)行為監(jiān)督者。生產(chǎn)服務(wù)網(wǎng)絡(luò)中的農(nóng)資供應(yīng)商、銷售商、農(nóng)業(yè)主體都需要經(jīng)過(guò)申請(qǐng)、注冊(cè)和壟上新公社的審批,壟上新公社可以通過(guò)為注冊(cè)用戶宣傳或提供定制化服務(wù)等方式獲得更高的收益。這種新運(yùn)作模式可以將壟上新公社從農(nóng)資、農(nóng)產(chǎn)品的流通盈利環(huán)節(jié)中剝離出來(lái),并在服務(wù)提供商的自由競(jìng)爭(zhēng)中承擔(dān)對(duì)市場(chǎng)的價(jià)格、產(chǎn)品質(zhì)量、服務(wù)水平的指導(dǎo)和監(jiān)督職能,防止欠發(fā)達(dá)地區(qū)農(nóng)資、農(nóng)產(chǎn)品在區(qū)域統(tǒng)一的生產(chǎn)服務(wù)網(wǎng)絡(luò)中形成價(jià)格壟斷,也有利于豐富壟上新公社的盈利渠道。
3.4 市場(chǎng)化溢出階段的服務(wù)體系
區(qū)域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服務(wù)網(wǎng)絡(luò)可將促進(jìn)欠發(fā)達(dá)地區(qū)高質(zhì)量農(nóng)產(chǎn)品的規(guī)模化、生產(chǎn)成本下降以及品牌化農(nóng)產(chǎn)品誕生,區(qū)域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比較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進(jìn)一步加強(qiáng)。這種變化會(huì)引起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突破主要面向區(qū)域城鎮(zhèn)居民的服務(wù)定位,產(chǎn)生區(qū)域優(yōu)勢(shì)農(nóng)產(chǎn)品向區(qū)域外流通的趨勢(shì)。因此,市場(chǎng)化溢出階段的主要任務(wù)是以加強(qiáng)對(duì)外合作和交易的方式,促進(jìn)比較優(yōu)勢(shì)向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轉(zhuǎn)化。該階段欠發(fā)達(dá)地區(qū)的農(nóng)產(chǎn)品交易龍頭企業(yè)可建立“農(nóng)業(yè)市場(chǎng)化綜合服務(wù)平臺(tái)”。該平臺(tái)以提升區(qū)域農(nóng)業(yè)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的社會(huì)責(zé)任為導(dǎo)向,通過(guò)適當(dāng)?shù)钠跫s安排對(duì)農(nóng)產(chǎn)品生產(chǎn)和流通所依附的核心資源進(jìn)行組織和協(xié)調(diào),有利于實(shí)現(xiàn)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鏈內(nèi)外優(yōu)勢(shì)資源的虛擬集成,并有針對(duì)性開(kāi)展多種形式的宣傳、展銷和合作,從而實(shí)現(xiàn)區(qū)域品牌農(nóng)產(chǎn)品的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向外部區(qū)域溢出。根據(jù)促進(jìn)比較優(yōu)勢(shì)向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轉(zhuǎn)化,形成區(qū)域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集群的需要,“農(nóng)業(yè)市場(chǎng)化綜合服務(wù)平臺(tái)”的建設(shè)可分為市場(chǎng)化綜合服務(wù)實(shí)體平臺(tái)建設(shè)、實(shí)體平臺(tái)運(yùn)營(yíng)模式網(wǎng)絡(luò)化以及市場(chǎng)化綜合服務(wù)虛擬平臺(tái)建設(shè)3個(gè)階段,綜合服務(wù)平臺(tái)的演化過(guò)程見(jiàn)圖3。

3.4.1 市場(chǎng)化綜合服務(wù)實(shí)體平臺(tái)建設(shè) 市場(chǎng)化綜合服務(wù)實(shí)體平臺(tái)建設(shè)的主要功能包括完善農(nóng)產(chǎn)品交易的市場(chǎng)機(jī)制,引導(dǎo)欠發(fā)達(dá)地區(qū)優(yōu)勢(shì)農(nóng)業(yè)資源的自主發(fā)展,解決政府導(dǎo)向所致的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趨同和農(nóng)產(chǎn)品同質(zhì)化問(wèn)題;將低成本、高質(zhì)量的規(guī)模化農(nóng)產(chǎn)品推向更大范圍的市場(chǎng);提供農(nóng)產(chǎn)品交易場(chǎng)所,并以“非生產(chǎn)性就業(yè)”帶動(dòng)欠發(fā)達(dá)地區(qū)農(nóng)業(yè)剩余勞動(dòng)力創(chuàng)業(yè);承擔(dān)區(qū)域優(yōu)勢(shì)品牌創(chuàng)建、區(qū)域內(nèi)外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鏈集成等功能。為此,市場(chǎng)化綜合服務(wù)實(shí)體平臺(tái)至少需要建設(shè)農(nóng)產(chǎn)品交易物流中心、高科技農(nóng)產(chǎn)品加工中心、農(nóng)業(yè)科技研究中心、品牌農(nóng)產(chǎn)品博覽中心等主要功能實(shí)體。此外,還可以實(shí)時(shí)地監(jiān)控區(qū)域農(nóng)產(chǎn)品價(jià)格指標(biāo)、競(jìng)爭(zhēng)力指標(biāo)、發(fā)展?jié)摿χ笜?biāo),承擔(dān)區(qū)域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數(shù)據(jù)統(tǒng)計(jì)、信息發(fā)布、政策咨詢、市場(chǎng)變化預(yù)警等公益性責(zé)任,為欠發(fā)達(dá)地區(qū)政府對(duì)農(nóng)產(chǎn)品市場(chǎng)的宏觀調(diào)控提供參考。
3.4.2 市場(chǎng)化綜合服務(wù)實(shí)體平臺(tái)經(jīng)營(yíng)模式網(wǎng)絡(luò)化 運(yùn)營(yíng)模式網(wǎng)絡(luò)化是實(shí)體農(nóng)業(yè)交易平臺(tái)發(fā)展到一定程度后,進(jìn)一步擴(kuò)展影響力和服務(wù)能力需要經(jīng)過(guò)的新階段,其核心是結(jié)合欠發(fā)達(dá)地區(qū)農(nóng)產(chǎn)品實(shí)體交易的特征,運(yùn)用B2C、B2B、O2O等電子商務(wù)模式進(jìn)行網(wǎng)絡(luò)化運(yùn)營(yíng)模式創(chuàng)新。運(yùn)營(yíng)模式網(wǎng)絡(luò)化的目的在于,擴(kuò)大區(qū)域農(nóng)產(chǎn)品生產(chǎn)規(guī)模,提高生產(chǎn)效率、產(chǎn)品質(zhì)量、農(nóng)產(chǎn)品知名度,整合區(qū)域內(nèi)外優(yōu)勢(shì)資源,促進(jìn)區(qū)域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集群的形成。實(shí)體平臺(tái)運(yùn)營(yíng)模式的網(wǎng)絡(luò)化可利用B/S網(wǎng)絡(luò)構(gòu)架和現(xiàn)代通信技術(shù)使各區(qū)域內(nèi)外的農(nóng)業(yè)主體能實(shí)現(xiàn)農(nóng)資、農(nóng)產(chǎn)品、農(nóng)業(yè)科技及農(nóng)業(yè)信息等方面的線上交易。中國(guó)農(nóng)產(chǎn)品網(wǎng)(www.zgncpw.com)是實(shí)體平臺(tái)網(wǎng)絡(luò)化運(yùn)營(yíng)的典型代表,目前已成為國(guó)內(nèi)最具規(guī)模和專業(yè)化的網(wǎng)上農(nóng)產(chǎn)品交易服務(wù)平臺(tái)。湖北荊州兩湖綠谷確立了依托兩湖實(shí)體市場(chǎng)化服務(wù)平臺(tái)的農(nóng)產(chǎn)品資源和農(nóng)商資源,大力發(fā)展農(nóng)產(chǎn)品網(wǎng)絡(luò)化經(jīng)營(yíng)戰(zhàn)略規(guī)劃,遵循集農(nóng)產(chǎn)品信息、交易、物流配送三大板塊于一體的原則,開(kāi)始著力建設(shè)“中國(guó)綠谷網(wǎng)”。目前,中國(guó)綠谷網(wǎng)已經(jīng)建設(shè)了覆蓋全國(guó)大多數(shù)省市的農(nóng)業(yè)信息和服務(wù)網(wǎng)絡(luò)體系,擁有農(nóng)業(yè)主管部門的監(jiān)管和支持平臺(tái)、一大批農(nóng)業(yè)專家顧問(wèn)隊(duì)伍、農(nóng)產(chǎn)品供應(yīng)商和認(rèn)證農(nóng)產(chǎn)品資源數(shù)據(jù)庫(kù),能為涉農(nóng)企業(yè)和生產(chǎn)主體提供大容量和迅捷的網(wǎng)上網(wǎng)下商務(wù)貿(mào)易服務(wù),具備產(chǎn)品信息、物流管理、在線交易、綜合管理、行業(yè)動(dòng)態(tài)、信息采集發(fā)布等功能。
3.4.3 市場(chǎng)化綜合服務(wù)虛擬平臺(tái)建設(shè) 市場(chǎng)化綜合服務(wù)虛擬平臺(tái)的作用是將跨區(qū)域的、具有核心能力的農(nóng)業(yè)主體在邏輯上集成一個(gè)面向合作或交易項(xiàng)目的整體,使平臺(tái)內(nèi)的農(nóng)業(yè)主體可以方便地同區(qū)域外的優(yōu)勢(shì)資源進(jìn)行合作,從而實(shí)現(xiàn)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的聚集、整合與溢出。市場(chǎng)化綜合服務(wù)虛擬平臺(tái)并不限于僅對(duì)其經(jīng)營(yíng)企業(yè)提供服務(wù),任何在平臺(tái)注冊(cè)的農(nóng)業(yè)主體均可利用該平臺(tái)選擇潛在合作對(duì)象或主動(dòng)參與合作項(xiàng)目,而市場(chǎng)化綜合虛擬服務(wù)平臺(tái)可同時(shí)為多個(gè)跨區(qū)域的農(nóng)業(yè)虛擬合作項(xiàng)目提供服務(wù)。市場(chǎng)化綜合服務(wù)虛擬平臺(tái)首先要具有跨區(qū)域農(nóng)業(yè)優(yōu)勢(shì)資源和業(yè)務(wù)流程集成的功能。各參與合作的農(nóng)業(yè)主體必須嚴(yán)格履行市場(chǎng)化綜合服務(wù)平臺(tái)所制定的規(guī)則,可將基于XML的SOAP協(xié)議作為標(biāo)準(zhǔn)通信協(xié)議[20],促進(jìn)優(yōu)勢(shì)資源和業(yè)務(wù)流程的無(wú)縫集成,再以Web Services的方式去完成其在合作過(guò)程中的角色和任務(wù)。其次,虛擬市場(chǎng)化綜合服務(wù)平臺(tái)還需要對(duì)跨區(qū)域的合作項(xiàng)目進(jìn)行全過(guò)程監(jiān)控,具備合作信息發(fā)布、過(guò)程管理、沖突協(xié)調(diào)、合作績(jī)效評(píng)價(jià)和合作信譽(yù)通報(bào)等功能。此外,市場(chǎng)化綜合服務(wù)虛擬平臺(tái)可進(jìn)一步增強(qiáng)服務(wù)于欠發(fā)達(dá)地區(qū)內(nèi)外各類農(nóng)業(yè)主體的社會(huì)公益功能,如整合地理信息(WebGIS)、全球定位、遙感技術(shù)等技術(shù)手段,統(tǒng)籌區(qū)域內(nèi)外的種植、養(yǎng)殖、流通渠道、土地資源、服務(wù)企業(yè)、政策優(yōu)惠等優(yōu)勢(shì)產(chǎn)業(yè)資源;提供農(nóng)業(yè)、農(nóng)產(chǎn)品相關(guān)數(shù)據(jù)的獲取、統(tǒng)計(jì)、決策、專家在線咨詢等功能;還可以建立農(nóng)產(chǎn)品供需、價(jià)格等方面的預(yù)警機(jī)制,面向農(nóng)民、涉農(nóng)企業(yè)及欠發(fā)達(dá)地區(qū)農(nóng)業(yè)管理部門提供生產(chǎn)和經(jīng)營(yíng)方面的決策依據(jù)。
4 結(jié)論
筆者將研究視角定位于全面實(shí)現(xiàn)我國(guó)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最需要市場(chǎng)化服務(wù)體系支撐的欠發(fā)達(dá)地區(qū)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彌補(bǔ)當(dāng)前理論和實(shí)踐研究主要關(guān)注農(nóng)業(yè)優(yōu)勢(shì)突出、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區(qū)域[21-23]的不足。欠發(fā)達(dá)地區(qū)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面對(duì)宏微觀資源條件欠佳的發(fā)展環(huán)境,可以利用“適應(yīng)性優(yōu)勢(shì)分析模型”挖掘出響應(yīng)區(qū)域城鎮(zhèn)居民特殊要求的區(qū)域適應(yīng)性優(yōu)勢(shì),從而找到進(jìn)行初步市場(chǎng)化的突破口,建立起主動(dòng)參與市場(chǎng)化的信心。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市場(chǎng)化的可持續(xù)性從根本上依賴于區(qū)域農(nóng)業(yè)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的培植,因此,其市場(chǎng)化服務(wù)體系要針對(duì)性地服務(wù)于欠發(fā)達(dá)地區(qū)適應(yīng)性優(yōu)勢(shì)向比較優(yōu)勢(shì)、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逐漸轉(zhuǎn)化的過(guò)程,可分為市場(chǎng)化奠基、市場(chǎng)化提升、市場(chǎng)化3個(gè)階段分別建立起“適應(yīng)性優(yōu)勢(shì)集成平臺(tái)”“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服務(wù)網(wǎng)絡(luò)平臺(tái)”“市場(chǎng)化綜合服務(wù)平臺(tái)”,各個(gè)平臺(tái)都具有特定的競(jìng)爭(zhēng)力培植服務(wù)目標(biāo),平臺(tái)的運(yùn)營(yíng)模式要強(qiáng)調(diào)服務(wù)于欠發(fā)達(dá)地區(qū)農(nóng)業(yè)主體市場(chǎng)化的社會(huì)公益性。湖北省荊州市的特色農(nóng)產(chǎn)品合作社、壟上新公社以及兩湖綠谷的運(yùn)營(yíng)實(shí)踐表明,本研究提出的欠發(fā)達(dá)地區(qū)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市場(chǎng)化服務(wù)體系對(duì)促進(jìn)欠發(fā)達(dá)地區(qū)新型農(nóng)業(yè)主體和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主體共同市場(chǎng)化,增強(qiáng)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持續(xù)發(fā)展的內(nèi)生動(dòng)力,建設(shè)集約化、專業(yè)化、組織化、社會(huì)化相結(jié)合的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yíng)體系和服務(wù)體系具有較好的實(shí)踐價(jià)值。
參考文獻(xiàn):
[1]劉 松. 弱勢(shì)農(nóng)業(yè)主體的發(fā)展模式研究[J]. 湖北農(nóng)業(yè)科學(xué),2014,53(11):2720-2724.
[2]羅 丹,陳 潔. 域外經(jīng)驗(yàn)、當(dāng)下?tīng)顩r與中國(guó)特色農(nóng)業(yè)組織體系構(gòu)建[J]. 改革,2013(3):91-102.
[3]吳仲斌,劉斌樑. 準(zhǔn)確把握新型農(nóng)業(yè)社會(huì)化服務(wù)體系建設(shè)的四個(gè)關(guān)鍵問(wèn)題[J]. 中國(guó)財(cái)政,2013(8):58-59.
[4]孫瑞玲. 中國(guó)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建設(shè)的路徑與模式選擇[J]. 洛陽(yáng)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8,27(2):163-166.
[5]張照新,趙 海. 新型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yíng)主體的困境擺脫及其體制機(jī)制創(chuàng)新[J]. 改革,2013(2):78-87.
[6]戴孝悌. 產(chǎn)業(yè)鏈視域中的法國(guó)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發(fā)展經(jīng)驗(yàn)及其啟示[J]. 江蘇農(nóng)業(yè)科學(xué),2012,40(9):387-390.
[7]Sassi M. Agricultural convergence and competitiveness in the EU-15 regions[C]//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gricultural Economists. 2006.
[8]Gunjal K,Pound J,Delbaere J. FAO/WFP crop and food security assessment mission to Zimbabwe[C]//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2010:1-34.
[9]Anderson J R. Difficulties in African agricultural systems enhancement? Ten hypotheses[J]. Agricultural Systems,1992,38(4):387-409.
[10]周曉慶. 中日韓農(nóng)業(yè)社會(huì)化服務(wù)體系比較研究[J]. 世界農(nóng)業(yè),2010(11):70-74.
[11]Hinrichs C C. Embeddedness and local food systems:notes on two types of direct agricultural market[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00,16(3):295-303.
[12]Fritz M,Hausen T,Schiefer G. Developments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s of electronic trade platforms in US and European agri-food markets:impact on sector organization[J]. International Food and Agribusiness Management Review,2004,7(1):1-9.
[13]Loch D S,Boyce K G. Balancing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 roles in an effective seed supply system[J]. Field Crops Research,2003,84(1/2):105-122.
[14]高志敏,彭夢(mèng)春. 發(fā)達(dá)國(guó)家農(nóng)業(yè)社會(huì)化服務(wù)模式及中國(guó)新型農(nóng)業(yè)社會(huì)化服務(wù)體系的發(fā)展思路[J]. 世界農(nóng)業(yè),2012(12):51-55.
[15]Aciksoz S. The cluster of urban agriculture:case of Bartin-Turkey[J]. Tarim Bilimleri Dergisi-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2009,15(4):348-357.
[16]李春海. 新型農(nóng)業(yè)社會(huì)化服務(wù)體系框架及其運(yùn)行機(jī)理[J]. 改革,2011(10):78-84.
[17]Brown C,Miller S. The impacts of local markets:a review of research on farmers markets and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CSA)[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8,90(5):1298-1302.
[18]聶華林,楊敬宇. 特色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是我國(guó)西部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的基本取向[J]. 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研究,2009,30(5):514-519.
[19]丁 勤,田 甜. 《壟上行》:服務(wù)成就價(jià)值[J]. 中國(guó)廣播電視學(xué)刊,2012(8):31-33.
[20]田世海,高長(zhǎng)元. 基于Web Services的高技術(shù)虛擬企業(yè)信息集成[J]. 中國(guó)軟科學(xué),2006(6):151-154.
[21]羅兵前. 江蘇省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建設(shè)對(duì)策[J]. 江蘇農(nóng)業(yè)科學(xué),2016,44(5):557-559.
[22]錢 晨,朱戰(zhàn)國(guó). 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背景下消費(fèi)者對(duì)本地食品的偏好研究[J]. 江蘇農(nóng)業(yè)科學(xué),2016,44(5):553-557.
[23]仲亞美,葉長(zhǎng)盛. 基于生態(tài)位的鄱陽(yáng)湖地區(qū)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空間分異及類型[J]. 江蘇農(nóng)業(yè)科學(xué),2016,44(7):572-578.
- 江蘇農(nóng)業(yè)科學(xué)的其它文章
- 農(nóng)村土地承包經(jīng)營(yíng)權(quán)抵押貸款的供給與需求分析
——以天津市為例 - 農(nóng)村土地經(jīng)營(yíng)權(quán)抵押貸款供給困境的多方演化博弈分析
- 農(nóng)戶的耕地流轉(zhuǎn)意愿價(jià)格及其影響因素分析
- 金融知識(shí)對(duì)農(nóng)戶金融行為的影響研究
——基于江蘇省522個(gè)農(nóng)戶調(diào)查數(shù)據(jù) - 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化龍頭企業(yè)社會(huì)責(zé)任履行研究
- 基于灰色關(guān)聯(lián)的安徽省耕地資源利用效率影響因素分析